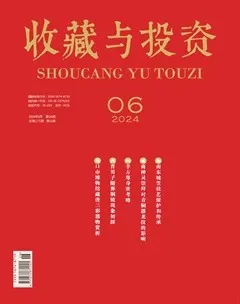探究工筆畫的美術語言
摘要:工筆畫作為傳統繪畫的一種,在色彩運用、構圖位置、人物刻畫等方面呈現出獨特之處。其中,色彩作為美術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畫家藝術情懷和思想情感的傳達媒介。本文主要從歷史和審美的角度對中國傳統工筆畫《女史箴圖》的色彩運用、構圖位置、人物刻畫進行分析、鑒賞和借鑒,揭示中國工筆畫美術語言的獨特之美。
關鍵詞:工筆畫;女史箴圖;色彩;美術語言
西晉惠帝時期,賈后專權失敗后,張華作《女史箴》,對宮中婦女進行道德教化,教導其遵從婦德,以得到榮譽。之后,顧愷之將《女史箴》融入自己的繪畫理念,繪成《女史箴圖》,展現了傳統工筆畫的輝煌成就,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女史箴圖》值得我們進行研究探討,吸收借鑒傳統工筆畫的獨特美術語言。除此之外,顧愷之在人物塑造方面達到了傳神的境界,因此,《女史箴圖》是集教化與審美于一身的優秀繪畫作品,在呈現美的同時,教化宮中婦女培養品德。
一、《女史箴圖》作品簡要概述
《女史箴圖》是東晉時期人物畫的杰出代表,關于此圖的研究,徐邦達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提到:“人物衣紋作‘高古游絲描’,運筆飛動,真有春蠶吐絲之妙。設色多用朱墨,色調古艷。”[1]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工筆人物畫作品之一,是東晉畫家顧愷之創作的絹本繪畫作品,現藏于大英博物館。此圖系作者根據西晉張華《女史箴》一文而作。畫中所提到的女史主要是侍奉皇后左右,專門記載皇后言行的女官。其中,箴是規勸、告誡之意,旨在規勸婦女如何立身處世,培養良好品德,樹立高尚的道德品質。
(一)從《女史箴》到《女史箴圖》
《女史箴》是西晉張華為諷諫賈后所寫的一篇辭賦。賈后是大功臣賈充的女兒,性格暴躁、性情善妒、兇狠狹隘。司馬衷登基后冊封其為皇后,賈后的野心逐漸暴露無遺。其為謀劃皇位,奪取政權,清除異己,殺死當時輔政之臣數人。顧愷之據《女史箴》作《女史箴圖》,旨在勸誡女性提升道德修養。

二、《女史箴圖》工筆人物畫語言分析
(一)色彩特征
工筆畫作為中國傳統繪畫主要表達形式之一,其特點是準確、細致、富有層次感。工筆畫色彩運用已經十分成熟,常用色調有暖色調和冷色調以及深色和淺色的組合。在工筆畫中,一般以固有色調為主,設色明快、艷麗、沉著、高雅,整體畫面具有中國傳統民族色彩審美意趣。中國工筆畫色彩在發展歷程中,主要依賴傳統顏料特性。東晉時期的工筆畫顏料基本上都是礦石,所以其受制于顏料特性。畫面主要體現了重彩的藝術特點,用色具有粗獷、深厚、斑斕的強烈色彩特點。通過分析《女史箴圖》,我們可以看出工筆畫的這一特性,呈現了強烈的畫面效果。對于色彩與技法,二者應有機結合,不可割裂。除了將水色和石色高度聯合,還須有效結合顏色和結構,使色彩和線墨有機融合,才能使畫面豐富且協調,從而呈現虛實結合與濃淡相間的畫面效果。
(二)《女史箴圖》色彩的寫意性
東晉時期,工筆畫家的繪畫思想受宗教、哲學以及統治者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時具有一種主觀寫意性,這種寫意性是對于時代精神、社會主流思想文化與自我思想情感的一種融合后的體現,是體現畫家本人繪畫情感的一種方法。《女史箴圖》中的人物色彩表現具有很強的寫意性,畫中描繪了宮廷婦女的節義行為,表現了她們舍己為人的英勇行為,塑造了具有英雄氣概的宮廷婦女形象,從而起到教化的作用。畫中較為出色的兩處故事是“馮媛擋熊”和“班姬辭輦”。顧愷之根據不同的主題,生動地反映了貴族婦女的形象和特征。畫中的婦女神采動人,裙邊或飄帶處略微敷色,顯得柔軟纏綿,靚麗奪目,呈現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緊勁連綿,循環超乎”的運動感和飄逸氣息,呈現出顧愷之設色的“寫意性”,而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現實生活中的畫面。
(三)《女史箴圖》色彩的主次性
色彩的主次搭配是畫面形式美的一個重要體現,色彩在工筆畫中的地位非常高,畫家既要保持畫面主體物的固有色又要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表現畫面色彩的整體效果。中國畫用色注重分類,畫面顏色豐富但不雜亂,一種主色統領整體畫面,為主色調,其他顏色作為次要顏色,輔助主要顏色共同呈現畫面效果。畫面有一個大的色彩方向,表現畫面整體色彩傾向。在“馮媛擋熊”的場景中,主人公馮媛形象宏偉高大,所穿服飾設色明艷、沉著、歡快,突出了主人公地位,與其他侍從相比,服飾更加精致而且顏色細膩。
(四)《女史箴圖》色彩的裝飾性
將中國畫與西洋畫相比,可看出西洋畫設色以再現事物為目的,但中國畫設色講究從固有色出發,畫師根據固定色以及自己內心的情感變化,表達繪畫的主題色彩[2]。中國畫的色彩是墨與色的結合,畫家在墨色與色彩的對比之間尋求“沖突的和諧”,達成畫面統一的效果,尋求一種統一、和諧、融合的境界。畫家根據自己的主觀思想與情感需要,對作品設不同的色彩,將客觀事物的固有色進行淡化處理,形成畫師心中主觀顏色。《女史箴圖》以墨色為主,以其他色相作為輔助,協調畫面,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增添了畫面色彩的裝飾意趣。
三、《女史箴圖》工筆人物畫構圖分析
《女史箴圖》是一幅插圖性質的畫卷,內容分為十二段,因年代久遠,損壞丟失了一部分,現存九段,以“馮媛以身擋熊,保護漢元帝”“班婕妤謝絕與漢成帝同輦”最為出色,十二段描繪的都是女范事跡。作品為絹本設色長卷,采用散點透視法進行構圖,散點透視法不同于西方的焦點透視,它是中國畫中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法。畫家將視點移動到畫布上,構造出多個消失點,從而形成一種靈活的時空境界。這種透視方法也叫作“移動視點”,能夠表現遼闊的畫面效果,視野廣闊,從而呈現更好的畫面效果。
顧愷之根據人物尊卑關系確定人物的比例大小,突出主體人物,畫面主次分明。如圖中“對鏡梳妝”片段,右側的女子手持鏡子觀察自己的妝容,身后侍女正為其梳頭。從構圖可以看出,畫面主要描繪了一位端坐在鏡子前的女子,其身體在前方,為完整刻畫,身后的侍女身體被遮擋了一部分。在“班婕妤謝絕與漢成帝同輦”的場景中,班婕妤身姿偉岸,與其旁邊的轎夫相比較,身形甚至更加高大,體現了顧愷之構圖的獨到之處:大小比例主次分明。此構圖亦凸顯了班婕妤深明大義的宮廷婦女形象。
四、《女史箴圖》工筆畫人物塑造分析
(一)“傳神論”
畫家不僅要顯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物理距離,更要如實描繪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心靈空間,這亦是繪畫的重要特點。有了心靈空間,便有了聯想,從而產生畫外音,動人心弦的意境便由此而生發。“心有靈犀一點通”“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這兩句話如果以繪畫的形式加以表現,只要把握好“悟對之通神”的訣竅,便能迎刃而解[3]。 顧愷之注重以形寫神,畫必形似,方能神似。顧愷之重視眼睛在人物繪畫中的傳神作用,正所謂“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他認為人物四肢畫得好與壞本無關緊要,使人物畫達到傳神境界的關鍵在于“阿堵”。因此,顧愷之對畫中人物眼睛的描繪慎之又慎。顧愷之以形寫神的畫論在于將畫中人物形象神化,塑造超凡脫俗的形象,使畫中人物不僅形似,更加神似。
(二)“游絲描”
顧愷之在繪畫技法上注重線條的運用,其線條呈現出連綿不斷、悠緩自然的節奏感,線條輕重控制有度,正如“春蠶吐絲”“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將自戰國以來形成的“高古游絲描”發展到了完美的境地。他采用描繪線條的手法,使畫面呈現出典雅、寧靜而又不失活力的氛圍。畫面中線條婉轉飛揚、悠緩自然、均勻優美,人物所穿衣物飄飄然,仿佛有風在吹動,生動至極。這種筆線被后人稱為“高古游絲描”。高古游絲描最早由明代鄒德中在《繪事指蒙》中提出。鄒德中特意用“高古”一詞去修飾“游絲描”,說明他意識到這種宛若游絲的線條產生的時間遠早于鐵線描、莼菜描等唐宋時純熟的描法[4]。
(三)剪影化造型
《女史箴圖》中人物造型如剪影一般,這與寫實高度成熟的唐宋工筆人物畫存在很大的差異。其中,人物塑造缺乏體量感、厚重感,呈現平面化的造型,比如“班婕妤謝絕與漢成帝同輦”這一場景中,八名抬轎夫所穿服飾飄然瀟灑,肩上所抬轎子似乎并無重量,可輕易托起,說明在塑造人物時,畫家并沒有營造事物的重量感。
五、《女史箴圖》道德教化思想
《女史箴圖》描繪女范事跡,有漢代馮媛以身擋熊,保護漢元帝的故事;有班婕妤拒絕與漢成帝同輦,以防漢成帝貪戀女色的故事;有描繪上層婦女遵守道德規范的場景。這類圖像帶有一定的說教性質,勸導宮中婦女修養自己的品德。如漢元帝遭遇黑熊襲擊,宮女躲在一旁,身旁侍衛雖手拿利器,卻畏畏縮縮,不敢向前,而馮婕妤昂首挺胸、義無反顧用身體擋住黑熊,保護漢元帝,表現出其無所畏懼、堅定不屈的內心狀態。從中可以看出顧愷之對宮中婦女的教育思想。
六、后人對《女史箴圖》的評價
自古以來,《女史箴圖》在中國畫壇占據一席之地,受到許多畫家的欣賞與研究。明代何良俊評價:“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后有清代書畫鑒藏家安岐:“色澤鮮艷,神氣完足。”顧愷之對于人物塑造的傳神之妙由此可見。
七、結語
《女史箴圖》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是集教化功能和審美功能于一身的成功典范,在設色、構圖設計、人物塑造等方面達到了傳神的境界。畫中人物神態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除此之外,通過人物的動作與表情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將兩漢以來人物畫的發展推向了新境界,對后世的繪畫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總之,《女史箴圖》是中國的繪畫寶藏,它不僅具備藝術價值,還具有歷史價值與史學價值,值得我們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去研究其隱藏的價值,發掘歷史與文化資源。

作者簡介
鄭秋霞,女,漢族,山東菏澤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學科教學(美術)。
吳新新,女,漢族,山東青島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學科教學(美術)。
參考文獻
[1]吳陽.六朝密體畫藝術風格探究—以《女史箴圖》為例[J].美與時代,2021(11):40-41.
[2]黃曦.探究中國畫的裝飾性表現[J].藝術與設計(理論),2014,(11):124-126.
[3]張愜寅.略論中國古代繪畫中的空間營造—以顧愷之《女史箴圖》為例[J].美術教育研究,2016(5):18-19.
[4]蘇醒.《女史箴圖》的風格與來源—兼論魏晉南北朝人物畫的兩大脈絡[J].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18(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