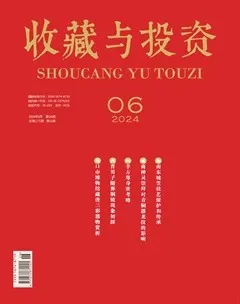唐代敦煌飛天形象中的藝術(shù)張力研究
摘要:唐代飛天作為敦煌壁畫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極具藝術(shù)張力,它所傳達(dá)的視覺(jué)效果與藝術(shù)理念都有對(duì)運(yùn)動(dòng)感的追求與表現(xiàn),但這一視覺(jué)形象從外部空間看是靜止的,并不存在真實(shí)的運(yùn)動(dòng)。本文試圖從飛天形象的造型、線條、色彩以及觀察者的視覺(jué)聯(lián)想等方面來(lái)分析唐代壁畫的藝術(shù)張力。
關(guān)鍵詞:唐代;敦煌飛天;藝術(shù)張力
一、唐代敦煌飛天形象
在中國(guó)的宗教藝術(shù)寶庫(kù)中,敦煌的壁畫閃耀著特殊的光芒,尤其是唐朝的飛天畫作,它們不僅代表了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頂峰成就,也展現(xiàn)了深厚的美學(xué)內(nèi)涵。這些飛天畫作繼承并發(fā)揚(yáng)了歷代的藝術(shù)傳統(tǒng),展現(xiàn)了藝術(shù)家對(duì)于超越塵世的向往以及對(duì)美好生活的憧憬。它們的創(chuàng)作不單是對(duì)美的追求,更融入了創(chuàng)作者的個(gè)人審美觀、豐富想象和生活體驗(yàn),展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和表達(dá)意圖。通過(guò)這些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象,唐代敦煌的飛天畫作不僅成為佛教藝術(shù)的精華,也成為中國(guó)古代文化和藝術(shù)創(chuàng)新精神的象征。
在中國(guó)繪畫傳統(tǒng)中,唐代敦煌飛天這一形象反映的是一種深刻的主觀美學(xué)理念,尤其體現(xiàn)在以人與自然和諧統(tǒng)一為核心的“天人合一”哲學(xué)之中。敦煌石窟藝術(shù),特別是其中的飛天畫像,是這一理念的杰出代表。這些飛天畫像遍布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以及東西千佛窟等數(shù)百個(gè)洞窟之中,歷經(jīng)從十六國(guó)時(shí)期至元朝晚期的千年時(shí)光,總計(jì)約有6000尊飛天畫像被創(chuàng)作出來(lái)。這不僅彰顯了中國(guó)藝術(shù)家對(duì)于美和精神追求的深邃理解。

唐代是敦煌飛天的全盛時(shí)期,唐代的飛天形象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在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上靈活超脫,在線條的勾畫與顏色的表達(dá)上有著強(qiáng)烈的順暢性與節(jié)奏感,并以一種富有節(jié)奏感的意象向人們展示著,因而也成了中國(guó)古典的一種文化與藝術(shù)象征,有非常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唐代的飛天形象色彩飽滿艷麗,在塑造藝術(shù)形象的技藝上實(shí)現(xiàn)了非凡成就。這些飛天畫作脫胎換骨,已融入中華藝術(shù)的獨(dú)特韻味,與西域原有的風(fēng)格大相徑庭,完成了藝術(shù)形象上的中國(guó)化轉(zhuǎn)型,并被賦予最豐富的藝術(shù)想象,呈現(xiàn)出靈動(dòng)和華美的形象。唐朝后期的飛天形象,在姿態(tài)表現(xiàn)方面則不如前期的活潑靈動(dòng)富有動(dòng)感和張力,甚至在藝術(shù)造型的設(shè)計(jì)上,服飾由原來(lái)的艷麗豐厚變?yōu)榈艈伪。硇我矎呢S腴的嬌嫩變成了單薄的消瘦等。飛天形象也不再是盛唐雍容華貴的風(fēng)格,逐漸變得姿態(tài)緩和,色彩冷淡,呈現(xiàn)出一種肅靜端莊之美。這些現(xiàn)象反映了唐朝后期的政治腐敗和國(guó)力衰退。總之,在大唐近300年的歷史中,飛天形象經(jīng)歷了由幼稚到成熟再到衰落的過(guò)程,這一過(guò)程也清楚地反映了那個(gè)時(shí)代民族藝術(shù)的變化脈絡(luò),保存至今的200多個(gè)洞窟成就了敦煌藝術(shù)無(wú)可替代的歷史價(jià)值。
二、張力及其表現(xiàn)形式
張力最早源于物理學(xué),指的是作用于物體內(nèi)部的一種分子運(yùn)動(dòng),是一種牽引力。20世紀(jì)后,隨著格式塔心理學(xué)的不斷興起,張力這一概念逐漸被引入美學(xué)領(lǐng)域,即藝術(shù)張力,它指的是藝術(shù)作品對(duì)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具體來(lái)講,就是一幅作品能被人感知的部分和不能被人感知部分的總和。
阿恩海姆在其《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中提出了四種“張力”的表現(xiàn)形式:由可視目標(biāo)的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所產(chǎn)生的力,由不同的物體和不同部位聚集而來(lái)的力,趨向于形態(tài)的張力,在視覺(jué)目標(biāo)上感知的定向張力和由視覺(jué)風(fēng)格自身和它們的結(jié)合而產(chǎn)生的視覺(jué)效果。西方格式塔心理學(xué)理論認(rèn)為,形式和人的潛意識(shí)形成“同構(gòu)”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精神共鳴,而張力就是一種同構(gòu)現(xiàn)象,是藝術(shù)作品和讀者的視覺(jué)神經(jīng)產(chǎn)生的共鳴現(xiàn)象。
藝術(shù)張力是藝術(shù)作品生命力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體現(xiàn),視覺(jué)層面的“運(yùn)動(dòng)感”“收縮感”,都是對(duì)張力的一般性理解,它不僅反映在藝術(shù)作品的外在形式上,也體現(xiàn)在作品內(nèi)部的精神層面。中國(guó)畫論中的“氣韻生動(dòng)”既注重形式方面的力度感,又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在的趣味和神韻。對(duì)于藝術(shù)作品“緊張力”和“生動(dòng)性”的體會(huì)和認(rèn)識(shí),還不足以更好地借助作品展現(xiàn)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它還包括“陌生感”“想象空間”“共鳴”等一切能引起觀者注意力的因素,這都是形成藝術(shù)張力的重要條件。
三、唐代飛天形象中的藝術(shù)張力
唐朝是敦煌飛天形象的鼎盛時(shí)期。由于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社會(huì)風(fēng)氣開放,民間對(duì)“姿容美豐艷”的藝妓日益推崇,促使飛天形象向“女性化”方向發(fā)展。與此同時(shí),唐朝的畫師也對(duì)飛天形象進(jìn)行大膽創(chuàng)新,在他們的筆下,飛天人物面容豐潤(rùn),五官精致,姿態(tài)優(yōu)美,彩帶綿長(zhǎng)優(yōu)美,甚至還出現(xiàn)了雙飛天、四飛天。這些栩栩如生的飛天形象在視覺(jué)上具有靜態(tài)性質(zhì),雖然它們前呼后應(yīng),卻蘊(yùn)含著動(dòng)感的靜態(tài)美。觀察者能憑借飛天飄舞的華帶、婀娜的體態(tài)、變幻的流云等視覺(jué)現(xiàn)象感受“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dòng)”的輕盈靈動(dòng)之感和奮發(fā)進(jìn)取的精神力量。這種不動(dòng)之動(dòng)就是藝術(shù)張力,是藝術(shù)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在造型方面,唐代飛天靈動(dòng)傳神,在“U”形和“V”形的動(dòng)態(tài)走向基礎(chǔ)上,衍生出更具曲線美的“S”形以及俯沖、環(huán)繞等動(dòng)感十足的新姿態(tài)。唐朝時(shí)形成了“其勢(shì)圓轉(zhuǎn)而衣服飄舉”的吳派畫風(fēng),盡顯大唐的繁榮與興盛。正如康定斯基所說(shuō),它們包含的是一種“具有傾斜性的張力”。這種造型與周圍的飄帶共同構(gòu)成“S”形輪廓,呈現(xiàn)出曲折回環(huán)的強(qiáng)烈節(jié)奏感。如盛唐時(shí)期莫高窟第217窟(圖1)中一身靈動(dòng)瀟灑、風(fēng)骨飄逸、拖著長(zhǎng)長(zhǎng)的飄帶、頑皮地蜿蜒穿梭于鐘樓的飛天,在祥云的襯托下,舒展雙臂,“S”形的妖嬈身姿呈現(xiàn)一種向上騰空的動(dòng)態(tài),勢(shì)若流星。畫面中,飛天的身影和垂直線成45度角,伸出的手臂也從身軀脫離。這種與垂直位置方向上發(fā)生的偏離產(chǎn)生的視知覺(jué)張力動(dòng)感強(qiáng)勁,讓觀者無(wú)不感受到飛天形象曲折回環(huán)的強(qiáng)烈節(jié)奏感,并在這種傾斜的姿態(tài)中感受到生命的活力。

線條在國(guó)畫藝術(shù)中始終占據(jù)核心地位。唐朝時(shí)期,線條的運(yùn)用達(dá)到了更高的嫻熟度和精致感,畫家們偏好使用柔和的朱砂色勾勒輪廓。在“吳派”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中,“吳帶當(dāng)風(fēng)”的描線技巧對(duì)敦煌飛天的生動(dòng)活潑、輕盈飛舞的形象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康定斯基認(rèn)為線是由運(yùn)動(dòng)產(chǎn)生的,是由靜到動(dòng)的一步,肯定了線條具有一定的內(nèi)在張力。在敦煌飛天形象的線條表現(xiàn)中,有抑揚(yáng)頓挫的運(yùn)筆方式,有疏密穿插的錯(cuò)綜變化形式,還有曲直長(zhǎng)短形態(tài)各異的表現(xiàn)形式。這些表現(xiàn)形式在視覺(jué)對(duì)比上形成強(qiáng)烈反差,無(wú)不彰顯著行云流水,天衣飛揚(yáng)的飄忽渺渺的美感。從盛唐時(shí)期莫高窟第39窟飛天形象(圖2)可以看出,飛天衣飾的蘭葉描線條細(xì)長(zhǎng)舒展,婉轉(zhuǎn)流暢,運(yùn)筆速度快而富有變化。裙帶轉(zhuǎn)折處筆法圓轉(zhuǎn)流暢,衣飾褶皺處部分區(qū)域用的是粗細(xì)不同的短線,這種線條的運(yùn)用細(xì)膩地表達(dá)了飛天衣飾的質(zhì)感和“其勢(shì)圓轉(zhuǎn)而衣服飄舉”的節(jié)奏感。在祥云的襯托下,人物體態(tài)和裙帶的處理栩栩如生,表現(xiàn)出凌空飛舞的感覺(jué)。所以,飛天的渲染力,很大程度取決于最后的定性線。
色彩語(yǔ)言作為視覺(jué)藝術(shù)中最直觀的因素存在,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也為畫面平衡做出了張力貢獻(xiàn)。對(duì)于唐代飛天形象而言,其絢麗至極的色彩給人呈現(xiàn)的強(qiáng)烈藝術(shù)張力和恢弘的美感足以支撐起整個(gè)藝術(shù)形象的靈魂。色彩之間互補(bǔ)色對(duì)比是藝術(shù)張力最主要的形成方式,其所發(fā)揮的對(duì)抗性能更大限度呈現(xiàn)出濃烈視覺(jué)效果。以初唐第321窟柔美的雙飛天為例(圖3),畫面底色整體為明亮單純的淺藍(lán)色,在這個(gè)背景中,兩身飛天的皮膚呈現(xiàn)絳黑色,配飾運(yùn)用了能產(chǎn)生補(bǔ)色對(duì)比效果的土紅和石青,服飾賦上了淡黃色,畫面在冷暖色對(duì)比基礎(chǔ)上也存在三原色對(duì)比。另外,調(diào)和色發(fā)揮的“配角”作用進(jìn)一步使畫面的視覺(jué)美感達(dá)到巔峰,在雙飛天形象中黑、白、灰等調(diào)和色的存在,使畫面視覺(jué)統(tǒng)一又不失節(jié)奏,利用石青與灰色調(diào)和增強(qiáng)了畫面和諧統(tǒng)一,賦予畫面一定的神秘莊嚴(yán)之感。此外,欣賞者的主觀聯(lián)想同樣增強(qiáng)了畫面視覺(jué)感受力和藝術(shù)張力。
總而言之,唐代的飛天形象在承襲傳統(tǒng)技藝的基礎(chǔ)上,巧妙地融合了外來(lái)藝術(shù)的精髓,創(chuàng)造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這種藝術(shù)風(fēng)格不僅展現(xiàn)了文化多元融合的魅力,也反映了唐朝社會(huì)的繁榮、藝術(shù)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作為佛教藝術(shù)的瑰寶,唐代飛天以其精湛的技藝、靈動(dòng)婀娜的身姿、優(yōu)雅大方的氣質(zhì)、鮮明對(duì)比的色彩、流暢生動(dòng)的線條,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古代藝術(shù)家們的卓越才情和藝術(shù)表達(dá)力。敦煌的唐代飛天,以其飛翔的動(dòng)態(tài)美,完美地結(jié)合了雄渾力量與靈動(dòng)飄逸,蘊(yùn)含傳統(tǒng)情感內(nèi)核,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中一道獨(dú)特的審美風(fēng)景線。

作者簡(jiǎn)介
孫映琦,女,漢族,山東日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槊佬g(shù)學(xué)、油畫。
張曉穎,女,漢族,廣東韶關(guān)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槊佬g(shù)學(xué),美術(shù)史論。
參考文獻(xiàn)
[1]季羨林主編.敦煌學(xué)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2]榮新江.敦煌學(xué)十八講[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
[3]鄭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藝術(shù)概論[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
[4][英]荷加斯:美的分析[M].楊成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
[5][美]阿恩海姆.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6][俄]康定斯基.論藝術(shù)的精神[M].查立,譯,滕守堯,校.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7.
[7][俄]維戈斯基.藝術(shù)心理學(xué)[M].周新,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