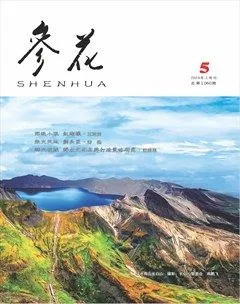馬勒交響創作思維中的鋼琴伴奏
馬勒一生中創作了大量音樂作品,其中尤以藝術歌曲和交響曲居多。他獨創了用管弦樂隊為藝術歌曲伴奏的音樂形式,在交響曲中融入藝術歌曲旋律,并且對人聲進行器樂化處理,無不彰顯其交響性的創作思維和交響化的創作手法。在聲樂套曲《亡兒之歌》中,馬勒用豐富的音色、節奏、和聲、力度對比,將復雜變化的情緒充分表現,讓鋼琴伴奏藝術進入全新境界,更賦予藝術歌曲新的音響效果。
一、馬勒的作品與創作思維
馬勒一生的音樂創作以藝術歌曲和交響曲最為著名,盡管其《大地之歌》常常被劃分為管弦樂,而非聲樂曲或交響曲,但這正充分說明了其音樂創作對體裁界限的模糊。這種模糊,正是基于其創作中的交響性創作思維和交響化創作方法。
(一)馬勒的藝術歌曲與交響曲
古斯塔夫·馬勒,出生于1860年7月,奧地利著名作曲家、指揮家。其父親對馬勒自幼表現出的與生俱來的音樂天賦極為認可,于是1875年15歲的馬勒正式于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音樂教育。
馬勒畢生共創作了近50首藝術歌曲和10部交響曲(第十部未完成),可以說藝術歌曲和交響曲幾乎占據馬勒音樂創作的全部。在10部交響曲中,有6部加入了人聲,其他幾部同樣或多或少與其創作的藝術歌曲相呼應。正因其將藝術歌曲和交響曲相融合,馬勒成為西方音樂史上著名的音樂家,在20世紀60年代更是掀起了一股“馬勒復興”的熱潮。
縱觀馬勒的一生,其音樂創作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第一至第四交響曲組成,同時又包含聲樂套曲《旅行者之歌》和歌曲集《少年的奇異號角》。其中《第一交響曲》與聲樂套曲《旅行者之歌》相聯系,其他三部交響曲與《少年的奇異號角》相聯系。第二階段由三部純器樂交響曲、兩部歌曲集《亡兒之歌》《呂克特詩五首》組成,這三部交響曲與《亡兒之歌》之間同樣存在緊密關聯。第三階段由最后三部交響曲組成,其中《大地之歌》更是一部將聲樂與交響曲融合至極的巔峰之作,既可以稱其為交響性的聲樂套曲,也可以說它是一部歌曲交響樂。
由此不難發現,在馬勒的創作生涯中,藝術歌曲與交響曲始終緊密結合,藝術歌曲中的旋律常常在交響曲中有所體現。例如《第五交響曲》第一部分第一樂章回旋曲的第二個插部主題,便是馬勒從《亡兒之歌》中提煉出來的表現憂郁的旋律;第四樂章則與《呂克特詩五首》中的第四首歌《我在世上不復存在》有著明顯聯系。而在第二、第三、第四、第八交響曲中,馬勒總是在交響曲的架構中融入聲樂,要么成為某一樂章的段落,要么則成為一個完整的樂章。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交響”是馬勒在音樂創作中自然形成的個性化標志,它充分體現在其相互貫通的歌曲與交響曲作品中。
(二)馬勒的交響性創作思維
在馬勒的音樂創作中,除了最初幾首鋼琴伴奏的歌曲之外,其全部作品都是為人聲和管弦樂隊而創作的。這充分說明在馬勒的創作思維中,歌曲與交響曲幾乎不分彼此,而在馬勒的音樂作品中也呈現出這一鮮明特征,即藝術歌曲中管弦樂隊的伴奏形式和交響曲中大量的人聲融入。
聲樂交響曲是一種以交響樂的形式將歌曲融入器樂之中的音樂形式。這種形式或許是馬勒受到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的啟發,因此許多人將馬勒的《第八交響曲》與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相提并論,認為它是20世紀的“合唱交響曲”。
除了將聲樂加入交響曲以外,馬勒還大量用管弦樂隊為歌曲進行伴奏,尤其是其大部分歌曲并非用只鋼琴填充聲部,而是在用鋼琴配器后,又重新用管弦樂進行配器。在馬勒的藝術歌曲中,有28首配有樂隊伴奏。如《當我的戀人舉行婚禮的日子》中使用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單簧管、大管、圓號、豎琴、鐘琴、定音鼓、三角鐵和弦樂組;《我有一把火熱的刀子》使用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單簧管、大管、圓號、小號、長號、定音鼓、三角鐵、缽、大鼓、小軍鼓和弦樂組。
然而,馬勒這種管弦樂隊的伴奏不同于其他作曲家醉心于“音色混合”的試驗,而是對挖掘各種樂器音色表現的可能性頗感興趣。他所用到的演奏樂隊編制極其龐大,但卻以純音色作為配器基礎,然后使用各種演奏技法突出不同樂器在不同音區中所產生的特殊音色效果,從而使整部作品具有極其豐富的音色變化。
在這樣的創作思維下,人聲不僅僅作為表達歌詞內涵的媒介,更是一種被升華的音樂旋律,成為馬勒音樂創作的特色,作為一種特殊“樂器”豐富音樂的織體,由此實現了藝術歌曲與交響曲兩種不同音樂體裁的有機融合。因此,交響曲一詞對馬勒而言,意味著以所知的一切技法創造出一個世界。
二、《亡兒之歌》的創作背景
在交響性的創作思維和交響化的創作方法下,馬勒創作了大量藝術歌曲和交響曲作品。在這些音樂作品中,他融入了自己對生命的思考,對人生、自我的追問。也正是漂泊的人生經歷,造就了馬勒音樂作品極具現實性的特點。
《亡兒之歌》是馬勒第二創作階段的重要聲樂套曲,是為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呂克特同名詩作譜的曲。在這部詩集中,馬勒仿佛讀到了自己的內心感受。馬勒的父母共生育了14個孩子,但大多夭折,尤其是1874年前后,其最疼愛的弟弟恩斯特離世,給馬勒帶來巨大的創傷。于是1901年至1904年,馬勒深受呂克特詩集的觸動,便從中挑選了五首詩,創作了聲樂套曲《亡兒之歌》。在馬勒的音樂作品中,人們常常能夠發現他對命運的沉思,從《亡兒之歌》到《大地之歌》無不如此。
三、《亡兒之歌》的音樂分析
(一)《亡兒之歌》的音樂結構
《亡兒之歌》是寫給管弦樂隊與女低音的聲樂套曲,由五首藝術歌曲組成,分別是《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現在我看清了火焰為什么這樣陰郁》《當你親愛的母親進門時》《我總以為他們出遠門去了》《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們出門》。在《亡兒之歌》的創作中,馬勒擺脫了早期藝術歌曲的風格特征,達到了新的高度,開辟了他在譜曲上的新紀元。
第一首歌《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旋律與和聲在d小調上進行,整首歌中d小調和D大調交替出現,并且通過半音模進的方式進行純器樂部分的連接。這種大小調的交替,在歌曲中意味著特定情緒、特定形象的轉變。
第二首歌《現在我看清了火焰為什么這樣陰郁》的調性更加不穩定,在c小調、C大調、D大調之間轉換,同時力度變化、調性變化、和聲變化更多,由此來展現這首歌曲情感上的激烈變化。
第三首歌《當你親愛的母親進門時》是再現的單二部曲式,在和聲部分體現這首歌曲為c小調與g小調交替的調性特征,其音樂結構也明顯以此為劃分依據。從開始的沉重憂郁到情緒激動,八度持續音的延長充分彰顯了父親內心的波動。
第四首歌《我總以為他們出遠門去了》通過bE、be、bG三個同主音大小調、關系大小調進行對比,在呈示部進行了兩次變化,且旋律起伏較大,與前三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五首歌《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們出門》是套曲中的高潮,二段體的結構將歌曲分成兩個部分,也以高潮為界限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在d小調,第二部分在同主音的D大調,僅僅在A大調片刻停留,最后回歸D大調終止。同主音大小調的變化與第一首歌曲《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首尾呼應,也意味著兩種情緒的變化,最終將歌曲升華。
(二)《亡兒之歌》伴奏的交響性特征
在《亡兒之歌》的伴奏中,馬勒的交響性創作思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尤其是配器、和聲、伴奏、音色等方面,鮮明地體現出他“交響化”的創作方法,以及在各種音色、力度、節奏對比上的巧妙運用。
在第一首歌《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中,整體音色呈現給人以純凈的感覺,盡管有整個管弦樂隊進行伴奏,但在音樂中卻呈現較為單一的織體。從圓號、雙簧管的孤獨,到淡淡的歌聲與低沉的大管,與歡快的歌詞形成鮮明的對比。尤其是豎琴的使用,為整首歌曲賦予了寧靜的色彩,而終止時的鐘琴搭配歌詞“向人世的歡樂之光”更讓人感到音樂情感流露出的悲傷。
第二首歌曲《現在我看清了火焰為什么這樣陰郁》同樣使用了豎琴,但卻加強了弦樂器的使用,用大提琴貫穿全曲,通過強烈的力度對比加強人聲,又用小提琴和木管進行和聲填充。歌曲開始的低音提琴和突強的大提琴,充分體現了人物的痛苦與掙扎,而pp的弱高音則展現出深深的自責。
第三首歌曲《當你親愛的母親進門時》同樣充斥著憂傷,其節奏規整,表現出人物對自己內心躁動的壓抑。但與第二首歌曲不同,這首歌曲不再沿用豎琴,轉而使用木管作為背景音,使音色對比更加明顯。英國管的使用成為這首歌曲中最鮮明的特征,渲染出哀傷、沉悶的情緒。
第四首歌《我總以為他們出遠門去了》是作者內心的獨白,用圓號和弦樂隊配合號角聲,制造出曠野般的荒蕪,然后不斷安慰自己“他們只是出遠門去了”。但通過幾次調式、調性的對比,反映出內心更深的絕望。這首歌曲中,以木管、弦樂的混合音色為主,與前三首歌曲在音色上形成對比,而優美的豎琴總是將作者即將失控的情緒牽扯回去,形成段落內的音色對比。
第五首歌《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們出門》作為整個套曲的高潮,在音色與音區上都有了極大的擴張。頻繁的裝飾音以及大提琴的顫音,都將主人公內心的恐慌暴露無遺。第五首歌曲與第一首歌曲不僅在調式、調性上形成了呼應,而且鐘琴的使用同樣與第一首歌曲形成了呼應。在第五首歌曲中,其和聲半音化程度較高,大量半音化的和聲凸顯了緊張色彩。從pp到ff的力度變化,不斷推進著情緒的走向,定音鼓、大鑼、鐘琴的出現,標志著主人公對無謂掙扎的放棄,震撼了聽眾的心靈。最終,歌曲回到了明亮的D大調上。
鐘琴與調式、調性的呼應,豎琴與木管的背景音,圓號、定音鼓、大鑼、大提琴、雙簧管的運用,從pp到ff的強度對比,無不彰顯了馬勒的交響性創作思維。正是在這樣龐大的管弦樂隊伴奏下,五首藝術歌曲演繹出的復雜的情緒變化與內心波動,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四、結語
《亡兒之歌》的創作標志著馬勒音樂創作的新紀元,透過馬勒的音樂作品,我們能夠發現他作品中交響性的創作思維和交響化的創作手法。或許正是坎坷的人生經歷才使他始終追求具有強大表現力的交響效果,從而表現他內心的復雜。馬勒的藝術歌曲,不僅開創了用管弦樂隊進行歌曲伴奏的先河,也為藝術歌曲的創作、鋼琴伴奏的表現力提供了新視野。正是其交響性的創作思維,讓鋼琴伴奏不僅僅是簡單的音符彈奏,而是一整支交響樂隊的全新演繹,為藝術歌曲賦予新的音響和音效。
參考文獻:
[1]陳可.死亡陰影下的釋然與解脫 從馬勒的《亡兒之歌》到《大地之歌》[J].音樂愛好者,2021(01):49-52.
[2]黃李艷.世紀之交的挽歌[D].湖南師范大學,2017.
[3]莫成練.馬勒聲樂套曲《亡兒之歌》鋼琴伴奏分析[J].藝術探索,2013,27(06):88-89+105.
[4]宋靜.歌曲創作中的“器樂化”思維[J].人民音樂,2012(11):38-40.
[5]孫絲絲.“世紀末”的心靈探尋:馬勒三首中期交響曲研究[D].上海音樂學院,2012.
[6]袁暉.交融與升華——馬勒《第三交響曲》與藝術歌曲的關聯[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0(01):121-127.
[7]伊楠.古斯塔夫·馬勒音樂創作特點探究[J].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2009(S1):179-180.
[8]劉鑫.馬勒《亡兒之歌》演唱藝術研究[D].上海音樂學院,2011.
[9]孫舒君.略談馬勒“歌曲—交響曲”的風格特點[J].音樂天地,2008(09):60-61.
[10]李怛.愛告訴我說:馬勒的第三交響曲[J].愛樂,2007(04):65-72.
[11]李永鐸.《大地之歌》——馬勒交響性的聲樂套曲[J].音響技術,2006(02):71-73.
[12]李慶榮.馬勒的藝術歌曲和交響曲[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2,18(01):86-88.
[13]黃乃志.最后的波浪——記馬勒及其交響曲[J].音響技術,2000(02):72-75.
[14][奧地利]布勞科普夫.古斯塔夫·馬勒:未來的同時代人[M].高中甫,譯.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
[15]周雪石.馬勒[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16]孫國忠.馬勒交響曲的哲理內涵[J].中國音樂學,1989(04):77-85.
[17]孫國忠.論馬勒的交響思維[J].音樂藝術,1988(03):81-88.
[18][德]布魯諾·沃爾特.古斯塔夫·馬勒[M].馬楠,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7.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交響性與戲劇性的有機統一——馬勒藝術歌曲的藝術指導教學研究”(項目編號:2021SJA0405)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林甦,女,碩士研究生,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鋼琴表演)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