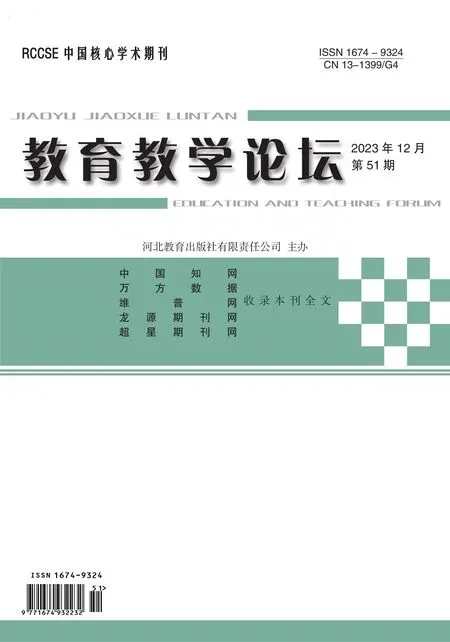西部高校教師隊伍的發展困境與應對策略
鄧詠梅,謝語前
(西安工程大學 a.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b.新媒體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8)
高等教育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提供高層次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撐,是西部全面振興的戰略有生力量。國家出臺《關于新時代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見》等政策,推動西部高等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高質量教師隊伍是激發西部高等教育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的關鍵。本文基于2020年教育統計數據,比較了西部與東部教師隊伍發展現狀,分析了存在問題和根源,探索了擺脫西部教師隊伍發展困境的對策方法和解決途徑。
一、東西部高校教師隊伍主要特征分析
我國有東西部地區和東中西部地區的劃分[1]。在教育優先發展的國家戰略指引下,中國高等教育整體進入世界第一方陣。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4.4%,穩步進入普及化階段[2]。但高等教育內部要素呈現東強西弱的不均衡態勢。
(一)專任教師規模
西部地區高校專任教師為45.9萬人、東部地區為82.1萬人(不含港澳臺地區)[2]。教育對社會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貢獻也是東部地區顯著高于西部地區。生師比體現高校教師數量滿足學生教育需求的程度,以及教師隊伍規模設置的科學性。西部地區普通高校總生師比為19∶1,遠高于東部地區的17.7∶1,也明顯高于國家標準18∶1[2]。從校均規模來看,西部地區普通高校校均專任教師為619人/校,東部地區為712人/校,教師集群程度呈現從東到西依次遞減的特征。
(二)專任教師結構
專任教師結構包括職稱、學歷、年齡、學科等維度。東部地區專任教師82.1萬人,西部地區專任教師45.9萬人。從分布占比來看,西部地區正高級專任教師占比為11.5%,副高級專任教師占比為28.9%,中級專任教師占比為36.9%,初級專任教師占比為12.2%,未定級專任教師占比為10.5%,職稱結構呈正態分布。東部地區正高級專任教師占比為15.5%,副高級專任教師占比為31.4%,中級專任教師占比為38.6%,初級專任教師占比為7.7%,未定級專任教師占比為6.8%,職稱結構呈正態分布[2]。東部地區教師職稱全面優于西部地區。
2020年西部地區高校專任教師博士占比21.6%,碩士占比39.8%,本科占比37.7%,專科及以下占比0.9%。東部地區高校專任教師博士占比35.0%,碩士占比34.4%,本科占比30.0%,專科及以下占比0.6%[2]。各級學歷專任教師人數東部呈梯度分布,而西部與全國均呈正態分布。博士占比西部比東部低13.4個百分點,東西部的差距較為顯著。
以陜西為例分析專任教師年齡的結構特征。陜西省普通高校專任教師7.3 萬人,29 歲以下占比10.3%,30~39歲占比40.0%,40~49歲占比29.8%,50~59歲占比17.4%,60歲以上占比2.5%[3]。中位數在39歲,年齡分布整體呈正態分布。中青年成為教師隊伍主體。
專任教師學科專業領域構成狀態可看成教師的科類結構。高校在較短時期內引入大批博士青年教師,部分新進教師專業背景與所在學院學科不匹配。開展學科專業結構調整,撤銷的學科專業教師轉型消化困難,而新建學科專業人才不足。多種因素導致教師隊伍存在明顯科學專業結構性問題。
(三)高層次人才隊伍
高層次人才是學校創新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十三五”期間,西部地區高層次人才雖逐年增長,但高層次人才隊伍整體規模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在西部地區的分布也極不均衡,主要集中于“雙一流”建設高校或部屬高校。高層次人才隊伍的收入東西部地區差異很大。如東部高校“杰青”的年薪高達100~200萬元,而西部高校一般僅為40~60萬元[4]。經濟收入等因素導致高層次人才很容易流向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
二、西部高校教師隊伍建設的困境和挑戰
教師隊伍建設還不能完全適應新時代賦予的新使命。西部高校教師隊伍建設面臨內外困境與挑戰。
(一)社會地理條件
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充足條件和深厚積淀。西部地區高校867所,東部地區高校1753所,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2.2 倍。西部地區只有1 省的普通高校數排在全國前1/3 位,有7 省排在后1/3位,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2]。高校規模成為東西部地區教師隊伍規模差異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區除了西安、成都、重慶等城市外,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洼地”[1]。我國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呈東南地區較為發達、向北向西輻射發展水平逐步遞減的態勢。西部地區高校大多數屬于地方高校,對地方財政供給的依賴程度很大。但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恰恰對高校的哺育能力又很弱,資源配置不足成為教師隊伍發展的重要瓶頸。
(二)高校舉辦格局
政府是高校管理主體。西部地區的中央部門直屬普通高校18所,占本區域高校的2.5%;而東部地區有81所,占本區域高校的7.1%[2]。“雙一流”建設高校西部地區入選28所,占總數的20.4%;東部地區入選92所,占總數的62.6%。高水平大學的東西部地區布局存在巨大差異。西部地區的獨立學院和民辦其他機構僅135所,而東部地區606所,民間資本對教師隊伍的補充貢獻有限。西部地區本科院校與高職(專科)院校比例為1∶1.4,而東部地區為1∶1。院校層次差異也對教師隊伍的結構和質量產生了影響。
(三)人才理念和引才政策
西部地區很多高校缺乏開展教師隊伍的頂層設計,教師隊伍建設的基礎性工程地位還沒有真正落實。部分西部地區高校教師隊伍必要的規模無法到位,導致教師教學科研投入不足,也很難形成邊際效益。面對東部發達地區多措提升吸引高端創新人才能力,西部地區高校政策力度不夠、措施不靈活、信息不足。學校穩才機制還不健全,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存在本土適應、學科融入、聘期延續等問題。優秀博士和高級職稱教師也存在“孔雀東南飛”的現象。西部地區高校面臨發達地區對優秀人才吸引爭取的嚴峻挑戰。
(四)管理體制機制
西部地區高校要持續健全師德建設長效機制。教師隊伍的分類設置崗位、分類管理、分類評價考核機制,以及獎勵激勵、收入合理增加機制改革還需不斷推進。教師培訓體系還未健全、學習交流機制還不完善,職業發展水平也遠低于東部地區。人才培育和成才的學術環境、文化氛圍還有待成熟。西部高校教師隊伍面臨激發教師隊伍內生活力、應對教育提質增效復雜性和艱巨性的挑戰。
三、西部地區高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思考與探索
西部地區高校要深刻領會黨的二十大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統籌部署,在教師隊伍建設上推動思想、機制、方法的創新。
(一)精準制定西部地區高教戰略發展規劃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質量內涵發展的新階段,國家應進一步制定高等教育布局優化調整戰略規劃,為西部教師隊伍發展提供政策、資源、機會等基礎平臺。建立高等教育資源統籌機制,將高等教育發展的增量主要用于西部等地區[1,5]。在以效率導向布局重點院校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高校對西部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效益,強化重點高校在西部的布局。激勵西部地方政府加大對省屬高校的政策支持和財力投入。鼓勵對人才和創新需求較高的非省會城市新增高校或新建較有實力高校的新校區。建立政府、高校和社會協同發展機制。通過民辦高校、合作辦學、產教融合等社會辦學方式,為西部高等教育補充有益力量。
(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頂層設計
西部地區高校要加強黨對教師工作的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要深刻認識大學競爭的本質是高水平師資的競爭,切實將教師隊伍建設放在“優先中的優先”地位,將有限的建設資源優先向教師隊伍傾斜,補齊師資隊伍規模和質量“欠賬”。高校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生態環境建設等西部重大戰略,特色布局,錯位競爭。要對重點發展的優勢特色學科教師隊伍供應和需求開展精準研判,協調好教師團隊與大項目、大平臺等教育要素的內在邏輯關系。以歷史眼光、開放視野、系統思維,不斷提高西部教師隊伍建設的頂層設計水平。
(三)創新人才引進使用機制
加強與西部大開發國家發展戰略相適應的西部特別支持高層次人才項目建設,建立西部高層次人才的結果應用與依托地區高校關聯的穩才機制。地方政府要為人才引進制定優化政策和平臺,促進人才鏈和創新鏈融合。西部高校要開闊視野,暢通人才信息,加強國際人才市場中的高層次人才引進。要創新引進政策,采用差異化引進、柔性引進等方式增大引進力度。要以中省人才計劃項目為抓手,以人才標準為靶向目標,對標對表做好西部高校自有師資隊伍高層次人才建設的引導、扶持、組織和保障工作。要樹立主動服務人才的理念,簡化行政辦事程序,對教師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困難及時解決。
(四)完善教師隊伍治理體制機制
在推進高等教育治理機制創新的過程中,“放管服”改革是關鍵[6]。要健全放權松綁與約束監督相結合的人才管理機制。將辦學自主權逐層下放,充分調動高校辦學主體積極性。以師德師風作為教師評價的第一標準,實行一票否決制。加強教師崗位分類設置、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為在教學、社會服務上有突出成績的不同類型教師構建職務晉升通道。堅持扭轉“五唯”傾向,創新崗位聘用、周期性考核、績效獎勵機制。要建設好教師隊伍職業發展機制,形成學歷學位提升、機構培訓、企業實踐、海外研修等相結合的教師培養模式。加強西部高校之間、中東部和西部高校聯盟工作,促進教師交流培養。要平衡好引進人才和自有人才的重視程度和扶持政策,讓兩類人才協同發力,相得益彰。高校要以人為本,形成鼓勵大膽創新和寬容失敗的氛圍。
(五)以數字化促進素養能力全方位養成
教育數字化是普及化階段的必然趨勢[7]。西部地區要抓住我國高等教育領域不斷深入推進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契機,以“互聯網+教育”助推教師隊伍建設的深刻變革。國家、地方和高校協同創新,構建數字化教師培育機制和平臺,建立優質教學資源開放共享應用機制,創新人工智能助推教師隊伍建設等新模式,提升教師信息化素養和育人能力。西部高校要加大信息化建設投入,改善信息化基礎條件,引導教師主動適應信息化教學技術環境。
(六)多措匯集資源,提高教師建設投入和收入待遇
西部地方政府要通過“雙一流”、高層次人才、創新平臺等項目傾斜,以及科研成果轉化成效分享機制等改革創新,加強對地方高校教師隊伍的支持。西部高校自身要通過提升辦學質量績效、社會服務、校友捐贈、校銀合作等渠道,開拓資源渠道。要加強內部資金績效管理,優先保障教師隊伍建設發展資金。要深化教師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教師基本工資收入,健全以學校發展重點和關鍵的業績為導向的績效工資分配機制,在創新人才中探索年薪制、項目工資等多種分配方式。
西部地區各方面要深刻認識高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堅持優化高校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優化引人機制、提升治理能力、強化鍛造培養、提高教師收入待遇等多向發力,建設一支能擔負新時代責任的西部教師隊伍,為振興西部高等教育、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創新動力和堅實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