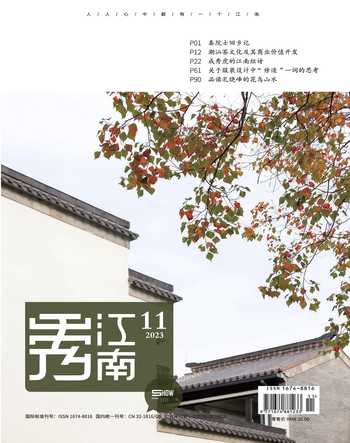心若無鶩,隨遇而安
詹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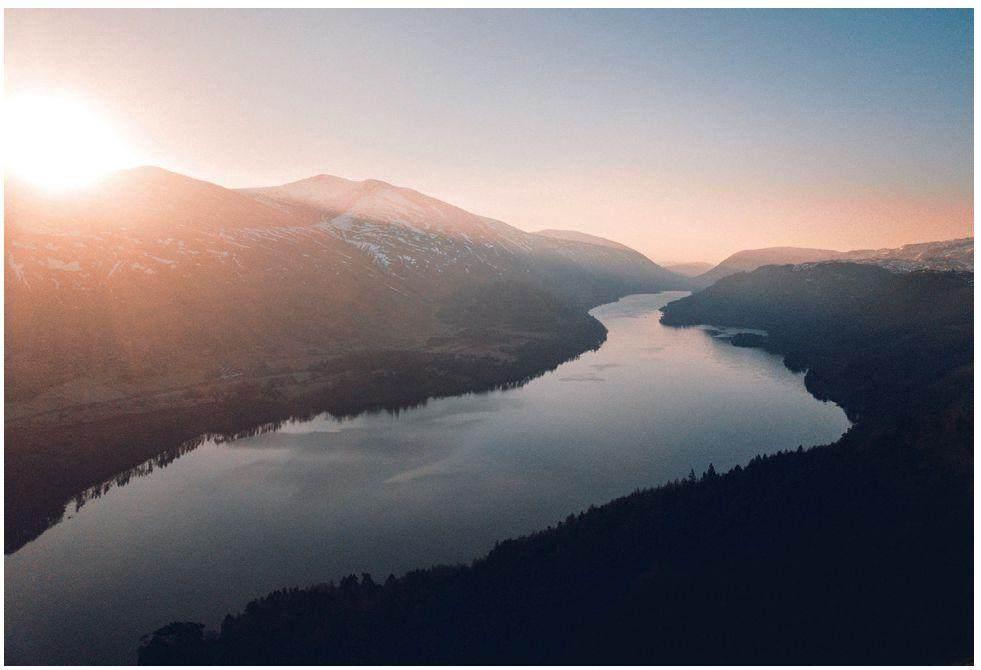

《白貘夜行》系雜志《十月》第二期女性作家專題下江蘇作家孫頻的一篇中篇小說。文章立意新穎,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別出心裁,通過褒貶結合的手法刻畫了生動的人物形象。作者擅長刻畫細節、設置情節,尤其善用心理描寫和隱喻、白描等修辭手法,寫作功底可謂爐火純青。文章最吸引人的莫過于一個四十歲中年婦女的賣餅生活打破了小煤城的平靜,昔日故友紛至沓來,或懷輕蔑、或懷同情、或懷敬畏,但未有人想到其生活是一種令人艷羨的幸福狀態。小說結構不卑不亢,通過對最平靜的生活的描寫呼出主題。主人公康西琳作為一個“吃”掉了自己夢的人,生活窘迫、居無定所,何以比她們所有人都過得更加心安?繼而引發了對當代社會語境下女性主義的再定位及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當代女性主義追求和企及?同時,小說成功地將個性與共性相結合,具有更加普遍和深刻的意義,而不僅限于將女性作為受眾,提出了一個不區分男性、女性的問題—何為人生價值?
寫作手法的嫻熟決定了小說在閱讀上吸引讀者,結構的設置使文章脈絡清晰有層次。在寫作手法上,作者采用了主人公康西琳同事的視角,無疑增加了小說的客觀性與可信力。作者以第三人稱對康西琳進行側面描寫,講述小說中“我”與康西琳的故事,即以“我”的角度對康西琳的故事進行偽客觀的敘述。小說結構可以分為兩個板塊—二十年前與現在,中間間隔的二十年是康西琳離開小城的二十年。對于這消失的二十年,作者與讀者態度相同,沒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發生了什么。二十年前,“我”與康西琳、曲小紅、梁愛華四人師專畢業分配到同一所中學當老師,這段短暫的工作經歷為二十年后的故事奠定了基礎,現在四人的生活與二十年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文中“我”與落魄的康西琳的對比,清晰地表達了文章所要探求的主要問題—比一比同宿舍的四個人誰過得更好?
作者極擅細節描寫,通過修辭手法的嫻熟運用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例如小說第二節這樣寫道:“不管美術老師畫得好不好,他畢竟人高馬大,畢竟是個年輕男人,還是學美術的,但他敲門從來只找康西琳。片刻之后,她忽然又伸手在我肩膀上打了一下,我一扭頭,她正笑嘻嘻地看著我,見我看她,忙又在我胳膊上捏了一把,說‘你就是骨頭架子小,我真羨慕你這樣的,永遠都不會長胖。我心里忽然一陣厭惡,繼續低頭備課,視角里恍惚看見她抓起一支筆。”“我”與康西琳的關系素來不錯,卻因這個美術老師的叨擾打翻了友誼的小船。此處作者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和因果照應將“我”作為一個小女人的形象成功塑造起來。“胡亂備了一會兒課,心里愈加不舒服,就那個美術老師,一個從來不畫畫的美術老師,不是在看書就是在做好吃的。就這樣一個男人。我不該這樣對她,我為自己感到羞恥。正在這時,她忽然把一張鋼筆速寫伸到了我眼前,是她剛才畫的,畫中的我正伏案備課,看起來有些駝背。談不上多喜歡,但我還是把這張鋼筆速寫掛在了床頭。后來發現曲小紅和梁愛華也各有一張的時候,我就悄悄把它撕了下來,藏在了抽屜的最里面。”“我”想了想那個男人,發現其一無是處,所以為自己方才對康西琳的惡心而羞愧,可這時康西琳送了張速寫給“我”,卻讓“我”發現曲小紅和梁愛華也有,于是我將其撕了下來。作者巧妙地設置情節,簡短的兩個段落內容上卻是一波三折,“我”表面平靜如水,實則內心已經翻江倒海了好幾回。在文章結尾,留守小煤城的“我”與曲小紅、梁愛華三人對康西琳生活狀態的懷疑終于促使“我們”在冬夜里去往汾河水庫,去見證康西琳是否每天都去冰河里游泳。作者運用了比喻手法,將康西琳比喻為水中非人非魚的黑影,康西琳的行動已然證實了她口中的一切,抽象的表達給予小說一個絢爛多彩、令人遐想的結局。
小說體量雖小,人物設置卻是精妙,每個人的身份都成功樹立了“典型”。文中的主要人物即二十年前同一宿舍的四人—“我”、康西琳、曲小紅、梁愛華,其中,“我”是一個沒有遠大抱負、安于現狀的普通人,曲小紅則是一個為了金錢嫁給煤老板兒子的虛榮之人,梁愛華是一個既沒什么性格也沒什么追求的“大傻個兒”,康西琳則完全是一個“另類”,她有理想、追求自由,總想著走出小煤城,也在一天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了出去。同時,四人間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勾心斗角,表面上又能親如一家地去逛商場,維持著表面的和諧。二十年后,康西琳回到小煤城賣烙餅,生活窘迫卻活得很開心。康西琳的生活狀態令留在小煤城的三人不解,曲小紅一口認定康西琳是裝的,“我”則因為多次去五一大樓觀察康西琳而確認她是真的過得好。曲小紅一直對康西琳持一種近乎敵視的態度,從前文看源于校長辦公室的爭執,曲小紅與康西琳在那句“傻X”上結下了梁子。可細思康、曲二人的角色,其實二人都屬于不甘于平庸生活的人,不過一個生機盎然、追逐理想,另一個期盼捷徑、屈于現實。曲小紅對康西琳的偏見與敵視似乎是一種現實對理想的恐懼,而“我”的角色更傾向康西琳,帶著尊重與崇敬,甚至夾雜著羨慕,因為此刻的康西琳雖然落魄卻享有所有的自由,而“我”只能在丈夫、女兒睡后的深夜倒上一杯酒爬上窗臺。
小說結構清晰、邏輯嚴密,通過對康西琳與“我”的生活進行潛在的比較以及我對康西琳的“幸福生活”透露出的一種隱約的羨慕,將康西琳式的自由呼出。康西琳懷揣著理想與抱負毅然走出了小煤城,卻在二十年后落魄不堪、居無定所,回到小煤城。相比留在煤城的“我們”,在物質生活上她是潦倒的,可即使她在賣烙餅,她的生活依然精致、豐富,同時她有一個令“我”艷羨的自由的靈魂。康西琳的人生重新樹立了一個新女性的典型,雖然物質生活貧瘠,但是以富裕的精神實現了生命的自由。作者從女性角度出發卻成功打破了女性寫作的壁壘,以個性展現共性—康西琳是否是一個活得好的女人倒是其次,其對于生命的詮釋值得所有讀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