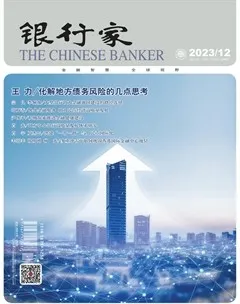廠商理論(十)
——廠商:走向未來
張興勝
1859年,在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廠商”蓬勃涌現的特殊背景下,查爾斯·狄更斯的長篇歷史小說《雙城記》出版。《雙城記》開篇即講:“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的生動筆觸,映照了廠商經營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兩面。我們討論的廠商,“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在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歷史實踐中,展現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我們討論的廠商,在自身發展和剩余價值生產中同樣存在“用血和火的文字”書寫的一面。1825年7月爆發了第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更是展現了廠商剩余價值生產的內生矛盾。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學家的如椽巨筆,期待更公平社會生產的正直愿望,都在不斷激勵廠商自身的探索變革,推動廠商走向未來。
資本來到人間
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講過,工業革命以后,“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哪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的圣人。”馬克思和他的后人的著作,展現了廠商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用血和火的文字”書寫的一面,生動描述了資本來到人間后毛孔中滴著的“血和骯臟的東西”。
追逐利潤。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各類自耕農、佃農等勤苦勞作,期于果腹;貴族、地主等組織生產,往往追求奢侈消費;以“賤買貴賣”為目標的商人,游走在封建經濟的縫隙中。廠商興起后,追求利潤是其公開的目標,逐利成為刺激社會生產的直接動力。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在履行資本職能時,如果有20%的利潤,就會活躍起來;如果有100%的利潤,就可能踐踏一切人間法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所謂原始積累》中引述托·約·鄧寧《工聯和罷工》的片段,作了生動的描述:
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
廠商持續發展并在社會生產中占據統治地位,逐利之風大興,摧毀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增大了”,藏鏹追金成為時尚。大航海時期哥倫布就贊嘆:“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廠商追逐利潤的流風所及,使整個社會都變成一個“蒸餾器”,正如《資本論》第1卷中所描述的:
因為從貨幣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東西轉化成的,所以一切東西,不論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轉化成貨幣。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
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13世紀時期,地中海周邊尋求海外財富的探險潮,引發了地理大發現及空前的海外貿易需求。許多雇工生產海外貿易、皇室采購或國內銷售商品的富商,獲得了“第一桶金”,社會財富日益表現為“商品的堆積”,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到了現實生活。
資本登上歷史舞臺并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需要日益擴大的市場、原材料及進入工廠的雇傭勞動力。實現這一條件的歷史過程,就是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
資本原始積累是消滅封建自耕農的過程。14世紀—17世紀,西歐貴族、地主與新興資本家結合,利用封賜、強買強賣、強占等各種手段侵占公有土地、剝奪自耕農耕地,征占摧毀自耕農村舍、住宅用于養羊,史稱“圈地運動”。對失地流浪者處鞭刑、割耳、處死等刑法的法律,將人類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的小生產者驅趕進工廠。1750年,英國自耕農被消滅,到18世紀末,農民公有地最后的痕跡也蕩然無存了。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工廠,資本雇傭勞動成為新生產方式的特點。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引發社會革命,并“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世界近代史掀開了歷史面紗。“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
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具有持續進行市場擴容的客觀需要,工業革命后的“船堅炮利”給了野蠻擴容的力量,殖民掠奪以幾近瘋狂的節奏狂飆突進。美洲金銀產地被發現后,土著民族被剿殺、奴役和埋葬于礦井中,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海盜劫掠及奴隸貿易為殖民者賺來了滿船金銀。所謂資本原始積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絕對剩余價值生產。1867年,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提出并論證了“兩種剩余價值生產”。其中,以延長勞動時間、野蠻加大勞動強度為特點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直接展示了廠商生產中“血與火”的一面。
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在殖民地更為血腥。在美洲大陸,“當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滿足本地需要時,黑人勞動還帶有一種溫和的家長制的性質”,當主要滿足巨大的棉花出口生產時,“黑人所從事的過度勞動,有時只要七年就能把生命耗盡。”在1863年的英國火柴廠,“工作日從12到14小時或15小時不等”,大量的童工在充滿磷毒的空間奔波,馬克思感嘆:“如果但丁還在,他一定會發現,他所想象的最殘酷的地獄也趕不上這種制造業中的情景。”工作日的減少、工作環境的改善以及已被視為當然的“以人為本”的企業發展理念等,都是偉大的思想家及正直的人們歷經無數奮斗才成為人間的文明成果。
不平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并深刻論述了剩余價值理論,其他經濟學家也從不同角度討論了資本生產中的不平等問題。1879年,亨利·喬治風行一時的名著《進步與貧困》出版,亨利·喬治提出:
看看我們的廣闊城市,我們看到了什么?一邊是極少數的人非常富有,遠遠超過一個人應該有的體面生活,另一邊是大量男人和女人為了可憐的生計而掙扎、擔心和疲憊。
亨利·喬治旗幟鮮明地提出,不平等的基本經濟根源是生產要素的不平等回報。在亨利·喬治看來,經濟發展中租金持續上漲,主要原因在于壟斷土地的人們在與競爭性地提供勞動力的勞動者競爭中,賺取了“生產成果的全部剩余價值”。
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出版,保羅·克魯格曼、羅伯特·索羅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專門撰寫了書評,《經濟學文獻》稱贊此書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學領域最好的一本著作”。托馬斯·皮凱蒂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觀點:資本的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資本所有者的財富增長快于社會中其他人的財富增長,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托馬斯·皮凱蒂以事實批判了經濟增長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的流行觀點,“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固有現象”。托馬斯·皮凱蒂還發現,資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勞動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階層的收入中資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所以資本份額與整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是正向相關的。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1825年7月,工業革命以來一直蓬勃發展的英國“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爆發,市場商品滯銷,物價暴跌,大量工商企業破產。到1826年10月,3500多家工商企業破產,70多家銀行倒閉,棉布出口量下降23%,機器制造業、建筑業以及其他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遭到了沉重打擊,大量工人失業,整個社會經濟處于極度恐慌和混亂之中。這場危機之后,每隔十年左右,資本主義國家就要發生一次經濟危機,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資本主義國家大多不同程度地爆發了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造成的社會財富浪費及低收入者災難,給社會各界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被普遍視為一種“社會瘟疫”:
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共產黨宣言》)。
危機震驚了世界,危機深刻改變了經濟學理論視野,危機推動廠商制度演進及社會生產方式變革。對經濟危機成因的分析及矯治出路的討論,成為推動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強大動力,導致政治經濟學研究不斷經歷模式更新。從古典經濟學時代到21世紀,討論經濟危機的經濟學群星璀璨,“時代之問”引導思想變革。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與批判視野,透過廠商生產表相,深刻地改變著社會面貌。
從薩伊定律到“鐵的必然性”
1825年,英國經濟危機爆發時期,與商品滯銷、百業凋敝、無數企業破產的現實形成強烈諷刺的是,經濟理論界仍然漫著市場自動平衡供需、經濟只有波動而不必擔心危機的思想,其核心思想被稱為“薩伊定律”。
薩伊定律,也稱薩伊市場定律(Say’s Law of Market)發明人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是位出身里昂的法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馬克思稱為法國庸俗經濟學的鼻祖。薩伊個性倔強,因經濟學才識被拿破侖賞識,又因鼓吹自由貿易、反對拿破侖的關稅保護政策而被解職。1803年薩伊出版《政治經濟學概論》,宣揚貿易自由放任思想,其自由主義思想經英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提煉,被稱為“薩伊定律”。
在薩伊看來,生產商品過程中廠商采購原料的支出,就是原料供應商的收入;雇傭工人的支出,就是工人的收入。商品生產的同時,工人及原料供應商收入對應產生,收入是消費的基本,“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供給增減時消費也會相應增減。薩伊主張經濟學應研究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問題,提出工資、利息、地租三種收入組成商品價值,提出了“三位一體的公式”,稱利潤是企業家才能的報酬。薩伊的自由主義思想受到李嘉圖忠誠的學生詹姆斯·穆勒(又稱“老穆勒”)的喝彩,這位提煉出了“薩伊定律”的經濟學家可能沒想到的是,反對他鼓吹的薩伊定律的人們中,包括他的兒子——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穆勒(又稱“小穆勒”)。
馬克思深刻批評了薩伊鼓吹的經濟思想。馬克思承認一切生產活動都為了消費,但是并不是廠商生產出商品就有人購買,“人們并不是一有銷售就非購買不可,賣和買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是分開的”,供給并不能同時自動地獲得需求。在馬克思看來,流通之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回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因此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之間天然存在著“驚險的飛躍”。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自1825年英國爆發世界上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便在繁榮與蕭條中交替運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表明,“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僅存在,而且還存在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鐵的規律性”。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表面看來是商品流通領域供求失衡的結果,實質是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矛盾的表現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大工業生產方式具有一種跳躍式的擴張能力,“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張的能力”,生產規模總是實現跳躍式的膨脹。從社會消費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相對人口過剩,失業人數增加,對抗性的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必然造成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對縮小。跳躍式膨脹的生產規模和相對狹隘的社會消費,產生商品生產與實現的矛盾,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危機的出現: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馬克思在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和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示了跳躍式膨脹的生產規模和相對狹隘的社會消費矛盾的根源。在生產領域,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剩余價值規律、市場競爭規律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能力的跳躍擴展,提供了強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壓力;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工廠制度、股份公司制度為生產能力的擴展、資本突然擴展能力的增長提供了有激勵效應的微觀制度結構;社會鼓吹的自由經濟思想、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為社會生產的盲目擴展提供了“寬松”的外部環境。從社會消費領域看,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分配及社會產品分配,使勞動者的相對甚至絕對貧困化成為市場結果。
馬克思指出,“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并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馬克思繼承了西斯蒙第的觀點,主張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本質,即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及資本雇傭勞動,這一生產條件運動發展的“鐵的必然性”,就是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給社會生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使人們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認識到了“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
從《烏托邦》到圣西門
“用血和火的文字”書寫的社會罪惡、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都在激勵正直的人們,尋求更公平、更理想的廠商生產和分配模式,構想未來更公平、更理想的社會。
早在1516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出版《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書》(又稱《烏托邦》)。書中虛構了一個航海家航行到一個奇鄉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那里財產公有,人民平等,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大家穿統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官吏由公眾選舉產生。莫爾同時設想,烏托邦生產力十分發達,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起碼領先1000年以上,所有人都有服一個月工役的義務,以便供應免費市場。
1819年,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西斯蒙第(Sismondi,1773—1842)發表獨出新見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提出了一系列后世稱為經濟浪漫主義的新思想。西斯蒙第原籍意大利,曾在里昂一家銀行當職員,法國大革命時還曾被捕入獄,1800年重返瑞士后一直從事著述活動。法國大革命后小生產者的破產分化和英國的經濟危機,促使西斯蒙第成了當時頗為盛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激烈反對者。西斯蒙第反對將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張,認為經濟自由主義給社會帶來災難,提出保持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是社會經濟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要求依靠國家政策調節社會經濟生活。在西斯蒙第看來,機器大工業發展及企業不斷集中造成生產的無限擴張,不公平的社會分配使財產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不斷縮小的矛盾,使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遭到破壞,最終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斯蒙第還提出,“今年產品成本支出(原料商及工人收入)往往在去年,生產不斷擴大,今年的產品總是超過去年原料商及工人收入,生產和收入失調導致消費不足,使得經濟危機不可避免。”
西斯蒙第期望用宗法和行會原則來組織社會經濟,將城鄉中的大工業企業分散成眾多的小農場和小作坊,要求法律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實行“完全合理的裁判”,促進遺產分散,保證工人能夠分享利潤,避免私人利益給社會帶來過大的不幸。他贊美中世紀行會手工業和宗法式農業的原則和規范,其思想后來被稱為“小資產階級經濟浪漫主義”。
1802年,杰出的思想家克勞德·昂利·圣西門(Claude-Henri de Rouvroy,1760-1825)發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這位與傅立葉、歐文并列為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偉大學者,發表了《人類科學概論》(1813)、《論歐洲社會的改造》(1814)、《論實業制度》(1821)、《實業家問答》(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系列著作,把“發明”和論證未來新社會制度作為畢生的使命。
恩格斯講過,“圣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圣西門思想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親眼看到革命后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只給少數富有者和大資產階級帶來了利益,三權分立并沒有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法國革命“這一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只是產生了新的奴役形式”。他批評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認為需要以一個“旨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數的窮苦階級命運”的新社會取而代之。他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不是偶然事件的聯結,而是與整個宇宙發展過程一樣按規律進行的,是一個連續的、上升的、進步的發展過程,封建制度崩潰后資本主義取而代之,而資本主義也終將走向衰亡,另一個更高級、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必然要出現,他預言舊的社會制度必將為理想的“實業制度”所代替。
圣西門設想的“實業制度”下,不再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私人企業的生產要受國家監督,統一安排,按計劃進行,人人都要勞動,經濟按計劃發展,個人收入應同他的才能和貢獻成正比,政治學將成為生產的科學。他把自己的理想社會制度學說稱為“新基督教”,認為“要從事一項偉大的事業必須有激情”,只要大家都信奉他的這種新宗教,新的社會制度便可以實現。
圣西門的偉大思想影響了無數的人,其中包括老穆勒傾盡心力超前教育培養的大學者小穆勒。小穆勒感嘆,圣西門“對一般自由主義理論的批評,在我看來充滿著重要的真理”,“如果要在擁有一切可能的共產主義和具有各種苦難和不公的現存社會秩序之間作選擇”,“如果私有制必定帶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后果,即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和勞動成果成反比”,“共產主義的一切困難在天平上都輕如鴻毛”。
走向未來
廠商是特定生產方式的承擔者。廠商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需求、相關利益方生產生活情況及思想意識,是廠商行為理論變革發展的土壤。廠商在持續變革。除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外,經濟思想的嬗變演化、各國政府的探索實踐、社會各界的關注思考,都在推動廠商走向未來。
經濟思想的嬗變發展推動廠商走向未來。古典經濟學時代,集大成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薩伊等的經濟自由思想的基礎上,吸納了西蒙配第、圣西門、小穆勒等人分析討論經濟危機的思想觀點,構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偉大廈。馬克思深受圣西門等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激勵,他更現實地認識到,“實業制度”的實現,要求工人階級自身的覺悟和組織,需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實現圣西門所稱的理想的“實業制度”的崇高理想和思想主張,開啟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歷史新篇章。共產主義者聯盟、巴黎公社、社會主義革命等恢宏的歷史篇章,從這一崇高理想起步。孫中山先生就剴切地指出:
至于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后,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著他走……馬克思的這種發明,有比之于牛頓所發明天文學的重心學說一樣。
各國政府及社會組織的探索實踐推動廠商走向未來。19世紀后,歐美各國政府均大力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德國率先組建了政府投資的交通運輸及郵政電訊投資運營企業。歐美發達國家先后開征累進的所得稅、遺產稅,“施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征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流行,歐美國家的消費合作社興起,“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孫中山先生稱“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國有企業、合作社等的興起,政府組建基礎設施投資運營企業并開征累進的所得稅、遺產稅等,徹底改變了以19世紀上半葉英國工業企業為代表的廠商形象。前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全民八年義務教育、免費職業技術教育、免費高等教育、全民公費醫療制度(住院免付伙食費),城市居民可在政府免費供地上自建住宅,政府供應廉租房或廉價房,各類職工在職期間均享有時間不等的帶薪休假福利,這些改革一時驚艷世人。可能令世人意外的是,被孫中山先生稱為“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的一系列政策,其實出于鐵血政府之手。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時期,規定了8小時工作制,徹底改變了當時普遍存在的16小時工作制;發布了一系列規范青年和婦女用工年齡和工時的法令,國家統一籌集社會養老費和醫療保險費,等等。在有許多資本家反對的情況下,這位鐵血宰相“用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廠商變革的背景,是一部復雜的近代社會變革史。
社會各界的呼吁探索推動廠商走向未來。西方政府改善工人勞動福利與保障政策的出臺,往往是工人群體持續努力的結果。一些“資本家”也推動了廠商的巨大變革。亨利·福特(Henry Ford)1913年在密歇根州開始了工業流水線生產,開始了工業流水線生產時代。美國實業家、慈善家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既是“鋼鐵大王”,又被世人譽為“美國慈善事業之父”,設立了大量的工人救濟和養老基金,興辦3500座圖書館,創辦卡耐基大學。
廠商在變革,廠商行為理論也在持續發展。回望歷史,翻檢舊章,是為了汲取歷史的智慧,讓充斥各種曲線、定理的黑板經濟學走向真實的經濟世界,更好地面向未來。普羅大眾如我等,其實“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人們從不同視角討論廠商由來已久,今天的人們對廠商的新見奇談,幾乎都能在歷史討論中找到注腳。我們當下的討論,仿佛是與前賢對話。我們回望廠商理論,其實是在期待更理想的企業制度和社會生產方式。希望我們關于廠商行為理論的系列隨筆,能夠不攪擾讀者諸君閱讀的清雅。希望靚裝輕步的人們點撥教正之余,能夠始終銘記偉人馬克思的規箴——
“閣下,這里說的,正是您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