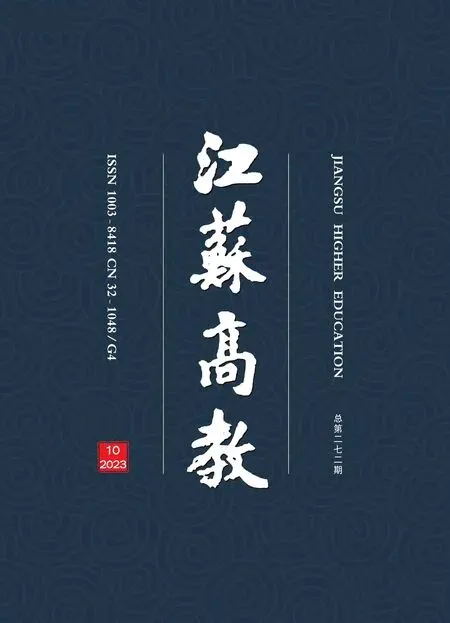新時代增強高校師德建設有效性的路徑論析
劉璇 ,呂立志 ,吳永祥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0016;2.南京市教育局 督導室,南京 210008)
一、當前高校師德建設的現實困境
從2014年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到2019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師德師風建設的意見》,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師德師風建設的政策法規與制度文件。當前,各高校設立了師德建設委員會,成立了黨委教師工作部,制定了師德失范行為負面清單和處理辦法等,師德師風建設得到了一定的加強和推進[1]。然而,近年來,高校師德失范行為屢禁不止、時有發生,高校師德建設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一些教師背離了自身作為“教育工作者”“知識分子”和“學者”的初心與使命,損害了高校教師的社會形象和高校的社會聲譽,影響了師德建設的實效。
(一)身份角色的錯位導致教師育人意識淡薄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認為“在敢于擔當培養一個人的任務之前,自己就必須是一個值得推崇的模范”[2]。教書與育人的高度統一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教育。現實中,多數高校教師能充分認識立德樹人的重要性,但部分教師出現“重業務能力輕政治素養”“重科學研究輕教書育人”等問題,高校一定程度陷入“非理性繁榮”的價值困局。部分教師上課敷衍塞責,缺乏教學熱情和教學創新,教書育人從“價值實踐”異化為“技術操作”;極少數教師思想偏激,在教育教學活動及其他場合中存在損害黨中央權威、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行;極少數研究生導師言行失范,以“老板”自居,屢屢要求學生處理與教學、科研等無關的個人私事,向學生索取財物。究其原因,雖與高校重視科研與學科建設的整體導向有關,但關鍵在于教師角色認知錯位,缺乏應有的責任感。
(二)競爭的“內卷化”誘使教師學術責任缺失
學術性和文化性是高等學校的本質屬性。當前,學風浮躁、學術腐敗已成為大學教師師德失范現象的突出問題。部分教師重市場價值輕學術價值,學術理想淡漠,“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執著缺失;部分教師為拿課題、發文章、評職稱弄虛作假,抄襲剽竊他人學術成果;部分教師把社會服務當作交易,“學術自由”演變為“市場自由”,“研究學問”演變為“經營學問”,科研在市場的推波助瀾下異化為私有財富[3]。究其原因,與高校“內卷化”競爭下教師道德滑坡、心態扭曲密切關聯。
(三)制度的“不道德”沖擊高校師德治理生態
當前,不同高校或高校內部不同師德建設主體在師德建設理念、層次與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在師德實施細則上,一些高校“過于粗糙”或“過于細致”,閉門造車,缺乏應對新問題的彈性;在師德教育上,一些高校方法陳舊,載體單一,存在“重職前師德培訓輕職后師德教育”等現象;在師德考核上,一些高校定性評價多、定量評價少,可操作性不強,可信服度不高;在師德失范治理上,一些高校或以教育為主而包庇縱容,或在社會輿論“聚光燈”下“沉疴下猛藥”;在師德問責上,一些高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失衡,問責職責存在重疊、錯位或缺位[4]。究其原因,在于師德治理制度本身缺乏一定的合法性、正當性,因而難以得到教師的體認支持。
(四)環境體制的“不公平”忽視教師合理發展訴求
高校教師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抽象人,而是有著生存與發展需要的世俗存在體,教師的工作環境是影響教師師德修養的重要因素。在高校行政權力的強力主導下,有限理性決策依然存在,教師決策參與權存在虛位現象,許多青年教師面臨“非升即走”“準長聘”等現實壓力,高校對教師發展的人文關懷不夠,從而導致教師個體價值目標與大學組織價值目標出現內在沖突[5]。同時,一些高校管理人員演變為以權謀私的政治人,他們在對與教師權利有關的資源分配、評比評審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現象,擠壓學術權利空間,教師的學術權利和發展訴求得不到應有保障,“教師個體和學校組織對彼此責任的感知、認同和期許存在差距”[6]。究其原因,關鍵在于高校管理中科學主義、管理主義色彩依然濃厚。
二、增強新時代高校師德建設有效性的路徑選擇
(一)在明責中強化師德認知,增強教育引導深度
師德具有規范功能,能在規約教師言行中引導和促進教師崇德向善。師德規范是師德認知的源頭。高校教師具有相較于中小學教師不同的職業特性,高校教師的職業勞動包括教書育人、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等。因此,高校需要從政治道德、育人道德、學術道德三個方面厘定何謂其職業責任。其一,在政治道德上,以堅定政治方向為關鍵。高校教師要牢記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使命,提升政治站位,不斷增強政治領悟力、政治判斷力、政治執行力。其二,在育人道德上,堅持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美國康奈爾大學原校長羅德斯認為,“教學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職業。它不僅提高領悟能力,還規范了行為;它不僅影響和塑造智力,同時也影響和塑造意愿;它不僅對思想而且對心靈進行教化”[7]。高校教師要堅持教書與育人相統一、“經師”與“人師”相統一,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師生觀,當好青年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其三,在學術道德上,以堅守學術良知為前提。高校教師要崇尚學術自由、學術民主,恪守學術理想、學術誠信,在學術與市場中保持必要的張力與自律精神。高校教師只有在“明責”中將“政治方向”“育人導向”“學術志向”有機融合,才能深化師德規范的接納度、強化師德教育的感染力,才能增強師德認知的效度。
一是增強師德規范的接納度。對師德規范的認知,能夠幫助教師全面認識崇高師德的理想圖景和師德失范的紅線底線,避免出現認知上的模糊與偏差。師德規范理應是來源于“生活世界”并基于“規則范疇”而由“公眾”制定的。高校在師德規范制定過程中要賦權教師參與協商討論,將外在規范轉化為教師的內在德性;否則,如果其他利益相關者過多參與,則可能導致教師在師德建設中自主建構的進程被滯塞,進而阻滯師德建設的有效性。與此同時,為了教師真正接納師德規范,還要兼顧“底線師德”與“高位師德”的關系。教師對“底線師德”的遵守,追求的是“教育有效善”;而教師對“崇高師德”的向往,追求的則是“教育優秀善”。因此,高校要將“正面引導”與“負面約束”統一起來,引領教師對自身職業行為進行反思批判和道德拷問。
二是提升師德教育的感染力。師德規范的確立并不意味著教師師德修養的必然提升,教師參與師德教育的態度、教師提升師德涵養的程度都對師德建設的成效產生重大影響。師德教育是“內修外塑”的過程,是教師個體與學校組織交互作用的過程。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要改變政治式、命令式、口號式的教育引導,激發教師師德認知的內生性,建構全覆蓋、全過程、全方位、全時空的“四全”教育模式。在全覆蓋師德教育方面,師德教育既面向專任教師,又面向高校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既包括入職崗前培訓,又包括職后師德培訓。在全過程師德教育方面,以政治道德教育、育人道德教育、學術道德教育為重點,把師德教育貫穿教師職業行為各環節、職業生涯全過程。在全方位師德教育方面,堅持有組織的師德教育與自我師德教育相結合、師德榜樣引領與師德警示教育相結合、師德教育與黨風教風學風相結合。
(二)在樂責中升華師德情感,激發環境凝聚效應
教師的師德情感并非產生于“真空”,也并非教師“與生俱來”,而是教師在一定環境與條件促成下的情緒反應,是與高校組織環境、個體生活世界緊密相連的。高校教師是情感體驗和價值追求的道德主體、倫理主體,更加注重內在品質、精神滿足和自我實現。幸福道德作為一種崇高師德,是主觀感受與體驗的道德,是教師在教育事業與學生朝夕相處中獲得的。因此,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要重塑激發師德情感的理論前設。教師的身份角色決定了高校激發教師師德情感的價值取向與人性基礎,合乎幸福道德的教師發展生態是師德由他律轉向自律的關鍵。首先,要“把人當人看”。高校要構建“生命人”的人性假設,承認教師的自尊與良知,維護教師作為人的主體權利。其次,“使人成為人”。高校要以教師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旨歸,把教師的“物質富有”與“精神富有”融合起來,把促進教師敬業奉獻與幫助教師自我成就統一起來。只有建構“富有道德感召力”的教師發展生態,找準師德建設與教師發展的共鳴點,才能充分、有效激發教師的師德情感體驗和情感認同,從而使教師自覺弘揚崇高師德、堅決抵制師德失范,實現教師生命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一是確立適切的職業生態位,進行積極的情感體驗。動機目標理論認為:不良的心理動機往往會造成不良行為的發生。高校教師的行為模式與教師的師德情感密切相關,其師德失范行為常常與過高的目標期望、過大的心理壓力密切相關。教師的師德情感直接影響著教師的需求偏好、價值偏好,并使教師對師德產生差異化的理性認知與理性判斷。生態學理論認為,每個生物體都有一個位勢,當兩個生物利用同一資源或共占相同環境變量時,則出現生態位重疊現象。高校作為一個場域,場域活動的自主性為教師根據自身能力、興趣、需要來選擇競爭策略提供了更多可能。每位教師都是自身職業的主人[8],要敏銳地感知內外部環境變化,客觀分析自身優劣勢,在獨立于外部壓力與干擾下確立適切的職業生態位,妥善處理教學與科研、教書與育人、競爭與合作、自由與創新等學術生產關系;要及時拓展生態位寬度,在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主動開展可用資源的拓展,在遞進累加中提升競爭優勢、積聚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高校教師要用積極心理學理論武裝自己,主動培育毅力、創造性、洞察力等積極的人格特質,主動增強職業韌性、紓解職業壓力,自主構建自知、自尊、自信、自強的自我系統,在幸福快樂的情緒體驗下規避師德失范行為發生。
二是優化教師發展生態,創設教師權益保障體系。觀照教師的人格尊嚴和主觀幸福感在師德建設中同樣重要。教師的幸福感會激發并增強教師的正向道德情感,從而使教師積極并樂于履行自身的專業職責與道德責任。如果教師缺乏組織歸屬感,就難以做出與師德規范相吻合的師德選擇。一是要強化公平競爭的力度。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妥善處理高校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利的關系,為教師提供更多的發展通道,創設“讓能者有位”的公平競爭文化。二要增強人文關懷的溫度。深化高校民主管理機制改革,完善教師利益表達機制與政治參與機制,在平等民主、協商對話的基礎上構建以教師法、大學章程等為基礎的教師權利義務保障體系。三要烘托尊師重教的熱度。全社會要弘揚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不僅要提升教師的經濟地位、物質待遇,而且要提升教師的社會地位、職業聲望。
(三)在監責中磨礪師德意志,增強師德治理效能
外在道德規范要轉化為內在自覺,必然受個體經過內心加工而形成的信念的支配,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只有具備長期遵守道德的習慣,才可能成為有美德的人”[9]。教師只有不斷增強對師德規范、責任擔當的理解,常態化對自己的道德判斷進行自我省思,才能不斷提升對師德的自我評價能力、自我監督能力,從而形成積極正向、持久穩定的師德意志。與此同時,在新時代,人的歷史性存在或關系性存在的屬性更加突出,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僅僅依靠教師的內省、反思和自塑是不夠的,還應當通過制度外力的導向作用,在普遍聯系中培養有理想的人和生活中的人。師德治理是使師德理想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保鮮劑”,是教師選擇職業行為的“風向標”。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要切實擔負師德督導的責任,充分發揮師德的調節功能,破立結合,標本兼治,通過師德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將師德治理正當性與師德治理協同性有機結合,在恪守師德治理正義的前提下推進師德治理效率變革,在強化師德治理的導向中促進教師知敬畏、存戒懼、重自省,從而提升師德治理效能。
一是在師德治理正當性中強化師德意志。正當合理的師德治理制度所體現的督導功能理應彰顯教育的價值旨趣。在此情況下,教師會自發萌生對制度內在權威的情感認同和心理承諾。高校要堅持師德治理內容與治理程序相統一,保障制度制定、執行與供給的正當屬性與道德理性,激發教師對制度規范的自由超越[10]。一方面,師德治理制度的制定,應堅持事實有效性與法律規范有效性相統一。哈貝馬斯認為,法律的有效性應包含“行為的合法律性”和“規則本身的合法性”兩個維度,前者是事實有效性,后者是法律規范有效性。在此理念觀照下,教育主管部門應進一步健全完善師德相關的法律法規,充分滿足高校師德治理需要;高校要堅持政策保障、制度規范、法律約束相銜接,各項師德治理制度不得與上位法相沖突。另一方面,師德治理制度的有效執行離不開對行政權力的有效規約。師德制度的執行應當保持穩定且前后一致,對教師不正當行為的懲戒應一視同仁,防范“公共權力異化”,縮限“自由裁量空間”。在師德問責正當性方面,要堅持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相耦合、“對個體問責”與“對組織問責”相結合,合理劃定師德失范行為的問責等級、范圍與程度。只有這樣,才能使教師對自身職業行為進行合理預判,有利于教師在拒絕非正義的同時強化恪守師德治理制度的意志。
二是在師德治理協同性中強化師德意志。當前,高校師德工作機制亟須實現從“有序建起來”到“有效轉起來”的轉向,需要上下互動、左右協同、內外融合,形成最大合力。高校要優化師德治理結構,堅持主體間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妥善處理大學公共性與自主性的關系,厘清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既要吸收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師德治理,又要與社會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從而推進師德治理從共同治理走向有效治理。在師德隱患摸排協同化方面,要組織多方力量聯合對師德失范風險進行預測預警預防。在師德監督協同化方面,要探索構建政府、高校、教師、學生、家長和社會廣泛參與的“六位一體”師德監督體系,建立多元化的師德投訴舉報平臺。在師德懲處協同化方面,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打造集智能性、共享性、交互性、協作性于一體的新型師德治理模式。通過協同化師德治理,著力形成人格平等、品行高尚、情感融通的高校“師德共同體”,提升教師的道德自治能力,增強教師的正向師德意志水平。
(四)在擔責中投身師德實踐,增強師德內化程度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人的意識對實踐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道德立足于“現實生活”,又能改造“現實世界”。教師德性是一種實踐德性,教師要通過師德實踐,“既實現和肯定自己,又喪失和否定自己”[11],這是教師的個體意識與思維發展的自然結果。師德內化是社會層面的道德要求轉化為個體層面道德需要的過程,是外在規約與內在觀念趨向一致的過程,是教師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追求崇高師德是一種創造性、生成性的過程,需要廣大教師樹立起自主的責任意識。馮友蘭將人的境界分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堅持“大情懷”與“大先生”相統一,堅持“堅守大學本真”與“合理面向社會”相統一,就是高校教師的“天地境界”,這是提升師德內化水平的必由之路,是師德實踐對師德理想的自由超越。
一是樹立“大情懷”,爭當“大先生”。境界的高度決定了師德實踐的高度,“大情懷”是“大先生”的靈魂,“大先生”是“大情懷”的載體。依據高校教師的職業特性,高校教師的“大情懷”主要體現在“家國情懷”和“育人德性”上。“家國情懷”是教師對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折射出來的理想追求,廣大教師要在黨和人民的偉大實踐中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汲取養分、豐富思想,要堅持教育“為人民服務”與“讓人民滿意”相統一。高校教師的“育人德性”,追求的是一種自由、自主和自足的德性品質。師德實踐,單憑“大情懷”還不夠,還需要有高深的學識素養和過硬的能力本領。教師只有“知識淵博”才能對學生提供足夠的“知識供給”,廣大教師要充分認識“思維要新”與“視野要廣”的關系,積極進行教學創新與行動反思,以“大學問”成就“大先生”。
二是堅守大學本真,合理面向社會。高校是人類理想的精神寄托。綜觀世界高校發展史,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高校的發展形態總是伴隨內部組織需求、外部環境需求的變化而變化。當前,高校的公共責任和服務社會的使命日益凸顯,但是,高校的基本使命依然是“知識的傳播和創造”。因此,高校教師要堅守大學的本真,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方面,妥善處理“大學公共性本質”與“知識商業性傾向”之間的關系。芝加哥大學教授愛德華·希爾斯認為,“大學的存在依賴于維持其學術資本”[12]。學術資本本應具有道德約束性,否則必然導致學術資本化和學術資本主義。高校教師應以堅守學術良知為前提,清楚地界定其在服務社會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方面,積極投身“社會大課堂”。“社會大課堂”是師德實踐的必要延伸。高校教師要充分發揮社會場域的作用,以勞動實踐、掛職交流、志愿服務、調查研究等方式開展師德實踐,在社會大課堂中提升道德境界,在學思踐悟中增強培育時代新人和助推民族復興的使命擔當,從而真正使師德規范內化于心且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