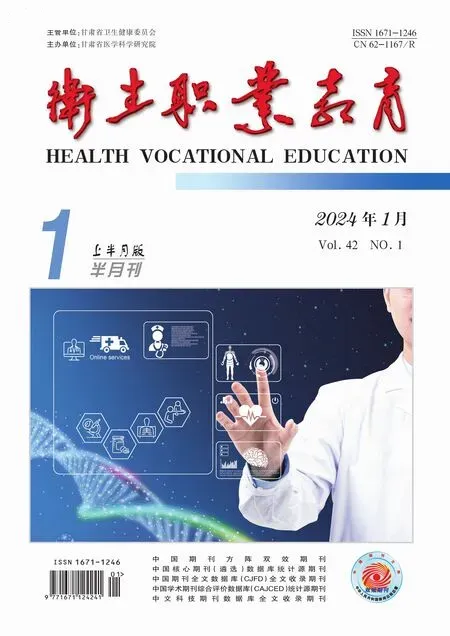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及安寧療護能力調查與對策
蘇立蕊,張朝輝,常銀橋,周榮慧,康利馨,黃志偉,孫亞楠,郝玉玲
(濱州醫學院護理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3)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 年我國死亡人口達1 041 萬人,相比上一年增長了0.19 個千分點[1]。死亡人口數量的不斷擴大意味著終末護理需求顯著增加,給護理服務行業帶來了更多挑戰。《“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進一步促進安寧療護一體化,優化護理服務。本科護生是安寧療護服務的后備力量,提升其死亡倫理認知水平及安寧療護能力至關重要。20 世紀20 年代,死亡教育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相繼展開,目前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教育體系,安寧療護也隨之迅速發展,而國內起步較晚,尚未形成適合我國的死亡教育和安寧療護能力培養體系[2-3]。本研究通過調查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及安寧療護能力狀況,分析其影響因素,為制訂切實可行的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培養方案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22 年9 月至2023 年1 月,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法,選取山東省某醫學院校在校本科護生(大二122 人、大三111 人、大四100 人)333 人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通過全國夏季高考統招錄取的護理專業學生;近一年無休學情況;知情同意且配合本次調查。排除標準:存在認知障礙或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1.2.1 觀察指標與調查工具(1)一般資料。參照相關文獻[4]結合教學經驗設計調查問卷,包括兩部分,共18 個條目。①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級、是否為獨生子女等12 個條目;②安寧療護相關特征,包括是否有照護臨終患者經歷、是否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等6 個條目。(2)死亡倫理認知。對岳帥等[5]編制的死亡倫理認知問卷進行修訂及專家審核,將原問卷的6個題目增加為9 個,涉及患者救治、死亡教育、死亡面對、安寧療護等方面。預調查顯示,該問卷Cronbach's α系數為0.826,信度良好。9 個題目中,前7 題為單選,“不同意”“不確定”“同意”分別賦值1、2、3 分;第8 題是第7 題否定答案的延續,所以不計分,但有助于分析原因;第9 題的6 個選項中,前5 項可多選,全選得3 分、選1~4 項得2 分,第6 項為否定答案得1 分。問卷總分為8~24 分,得分越高,說明死亡倫理認知水平越高。(3)安寧療護能力。采用趙敬等[6]編制的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包括有效的照護技能(6 個條目)、文化及倫理價值觀(5 個條目)、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5 個條目)3 個維度,共16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評分法,從“沒有能力”到“完全有能力”分別賦值1~5 分,總分為16~80 分,得分越高表明安寧療護能力越強。各維度平均分<3 分為能力不足,3~4 分為能力一般,>4 分為能力較強。問卷總Cronbach's α系數為0.964,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56、0.939、0.929,信度良好。
1.2.2 預試驗 選取本科護生25 人(大二10 人、大三9 人、大四6 人)進行預調查,了解其對該問卷內容、題量、可行性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之后對問卷進行完善,以保證調查質量。
1.2.3 調查方法 將問卷上傳問卷星平臺,進行無記名調查。研究者提前向調查對象解釋研究目的及意義,要求其掃描二維碼后獨立填寫問卷,調查過程中不可進行干預,耐心解答被調查者的疑問。共發放問卷339 份,回收有效問卷333 份,有效回收率為98.23%。
1.3 統計學分析
應用Excel 和SPSS 22.0 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進行t 檢驗、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描述;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了解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狀況和安寧療護能力的差異,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本科護生一般資料
2.1.1 人口學特征333 名本科護生年齡20~23 歲,平均年齡(20.75±0.78)歲;女274 人(82.28%),漢族325 人(97.60%),非獨生子女253 人(75.98%),生源地為農村的200 人(60.06%),父親文化程度為中學(或中專)的223 人(66.97%),母親文化程度為中學(或中專)的212 人(63.66%),父親職業為農民的152人(45.65%),母親職業為農民的156 人(46.85%),家庭月收入1 000~<3 000 元的115 人(34.53%),家庭常住人口為3 人的112 人(33.63%),曾擔任過學生干部的110 人(33.03%),獲得獎學金1~3 次的198 人(59.46%)。
2.1.2 安寧療護相關特征 有照護臨終患者經歷的47 人(14.11%),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的116 人(34.83%),愿意參加安寧療護服務的240 人(72.07%),愿意接受安寧療護相關培訓的259 人(77.78%),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的201人(60.36%),認為有必要設置安寧療護相關課程的284 人(85.28%)。
2.2 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情況
2.2.1 死亡倫理認知問卷得分情況 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問卷總分為(20.16±2.22)分,處于較高水平。各題目得分情況見表1。

表1 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問卷得分情況(n=333)Table 1 Score of Death Ethics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undergraduates(n=333)
關于第8 題“至親瀕臨死亡時,不愿放棄治療的原因”,選擇情感因素的16 人(80.00%),怕被說不孝的5 人(25.00%),經濟條件限制的7 人(35.00%),有法律方面顧慮的4 人(20.00%),其他原因1 人(5.00%)。對于問題“支持哪類身患絕癥并且非常痛苦的人群終止治療疾病,實施安寧療護,使其有質量地度過生命終期”,選擇老年人(≥60 歲)的255 人(76.58%),選擇嬰幼兒(0~4 歲)的119 人(35.74%),選擇少年兒童(>4~18 歲)的94 人(28.23%),選擇青年人(>18~35 歲)的95 人(28.53%),選擇中年人(>35~<60 歲)的106 人(31.83%),不支持對上述人群終止治療的50 人(15.02%)。
2.2.2 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存在差異 單因素分析顯示,不同人口學特征的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安寧療護相關特征的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不同安寧療護相關特征的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問卷得分比較(n=333)Table 2 Comparison of Death Ethic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scores among nursing under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aceful treatment and nursing(n=333)
2.3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得分情況
2.3.1 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得分情況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總分為(48.16±13.60)分,總均分為(3.01±0.85)分;有效的照護技能維度得分為(17.03±5.70)分,文化及倫理價值觀維度得分為(15.98±4.36)分,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維度得分為(15.15±4.59)分。各條目均分及安寧療護能力狀況見表3,條目均分排名前5 及后5 的條目見表4。

表3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各條目得分情況(n=333)Table 3 Scores of each item in the Questionnaire for Evaluating the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to Treat and Care in Peace(n=333)

表4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條目均分排名前5及后5 的條目(n=333)Table 4 The top 5 and bottom 5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for Evaluating the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to Treat and Care in Peace(n=333)
2.3.2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單因素分析 將一般資料全部納入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得分在性別、母親文化程度、有照護臨終患者經歷、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單因素分析(n=333)Table 5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to receive hospice care(n=333)
2.3.3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以本科生安寧療護能力測評問卷總分為因變量,以性別、年級、生源地、母親文化程度、父親職業、家庭常住人口數、有照護臨終患者經歷、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愿意接受安寧療護相關培訓、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Table 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to receive hospice care
3 討論
3.1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服務意愿情況
本科護生對從事安寧療護服務的積極性普遍較高,但是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者占比相對較低,其中大三、大四學生占比均低于大二學生。分析原因可能與大三、大四學生正處于見習、實習階段,對該職業的認同感與適應能力較低有關。也有相關研究表明[7],面對被絕癥折磨的患者,臨床護士常因擔心自身照護能力不足、不愿意在氣氛壓抑的病房工作、安寧療護相關政策與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而不愿意從事該工作。此外,對臨終患者特殊的心理問題缺乏有效溝通技巧也會影響護生對安寧療護服務的態度,從而使其缺乏從事臨終照護工作的興趣[8]。為促進安寧療護服務行業發展,不僅要培養護生安寧療護綜合能力,而且要提供法律、政策與制度保障,維護護患雙方的合法權益。
3.2 本科護生死亡倫理認知情況
3.2.1 本科護生死亡教育需求較高 研究顯示,85.29%的護生認為有必要設置安寧療護課程,說明絕大多數本科護生有死亡教育需求,與張夢琴等[9]的調查結果一致。可能是因為本科護生在護理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接觸到與死亡教育相關的知識或在見習、實習中目睹過患者病危及死亡狀態,或經歷過對患者進行搶救的過程[10],認識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醫學院校應重視學生在該方面的動機和意愿,制訂合理的人才培養計劃,最大限度滿足護生死亡教育需求。
3.2.2 本科護生對安寧療護接受程度較高 研究顯示,大部分護生表示在自身瀕臨死亡時會選擇終止治療,實施安寧療護。隨著醫療技術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人們對生命質量愈發重視。本研究發現,大多數本科護生重視生命質量,表示如果身患重病治愈無望,會選擇接受死亡,實施安寧療護,少部分護生會考慮家人和朋友的意見而有所猶豫或選擇盡可能延長生命。
3.2.3 本科護生對至親瀕臨死亡時的治療態度有差異 本研究顯示,“若至親瀕臨死亡且無法表達意愿時,愿意終止對其治療”題目得分最低。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大部分人在臨終者的死亡選擇、姑息治療等問題上存在兩難的情況[10]。珍惜生命、關愛生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人們常常對談論死亡、身后事有所顧忌,然而意外和疾病往往變化無常,面對無法表達意愿的臨終患者,選擇放棄其生命的觀點仍難以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目前,為了維護患者的生命自主權、解決臨床治療與否的倫理決策難題,國外已實施預立醫療照護計劃(ACP),且取得了顯著成效[11-13]。但是,受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病情變化的影響,我國尚未建立與該照護計劃相關的法律法規[14],國內學者也在積極探討ACP 的科學性與可行性。值得思考的是,ACP 作為理想化的治療決策目標,往往受主觀因素影響,因此要大力宣傳“優逝”觀念,使人們敢于探討生死話題,支持和尊重患者意愿,幫助患者重塑個人生命價值。
3.2.4 本科護生對于安寧療護服務對象的判斷欠準確 安寧療護是針對所有疾病晚期的患者在治療手段用盡之后提供的有助于減輕疾病負面影響的照護方案[15]。本研究發現,76.58%的護生認為安寧療護服務對象是老年人,贊成對身患絕癥的少年兒童放棄治療并實施安寧療護服務的僅占28.23%,少部分護生不支持終止治療。這提示部分護生對該知識點的掌握出現錯誤,也反映出本科護生對安寧療護服務對象的判斷不夠準確。安寧療護的服務對象涵蓋全生命周期的臨終患者及其家屬,而不是僅針對某一類人群。對此,加強醫院與學校安寧療護專兼結合的教師團隊建設,使其通過多種形式對本科護生進行正確的教育引導至關重要。
3.3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情況
3.3.1 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有待提升 研究結果顯示,本科護生有一定的安寧療護理論知識和正確的價值觀,但缺乏有效的照護技能和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安寧療護能力3 個維度得分中,>4 分者不足10%,75.38%的護生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不足,有效的照護技能維度中有5 個條目得分排名處于后5項。原因可能是,大多數醫學類院校未開設安寧療護相關課程,雖然部分護理學教材的某些章節提到了臨終關懷與護理,但是內容不夠豐富和深入[16]。安寧療護師資力量不足也是阻礙安寧療護專科發展的關鍵因素[17]。本科護生不僅缺乏相關理論知識,還由于缺乏安寧療護實踐技能培訓以及在臨床中與患者、其他醫護人員接觸的機會,導致安寧療護能力處于較低水平。
3.3.2 重視相關因素對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性別、生源地、母親文化程度、家庭常住人口數、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是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的主要影響因素(P<0.05)。分析原因可能為以下幾方面:(1)男生安寧療護能力較女生強,可能是因為男生在身體素質、適應新事物等方面優于女生,能更好地應對高強度的護理工作[18]。(2)城市學生安寧療護能力優于農村和鄉鎮學生,原因可能為城市的安寧療護相關教育資源比較豐富、師資力量相對雄厚,學生綜合素質比較高。(3)母親文化程度越高,護生安寧療護能力越強,究其原因可能為母親文化程度會影響其教育方式,文化程度越高,采取的教育方式越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本科護生的安寧療護能力。(4)家庭常住人口越多,護生安寧療護能力越強。家庭成員多的護生,可能更懂得人文關懷,溝通能力更強,能夠更好地與患者相處,尊重、理解患者。(5)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的護生安寧療護能力較強,原因為接受過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的護生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能夠正確認識死亡,在面對死亡時能保持冷靜,并理性地安慰死者家屬,這也提示安寧療護及死亡教育對護生安寧療護綜合能力的重要性。(6)愿意成為安寧療護專科護士的護生安寧療護能力較強,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這部分護生會更加主動地學習相關知識,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愿意主動提升自身安寧療護能力。
4 對策
4.1 加強護生死亡倫理教育
作為未來臨床護理和健康維護的主力軍,本科護生的死亡觀對其職業發展和身心健康均有重要作用[17]。在護理專業設置死亡教育課程,能夠有效改善護理專業學生的死亡態度[19]。目前,我國死亡教育仍處于起步階段,醫學院校死亡教育課程的實踐內容極少,尚未形成系統、完善的課程體系[20]。應根據學生特點和我國國情完善死亡教育體系,形成以人才培養目標為根本,以教師和輔導員為引領,課程教學與第二課堂教育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圍繞生命教育、死亡倫理、職業信念等開展多元化教育。同時,根據不同年級醫學生的心理變化以及成長軌跡,創建具有各自特點的死亡教育模塊[21],與安寧療護課程教學協同進行。如針對低年級學生,可不定期開展生命教育專題講座及社會實踐活動,通過海報、校園廣播、宣傳欄等普及死亡教育知識,專業課學習及實習階段可通過模擬臨終情景演練,在帶教教師引領下與臨終患者及其家屬交流等,從而培養學生死亡倫理道德情感,降低學生死亡應激敏感性,使其積極地面對生命,樹立堅定的人生信念。
4.2 重視護生安寧療護能力培養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惡性腫瘤、慢性病發病率與病死率也在逐年上升,安寧療護的服務人群已從晚期癌癥患者逐漸擴展到臨終老年患者、急危重癥終末期患者及其家屬,需求量不斷增加[22-23]。護士作為安寧療護的主力軍,其照護能力水平將直接影響安寧療護實施效果。本研究顯示,本科護生安寧療護能力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有效的照護技能較薄弱,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文化及倫理價值觀水平都有待提高。因此,提高護生安寧療護能力尤為重要。
4.2.1 制定相關政策,完善安寧療護教育體系 目前,我國的安寧療護教育還處于探索階段,沒有形成完善的安寧療護教育體系,開設安寧療護課程的醫學院校不多,沒有統一的教材,師資力量不足[17,24-25]。因此,教育行政部門應做好安寧療護人才培養規劃,制定統一的教育指南,在安寧療護教育專家引領下編寫高水平教材,供院校使用,重視護生安寧療護教育,提高其安寧療護能力,推動安寧療護事業發展。
4.2.2 優化培養模式,使安寧療護教育系統化、全程化 護理學院可將安寧療護能力培養納入人才培養方案,開設安寧療護課程,編寫課程教學大綱,使其與其他專業課內容相輔相成。(1)課程內容[26-27]應適應我國傳統文化特點,主要包括:安寧療護概述、法律及倫理、人文關懷與溝通交流、癥狀管理與舒適照護、心理護理、生死教育、社會支持、居喪期護理、自我照護和專業發展等相關知識與技能,知識體系涵蓋臨床醫學、護理學、心理學、社會學、人文與哲學等多方面。有研究認為[24],安寧療護理論課應不少于30 學時,實踐課為8~16 學時。(2)學習方式多樣化。建議根據不同年級采取全程分階段教育模式,可采取理論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由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大一、大二可采取課堂講授、主題班會、典型案例分析、小組討論、辯論賽等形式開展尊重生命教育,學習安寧療護基礎知識;大三可結合專業課學習進行安寧療護專業知識與技能學習,通過醫院見習、情景模擬、角色扮演、虛擬仿真訓練等形式進行;大四可通過臨床實習階段在臨終患者的護理實踐中學習,利用專家講座、臨床病例討論等提高安寧療護水平,可酌情安排1~2 周安寧療護實習。(3)課程評價方式可采取多種形式,如情景模擬、實踐考核、常規理論考試等[17],通過考核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發現教學中的不足,不斷優化教學過程,以保證學習效果。
4.3 建設專兼結合的師資隊伍
打造高素質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是保障教學質量的根本。我國目前關于死亡教育的專業人員較少,學校層面應充分整合教師資源,形成由輔導員、專任教師、倫理學專家、心理學專家等組成的死亡教育師資團隊,對其進行系統培訓,提高其教學水平。聘請臨床教師,開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實踐教學,形成醫教協同的教育模式[28]。由于我國安寧療護起步晚,發展緩慢,絕大部分學校教師未參加過系統的培訓,臨床護士中同時具備安寧療護理論知識與臨床經驗的師資也十分稀少,缺乏安寧療護優質的教師資源[17]。建議學校與教學醫院協同,選拔整體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專任教師和臨床兼職教師接受安寧療護專科培訓,實施專任教師定期參加臨床實踐和兼職教師定期進行教學能力培訓制度,建立專兼結合的優秀教師團隊,采取院校共建培養模式[29],從理論到實踐逐步培養和提升學生安寧療護專科知識和技能水平,提升其專業認同感與從業能力,為將來從事臨床護理和安寧療護工作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