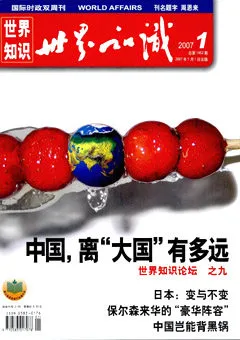中美關系“新常態”正在生成
達巍(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后,兩國關系呈現出某種進入“新常態”的跡象。這種“新常態”并非積極合作互為伙伴的“常態”,而是一種在長期博弈中爭取和平共處的穩定狀態,也是雙邊關系長期處于比較困難的條件下的穩定狀態。再進一步講,中美關系經過自2017年以來類似于“自由落體”的惡化過程,現在觸底企穩了,雙方對彼此關系的認知形成了一些共性。
兩國現在能夠平心靜氣地接受一個現實,即中美結構性矛盾難以調和,博弈是長期性的,回不到從前那種合作為主的狀態了。雖然兩國仍不能達成對彼此關系的共同定義,中方也不可能接受美國對兩國關系的“戰略競爭”定義,但對于這一關系已經構成積極面小于消極面、競爭面大于合作面的現實,雙方各界從上到下基本都是這樣的認知。盡管這種認知有其消極性,但如果雙方認知比較接近,就相對好管理一些。如果一方認為關系還可恢復,另一方認為已經不可能了,這種認知落差反而才是更危險的。
中美雙方逐漸確信對方并不希望彼此關系徹底破局,不管是全面脫鉤還是陷入美蘇式的冷戰,抑或軍事沖突,對雙方而言都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盡管這樣的認知在兩國國內均存在反對意見,但正在成為相對主流的觀點。一年前的巴厘島會晤從最高層面發出穩定中美關系的明確信號,此后經過“氣球事件”等挫折,兩國領導人在舊金山會晤上再次發出了穩定中美關系的信號。這種企穩信號經過挫折得到重新確認,其分量比一年前還要重,反映了兩國高層的真實意愿,也更有可信度。
中美雙方都逐漸意識到各自力量是有限的,對方力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推動兩國博弈完全按照自己的戰略規劃發展演變。我們不希望美國的盟友過度向美國戰略靠攏,不希望它們加入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禁運,但是這些情況還是發生了。美國政府一度想引誘甚至逼迫本國企業離開中國市場,但很多美企有自己的觀察和考量,高管紛紛來華考察,回去以后有的制訂了新的投資計劃,有的維持在華業務繼續觀望,美國政府的很多想法其實是落不了地的。
經過幾年博弈,兩國都看到了自己和對方的韌性與短板之所在,各自對開展長期博弈有了更多把握。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焦慮感一直存在,但與此同時發現自己在科創、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領先優勢似乎還在擴大。中國經濟雖然面臨一些困難,但今后若干年很有可能保持中速增長,將來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仍是大概率事件。

2023年7月7日,美國財長耶倫訪華期間,與在華美國企業代表舉行座談。耶倫表示,美國不尋求與中國脫鉤,而是尋求“多樣化”。
如果以上共性是立得住的,中美兩國主流認知都逐漸接受這樣的判斷,中美關系進入“新常態”就是可能的。這次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重要成果還在于,雙方建立或重啟了關鍵領域高層和工作層對話、溝通機制。中美現在已建有八個聯合工作組,未來也許還會有更多的聯合工作組,這就為“新常態”提供了某種機制保障。舊金山會晤在經貿、兩軍交往、禁毒、民航、人工智能、人文、氣候等領域宣布了一些具體成果,未來還會有更多具體成果出臺,以維持中美關系的企穩勢頭。
當然,中美關系的不確定因素仍有很多,2024年仍是充滿挑戰的。個人認為最大的風險在于:第一,中美在南海、臺海短期內仍存在局勢升級和發生意外的危險。第二,美國大選的過程和結果給世界以及中美關系帶來的不確定性。目前看,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無人能敵,卷土重來再掌白宮是有可能的。無論誰在這次選舉中獲勝,對陣另一方都難以接受。如果特朗普重新上臺,美國甚至可能經歷一場憲政危機,共和黨建制派、聯邦和地方州公務員隊伍、聯邦政府內的獨立機構會不同程度地遭到清洗。特朗普及其側近已開始做這方面的籌劃。歐洲盟友也非常擔心,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將會推行更為極端的“美國優先”、孤立主義政策。如果把下一次“特朗普沖擊波”比作一場爆炸,首先沖擊的是美國國內政治,第二波將沖擊美國的盟友關系,歐洲首當其沖,第三波則會沖擊中美關系。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目前初步呈現的“新常態”有可能歸零,一切從頭再議,好不容易恢復的穩定會再度被打破。
中美兩個全球大國之間的博弈將是長期性的。如果博弈雙方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那就意味著不會有一方速勝,也不會有一方速敗。對我方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畢竟,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國博弈,歸根結底“勝在國內”。誠如習近平主席2023年11月15日晚在舊金山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辦的歡迎宴會時指出的,“和平共處是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更是中美兩個大國必須守住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