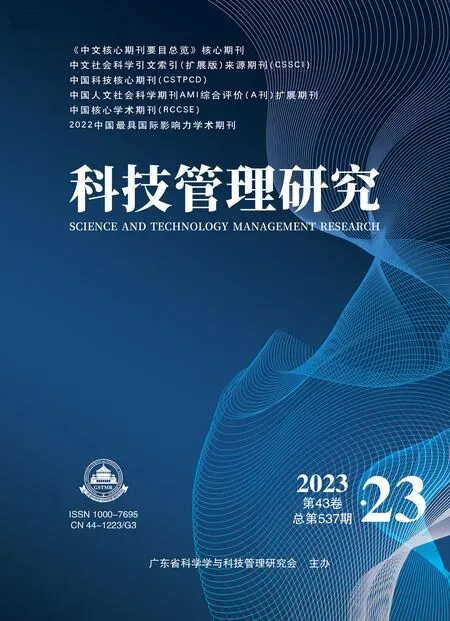典型國家創新能力評價體系指標分析
陳秋陽,陳云偉
(1.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科學計量與科技評價研究中心,四川成都 610041;2.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系,北京 100190)
1 研究背景
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創新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全球科技呈現出突破性快速發展態勢,國際科技創新環境與競爭格局加速調整[1]。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里,世界科技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系統化突破性發展態勢,世界已經進入以創新為主題和主導的發展新時代,《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指出全球科技創新效率在2020 年顯著高于過去10 年的平均值[2]。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科技創新步伐,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科技競爭[1]。縱觀世界科技強國及創新型國家,紛紛加強對科技創新的戰略規劃,以求引領新一輪科技創新[3]。與此同時,我國科技整體實力也邁向系統性提升新階段,我國在2016 年便提出在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并在2017 年將躋身世界創新型國家時間節點提前到2035 年[4]。
對全球主要經濟體而言,向創新驅動發展轉型或強化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是其共同的戰略取向。在創新驅動發展的具體戰略實踐過程中,如何評判一個國家努力的成效,需要借助具體的衡量指標進行評價[5]。其中,國家科技創新效果評價指標包括定性和定量兩大類指標,尤其是定量指標在科技評價實踐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限定應用邊界的前提下,這些量化的指標可以從特定角度反映科研水平或影響力,成為定性評價的有力數據支撐[6]。近年來,世界各經濟體、科研機構等開始重點關注創新型國家的評價體系搭建。在國內影響力較大的創新指標體系有中國科學院創新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中國創新發展報告、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科技部發布的中國科學技術指標以及全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研究中心發布的二十國集團(G20)國家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和世界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等。而國際上目前比較主流的國家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多引用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歐盟的創新聯盟記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以及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科學技術與工業記分牌。目前,國內外對于國家創新能力指標體系的研究熱度不減,但多是將不同指標體系分別展開進行縱向研究,如桂黃寶[7]對全球創新指數進行了縱向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有利于創新的政策框架、加強協作以及注重創新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徐婕等[8]則從縱向介紹了GII 的評價體系、評價方法與數據來源,并針對該指標體系中我國的表現提出相應政策建議;方陵生等[9]則從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出發,詳細介紹了該指標體系的構建要素,并在該報告的基礎上探究全球創新的發展趨勢。但是其針對國家創新指標體系共性將不同維度指標進行歸類的橫向比較研究還有所欠缺;張志強等[3]通過梳理現存典型科技強國科技指標體系,橫向對比世界科技強國的科技實力,揭示我國在主要科技指標上的表現與差距;李雨晨等[10]通過橫向對比典型科技創新基礎指標,系統地解釋了規模性指標與相對性指標對科技創新能力評價產生的差異性影響,并指出指標類型的不同會對一國科技創新能力水平的評估存在較大影響。
基于此,本研究在對國內外主流的國家創新能力指標體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比較不同創新指標體系的異同,并根據科研產出能力、技術創新能力以及科研影響力三維測度將共識性較高的科技創新相關評價指標進行歸類,構建能真實揭示且反映科技創新實力的國家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以便更好理解國家科技創新能力評價原理,準確觀察我國科技創新水平及國際地位,對加快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
目前關于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以下簡稱“國家創新評價體系”)的相關研究主要分為3個類別,分別是國家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以下簡稱“創新能力體系”)、國家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以下簡稱“競爭力體系”)與國家科學技術活動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下簡稱“科技活動體系”)。其中,國家創新評價體系旨在將創新活動作為一個整體,對國家的創新能力進行評價,分析相對優勢和劣勢并幫助確定各國需要加強的領域,該評價指標體系以全球創新指數(GII)、歐洲創新聯盟記分牌(EIS)為主要代表;競爭力體系主要以波特競爭優勢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技術內生化經濟增長論等經濟學理論作為理論依據[11],其中以世界競爭力年鑒(WCY)、全球競爭力報告(GCI)最為典型,其主要作用是對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綜合競爭力進行排名和評價;科技活動體系則更關注科學、技術活動等對創新發展的貢獻力,以OECD 科學、技術與產業記分牌為主要代表,旨在全面系統地反映各國家在科學、技術、創新及工業領域的發展狀況。
2.1 典型國家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2.1.1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的指標體系構建
GII 每年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聯合發布,旨在通過超越傳統的創新評估方法,測度經濟體或國家的創新能力,從而更好地描述社會創新活動[7]。自2007 年首次發布以來,為全球范圍內的政府決策者、企業高管以及在創新方面有所創見的人員所使用,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創新力評價指標[12]。作為衡量各國創新的風向標,我國也高度重視GII 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國家知識產權局、WIPO 中國辦事處均對我國在GII 中所體現的成績展示出了高度的關注[13-14]。GII 由創新投入和產出指數兩部分組成,2020 年發布的《Global Innovation Index2020》主要分為體制、人力資本和研究、基礎設施、市場成熟度、商業成熟度、知識和技術產出和創造性產出7 大板塊,其中前5 個一級指標被歸納為創新投入指數,后2 個一級指標被歸納為創新產出指數。每個一級指標均由3 個二級指標構成,共有21 個二級指標和81 個三級指標[2]。上級指標由下級指標的算術平均得出,最后7個一級指標加總即為全球創新指數的總得分。
2.1.2 歐洲創新聯盟記分牌指標體系
歐盟自2001 年起正式發布歐洲創新聯盟記分牌(EIS),該報告以美國和日本作為參照對象,通過創新指標體系對歐盟成員國家的創新績效進行定量比較。2020 年的《歐洲創新聯盟記分牌》中,已經將比較對象增加為中國、俄羅斯、加拿大、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和美國[7]。為了客觀反映實際情況中國家創新的現狀,有利于進行國際創新能力的比較,EIS 使用歐盟創新調查、成員國或國際其他組織的統計資料作為評價數據[15]。EIS最大的特點是動態調整評價指標,2001 年EIS 指標體系包含4 個維度,分別是人力資源、知識創造、新知識傳播與應用以及創新金融、創新產出與創新市場,一級指標下另包含18 個二級指標;2008 年,歐盟對指標體系做出調整,增設了三級指標,并將一級指標調整為創新驅動、企業創新行為、創新產出3 個維度,具體指標個數由2007 年的25 個增加為30 個[16]。在2021 年發布《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2021》中,一級指標從簡單的“投入-產出”維度逐漸完善成“科技基礎條件—科技創新投資—科技創新活動—科技影響分析”的閉環,并有12 個二級創新維度,總共包含32 個指標。每個一級維度包括數目相等的指標,在綜合評價指標中所占的權重相等[17]。
2.1.3 歐盟創新指數報告指標體系
歐盟創新指數報告(Global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GSII)是歐盟自2006 年起提出的針對全球創新型國家的創新績效進行定量評估的報告。在GSII中,歐盟設定了創新驅動、知識生產、創新擴散、創新應用以及知識產權5 個主要維度[18]。其中,創新驅動主要關注高等教育與研究人員人口占比、知識生產主要測度政府與企業的研發投入、創新擴散關注ICT 消費占比、創新應用聚焦高技術活動與產品的產出情況、知識產權則重點關注專利數量。除此之外,GSII 對各國的創新績效進行集群分層,將所有具有相似績效屬性的國家進行組別劃分[19]。
2.1.4 創新聯盟記分牌指標體系
創新聯盟記分牌(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IUS)是基于歐洲創新記分牌提出的用于分析歐盟27 個成員國創新績效,以及研究創新體系相對優劣勢比較的評價指標,其評價維度的選取側重于相對指標,并未涉及反映規模和總量的指標[20]。2009年,EIS 中的29 項指標經過刪改整合后保留18 項至IUS,加之新出臺的7 項指標形成了IUS2010。IUS2010 從創新驅動、創新行為、創新產出3 個維度設置一級指標,整個評價體系包含8 個二級評價維度和25 個指標[16]。
2.1.5 國家創新指數報告指標體系
國家創新指數報告是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于2011 年起用于監測評價國家層面創新發展水平而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21]。該報告選取40 個科技創新活動活躍的國家作為評價對象,充分借鑒了國內外關于國家創新與競爭力評價的理論與方法,建立了以創新資源、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創新績效、創新環境為一級維度的國家創新評價體系。《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0》由30 個指標組成,其中有20個突出創新規模、質量、效率和國際競爭能力的定量指標,10 個反映創新環境的定性指標[22]。
2.2 典型國家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2.2.1 全球競爭力指數指標體系
世界經濟論壇自1979 年以來每年發布一份衡量全球140 個世界主要經濟體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該報告基于全球競爭力指數(GCI)進行競爭力排名[23]。基于40 年的競爭力基準經驗構建,GCI 已經逐漸演變為新型的綜合指標,其中包含12 大支柱(包含基本需求、效率提升和科技準備度3 個一級指標)與98 項基本指標[12],12 個大支柱為法律和行政架構、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整備度、宏觀經濟環境、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體系、市場規模、商業成熟度和創新能力。在科技準備度的層級指標中,指標權重占比總指數最高,高于其他具體指數重要性的2~4 倍。除此之外,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整備度等維度中也包含對經濟體科技競爭力的測度。可見,GCI 在40 年的演變中,已逐漸由對國家整體競爭力進行評價的方法演變成以科技競爭力為主導的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15]。
2.2.2 世界競爭力年鑒指標體系
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自1989 年起每年發布世界競爭力年鑒(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WCY),該報告是全球范圍內影響力最廣的國家競爭力評價報告之一[15],通過科學地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對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綜合競爭力進行排名和評價[24]。該報告認為國家競爭力是國家創造、維護并保持企業競爭力環境的能力,這種核心思想促使其將指標體系的一級指標分為經濟運行、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4 個維度,包含20 個二級評價指標[24]。其中對于科技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維度的技術和科學2 項,與科技相關的三級指標占總指標的17.6%[25],可見WCY 并不是非常重視科技評價。
2.2.3 ITIF 創新競爭力指標體系
美國科技創新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聯合歐美商業理事會(現并為大西洋商業理事會),截至目前,已發布了2009、2011 年兩版《跨大西洋地方競爭力指數》(The Atlantic Century: Benchmarking EU&U.S.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其指標體系由6 個一級指標,16個二級指標構成。ITIF 跨大西洋地方競爭力指數的數據來源于OECD,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使用原始分數逐一計算各個國家的各項指標,并根據各項指標的重要性設計其權重比例[26]。
2.3 典型國家科學技術活動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3.1 OECD 科學、技術與產業記分牌指標體系
OECD 自1997 年起,每2 年發布1 份科學技術和工業記分牌(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STI)報告,通過記分牌的形式對OECD 成員國形成動態的檢測系統,提供了對成員國科學技術和產業活動績效比較分析的框架[18]。STI 的發布揭示了數字轉型對科學、創新、經濟以及人們工作與生活方式產生的影響,旨在幫助政府在瞬息萬變的數字時代制定科學、創新和產業政策,通常用于監測科學、技術、創新及工業領域發展狀況的指標[27]。OECD科學技術指標選取以高質量的統計數據和穩健的分析原則為基礎,而且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指標,并具有隨時間推移進行改進的前景。其指標體系主要包括R&D 和創新、人才和技能、專利、信息與通信技術、知識流動和全球企業、知識在生產活動中的影響6 部分,共76 個指標,全面系統地反映了科學、技術、全球化和工業等領域的績效,并由OECD 科學技術和產業司開發的數據庫進行支撐。
2.3.2 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體系
美國的科學與工程指標(science &engineering indicators,SEI)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于1972 年起每2 年發布1 次。旨在通過分析全球主要國家的科學工程發展現狀,為美國政府制定國家政策提供依據[28]。該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科學與工程高等教育、科學技術研發活動、技術產業革新、K-12 教育、科學工程勞動力、公眾對于科學技術的態度以及學術研發7 個部分[28]。其中與教育相關的指標有2 個,其余指標與科技、學術研發以及產業界和全球市場的互動關系等情況相關。
2.3.3 日本科學技術指標體系
1991 年起,日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每年發布1 份科學技術指標(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JSTI)報告,將日本與全球主要國家的科技活動進行對比,以此反映日本科學技術發展整體情況[29]。科學技術指標主要由研發支出、研發人員、高等教育、R&D 產出以及科技創新5 大支柱構成,共計170 個指標[29]。2021 年8 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發布了《科學技術指標2021》,該報告繼續沿用原指標體系,也在此基礎上新增了選定國家的每個行業在總增加值中的份額、向特定國家提出的商標申請和來自特定國家的商標申請的狀況、研究機構的科學傳播和人們對信息的認識和對網絡新聞的信心等新指標[30]。
2.3.4 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體系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于2018 年起發布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該指標主要包含科技人力資源、科學與工程的高等教育、中小學數學與科學教育背景、R&D 發展的經費投入、科研產出和影響力、國家科技基礎條件資源、高技術產業與貿易發展以及公民科學素質及對科學技術的態度這8 個維度,25 個一級指標以及203 個基本指標[31]。該指標體系的構建遵循科學與系統性的原則,并充分考慮指標的可比性與有效性,指標基礎數據均來自于OECD、世界銀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世界公開統計數據[12]。報告旨在通過對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的科技發展資源、能力以及發展趨勢進行對比從而系統地分析我國科學技術現狀 。
3 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的科技創新指標分析
基于對現有世界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指標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多聚焦于國家整體創新能力的評價,單一衡量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指標為少。而科技創新能力作為創新系統理論研究的延續和深入,已成為國際比較科技政策制定與導向的基本依據,全面地測度和評估科技創新能力對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1,10-11]。為進一步探究現存國家創新評價體系對于世界各國科技創新水平的評價效果,將上述報告中指標根據科研產出能力、技術創新能力以及科研影響力3 個維度進行分類,其中科研產出能力代表該國家的研究人員、研發投入等科研條件是否具備論文、專利、科學獎項等科研成果的產出能力,并對其科研成果的產出數量和質量加以衡量;技術創新能力旨在衡量該國家以創造新技術為目的或以科學技術知識及其創造的資源為基礎的創新能力;科研影響力旨在反映該國家所產出的科研成果對于學術界乃至學術界之外所產生的、可被證明的益處。構建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關于3 個維度的科技創新指標分布如表1 所示。

表1 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科技創新指標分布
從表1 可知,國家創新能力評價類指標與國家科學技術活動發展評價類指標體系較好地兼顧了上述3 項科技創新評價,科研產出、技術創新與科研影響力類指標均在該類評價體系中有所體現,尤其是對于科技創新針對性更強的科學技術活動評價類指標體系,如OECD 主要科學、技術產業記分牌包含66項科研產出能力指標、日本科學技術指標(JSTI)則包含14 項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而國家競爭力評價類指標體系則對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關注較少,如全球競爭力指數(GCI)沒有涉及技術創新能力與科學影響力的相關指標、跨大西洋地方競爭力指數也僅對國家的科研產出能力做出了評價。
3.1 科研產出能力相關指標
科研產出能力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是否具備良好的科研成果產出的數量、穩定增長等能力,且能產出高質量的論文、專利、標準等科研成果。歸納國家創新評價體系中的科研產出能力相關指標及來源如表2 所示,可以發現目前對于科研產出能力的評價主要集中在科研人員、研發支出、高校水平、研發強度以及高技術產業發展規模等維度。

表2 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科研產出能力相關指標
科研人員數量的評價方式多以基礎計數的方法為主,但也有一些指標體系對原有評價方法進行了改進,如WCY 和OECD 采用某類人群中研發人員總數或占比來比較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科研人員數量之差,如企業人均研發人員總數和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總數等。除此之外,OECD 將科研人員的年復合增長率作為衡量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科研人員數量變化的一種計算方式,相比基礎計數,年復合增長率更能表現該國家當年的科研人員數量增長趨勢。
對于研發支出,不少報告對其進行了細分,從公共部門、企業等角度分別對研發支出進行了統計,如公共R&D 經費占GDP 的百分比、政府資助的GERD 占GDP 的百分比等。除此之外,OECD 主要科學、技術產業記分牌還從各部門完成研究經費占比的角度進行考量,如高等教育部門完成GERD 的百分比、政府部門完成GERD 的百分比等。
3.2 技術創新能力相關指標
國家或世界經濟體的技術創新能力旨在衡量其以科學技術創新為目的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產業創新的能力,并對其創新產出效果進行評價。表3 歸納了世界典型性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表達技術創新能力的相關指標,科研論文、專利、企業創新產出、創新型產業以及世界知名獎項等是現有的主要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專利作為知識產權的核心要素,因涵蓋科技信息的90%~95%而被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表現形式[32],加之專利數據自身具備地域性、時間性與可獲取性等屬性,使得專利成為集聚科技創新成果的智庫[33],被廣泛運用于測度不同主體的技術創新能力。在已有評價指標體系中,專利的評價表現形式常以計算各類專利申請數量為主,如PCT 專利申請數、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三方專利數量等。除此之外,一些評價指標會從人均占比、世界占比等不同計數角度對世界各經濟體的專利量進行橫向比較,如百萬人口發明專利申請數、人均專利申請量、主要國家按技術部門劃分的專利組數量百分比變化等。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評價體系將性別、學科領域納入專利統計甄別范疇,OECD 分別統計了信息通信領域與生物技術部門的專利數量,美國科學工程指標SEI 統計了至少有1 名女性被列為發明人的專利申請數量,該評價體系將性別納入技術創新考核從而創新性地凸顯被評價個體的技術創新平等性。
國家創新系統是由多種主體構成的,包括企業、政府、科研部門、大學和中介機構等不同層次的參與者。其中,企業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們既是生產和創新的中心,也是整個創新系統的核心[34]。企業創新產出又分為產品創新、合作創新以及工藝創新等。在已有創新評價體系中對于企業創新產出的評價不在少數,EIS 對于是否有產品創新以及商業創新流程的中小企業數量進行了統計、JSTI 則比較了企業和市場創新產品的銷售總額、IUS考量了企業創新產出(工藝或產品創新、營銷或組織創新)比例。
自18 世紀國際科學獎項的設立以來,都是為了表彰在科技進步活動中為世界帶來超越性突破的公民和組織[35]。這些獎項代表了國際相關領域科學共同體對獲獎者在學術成就和貢獻方面的肯定與贊揚。其有助于推進科學項目和技術研究的發展,為那些在科學界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公正公開的方式,讓其努力和創新能得到全球認可[36]。世界知名科學獎項有諾貝爾獎、波爾國際獎、圖靈獎、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等,國際科學獎項是衡量世界各國在特定學科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指標。但縱觀世界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僅有WCY 和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將其考慮在內:WCY 對國家諾貝爾獎獲得數量和人均諾貝爾獎獲得者進行了統計;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則對世界各國獲得國際科技獎項的能力進行了綜合比較分析。
對于論文產出,不少報告對特定領域、期刊的論文數量進行統計,如Science &Engineering 科技出版物文章、科技論文的總量及變化趨勢、主要國家各領域論文數量的百分比變化等。除了基礎計數外,論文數量的份額占比、百分比變化以及學科/機構分布等創新評價方法也層出不窮,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主要國家的論文數量、前10%論文、前1%論文的占比及變化、國內科技論文的學科/機構分布等。
3.3 科研影響力相關指標
科研影響力旨在表示該國家科研的科學影響、社會經濟影響、文化影響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引文指標、創新產出貿易出口情況、大學/產業合作、合作出版物以及國家之間合作情況是當前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科研影響力的主要測度方向(如表4 所示)。

表4 典型國家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科研影響力相關指標
引文指標旨在由針對某期刊或領域歸一化后計算的可用于跨學科衡量引文影響的一個度量。引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客觀反映出期刊、學者、機構乃至國家在該學科領域的科學影響力。對于引文的評價方式也有很多種,GII 運用可引用論文的h 指數進行評價,國家創新指數報告與IUS 將國家之間被引率較高的期刊占比進行比較,JSTI 除了考慮出版物外還將專利的引用納入其中。
創新產出的貿易出口直接反映了國家科研影響力對于社會經濟及生活的影響。從表4 可以發現,現存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也將這一點作為重要的國家創新考量指標。評價方式主要衡量高科技/ICT服務出口占貿易總額/制造業出口比重、高技術服務業國際貿易的國別分析以及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力、結構規模分析。
國際科研合作能更好地推動國家之間的科技創新,并從本質上反映該國的科研能力強弱。目前的國際科研合作主要集中評價國際科學聯合出版物數量、某領域出版物的國際合作數量以及探索國家出版物之間合著形式變化規律。
4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經過橫、縱向對比分析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總結歸納現存評價體系中有關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標的以下特點:
(1)缺少針對國家科技創新評價的完整指標體系。縱觀國內外典型國家創新評價體系可以發現主要分為國家創新能力評價、國家競爭力評價以及國家科學技術活動發展評價。其中國家科學技術活動發展指標體系上述評價體系重點關注全球主要國家的科學工程發展現狀,對于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關注度不夠。現存指標缺乏對于科技活動及創新產出的客觀評價以及關鍵領域科技創新的分析和研判。
(2)指標評價方式較單一,忽視指標數據的多樣表達。現有國家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更多地基于固有指標評價方式,如對文獻、專利、科研人員數量等進行單純的計數評價。忽視了不同國家之間由于體量差異而可能造成的個體總量差異,這些都是單純計數統計無法發現的問題。為了改進這一問題應重視指標數據的多樣表達,以日本科學技術指標(JSTI)為例,該指標體系同一大類下又分為描述型、分析型與評價型指標,且對于每一大類的分析角度并不局限于單純的統計計數,而是利用百分占比、數量變化趨勢等多元化統計方式進行表達,能有效規避由于國家體量差異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3)評價指標較為固化,指標創新性有限。通過分析幾個主要國家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發現現存對于科技創新評價的指標新穎性較低。以針對國際知名科學獎項以及專利的評價指標為例,現存對于國際知名科學獎項的評價指標僅在世界競爭力年鑒(WCY)與中國科學技術與工程指標中有所體現,且獎項僅聚焦于諾貝爾獎,沒有將更多的世界知名科技獎項納入考量范圍。對于專利的評價也僅止步于三方專利,對于現有的四方、五方專利并未在已有指標中有所體現。
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認清我國科技能力所處的世界地位,必然需要強化對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評估,在建立創新能力評價體系的基礎上重點聚焦國際科技活動與創新產出及關鍵領域科技創新的分析研判。與此同時,多元化指標的數據表達方式,指標分析的角度不應僅局限于單一的數理統計,而是采用歸一化、變化趨勢等數據表達方式。最后,在選擇科技創新能力指標時,應突破當前世界科技發展普遍聚焦的關鍵技術領域傳統簡單的專利、論文導向的分析模式,轉而重點關注具體技術領域的成果表現形式,從而真實有效的評價國家科技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