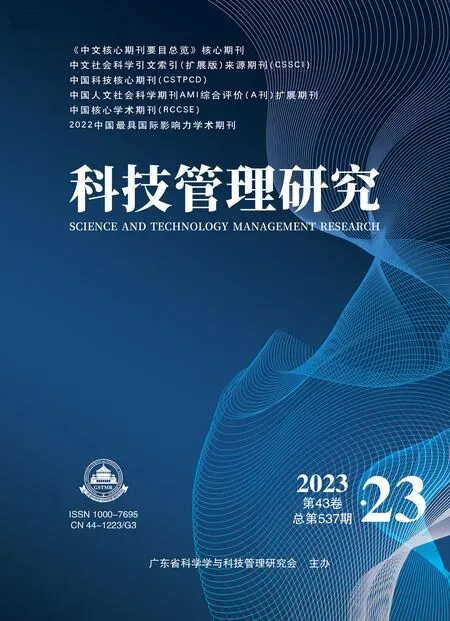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研究進展
鄭玉萍,喬 琴,張恩祥,李金花,韓永偉
(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所,北京 100012;2.蘭州大學生態學院,甘肅蘭州 730199)
1 研究背景
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由人類活動導致的大氣污染、溫室效應、土地退化、生態結構破壞等問題對各國造成的生態威脅日趨突出[1],開展城市這一人地矛盾集中爆發地的生態規劃逐漸成為人們共識。現代城市生態規劃相關方法與技術的提出與實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 年霍華德(Edward Howard)的田園城市理論,以生態化的空間布局模式緩解城市無限擴張的規劃設計體現了早期的城市生態思想[2]。此后,城市生態規劃的技術方法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經驗,城市生態規劃作為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城市范式得到廣泛的認可[3]。1957 年,中國學者吳人韋[4]、趙景柱[5]開始對城市綠地系統、景觀空間開展研究,國內城市生態規劃及其技術方法研究初具雛形。較為系統的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研究起步于20 世紀80年代,城市生態學者馬世駿等[6]、歐陽志云、黃光宇等[9]為解決城市生態問題提出了相關判斷標準、制定原則、管理與規劃方法,為國家城市生態規劃的起步打下堅實基礎。城市生態規劃的技術與方法研究實質是運用生態學原理調控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相關關系,以構建社會、經濟、自然、文化各維度協調發展的城市生態系統及人類聚居環境。城市生態規劃的內涵是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審視城市[10],以生態優先原則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能實現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戰略。
進入到21世紀,可持續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11],在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實踐中進一步審視城市化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成為時代要求[12]。如今,我國城市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日趨增大,開展城市生態規劃研究對于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當前的生態城市規劃技術指南中,生態系統功能的提升成為追求共識。在大量以可量化為目的的生態化改造投入下,具有展演性、指標性及趨利性景觀在很大程度上占據了現有的城市生態空間,過分強調的數量達標和經驗主義成為主流規劃模式[13]。同時,對于生態規劃方法論層面的探究偏弱,不利于城市生態規劃科學性的提升。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對現有的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研究進行梳理評述,總結當前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架構,以期為可持續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研究和實踐應用提供參考。
2 城市生態規劃的原理依據
2.1 自然生態學原理
城市作為一個與自然生境交互耦合的有機體[14],具有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似的復合特征,以自然生態學原理為基本指南進行技術與方法構建,是城市生態規劃涵蓋生態學科學內涵的集中體現。因此,自然生態系統的基本原理常以其指導性作為城市生態規劃的遵循總則,從具有規律性的科學原理上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城市生態規劃的前、中、后期都具有重要意義。總體而言,自然生態學原理應用于城市生態規劃中,通常指基于生態系統演替的傳統觀點上[15],評估生態系統的能力,以進行城市生態規劃。本文通過文獻分析表明,普遍使用的城市生態規劃中的自然生態學原理有3 個方面:(1)生態位理論;(2)生態平衡與協調原理;(3)經典景觀生態學理論。
2.1.1 生態位理論
“生態位”指生物在棲息地所占據的單元[16]。而城市各要素的生態位則指城市各要素在環境空間中的位置,及其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地位和作用[17]。城市的發展是一個對生態系統生態位進行選擇、競爭與占有的過程[18],該過程不僅改變了原有的自然地理環境,同時導致城市結構和空間發生變化。現有的城市生態規劃中,生態位理論常用于指導土地利用評價,為城市生態規劃建立適宜性評估框架[19]。歐陽志云等[20]最早將城市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構成需求生態位,而待評價單元的資源供給空間則構成供給生態位,從而通過供需匹配程度判斷適宜性水平;陳亮等[21]將復合系統生態位劃分成資源生態位、環境生態位、經濟生態位和社會生態位4 個子系統生態位,對中國各省域進行定量評價;隨后在更多的實證案例論述中,王漢花等[22]利用生態位模型算法,對武漢市黃陂區城市土地利用現狀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對比分析,從生態位供需匹配的角度進行空間布局優化;單玉紅[23]通過住宅用地資源生態位主體、需求生態位主體兩者的相互作用過程,類比武漢市洪山及武昌兩區城市居住空間的擴展過程;劉春艷等[24]利用生態位計算模型對四川攀西地區國土空間功能重要性進行測度,判斷該區域生態系統服務高低值;李鑫等[25]利用內蒙古阿拉善盟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的大小量化自然生態位,并結合經濟、社會生態位進行該地區土地利用結構多目標優化研究。在城市生態規劃所依據的生態位理論研究中,根據生態適應性原理,挖掘并顯化積極因素,轉化并替代消極因素[26],是城市生態規劃及國土開發適宜性評價的重要思路。
2.1.2 生態平衡與協調原理
城市生態規劃所遵循的生態平衡與協調理論,主要指城市生態韌性、城市生態彈性理論。現有的城市生態韌性與城市生態彈性研究,常指通過衡量城市生態系統的抵抗力水平及適應性水平,判斷該系統的抵御風險及恢復能力[27]。在該理論的城市生態規劃研究中,既往學者傾向于從時間或空間維度對城市整體生態系統的韌性情況進行評估,如夏楚瑜等[28]通過城市生態系統的抵抗力、適應力及恢復力3 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評估了不同城市發展情景下的生態韌性水平空間分布情況;王松茂等[29]評估了山東半島城市群生態韌性的時空分異及演進規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判斷該地區范圍內的生態韌性障礙因子;王少劍等[30]構建出珠三角各大城市“規模-密度-形態”的生態韌性評價體系,從時空變化特征上分析出珠三角各市城鎮化水平與生態韌性水平的耦合協調特征。近年來,伴隨城市生態發展的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增加[31],基于城市生態韌性理論的城市生態規劃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為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提供現實指導。
2.1.3 經典景觀生態學理論
城市是受人類活動強烈干擾下形成的各種景觀斑塊的混合鑲嵌體[32]。從景觀生態學的觀點出發,劃分廊道、基質等景觀組分及要素是城市生態規劃的經典方法與技術手段。黃梅等[33]基于長沙市城市水生態韌性,構建“源地-廊道-節點”的水生態網絡,提出長沙市水生態網絡優化策略;吳靜等[34]分析江西省南昌市城市擴張趨勢,識別城市生態源地,模擬并構建當地城市生態廊道;田北辰等[35]考慮城市鳥類移動及生境,識別出了可結合鳥類生態的7 種城市廊道的構建方法,將物種移動納入城市生態規劃的考慮中。經典景觀生態學理論在城市生態規劃中多用于識別景觀類型,由此劃分出城市生態空間的建設布局,進行城市生態規劃結構優化。近年來,經典景觀生態學中的“源”“匯”理論廣泛應用于城市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中[36],“源”“匯”景觀的空間變化及其效益研究為生態城市的動態發展規劃提供了啟示。
2.2 人類生態學原理
人地關系是生態城市的本質[10]。除了自然生態學的基本理論方向外,城市生態規劃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區,這就要求相關方法與技術應遵循促進人與自然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理。具體而言,人與自然和諧需統籌考慮生態系統供給側與城市居民需求側兩大方面。
2.2.1 生態系統供給側
20 世紀上半葉,《雅典憲章》將城市劃分為生活、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基本功能,伴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游憩功能在未來城市中將尤其得到重視,城市生態空間則是居民最重要城市游憩場所[37],提供著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其中,城市綠地、濕地等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是城市和居民獲得持續生態服務的基本保障[38];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提出了“生態產品”概念[39],進一步從城市生態資源價值實現的角度衡量生態系統提供給人類社會使用和消費的終端產品或服務[40]。城市生態系統的供給總體而言可以總結為提供生態場所、生態基礎設施、生態系統服務、生態產品4 個基本方面,以生態系統供給側基本原理進行城市生態規劃,是從資源本底基本供給及服務情況入手進行科學規劃的重要表現。
2.2.2 城市居民需求側
在需求側方面,城市生態規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要求將視角轉移到對居民福祉的關注上。如何平衡生態系統服務供給及人類福祉需求[41],從而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的優化策略[42]是城市生態規劃重要命題。現有的研究主要圍繞居民健康、環境公平兩大議題進行展開:居民健康視角下,城市生態規劃既要求滿足城市居民生態宜居[43]、環境感官[44]、日常活動需求[45],在提高城市綠化率、規劃自然景觀、生態污染防治等常規方面上做出努力;同時,也要求將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納入考慮范圍,如考慮城市生態用地的社交屬性、社會韌性[46]、地方情感依戀等[47],從而體現人地互動的文化生態系統服務特性,發揮出自然環境對緩解城市居民精神壓力甚至產生特定“景觀療效”的積極作用[48];環境公平視角下,當前城市生態資源僅由少數人享有[49],供需匹配仍具有巨大矛盾,城市資源配置公平性成為突出問題。如何促進生態空間公平性以增進人類福祉是當前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50]。現有基于環境公平的城市生態規劃實證研究多從綠色可達性探討城市生態空間配置的供需匹配關系,如王敏等[51]以上海市徐匯區為例,通過對社會公平正義指標的構建,反映該地區城市公園綠地社會服務供需狀況;楊輝等[52]在針對陜西省子長縣城的案例研究中認為應依次圍繞地域適應性、空間公平性和社會公平性3 個層次進行城市生態空間布局。從實證研究來看,現有基于城市居民需求側的城市生態規劃研究集中于生態宜居、環境資源分配、使用公平等方面,如何從人居視角優化城市生態服務格局、提高生態資源綜合服務水平已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內容。
3 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影響因子
進入到后城市化時代,在城市與生態關系的重新認知與定位中,城市生態規劃已發展出各式不同的理論、模型及路徑,但具體而言,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都是由不同的影響因子相互作用配置而成,影響因子及其之間復雜相互關系的確定是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以往的城市生態規劃研究,在很長時間內局限于通過單個因素評價某種生態服務功能的實現程度,其中對城市綠地功能的關注較多,如根據城市的幾何形態特征考慮綠地布局[53]、分析高溫城市中綠地郁閉度及綠量對降溫增濕功能的影響[54]、測算城市綠地的雨水調節作用[55],更有甚者將城市生態規劃簡單等同于城市綠地規劃。隨著更為科學、全面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逐漸深入人心,諸如使用者感知等除了資源本底外的城市生態規劃影響因子逐漸得到重視,為相關技術與方法的研究多元化打下基礎。
本文將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影響因子歸納為主體因子與客體因子兩大部分。主體因子主要指與人及人從事的社會活動相關的因素,如人口密度、距離及行程、居民感知等因素;客體因子指與實踐和認識活動所指向對象有關的因素,具體而言指影響城市生態規劃的現實客觀條件,如政策方向、生態本底、環境限制性因素、環境協調度等(見圖1)。

圖1 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影響因子
4 城市生態規劃的建設模式及類型
不同的城市生態規劃建設模式及類型依據不同的建設原理,在技術方法上強調單個或多個不同影響因子,發揮出不同的主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如生態文明城市強調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政策方向,以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引領城市發展轉型[56];生態防護城市強調國家生態城市群區域防護骨架的“政策方向”[57],同時強調該地生態本底,提供如水源涵養、防風固沙等重點生態功能;山水園林城市強調依據城市生態本底進行景觀設計,將生態哲理與景觀美學涵蓋其中,構建具有山水物質空間形態環境和精神內涵的理想城市[58];海綿城市強調環境限制性因素,以解決城市洪澇災害、水資源短缺的城市生態問題為導向進行雨水利用規劃[59],關注城市水問題這一生態短板[60];低碳城市強調環境限制性因素,使城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處于較低水平[61],由此將綠色建筑作為城市建設的基礎,構建城市生產生活低碳化發展策略[62];綠色健康城市強調城市居民對心理及身體健康的使用者感知及使用者需求,呼吁規劃能直接為城市居民可用的城市綠色基礎設施,具有濃厚人文關懷,關注城市生態用地對公眾健康及福祉的影響[63],見圖2。

圖2 城市生態規劃的影響因子及其對應模式
需要說明的是,諸如海綿城市強調環境限制性因素指不同的城市生態規劃模式及類型強調的因素有所側重,在實際過程中各種不同模式及類型的生態城市都是在總體政策導向下,綜合考慮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復雜有機系統,城市生態規劃同樣應該堅持系統論與重點論統一,在綜合的、有機的科學發展框架下建設。
5 城市生態規劃的主要技術方法及其應用
5.1 指標評價法
以構建指標體系、評估框架進行城市生態規劃,在全國各地的生態城市實證研究中都得到了廣泛應用,應用范圍涵蓋了從規劃預測、規劃實施到規劃成效評價各個環節。如吳瓊等[64]在構建指標體系基礎上提出全排列多邊形圖示指標評價方法,評價并預測江蘇省揚州市生態城市在各個規劃時段的建設成效,以此衡量該生態城市模式的綜合發展能力;陳思含等[65]通過48 個指標構建城市可持續發展體系,評價湖南省郴州市生態規劃實施過程中的人類發展系統和自然環境系統耦合協調度,以此調整城市生態發展模式;宋冬梅等[66]對16 個沿海城市進行評價與對比分析,以沿海發達城市為切入點,評價我國總體城市生態化水平及生態城市建設進程。總體而言,城市生態規劃的指標體系構建結構主要有兩大類型,一類以自然、經濟、社會為框架搭建指標體系,強調城市生態的復合子系統;另一類則以結構、功能、協調度進行指標體系搭建,強調城市生態系統的內在屬性特征。本文在第一類構建結構的基礎上,增加城市生態安全相關的指標類型,綜合列舉了城市生態規劃的常用指標,如表1 所示。

表1 城市生態規劃的常用指標體系
5.2 模型模擬法
模型模擬的技術方法常基于指標體系構建的結果,加以特定公式進行導向性計算與檢驗。模型模擬在城市生態規劃中常用于描述特定城市生態功能或效應屬性,較為典型的有計算城市生態化水平的物元可拓模型[67]、城市綠色發展競爭力模型[68]、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模型[69];評價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狀況的生態足跡模型[70]、ARIMA(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71];分析城鎮化發展與生態系統耦合協同度的SOP“主體-對象-過程”模型[72]、PSR(壓力-狀態-響應)模型[73]、PVAR(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等[74]。同時,也有學者將不同模型以重新組合等改進的方式應用到城市生態規劃研究中,如將考慮橫向空間水平及縱向時間序列的物元可拓ARIMA 模型組合[75],多模型融合的應用使模型原有的預測(prediction)、解釋(explanation)和推斷(extrapolation)優勢得到更深入的發揮[76],在城市生態規劃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明顯成效。
5.3 遙感及地理信息技術(3S)
遙感及地理信息技術(RS、GIS、GPS)應用十分普遍,是城市生態規劃中的重要可視化工具。具體應用中,該技術的普遍操作過程為將相應因子柵格化,并賦予權重,對各因子進行加權疊加分析[77]。其中在權重的確定方式上,應用較為廣泛的有主成分分析法(PCA)、層次分析法(AHP)、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三類[78]。現代遙感及地理信息技術在城市生態規劃的應用已進入實質性階段,發揮著及時、準確、動態地獲取與傳輸可視化信息的重要功能,常見于城市生態的動態監控[79]、空間演變分析[80]、生態服務功能評價[81]、生態適宜度評價等城市生態規劃的重要領域中[80],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門綜合性技術的系統應用下,城市生態規劃形成了以城市生態學理論為基礎、基于3S 技術與野外調查方式、結合指標體系與模型模擬技術綜合分析的技術體系,這一體系得到廣泛使用。
5.4 質性研究方法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人本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背景下,城市生態規劃中對微觀主體人關注的呼吁越來越多[82],強調以人為本的城市生態規劃的質性研究方法順應產生。與上文定量的數據獲取技術相區別,質性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定性方法[83],以實地調查獲得社會經濟的具體性數據,關注城市微觀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強調規劃過程的公眾參與,由此提出城市生態規劃的具體性策略。近年來,質性研究方法在城市規劃領域已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應用趨勢,居民行為感知成為城市規劃的重要考慮方向。但具體到城市生態規劃上,質性方法的應用較少,傳統的城市生態設計將過多注意力投放于具有可視可量化成果的綠化運動中,人在其中扮演著被動的接受者角色,質性研究方法有待在城市生態規劃中得到推廣應用。
5.5 其他方法
伴隨著城市生態管理中多學科交叉、多技術融合的趨勢日益增強,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應用同樣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如針對生態系統服務評估開發的美國InVEST 軟件(生態系統服務和權衡的綜合評估工具)、ARIES 軟件(生態系統服務人工智能)、SolVES 軟件(生態系統服務社會價值評估)及我國的IUEMS 軟件(城市生態智慧管理系統)等[84]。這些可運行的生態軟件以模型庫為基礎,結合各個地區的具體技術標準規范,幫助人們更好進行城市生態管理分析、決策、評價與共享,是萬物互聯的新信息技術時代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研究的新興發展方向。
6 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架構
城市生態規劃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復雜交叉融合,需要在自然生態學、人類生態學的理論原理指導下,結合國家政策方向,在單個或多個影響因子的驅動和相關要素配置下,以城市生態規劃類型為建設導向,并因地制宜采用具體的技術手段進行規劃,最后在實際中不斷迭代與完善應用結果、實現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見圖3)。

圖3 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架構
對應上文從既有文獻中所綜述的原理、因子、技術、結果4 個部分,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架構可以分為4 個部分:機理(驅動力)、要素(驅動因素)、過程(驅動方式)、效應(驅動結果)。首先在城市生態規劃編制之初,需要有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通過機理分析認識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以此定義后續規劃的總體格局。科學理論作為后續規劃的動機目的形成了城市生態規劃的重要驅動力,是城市生態規劃涵蓋生態學、社會學等各學科科學內涵的集中體現;隨后,依據機理分析配置相應要素。城市生態規劃由不同的影響因子相互作用配置而成,在不同因子的驅動作用下導向了各式各類的城市生態規劃建設模式類型,由此形成了城市生態規劃的理論框架。如在生態平衡與協調理論指導下,結合碳中和、碳達峰的政策背景,規劃以環境限制性為主要驅動因素的低碳城市這一城市生態規劃模式類型。在理論框架確立后,篩選出相應的技術方法應用于城市生態規劃的具體過程中,在實踐中應用方法論,解決城市生態的實際問題;最后確立評價體系,檢驗理論框架及技術方法的可行性,進行城市生態的效應研究、評價研究。效應研究指在上述城市生態規劃的進展過程構成的因果現象,可以分為生態系統對城市的影響與城市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兩個方面。生態系統對城市的影響主要指評估城市的可持續性(如城市生態安全),城市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指進行城市擴張下的生態風險評價;評價研究指評估上述城市生態規劃的進展過程的應用性效果,具體分為橫向空間規劃(如城市生態空間分區規劃、生態網絡規劃)及縱向演變研究(如城市生態的時空格局演變、驅動機制)兩大部分。最后在評價及效應研究中優化方法論,對總體理論框架產生反饋及影響作用,在這一機理(驅動力)、要素(驅動因素)、過程(驅動方式)、效應(驅動結果)循環往復過程中,形成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與技術架構。
7 研究結論
本文以城市生態規劃的制定原理、要素配置、建設模式、技術手段對現有的文獻進行梳理評述,并提出以機理(驅動力)、要素(驅動因素)、過程(驅動方式)、效應(驅動結果)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生態規劃方法與技術架構,為可持續城市生態規劃的方法研究和實踐應用提供參考。到2050 年,接近70%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85],快速城市化與城市致密化發展,使城市生態環境和城市人居環境相互協調的需求愈加突出。城市生態規劃是城市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必經道路,我國城市生態規劃仍處于戰略定型的起步階段,目前亟需解決的幾項關鍵技術包括:
(1)建立完整的城市生態規劃技術架構。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都是復雜的巨系統,在人流、物流、能量流、信息流廣泛聚集與互通的現代城市中尤其復雜,應脫離單一學科、單一理論、單一類型、單一方法的傳統規劃模式,以整體性思維解決城市人地生態矛盾,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生態規劃建設架構。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總結,嘗試提出考慮制定原理、要素配置、建設模式、技術手段的城市生態規劃技術架構,但仍需繼續更深入的研究,未來可以進一步構建更為完整、協調、統一的城市生態規劃技術架構,并考慮采取綜合性的技術手段,加強相應軟件包的開發,推動建立更完備的城市生態規劃技術方法。
(2)界定統一的城市生態規劃內涵與學科范圍。界定概念內涵是開展研究的前提。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當前城市生態規劃僅局限于生態城市規劃之中,相比傳統的城市規劃類型,城市生態規劃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范圍還未得到明確界定,大部分人將城市生態規劃等同于城市綠地規劃。應研究提出更具體的城市生態規劃建設標準,通過城市生態規劃推動城市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全面生態化。
(3)完善以人為本的研究視角及技術方法。現有的大多數城市生態規劃研究與實踐將重點放在自然生態功能的提升中,為數不多的研究嘗試將人類福祉納入到城市生態規劃的技術方法架構中,人類成為城市生態規劃的被動接受者。同時,現有的考慮人類福祉的定性研究缺乏與定量結合的研究視角,如何定量評價人類福祉是城市規劃研究的重點難點。未來研究應突出人這一城市主體,并合理利用城市地區尤為顯著的人類活動對生態要素變化的影響,使人類行為決策與城市生態化發展路徑相輔相成,探求更加合理的城市發展模式和人類聚居模式,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