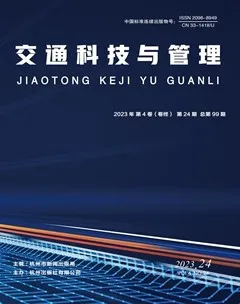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預估分析
李文彪



摘要 為探索動態回彈模量預估結果的合理性與準確性,對粉土、黏土、砂土等路基土材料物理性質進行測試,并以進口的UTM-130型萬能材料檢測儀為試驗設備展開動態回彈模量試驗,對影響試驗結果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同時采用SPSS軟件根據不同路基土試驗工況下動態回彈模量試驗結果選取預估模型,展開參數值擬合。結果表明,所選取的壓實度、含水率、CBR值、塑性指數等參數能顯著反映路基回彈模量取值情況;預估值與試驗值基本吻合,預估模型可靠性高,可作為路基路面設計的依據。
關鍵詞 路基土;細粒土;動態回彈模量;預估
中圖分類號 U416.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6-8949(2023)24-0124-04
0 引言
路基回彈模量主要體現為路基在受到車輪荷載作用后的應力-應變特性,也是路基設計中重要的參數之一。為保證路基設計方案合理適用,必須展開路基動態回彈模量預估。當前,確定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的方法主要有3種:室內反復加載動三軸試驗、現場試驗反算、模型預估。現場試驗反算法中室內試驗與現場測值修正相關關系的構建存在較大難度;室內加載試驗法操作簡單,但面臨較大的人為誤差;與室內反復加載動三軸試驗、現場試驗反算等相比,模型預估法時間短、成本低,預測值準確性有保證。
基于此,該文采用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法展開粉土、黏土、砂土等路基土回彈模量預測,并將預測值和室內測試值進行比較,得出相關結論,以指導公路工程設計實踐。
1 路基土基本性能測試
1.1 試驗材料物理性質
為了解土體顆粒組成情況及不同粒徑占比,必須展開土粒粒徑分析,通過篩余百分比表征這一特征,便于土體顆粒的工程分類。具體而言,取500 g土樣展開測試,按次序擺放好篩子后將土樣倒入,蓋上篩蓋后由搖篩機持續振搖15 min。此后依次取出土樣并稱重,記錄。根據試驗數據繪制不同土樣顆粒級配曲線[1],見圖1。
土樣在不同含水率下的物理力學性能、狀態均有所不同。黏性土在可塑狀和流塑狀間的臨界含水量即為液限;黏性土在半固體狀和可塑狀之間的臨界含水量即為塑限。液限與塑限之差是土體塑性指數。一般通過聯合測定儀展開土料液塑限取值的測定。
為展開不同類型路基土液塑限測定,取600 g過0.5 mm篩的風干土樣,分三份裝進盛土皿中,再摻加不同質量蒸餾水以使土樣達到不同液塑限狀態;攪拌均勻后靜置至少18 h。此后將土樣分層移置試驗皿內壓實,通過抹刀將表面刮平。將測試儀調平后在儀器底座處放置測試杯,按照試驗流程展開液塑限測定試驗。試驗結果見表1。
1.2 擊實試驗
該研究采用重型擊實干土法,在烘干土樣中摻加水,攪拌均勻后裝進密封塑料袋中悶料12 h備用。將土樣分5層擊實,各層擊實后均應拉毛表面層,增強層間黏合性;各層土樣全部擊實完成后,試件總高度不能超出試筒頂面5 mm。通過脫模機將試件脫出,并從中間斷開,展開含水率檢測,測值精確至0.1%。對其余試件也展開擊實、稱重操作,并依次測定含水率。
根據測定結果,與含水率相對應的干密度值見表2。根據測試結果,砂土干密度最大,取1.875 g/cm?。
1.3 CBR試驗
按照靜壓成型方式檢測不同含水率和壓實度下路基土試件CBR值。根據檢測結果,粉土CBR值最大,黏土CBR值最小,且均高出二級公路路床填料CBR下限值。可見,粉土、砂土和黏土承載力均符合路床填筑要求。
三種細粒土CBR值均隨壓實度的增大而線性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壓實度增大使土料中空隙減小,密實性和承載力均增大。此外,三種路基土CBR值隨含水率增大而先增后減,最大CBR值均出現在最佳含水率附近。在確定路基土含水率時,砂土對含水率變化的敏感程度明顯較高;而粉土和黏土隨含水率的變化不會快速、明顯膨脹和收縮,水穩性更好。
2 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試驗
2.1 試驗方法
根據《公路土工試驗規程》(JTG 3430—2020)《公路路基設計規范》(JTG D30—2015)及《公路瀝青路面設計規范》(JTG D50—2017)要求,應通過動態液壓伺服系統展開路基土及相關材料動態回彈模量測試[2]。該試驗以進口的UTM-130型萬能材料檢測儀為試驗設備,所使用的粉土、黏土、砂土等試驗土樣均為細粒土,故采用試驗規程中規定的試件加載序列。
按照試驗規程成型Ф100 mm×200 mm圓柱形試件,對開模上部和下部均設置墊塊和套箍,防止試驗過程中因過大的徑向壓力造成套筒變形。
測試開始前開啟冷卻循環水管及油泵,提前預熱15~20 min;將試件上塑料薄膜去除,并檢測試件直徑與高度。將試件放置于三軸室底座并固定,試件頂部則防止墊片,此后將試件送入三軸室并擰緊固定軸。將圍壓管、圍壓傳感器、位移傳感器等安裝在三軸室頂部,開啟氣泵使圍壓增大。按照規范要求及試驗目的設置好測試程序、試驗參數、加載程序后展開測試。
2.2 試驗結果分析
2.2.1 圍壓對動態回彈模量的影響
在路基土含水率、壓實度及偏應力等不變的情況下,展開圍壓對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影響的分析。在最佳含水率及95%壓實度下三種細粒土回彈模量變化情況試驗結果見表3。根據表中結果,隨著圍壓的持續增大,三種細粒土動態回彈模量均呈增大趨勢;不同偏應力下黏土回彈模量對圍壓依賴性增強,而其余兩種路基土回彈模量對圍壓的依賴性略微減弱[3]。隨著偏應力的增大,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降幅減小,表明這一過程中存在臨界點,若低出該臨界點,回彈模量會大幅提升。總之,三種細粒土動態回彈模量均隨圍壓的增大而呈明顯增長趨勢。
2.2.2 含水率對動態回彈模量的影響
結合重型擊實試驗結果確定出三種細粒土含水率取值范圍,并展開95%的壓實度下不同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試驗。限于篇幅,此處僅列示黏土動態回彈模量試驗值,見表4。
根據表中結果,在偏應力和圍壓相同時,細粒土在選定的含水率范圍內動態回彈模量均隨含水率的增大而減小;砂土回彈模量隨含水率的增大而線性遞減;黏土及粉土回彈模量的降速先大后小。通過進一步分析得知,水分增大使土體顆粒間水膜變厚,拉大了顆粒間距,其間的摩擦效應也隨之減小,土體顆粒間膠結能力與回彈模量均減弱[4]。
2.2.3 壓實度對動態回彈模量的影響
在不同壓實度下展開重復加載三軸試驗,并測試不同細粒土路基動態回彈模量變動規律。根據試驗結果,在偏應力與圍壓均一致時,不同路基土回彈模量與壓實度正向變動;其中,砂土路基回彈模量隨壓實度增大而緩慢增大,黏土回彈模量則快速增大,粉土路基接近線性增長。
通過分析原因看出,壓實度增大后路基土密實度隨之增大,土粒間嵌擠程度增強,接觸點也增多,受到外部荷載作用后接觸應力下降,變形減小,回彈模量增大;此外,還能較好阻止土粒間重新排列與滑動,抗變形能力提升。
3 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模型構建
3.1 模型構建
應用SPSS軟件根據不同路基土試驗工況下動態回彈模量試驗結果選取預估模型,并展開參數值擬合。基于前述試驗研究結果,用塑性指數表征土體類型,用含水率和壓實度表征土體物理性狀,用CBR表征力學強度,構建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模型。將不同類型土料重復加載三軸試驗結果視為整體,按照以下公式展開擬合[5]:
式中,Mr——路基土回彈模量(MPa);CBR——加州承載比;K——路基土壓實度(%);ω——路基土含水率(%);Ip——塑性指數;α、b、c、d——模型回歸系數。
按照非線性擬合思路,所得到的模擬參數值擬合結果見表5。回歸系數α、b、c、d依次取值55.293、0.08、3.054、7.224,相關系數R2=0.884 1,試驗數據擬合效果較好。所構建的預估模型采用塑性指數,物理狀態含水率、壓實度及強度指標展開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模型適用范圍廣,對于實際工程較為適用。將所得到的擬合結果與參數取值代入式(1)可以得到具體化的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模型,表示如下:
R2=0.884 1 (2)
3.2 預估值與試驗值的比較
應用SPSS軟件擬合出的回彈模量預估模型相關系數值較高,對回彈模量值與參數間的相關性及擬合公式預估精度均進行了較好驗證。將預估值與試驗值展開比較看出,在黏土含水率較大時兩者誤差超出30%,其余土體類型下預估值和試驗值誤差均在20%以下,最小誤差僅為0.78%;且粉土和砂土預估效果最好。如圖2所示,根據圖中動態回彈模量預估值與試驗值的對比看出,預估值與試驗值呈線性相關關系,擬合曲線相關系數R2=0.893;各點均勻分布于等值線兩側,體現出較高的預估模型準確度。
4 結論
該文在對黏土、砂土、粉土基本物理性質展開測試的基礎上,對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展開檢測,應用SPSS軟件選擇出合適的路基土回彈模量預估模型。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含水率、壓實度、塑性指數、CBR值均對路基回彈模量存在顯著影響。其中路基土類型通過塑性指數表征;強度由CBR值表征;物理狀態則由含水率和壓實度表征。
(2)結合現行規范中路基土回彈模量應力條件,借助軟件展開試驗值擬合,并將預估值與試驗值展開比較,兩者誤差小,表明預估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
(3)該文基于路基土物性指標構建起的動態回彈模量預估模型,能夠對公路路基設計起到一定參考;為保證預估模型的普遍適用性,可繼續展開專項研究,拓展該模型的適用范圍。
參考文獻
[1]黃崇偉, 朱寶兵, 章毅, 等. 潮濕路基水泥改良細粒土動態回彈模量試驗研究[J]. 中外公路, 2023(4): 18-23.
[2]歐陽衛鋒, 王業駒, 王志鑫. 紅黏土路基的動態與靜態回彈模量對比分析[J]. 中國公路, 2022(2): 110-111.
[3]劉君, 牛軍賢, 崔明. 路基非飽和土動態回彈模量計算模型對比研究[J]. 科學技術與工程, 2021(31): 13491-13496.
[4]王立功. 路基粉土動態回彈模量影響因素及預估模型研究[J]. 湖南交通科技, 2020(3): 16-20.
[5]張軍輝, 彭俊輝, 鄭健龍. 路基土動態回彈模量預估進展與展望[J]. 中國公路學報, 2020(1):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