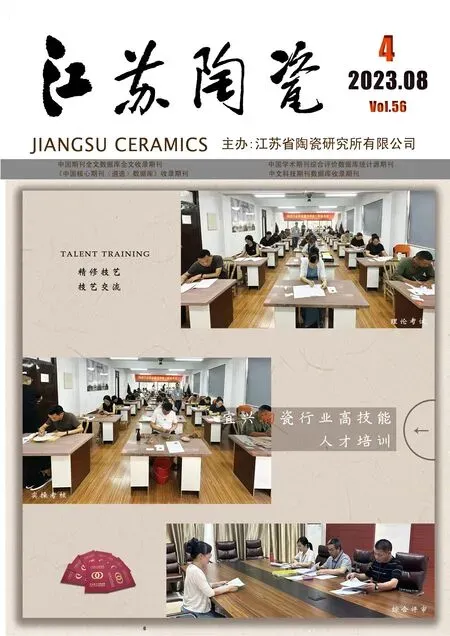“中國熱”時期歐洲對中國外銷瓷的模仿研究
王為效
(江蘇師范大學(xué),江蘇徐州 221116)
0 前言
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西方的航隊可以直行東方,暢通無阻,滿載東方貨物運輸?shù)轿鞣绞袌觯瑲W洲人民擁有了大范圍接觸使用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藝術(shù)品的機會。利奇溫將“中國熱”現(xiàn)象概括為:“中國熱,是一種由于中國的陶瓷、紡織品、漆器及其他許多貴重物在歐洲的輸入,引起西方廣大群眾的注意、好奇與贊美后,又經(jīng)過相關(guān)文字的鼓吹,進(jìn)一步刺激了這種感情,而最終形成的心理狀態(tài)。”[1]“中國熱”在歐洲持續(xù)了近兩個世紀(jì),在中西文化藝術(shù)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模仿中國外銷瓷的時代背景
中國外銷瓷流行時期恰巧與歐洲17 世紀(jì)的巴洛克風(fēng)格、18 世紀(jì)的洛可可風(fēng)格時期重疊,不能說中國外銷瓷刺激了這兩種風(fēng)格的產(chǎn)生,因為這是西方社會自身發(fā)展之必然,但可以說中國外銷瓷對兩者風(fēng)格的發(fā)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巴洛克在1600 年到1750 年間流行于歐洲,一反文藝復(fù)興時期嚴(yán)肅和含蓄的風(fēng)格,轉(zhuǎn)而追求富麗堂皇、氣勢雄偉。巴洛克的華麗富貴與中國外銷瓷精美、奢華、昂貴、典雅的特征不謀而合,所以歐洲本土瓷廠早期產(chǎn)品風(fēng)格更傾向于巴洛克多一些。
1715 年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王朝更替迎來了洛可可時代,洛可可一詞源于意大利語和法語,意為“貝殼”“巖石工藝”。洛可可風(fēng)格以小巧玲瓏為特點,摒棄了巴洛克的宏偉與浮夸,“它摧毀了時代精神和巴洛克政治意識形態(tài)所確立的規(guī)模和絕對主義,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巴洛克的正宗形式被洛可可的個人品位和多樣性所取代。”[2]它多采用淡粉、淡綠、淡藍(lán)等淺色調(diào),又被稱為“路易十五風(fēng)格”,被廣泛應(yīng)用到建筑、繪畫、雕塑、音樂、裝潢等領(lǐng)域。路易十五的寵妃蓬巴杜夫人更是此風(fēng)格的重要推動者,如擁有“蓬巴杜玫瑰”之稱的法國塞夫勒瓷便是在蓬巴杜夫人的影響下創(chuàng)造的,這位夫人“人們稱她為‘洛可可之母’,并把她視為洛可可時代的象征”[3],法國洛可可風(fēng)格也賦予了塞夫勒瓷中國主題產(chǎn)品的一種逸樂氣質(zhì)。
2 歐洲本土瓷廠探索制瓷工藝
中國瓷器憑借著精美的工藝與造型,為歐洲人提供了異國情調(diào)的審美體驗。瓷器貿(mào)易大致經(jīng)歷了預(yù)定瓷器、定制瓷器、進(jìn)口一般粗瓷器三個階段。在16世紀(jì)歐洲與中國開展貿(mào)易以來,最早輸入的是青花瓷,荷蘭人就對這種藍(lán)白相間的品種情有獨鐘,將其稱為“克拉克瓷”。“中國熱”催生了歐洲對于中國瓷器的模仿與圖案借鑒,一方面由于明清交替導(dǎo)致物流運輸不暢、商品緊缺,另一方面由于歐洲長期進(jìn)口中國外銷藝術(shù)品,導(dǎo)致大量白銀流失,模仿生產(chǎn)有巨大的利潤空間。歐洲模仿中國外銷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模仿中國的制瓷工藝,第二是模仿瓷器造型,第三是模仿色彩裝飾紋樣。
2.1 模仿中國的制瓷工藝
中國外銷瓷一開始就被歐洲受眾認(rèn)為具有某種神奇的特性,就如同鴕鳥蛋和水晶石一樣對于他們來說都是稀罕的玩意,始終有一種神秘的氛圍籠罩著這些物體,持續(xù)不斷地吸引著人們一探究竟。“有人認(rèn)為它是蛋殼制作的,但要埋在地下80 年,又有人認(rèn)為并不需要埋在地下,只是要風(fēng)吹日曬40 年”[4],如果歐洲能在很短時間內(nèi)攻克如何制作的難題,那么這些迷幻的傳說也不會散播出去。歐洲的各國國王們發(fā)動足智多謀的科學(xué)人才集中解決這個困擾多年的難題,而具有悠久傳承歷史的歐洲煉金術(shù)士們也暫停尋找點金石,期望發(fā)掘深藏其中的成分。
1575 年,歐洲第一個進(jìn)行嘗試生產(chǎn)陶瓷的為意大利佛羅倫薩弗朗切斯科工廠,因為仿制用到的成分較多,包括玻璃、沙子等,導(dǎo)致性質(zhì)不穩(wěn)定,成品釉陶釉面模糊,還有些許氣泡,遠(yuǎn)不如中國陶瓷的品質(zhì)。不過,它的制作工藝及選用中國白底青花圖案等為繼任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16-17 世紀(jì),人們追求東方風(fēng)尚,大眾對于仿制品的需求巨大,這進(jìn)一步加快了繼任者的研究腳步。16 世紀(jì)末,意大利佛羅倫薩仿造中國瓷器,即“梅迪西瓷”,它在紋樣上模仿青花瓷,但因為它是釉陶產(chǎn)品,又因為質(zhì)量不佳,數(shù)量少沒有銷量,于17 世紀(jì)初就已停止生產(chǎn)。制瓷工藝是如此的困難,堪比煉金術(shù),由于無法發(fā)現(xiàn)中國制瓷的秘密而只能燒制出軟瓷。
德國的約翰·波特哥也是一位煉金術(shù)士,1708 年他制造出第一件不上釉的白色硬瓷,這一結(jié)果也是帶有一定巧合的,陶土在燒制過程中發(fā)生了意外的變化。雇主對這一成果表示滿意,并在1717 年在德累斯頓的郊外梅森建立了一個皇家瓷器工廠。此后,波特哥認(rèn)真鉆研制瓷工藝,引入材料高嶺土抵御了高溫,最終燒制出硬質(zhì)瓷器,成為最接近的模仿,實現(xiàn)了西方歷史上首次對中國硬瓷的模仿,是歐洲生產(chǎn)的精品瓷之一,梅森瓷器廠也成為歐洲同時期影響力較大的瓷器工廠之一。
2.2 模仿瓷器造型
相較于神秘莫測、困難重重的制瓷工藝,模仿瓷器造型則簡單得多。中國常見的瓷器造型有瓶、罐、盤等,代爾夫特瓷器早就實現(xiàn)了對中國瓷器造型方面全要素的模仿,又因為成本較低,很快便占據(jù)低端市場,實現(xiàn)了東方式造型的傳播。隨著代爾夫特的發(fā)展、技術(shù)的成熟,他們開始將中國元素和歐洲元素結(jié)合起來,造型方面開始創(chuàng)新,如著名的《郁金香花插》。
歐洲人因為使用習(xí)慣和中國人不同,還會在瓷器的外形上做一些功夫,比如會在中國外銷瓷杯、瓷碗周圍加上金銀把手或底座,以此來適應(yīng)歐洲人習(xí)慣使用高腳杯的傳統(tǒng),還因為是貴重金屬而彰顯財富和地位。中國瓷瓶成為歐洲眾多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和裝飾品,贏得了廣大家庭婦女的喜愛,他們用貴金屬給瓷器鑲邊,既可以避免在日用過程中的損壞,還可以增添一種別樣的韻味。“在法國,路易十五還曾經(jīng)下詔以瓷代銀,即廢棄原來的銀制品,改用中國瓷器,由此掀起了一波日用品改革的浪潮。”[5]
當(dāng)梅森瓷器廠生產(chǎn)優(yōu)秀的硬瓷時,歐洲瓷器終于取得了在材質(zhì)、造型、裝飾紋樣與中國瓷器抗衡的資本。此后,梅森雕像進(jìn)一步發(fā)展,全盛時期大量占據(jù)著人們的家居生活,這些雕像造型各異,富有異國情調(diào),在坎德勒成為首席雕塑設(shè)計師后,表現(xiàn)題材范圍進(jìn)一步擴大,包括人物、動物、植物、各種職業(yè)場景展示等。“坎德勒的雕像有些甚至流傳到遙遠(yuǎn)的東方,被中國工匠仿制。”[6]梅森瓷器的工藝技術(shù)秘密即便被嚴(yán)加保密,但還是被雇員泄露出去。久而久之,硬瓷工藝通過最初的工廠傳遍整個歐洲,梅森瓷器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對歐洲瓷畫家和設(shè)計師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2.3 模仿色彩裝飾紋樣
藍(lán)、白二色是在歐洲人印象中最具中國特色的色彩組合,代爾夫特于17 世紀(jì)中期就開始生產(chǎn)白底藍(lán)花的釉陶產(chǎn)品,路易十四的特里農(nóng)宮裝飾外墻與室內(nèi)的貼磚也選用藍(lán)、白二色。色彩方面選用標(biāo)準(zhǔn)的藍(lán)、白二色,有時還會添上紅色,形成藍(lán)、白、紅三色組合。
17 世紀(jì)50 年代,一部分歐洲畫匠放棄了仿制中國明代裝飾,從東方裝飾約束中解放出來,隨心所欲地描繪自己對于中國的認(rèn)識,于是畫面轉(zhuǎn)變?yōu)樯碇嫜b及姿態(tài)奇異的中國人物、華麗的建筑房屋、神出鬼沒的龍等。代爾夫特一般生產(chǎn)藍(lán)、白二色的瓷器,與代爾夫特同時期一起憑借質(zhì)量高、藍(lán)白相間出名的制瓷廠還有法國的納韋爾。納韋爾早年在模仿中國瓷器的形狀裝飾圣經(jīng)等場景,并飾有歐洲或東方圖案,總體來說比代爾夫特生產(chǎn)的要隨意一些,但它卻憑借藍(lán)底白花開啟了歐洲制瓷業(yè)獨特的中國風(fēng)。
17 世紀(jì)末期至18 世紀(jì)初,中國外銷瓷由青花瓷轉(zhuǎn)向彩瓷,帶動歐洲各地的窯廠產(chǎn)品也隨之過渡,一時間“綠彩”“粉紅彩”等五彩瓷爭奇斗艷。中國外銷瓷的裝飾紋樣豐富多彩、題材眾多,承載了厚重的中華文化,所有的主題題材來自自然,來自百姓的日常生活,來自人們的美好愿望,是中國儒家“天人合一”哲學(xué)思想在瓷器裝飾紋樣領(lǐng)域的生動體現(xiàn)。早先代爾夫特模仿的裝飾題材有人物紋樣、動物紋樣、風(fēng)景紋樣、植物紋樣,裝飾技法多為開窗形式。模仿的人物紋樣以情景式展現(xiàn),包括神話傳說主題、小說戲曲人物主題、高士圖主題、歷史人物主題等。動物紋樣有麒麟、龍鳳等猛獸,還有象征愛情的鴛鴦紋樣。
“在曲解了中國瓷器的性質(zhì)以后,人們開始模仿或者說至少在當(dāng)?shù)氐漠a(chǎn)品上裝飾一下表現(xiàn)中國人物或者偽中國的主題。”[7]但是歐洲人不懂這些復(fù)雜圖案的象征意義,只是單純地把紋樣元素提取出來,有時還會出現(xiàn)差異,造成產(chǎn)品不中不西、不倫不類。如梅森瓷器上色彩艷麗的鮮花圖案更像是中國和印度花卉紋樣的一種融合,它們一部分取自從中國進(jìn)口瓷器上的綠葉和薔薇,而中國常用的牡丹和菊花等花卉還不為人們所熟悉。
3 結(jié)語
歐洲本土瓷器廠既是追求經(jīng)濟利益下誕生的產(chǎn)物,也是歐洲巴洛克、洛可可風(fēng)格和中國風(fēng)格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在“中國熱”早期,面對神秘而遙遠(yuǎn)的中國,歐洲將本土瓷器產(chǎn)品同巴洛克風(fēng)格結(jié)合起來,形成輝煌耀眼的裝飾效果,而到了“中國熱”中后期,中國形象變得清晰,歐洲將本土瓷器產(chǎn)品同洛可可風(fēng)格結(jié)合起來,形成精致逸樂的裝飾效果。此后,他們通過模仿瓷器造型、色彩裝飾紋樣到根據(jù)自己的喜好獨立創(chuàng)造,完成了模仿形態(tài)特征,創(chuàng)作理念的借用、借鑒與融合的一系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