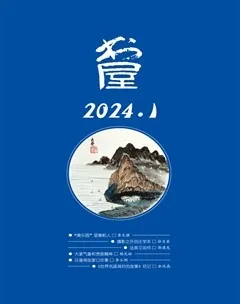攝影之外的莊學本
徐自豪
1941年,莊學本在重慶、成都、雅安三地舉辦了影響極大的西康影展,“觀眾之多,為過去任何展覽會所不及”。民族學家、中國早期邊疆研究者、金陵大學教授徐益棠盛贊莊學本“起初僅僅是一位攝影家,后來變成了一位專門的旅行家,現在卻已成為邊疆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說是民族學的研究者了”。可是其后幾年,莊學本卻遠離了他歷經艱辛才到達的領域。
1942年,莊學本以股東的身份加入康藏貿易公司,該公司成立于同年8月,總公司位于康定,在拉薩和印度的加爾各答設有分公司,印度、中國西藏及西康沿線均設有辦事處和運輸站。莊學本先后擔任康藏貿易公司駐印度加爾各答分公司經理,以及1944年2月由康藏貿易公司與國民政府交通部合辦的康藏馱運公司噶倫堡分公司經理,他依舊懷揣著十年前的夢想,試圖通過公司開辟的馱運路線從印度進藏。遺憾的是,由于印度政府拒絕簽發護照,莊學本的進藏之夢還是未能實現。莊學本在印度工作的三年間,先后到訪“新德里、孟買、大吉嶺、噶倫堡、鹿野苑、貝爾納斯、烏達坡等著名地方”,拍攝作品一千多幅。在印期間編輯完成的《印度畫冊》草稿今已不存,只出版了一冊纖薄的《西竺剪影》,記錄了他在異域游歷的點滴痕跡。抗戰勝利前夕,莊學本離開印度回到祖國。
1945年5月,《西竺剪影》于加爾各答出版,共收錄攝影作品:古廟(封面)、孤塔、恒河邊上之波羅奈圣城、回教大寺、喜馬拉雅山中之朝霧、佛光普照、釋迦佛成道處、土王之禁宮、村女、山市、舞、湖濱之晨、馴象,這十三張照片中只有一張收錄于《莊學本全集》的“印度之行”篇。筆者所藏的這冊影集,是葉淺予的舊藏——莊學本1945年9月來到成都后所贈。
莊學本與葉淺予年齡相仿,唯成名稍晚。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兩人都有到訪印度的經歷。
1943年夏天,經愛潑斯坦介紹,葉淺予作為訪問記者前往印度蘭姆伽,參觀中國遠征軍受訓,并繪制漫畫宣傳抗戰。蘭姆伽距離佛教圣地菩提伽耶不遠,葉淺予向鄭洞國借了吉普車,參觀了摩訶菩提寺。葉淺予回到加爾各答后,舉辦了重慶、香港題材的作品畫展,當地書店選取其中的二十二幅作品編印了一冊名為《今日中國》的畫集。
莊學本和葉淺予的交往也許開始于加爾各答。早些年在北京的嘉德拍賣會中,有一幅葉淺予為莊學本所繪的速寫頭像底下赫然寫有“1943印度莊學本”字樣,葉淺予知道莊學本的名字,可能時間更早一些。1930年,中國出現了好幾個步行團,莊學本是2月動身的“全國步行團”成員。而葉淺予則在靜安寺路雪園,與黃警頑、胡伯翔等人一起為6月啟程的“中國青年亞細亞步行團”餞行。胡、黃二人也是莊學本的熟人,為其西行攝影提供了很多幫助。
在目前見到的公開資料里,葉淺予與莊學本僅有的交集發生于1945年抗戰勝利后,葉淺予、戴愛蓮夫婦住在成都張大千家里,想去西康采風,于是請“在邊地很久,對西康風土人情尤為熟悉”的莊學本作向導,他們的合作非常愉快,葉淺予在《打箭爐日記》中有著精彩的記述。但是在前往西康前,莊學本忙于處理重慶事務,導致葉淺予在成都苦等了三個月之久,葉淺予眼見錢袋子日益干癟,被迫“四處奔走,托朋友賣畫”籌措旅費,方得成行。艱苦卓絕的抗戰取得勝利,大家在歡慶之后多忙于復員,回歸和平生活。如果葉淺予和莊學本只是初次合作,那么如此漫長的等待顯得異乎尋常。我嘗試著比對葉淺予的印度速寫(《印度風情》,湖南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和莊學本的印度攝影后,作品顯示他倆似乎在相近的時間去過相同的地點。
葉淺予旅印期間,“在加爾各答停留較久,除了北上蘭伽專訪中國遠征軍營地,還由朋友作向導,訪問了寂鄉詩人泰戈爾辦的國際大學”。他們借宿在國際大學內譚云山主持、吳曉鈴任教的中國學院,葉淺予在學院品嘗了以甜食為主的地道印度餐。恰逢泰戈爾忌辰,校內“幽雅肅穆,如履仙境”。在舞蹈學院的教室里,葉淺予開始領略到印度舞的美妙,并隨即對其產生濃厚的興趣,創作了大量以舞者和印度風光為主題的作品。他的繪畫風格也逐漸從漫畫式的辛辣諷刺轉向中國畫式的寫實。而莊學本所攝印度舞的地點,就在寂鄉小鎮,室內陳設也頗似舞蹈教室。
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以盛產紅茶而聞名于世,葉淺予、莊學本也都在此留下過足跡,創作有藝術作品,這兒的居民“抬頭就能看到白皚皚的雪峰,這塊仙境一般的寶地,注定要成為世界游客的樂園”。葉淺予所說的這座雪峰名叫喀欽姜伽(Kanchenjunga),今多譯為干城章嘉峰,位于印度和尼泊爾交界處,是世界第三高峰,藏語和錫金語意為“五座巨大的白雪寶藏”。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曾被認為是世界第一高峰。而莊學本的這幅攝影作品,限于相機畫幅,只擷取了最精華的干城章嘉峰臥佛像。在印時間不長的葉淺予也幾乎在同一角度創作了他的速寫。抵達當時交通頗為不便的大吉嶺,要從加爾各答經轉,而且受氣候影響,雪山有時會被隱匿在云層之中。能在目的地找到最佳創作角度并迅疾捕獲創作時機,通常來說,必須同時具備熟悉當地交通與氣候,以及有相當的藝術眼光這幾個條件。
不知何故,葉淺予在他印度旅行的回憶中并未提及“向導朋友”的名字,但是在同一時期莊學本僅存的印度攝影作品里就存有多幅與葉淺予速寫內容一致的作品,考慮到莊學本時任康藏貿易公司駐加爾各答分公司經理的身份,雖然暫無更多史料佐證,但筆者還是傾向于莊學本曾為葉淺予的印度之行作過向導。莊學本品性恂恂厚重,熟悉當地情況又具審美眼光,與這樣的同伴同行難得而又愉快,也因此才會有兩年后的再次同行。希望將來能見到更多史料,如莊學本、葉淺予等人的日記、文章、合影、新聞報道等,便可坐實這個推斷。
莊學本加入康藏貿易公司,先任總務、董事,后被委派到印度任加爾各答分公司經理。莊學本志在游歷,卻在印度足足滯留了三年之久。據他本人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所說,他當時“個人主要精力仍放在攝影活動上”,事實恐非完全如此。在印三年間,所得攝影一千余張,意味著日均攝影僅有一幅,這與莊學本民族攝影時期的成績相差太遠。但若對印度沒有興趣,又何以長住三年?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得從他所入職的康藏貿易公司、康藏馱運公司入手。兩家公司成立于1942年日軍占領緬甸,滇緬公路被切斷之際,時英屬印度政府禁止戰略物資出口,中國的抗戰物資補給受到嚴重威脅,這兩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通過自行采購、組織人力畜力,向大后方承運中國政府需要的抗戰物資。
莊學本所在的加爾各答分公司和噶倫堡分公司,各只有兩位職員,三年間莊學本做了大量實際工作:“以經營印度貨物,西藏土產及沿途驛運等為業務。”“為總公司采購西藥、布匹等貨物經西藏內運(國內)。”臺北“國史館”的一份檔案記錄了當時國民政府交通部的調查數據:“康藏馱運公司負責承運康印間物資,年約一千噸。”(轉引自馮翔:《少數民族商號的抗日救亡與籌推藏事——以康藏貿易公司為例》)康藏貿易公司還在開采西藏產的精煉硼砂后,幾乎獨家為抗戰大后方提供了巨量的硼砂。硼砂是軍工、機械行業重要的原料,此舉大大緩解了原料不足的困境,維護了大后方工業的穩定,抑制了物價的暴漲。
康藏貿易公司會計格桑扎西在“公司簡況”里如是評價:“公司生意雖然失敗了,但對聯合康藏,支援抗日、改善漢藏關系、促進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莊學本全程參與了康藏公司的在印業務,以個人之力投身于祖國的抗戰事業。
莊學本對于西藏和平解放也有貢獻。195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進軍西藏的決策,但缺乏行軍必需的大比例等高線地圖。一般史書只記載藏學家任乃強趕制了二十余幅康藏地圖給賀龍,然而任乃強的主要活動區域還是在四川,他本人也沒有去過西藏,當時中國國內僅有的零星幾種西藏地圖精度又不高,中文地名錯誤連連,他又是根據什么材料繪制成的高精密地圖?原來莊學本在印度期間注意收集當地出版的康藏書籍,曾為劉文輝收購關于西康、西藏的外文書籍達幾十種之多。作為對西藏極有興趣的同道,任乃強繪制康藏地圖的材料也源自莊學本。
2018年發表于《中國藏學》雜志的《〈西進集〉與在康定建省委員會的兩年——任乃強〈筱莊筆記〉節錄(五)》一文揭示,莊學本在印度期間經常寄資料給任乃強,其中就有印度出版的關于西藏的書籍和地圖,特別是他還出借了難得的由印度測量局制作的西藏地圖巨冊,這冊地圖的比例尺很大,精度極高,應該是當時最好、最新的版本。為了讓解放軍進藏時能夠拿到高清精準的地圖,任乃強以這冊地圖為參考依據,受命帶隊日夜趕制西藏地圖譯本,在連續高強度的工作中,還把原版地圖冊給弄壞了。幾年后任乃強欲將一件猞猁披風送給莊學本作為賠償,莊學本沒有收受。
莊學本一生三次想要進藏,均未得實現。但是他在印度購買并寄回國內的西藏地圖冊、西藏書籍,幫助任乃強圓滿地完成了繪制中文版西藏地圖的任務,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順利進軍西藏,間接地為西藏和平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莊學本積極響應號召,在四川阿壩馬爾康地區從事民族采訪工作的同時,還進行了活麝取香和人工養麝的科學試驗,歷經一個多月,成功地完成了世界第一例“活麝采取麝香”試驗。莊學本將其思考的科學方法總結為“獵網捕麝法”和“散放飼養法”,寫成“發展我國的麝香生產研究報告”。1959年莊學本編著的《養獐和人工采香試驗》一書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據稱中國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到現場觀察后,認為“可與古代養鹿取茸、畜蚌獲珠的發現相比美”。
由于棲息地被破壞和人類的亂捕濫獵,據國家林草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野生林麝數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二百五十萬只,到二十世紀末驟降至不到十萬只。另據最近的新聞報道,山西古交市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淘汰原有的焦煤產業,舉全市之力養殖林麝,進行活體取香,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莊學本六十多年前所從事的工作,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莊學本的養獐取香研究,在1965年那個特殊時期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導致其被“開除公職,清洗回鄉,自謀生計”。莊學本堅持申訴十年,1975年終獲平反。1987年,“林麝飼養和活體取香”成果獲國家發明二等獎,此時莊學本已去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