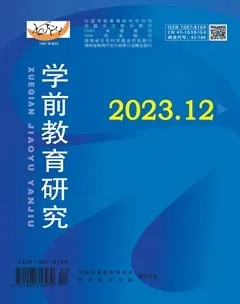我國“幼兒園課程”的概念史考察
[摘 要] 清末以來,官方、學(xué)術(shù)界及實踐領(lǐng)域?qū)Α坝變簣@課程”概念的理解,發(fā)生如下變遷:課程目標(biāo)從獲得知識到促進兒童健康成長;課程內(nèi)容從相互孤立、學(xué)科化到綜合化、整體化、生活化;課程實施從灌輸注入式到以游戲為基本活動,創(chuàng)造性地采用多種方法;課程編制從高預(yù)成、高計劃到園本化、個性化,并具有生成性、靈活性。幼兒園課程概念的變遷是幼兒園課程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相互建構(gòu)的過程。官方的、學(xué)術(shù)的課程概念最終要在實踐層面被認(rèn)識、被理解,方能被踐行。前瞻未來,在“以兒童為本位”的基本價值取向的引領(lǐng)下,幼兒園課程必將向著更“兒童”的方向發(fā)展。
[關(guān)鍵詞] 幼兒園課程;學(xué)前課程;課程概念;概念史
如果把課程看作教育的載體和內(nèi)容,那么,自從有了幼兒教育,便有了實際意義的課程。盡管中國蒙學(xué)歷史悠久,課程思想源遠流長,然而幼兒教育機構(gòu)化、專門化至今卻不過百廿周年。1903年,清政府創(chuàng)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xué)前教育機構(gòu)——湖北武昌蒙養(yǎng)院,這標(biāo)志著中國幼兒教育機構(gòu)的誕生,也標(biāo)志著正式意義上幼兒園課程的誕生。本文以此為起點,考察“幼兒園課程”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表達,通過對“幼兒園課程”流變的回溯與分析,增進對“幼兒園課程”的理解,并探討“幼兒園課程”概念的發(fā)展軌跡。
一、“幼兒園課程”概念的變遷
在概念史的視角中,要確認(rèn)和把握“幼兒園課程”概念,并非抓住“幼兒園課程”這個詞語就能達成的。這是因為,一個概念可能有多種不同表達亦即不同用詞,[1]“一個詞的含義總是指向意指之物,無論是一種思路還是一種情形……概念附著于詞語,但它不只是詞語”。[2]概念由于其復(fù)雜性、多義性,不能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定義,而是只能被闡釋。[3]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主體的“幼兒園課程”概念是有所不同的。清末以來,官方的政策文本、學(xué)術(shù)界的主流觀念以及幼兒園實踐,闡釋、表達了各自對“幼兒園課程”概念的理解。
(一)清末民初
西方學(xué)前教育的機構(gòu)化,是社會化大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伴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大量女工因參加生產(chǎn)勞動而無法照看幼童,學(xué)前教育機構(gòu)應(yīng)運而生。中國的學(xué)前教育機構(gòu)是西學(xué)東漸以及學(xué)習(xí)日本之后的產(chǎn)物。
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失敗,清政府震驚于新近崛起的東方強國——日本。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在短短的幾十年內(nèi)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通過考察日本的成功經(jīng)驗,清政府發(fā)現(xiàn),日本之所以能夠振興而與歐洲抗衡,改革教育、興辦學(xué)校至關(guān)重要。在學(xué)習(xí)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實踐后,清政府開辦了中國第一所官辦幼兒教育機構(gòu)——湖北武昌蒙養(yǎng)院,并于1904年頒布《奏定蒙養(yǎng)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清政府的學(xué)前教育政策文件、幼兒園開辦章程及幼兒園教育實踐,幾乎照搬照抄日本的幼兒教育。此時,對幼兒園課程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幼兒園課程是保育的條目、課目或科目。
《奏定蒙養(yǎng)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規(guī)定,“保育、教導(dǎo)之條目如下:(1)游戲;(2)歌謠;(3)談話;(4)手技”。[4]《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指出,“本園所定保育課目凡七,大概與日本幼稚園課目有出入。今列于下:行儀、訓(xùn)話、幼稚園語、日語、手技、唱歌、游嬉”。[5]《湖南蒙養(yǎng)院教課說略》羅列了其“所教主旨”,即談話、行儀、讀方、數(shù)方、手技、樂歌、游戲。[6]從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幼兒園課程指教育的內(nèi)容,常被表述為“條目”“課目”“科目”等。
第二,幼兒園課程也有教學(xué)進程之意。
在個別幼兒教育機構(gòu)的開辦章程和介紹日本幼兒教育的文獻中,“課”和“程”二字或組合成獨立詞“課程”,或加上其他字組成別的詞或短語,如“課程表”“課程門目”等,用以表征教學(xué)的進程。
張百熙、張之洞等人擬定的《奏定學(xué)堂章程》(1903)列出“蒙學(xué)堂課程門目表”和“蒙學(xué)功課年程”,并制訂了“蒙學(xué)堂課程十二日一周時刻表”,即“課程表”。[7]上海公立幼稚舍在其開辦章程中,指出“謹(jǐn)遵《奏定學(xué)堂章程》蒙養(yǎng)院辦法,參以東西幼稚園課程,定名幼稚舍”,并列出了該舍兩個班的課程單。1907年,上海《東方雜志》一篇《論幼稚園》的文章介紹了日本的幼兒園,并說到“日本幼稚園,每日課程,皆限自午前九點起,至午后一時半止”。[8]可見,在以上“課程”一詞的使用中,“課程”既有教學(xué)的時間、進程,又有教學(xué)內(nèi)容之意。
第三,盡管學(xué)前教育制度和政策文本明確指出,幼兒園的教育內(nèi)容與小學(xué)學(xué)科知識的學(xué)習(xí)不同,在一些幼兒園開辦章程中也強調(diào)“幼稚園重養(yǎng)不重學(xué)”,[9]幼兒園“以保衛(wèi)兒童健康為主,以誘啟知識為輔,并不多讀蒙書”,[10]然而當(dāng)時在幼兒教育實踐中,卻存在把課程當(dāng)作學(xué)科知識體系,向兒童分門別類傳遞知識的傾向:幼兒園通過歌謠、談話等形式,用說教灌輸?shù)姆绞剑瑔蜗虻叵蛴變簜鬟f知識或價值觀念。幼兒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xué)習(xí),只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教材從《三字經(jīng)》《百家姓》變成了游戲、歌謠、談話、手技。[11]
(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五四運動前,我國主要有日本式蒙養(yǎng)院和教會幼稚園兩種類型的幼兒園。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強烈的改革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影響下,一方面,宗教化、日本式小學(xué)化的幼兒園遭到批判;另一方面,西方教育家如福祿培爾、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思想與實踐被引進和傳播,尤其是杜威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想,對我國學(xué)前教育影響巨大。當(dāng)時,在模仿學(xué)習(xí)西方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情況,為了使幼兒教育科學(xué)化、本土化、中國化,以陳鶴琴、張雪門為代表的教育家做了種種嘗試和探索。
陳鶴琴認(rèn)為,幼兒園“課程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幫助兒童目前生活”,[12]盡管今日的兒童是將來的成人,但是不應(yīng)提前教兒童將來才能理解的內(nèi)容。陳鶴琴還提出,“所有課程都要從人生實際生活與經(jīng)驗里選出來”,[13]幼兒園課程應(yīng)根據(jù)兒童的環(huán)境來選擇課程內(nèi)容,而兒童的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應(yīng)利用這兩種環(huán)境作為幼兒園課程的中心。[14]陳鶴琴反對幼兒園進行分科教學(xué),認(rèn)為其違反兒童的生活和心理特點——兒童的生活是一個整體,所以幼兒園課程也應(yīng)是整個的、互相連接的。幼兒園應(yīng)采用“整個教學(xué)法”,把“各科功課打成一片”,“把兒童所應(yīng)該學(xué)的東西整個地、有系統(tǒng)地教兒童學(xué)”。[15]
張雪門認(rèn)為:“課程的本質(zhì)是對人類生活有價值的經(jīng)驗,是用最經(jīng)濟的手段,按有組織的調(diào)制,用各種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應(yīng)和活動。”[16]“幼兒園課程是給3~6歲的孩子所能夠做而且喜歡做的經(jīng)驗的預(yù)備。”[17]張雪門反對將幼兒園課程看作知識,認(rèn)為課程是適應(yīng)生長的有價值的材料。[18]幼兒園課程以兒童已有的經(jīng)驗為基礎(chǔ),幫助孩子在舊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建立聯(lián)系,獲得新的經(jīng)驗。這些新的經(jīng)驗應(yīng)來源于兒童的生活,符合兒童的興趣和需要,同時亦有教育意義和價值,可以滿足社會生活和發(fā)展的需要。[19]張雪門認(rèn)為,幼兒的生活是整個的、鮮活的、有機的,幼兒園課程也應(yīng)具有整體性和直接經(jīng)驗性。“幼稚園課程,學(xué)科式的不適合兒童生活需要,已失了課程的本意,當(dāng)然是不可用的”,[20]將經(jīng)驗劃分為各科目,是出于研究需要而進行的人為劃分,事實上,兒童感知的世界、兒童的生活、兒童的經(jīng)驗是一個整體,因而在幼兒園,各種科目是兒童整體生活的一部分,不應(yīng)按照學(xué)科的邏輯分門別類地向兒童傳授知識,“幼稚園的課程是一種具體的整個活動”。[21]
陳鶴琴、張雪門關(guān)于“幼兒園課程”概念的共同點在于:幼兒園課程是滿足兒童需要,是對兒童有教育意義的,來自兒童生活的經(jīng)驗;幼兒園課程應(yīng)具有整體性、直接經(jīng)驗性和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反對分門別類地教授兒童學(xué)科知識。
1925年,陳鶴琴、張宗麟在南京鼓樓幼稚園開始課程試驗,經(jīng)過三年的探索,形成了單元課程模式。1929年8月,教育部頒布《幼稚園課程暫行標(biāo)準(zhǔn)》,該標(biāo)準(zhǔn)主要依據(jù)南京鼓樓幼稚園的課程實驗成果而擬定,由陳鶴琴、鄭曉滄、張宗麟等人起草。《幼稚園暫行課程標(biāo)準(zhǔn)》體現(xiàn)了陳鶴琴、張雪門等人的課程觀,它的頒布有助于單元課程的推廣。在實踐中,諸多幼兒園開始探討單元課程理念,并學(xué)習(xí)單元課程模式。
(三)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
建國初期,在全面學(xué)習(xí)蘇聯(lián)方針的指引下,教育部先后聘請了蘇聯(lián)幼兒教育專家戈林娜、馬努依連科來我國傳授幼兒教育經(jīng)驗。在蘇聯(lián)專家的指導(dǎo)下,教育部頒布了《幼兒園暫行教學(xué)綱要(草案)》(1951年)和《幼兒園暫行規(guī)程草案》(1952年),并通知在全國幼兒園試行。這兩個文件初步奠定了我國幼兒園分科課程的模式。分科課程重視各門學(xué)科知識的傳授,認(rèn)為按照等級原則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對促進兒童的智力發(fā)展最為有效。[22]
有學(xué)者認(rèn)為,建國初期,我國教育理論幾乎完全套用蘇聯(lián)的教育學(xué)科體系,而在當(dāng)時的蘇聯(lián)教育學(xué)科體系中,課程論是缺失的,課程概念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它被置于教學(xué)論的概念體系之中,理解為學(xué)科或?qū)W科的總和。[23]事實上,不僅在基礎(chǔ)教育領(lǐng)域存在課程研究失語,課程概念被忽視的情況,同樣出現(xiàn)在幼兒教育領(lǐng)域——從20世紀(jì)50年代到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課程”一詞在幼兒教育領(lǐng)域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教學(xué)綱要”“教學(xué)計劃”“教學(xué)要點”“作業(yè)”等。
《幼兒園暫行教學(xué)綱要(草案)》在幼兒園教學(xué)暫行總則中指出:“幼兒園的作業(yè),暫定為體育、語言、認(rèn)識環(huán)境、圖畫手工、音樂、計算等六項。各項作業(yè)的總?cè)蝿?wù),是在有目的、有系統(tǒng),有組織地對幼兒順次傳達知識,發(fā)展他們的體力、智力;并培養(yǎng)優(yōu)良品德和習(xí)慣,打好準(zhǔn)備升入小學(xué)的一切基礎(chǔ)。”[24]“作業(yè)”一詞在分科課程中有特殊的含義,是“幼兒園教師根據(jù)各科大綱有計劃、有系統(tǒng)地,并由淺入深地選定內(nèi)容,在同一時間內(nèi)對全班幼兒進行的教學(xué)和復(fù)習(xí)。”[25]由此可見,“作業(yè)”即有計劃的集體教學(xué)活動。
《幼兒園暫行教學(xué)綱要(草案)》還規(guī)定了幼兒園每周必修作業(yè)項目和時間(次數(shù)),闡述了各年齡段幼兒的年齡特點和教學(xué)要點,并按照體育、語言、認(rèn)識環(huán)境、圖畫手工、音樂、計算的分類,詳細規(guī)定了各科要達成的具體目標(biāo)、教材大綱、教學(xué)要點等。各級各類幼兒園必須根據(jù)規(guī)定嚴(yán)格實施,不能輕易變動計劃。
20世紀(jì)80年代初,在“文革”結(jié)束之后,幼兒園恢復(fù)了分科教學(xué)和分科課程模式。在當(dāng)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對幼兒教育迅速恢復(fù)并逐步走上正軌是有利的。1981年,教育部頒布了《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草案)》[以下簡稱《綱要》(1981)],將幼兒園的教育內(nèi)容分為生活衛(wèi)生習(xí)慣、體育活動、思想品德、語言、常識、計算、音樂、美術(shù)等八個方面,規(guī)定通過游戲、體育活動、上課、觀察、勞動、娛樂和日常生活等各種活動完成教育內(nèi)容。[26]
《綱要》(1981)特別強調(diào),只有上課才能完成《綱要》(1981)是錯誤的觀點,在日常教育工作中,要避免只注重上課,而忽視其他活動的錯誤傾向。[27]然而,在實踐中,由于改革開放初期,教師的專業(yè)素養(yǎng)普遍比較低,教師未能真正理解《綱要》(1981)指出的“通過多種手段進行教育”,亦未能認(rèn)識學(xué)前教育與小學(xué)教育的差別,因而存在注重“上課”,注重通過教學(xué)傳遞學(xué)科知識,而忽視游戲等其他教育形式的問題。在分科教學(xué)的模式下,幼兒園課程就是各門學(xué)科的教學(xué)計劃及其落實的進程。
(四)從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jì)初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帶來社會全面蓬勃發(fā)展的新氣象,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交流日益增多,國外先進的兒童教育思想、課程理論被引進和學(xué)習(xí)借鑒,陳鶴琴的單元課程思想被重新認(rèn)識和肯定。在新觀念醞釀成熟的同時,由于分科課程弊端的凸顯以及新時期教育發(fā)展方向的確立,學(xué)術(shù)界開始了對幼兒園課程問題的討論。在實踐領(lǐng)域,一些學(xué)前教育工作者也開始對幼兒園課程改革進行探索。
1989年頒布的《幼兒園工作規(guī)程(試行)》(簡稱《規(guī)程》)提出“幼兒園教育活動”的概念,強調(diào)它是“有目的、有計劃地引導(dǎo)幼兒主動活動的,多種形式的教育過程”,還規(guī)定幼兒園要“以游戲為基本活動”,“合理地綜合組織各方面的教育內(nèi)容,并滲透于幼兒一日生活的各項活動中,充分發(fā)揮各種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28]《規(guī)程》凸顯了幼兒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明確了幼兒園的課程內(nèi)容應(yīng)具有生活性、綜合性,課程實施的手段應(yīng)具有靈活性、多樣性。[29]
這一時期,諸多學(xué)者在總結(jié)過去經(jīng)驗教訓(xùn),借鑒國外先進理論的基礎(chǔ)上,重新思考“幼兒園課程是什么”的問題,產(chǎn)生了對課程定義的三種傾向:學(xué)科傾向、活動傾向和經(jīng)驗傾向。
學(xué)科傾向的課程定義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期較為普遍。進入20世紀(jì)90年代后,在整體教育觀的影響下,幼兒園課程不再被視作單一的學(xué)科,而更加強調(diào)學(xué)科間的聯(lián)系,模糊學(xué)科間的界限,增強教育內(nèi)容的整體性,將兩門或幾門學(xué)科綜合起來合并成一個領(lǐng)域。
活動傾向的課程定義認(rèn)為幼兒園課程是兒童主動的學(xué)習(xí)活動,活動是動態(tài)的、過程性的,因而是課程動態(tài)的過程。經(jīng)驗傾向的課程定義認(rèn)為,幼兒園課程是有益于兒童身心和諧發(fā)展的經(jīng)驗。經(jīng)驗傾向的課程定義,既關(guān)注獲得經(jīng)驗的過程即兒童的活動,同時也關(guān)注經(jīng)驗的結(jié)果——兒童在活動中所得到的經(jīng)驗。無論是活動傾向還是經(jīng)驗傾向的課程定義,均反映了課程觀念的轉(zhuǎn)向:從以傳遞知識為中心到以兒童為本位,從把課程看作靜態(tài)的知識、教學(xué)大綱、計劃到課程是動態(tài)的過程,課程內(nèi)容從單一、割裂到具有整體性、綜合性;從注重計劃、預(yù)成到具有靈活性、生成性。
(五)21世紀(jì)以來
2001年,教育部頒布《幼兒園教育指導(dǎo)綱要》[以下簡稱《綱要》(2001)],為我國幼兒教育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幼兒園課程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綱要》(2001)這樣闡釋幼兒園課程:幼兒園應(yīng)讓兒童在快樂的童年生活中,獲得有益于身心發(fā)展的經(jīng)驗;幼兒園的教育活動,是教師以多種形式有目的、有計劃地引導(dǎo)幼兒生動、活潑、主動活動的教育過程;教育活動的目標(biāo)設(shè)置、內(nèi)容選擇、組織實施,均要根據(jù)幼兒的發(fā)展水平、經(jīng)驗和需要來確定;幼兒園的教育內(nèi)容應(yīng)是全面的、啟蒙性的,各領(lǐng)域的內(nèi)容要有機聯(lián)系,相互滲透;教育活動的組織與實施過程是教師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的過程;教育活動的組織形式應(yīng)具有靈活性、彈性,應(yīng)注重綜合性、趣味性、活動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戲之中……[30]上述內(nèi)容彰顯和傳遞了兒童本位的課程價值取向。
在《綱要》(2001)的指引下,新一輪幼兒園課程改革強調(diào)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注重幼兒園課程的園本化、生活化、整體化、游戲化。新世紀(jì)以來,為了讓幼兒園課程真正成為兒童的課程,教育者們在實踐領(lǐng)域進行了多樣化的探索。
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開始,意大利瑞吉歐方案教學(xué)風(fēng)靡全球,我國學(xué)者開始陸續(xù)介紹方案教學(xué)理念。瑞吉歐方案教學(xué)秉持“兒童中心”的基本價值取向,認(rèn)為兒童是有著巨大潛能的主動學(xué)習(xí)者,教師應(yīng)尊重兒童、傾聽兒童,圍繞兒童的生活、興趣,選擇項目活動的主題,兒童圍繞主題進行各種自主探索活動。兒童有權(quán)決定項目的主題、活動方式等,教師則傾聽兒童,鼓勵兒童主動活動,用靈活的方式引導(dǎo)兒童,為兒童的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持。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介紹、討論并學(xué)習(xí)瑞吉歐方案教學(xué)。進入21世紀(jì)后,方案教學(xué)的相關(guān)課程理念——幼兒園課程具有“生成性”,應(yīng)“跟隨兒童”“傾聽兒童”,根據(jù)兒童的需要確定項目主題,教師為兒童創(chuàng)設(shè)環(huán)境、提供支持,促使兒童主動探究學(xué)習(xí)等——被我國幼兒教育領(lǐng)域廣泛地學(xué)習(xí)、借鑒并進行本土化的實踐探索。瑞吉歐方案教學(xué)對中國學(xué)前教育所產(chǎn)生的重大啟示和影響,在于兒童自身是學(xué)前教育中的重要資源,從而大大地提高了兒童在學(xué)前教育中的地位。
近年來,兒童游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是因為學(xué)前教育應(yīng)以兒童為本位,尊重兒童的人格和權(quán)利,遵循兒童的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和學(xué)習(xí)特點,而游戲不僅是兒童的興趣和需要,是兒童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權(quán)利,更是兒童的主要學(xué)習(xí)和生活方式,所以,“幼兒園應(yīng)以游戲為基本活動,保教并重,促進每個幼兒富有個性的發(fā)展”。[31]在《綱要》(2001)精神的指引下,課程與游戲的關(guān)系,游戲?qū)φn程的意義、作用和價值等問題成為探究的新熱點。
江蘇“幼兒園課程游戲化建設(shè)”項目和以“安吉游戲”為代表的游戲課程,二者的理念與實踐反映了幼兒教育領(lǐng)域?qū)Α坝變簣@課程應(yīng)具有游戲性”這一觀念的新理解。
“課程游戲化”不是一種新課程模式,而是一種新理念和實踐,它源于對我國學(xué)前教育政策的領(lǐng)悟和幼兒園課程實踐問題的反思,如過于依賴教師的講解、過于強調(diào)集體教學(xué)、過于在意教師用書、過于在意一致化行動等。[32]課程游戲化,并非將所有的活動都變成游戲,亦非在現(xiàn)有課程體系中增加游戲內(nèi)容或時間,[33]而是在課程中滲透自由、自主、愉悅、創(chuàng)造的游戲理念和精神,讓課程更加貼合幼兒成長與發(fā)展的規(guī)律,貼近幼兒的生活和實際需要,成為有趣的、有效的、生動活潑的、兒童主動活動的過程。[34]
安吉游戲從尊重兒童出發(fā),認(rèn)為兒童是有著無限潛能的主動學(xué)習(xí)者,自由自主地游戲是兒童主要的學(xué)習(xí)途徑與方式,兒童在游戲和生活中獲得對生命與世界的身心體驗。安吉幼兒園將“以游戲為基本活動”的理念貫徹在課程改革的歷程中,在一日生活的各環(huán)節(jié)滲透游戲精神,讓兒童在自由自主的游戲與生活中,獲得關(guān)于世界的整體經(jīng)驗和人格個性的完整發(fā)展。[35]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反思與實踐,安吉游戲課程成為一種公認(rèn)的新課程模式。
安吉游戲是處于基層、作為“草根”的安吉幼教人對中國學(xué)前課程的一次創(chuàng)造和推進,表明中國文化自身亦可以成長為具有中國氣派的優(yōu)秀學(xué)前課程模式。它將兒童視為學(xué)前教育的核心資源,把兒童放在學(xué)前教育的“中心位置”,充分地保障乃至大大地激發(fā)了兒童在游戲中的豐富的、創(chuàng)造性的自我表達。安吉游戲不僅受到國內(nèi)同行的關(guān)注與借鑒,還受到一些國際同行的肯定與贊揚。
瑞吉歐方案教學(xué)、安吉游戲以及幼教界人士的本土性探索,均聚焦于“對兒童的發(fā)現(xiàn)”,聚焦于提升兒童在學(xué)前教育中的位置。因此可以說,進入21世紀(jì)以來,中國學(xué)前課程的觀念和實踐已經(jīng)進入繁榮局面。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學(xué)前教育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對于基礎(chǔ)教育改革亦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幼兒園課程”概念變遷的歷史規(guī)律
(一)“幼兒園課程”概念既是時代精神的寫照,又豐富著時代精神
歷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一個核心概念的建構(gòu),往往是一套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一個時代尋找和提煉概念的過程,也是在提煉認(rèn)識和思想。”[36]幼兒園課程就是這樣的核心概念,它是學(xué)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概念。
幼兒園課程概念的變遷,反映了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以課程的概念為中心,學(xué)前教育思想變遷的過程。而學(xué)前教育思想變遷的過程是時代精神的寫照,亦豐富著時代精神。
清末民初,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幼兒園課程從政策文件到課程內(nèi)容,都是在照搬照抄的日本幼兒教育的基礎(chǔ)上,加入“忠君愛國、忠孝節(jié)義”等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內(nèi)容,在課程實施方面,采用傳統(tǒng)的灌輸式教學(xué),充分反映清政府“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方針,試圖通過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的教育制度,培養(yǎng)既能維護封建統(tǒng)治又能為“救亡圖存”做出貢獻的人才。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鶴琴、張雪門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xiàn)實出發(fā),認(rèn)為每一個人都擔(dān)負著“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爭取民族獨立,肅清封建殘余,建樹科學(xué)民主”[37]的歷史使命與任務(wù),而“今日這樣小的兒童,就是將來民族的一分子。我中華未來的主人翁生命上第一步的建設(shè),全在我們的掌握中”。[38]在陳鶴琴、張雪門等人的課程思想和實踐中,促進兒童發(fā)展與滿足社會的需要,幼兒園課程科學(xué)化與中國化是其關(guān)注的重點。幼兒園課程從尊重兒童出發(fā),以兒童的生活為基礎(chǔ),以大自然、社會為“活教材”,圍繞某個主題設(shè)計一系列相關(guān)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整體性、綜合性,通過各種活動,豐富兒童的生活經(jīng)驗,培養(yǎng)他們的民族精神,做“現(xiàn)代中國人”。
新中國成立后的分科課程既是全面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結(jié)果,也與我國以傳遞知識為核心目的的傳統(tǒng)教育觀相契合——教育的目的是培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接班人,分門別類地教各門學(xué)科的知識被認(rèn)為是實現(xiàn)教育目的最有效的手段。
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來,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在學(xué)習(xí)借鑒西方先進教育思想、幼兒園課程理論與實踐的基礎(chǔ)上,伴隨著兒童觀、教育觀的變遷,兒童在教育中地位的承認(rèn)和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基本價值取向的確立,“幼兒園課程”概念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課程關(guān)注的焦點從知識轉(zhuǎn)移到兒童身上,這充分反映了解放思想、“以人為本”的時代精神。
(二)“幼兒園課程”概念是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相互建構(gòu)的過程
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的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39]概念既是歷史變遷的反映,也是歷史變遷的工具。[40]幼兒園課程概念的變遷是幼兒園課程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相互建構(gòu)的過程。幼兒園課程的概念,根據(jù)其來源,可以分為官方(即學(xué)前教育政策中課程概念的表達)、學(xué)術(shù)界、實踐者的課程概念。幼兒園的實踐反映了最廣泛層面上,對課程概念的認(rèn)識、理解和接受程度。官方的、學(xué)術(shù)的課程概念最終要在實踐層面被認(rèn)識、理解和接受,才能被踐行。
1904年,《奏定蒙養(yǎng)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把幼兒園課程理解為“科目”“課目”“條目”,認(rèn)為“蒙養(yǎng)院保育之法,在就兒童最易通曉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漸次啟發(fā)、涵養(yǎng)之;與初等小學(xué)之授以學(xué)科者,迥然有別”。幼兒園課程是“科目”“課目”“條目”,而非“學(xué)科”。前者是對教育內(nèi)容的粗略分類,后者則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幼兒園課程包含游戲、手技等幼兒教育階段特有的內(nèi)容,在與其他教育內(nèi)容相區(qū)別時,它們不能按學(xué)科來劃分,而籠統(tǒng)地被稱為“科目”“課目”“條目”。如此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幼兒園課程較之其他教育階段課程的獨特性。張宗麟在《幼稚園的演變史》(1935)中摘錄了《奏定蒙養(yǎng)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認(rèn)為其“還有幾分合理”,但“法令規(guī)定如是,在事實上還談不到如是”。[41]在實踐中,幼兒園課程小學(xué)化的傾向嚴(yán)重。究其原因,學(xué)前教育政策文件是對日本1900年出版的《幼稚園保育及設(shè)備規(guī)程》的復(fù)制與模仿,其體現(xiàn)出的“有幾分合理”的觀念并未被實踐者理解和接受。
“以游戲為基本活動”觀念的落實也經(jīng)歷了較為漫長的過程。早在1989年,《幼兒園工作規(guī)程(試行)》規(guī)定,幼兒園要“以游戲為基本活動”,[42]把游戲規(guī)定為幼兒園的基本活動,順應(yīng)了兒童的特點和需要,尊重了兒童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體現(xiàn)了“以兒童為本位”的觀念。此時,學(xué)術(shù)界認(rèn)識與學(xué)前教育政策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實踐中,盡管有部分幼兒園,進行了課程改革的探索,但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幼兒園課程小學(xué)化傾向一直存在,“以游戲為基本活動”亦未得到很好地落實。直到近幾年,浙江安吉經(jīng)過十多年的探索反思,形成了成熟的“安吉游戲課程”模式,真正將1989年提出的幼兒園課程“應(yīng)以游戲為基本活動”的理念落實到實踐中。這表明,一個時代的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實踐者的課程概念可能存在差異,而實踐者的課程概念是一個時代能否落實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課程概念的關(guān)鍵。
(三)“幼兒園課程”概念的建構(gòu)有賴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
回溯“幼兒園課程”概念的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清末民初的“幼兒園課程”與傳統(tǒng)觀念一致,即課程就是分門別類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及單向傳遞學(xué)習(xí)內(nèi)容的進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幼兒園課程”概念,反映了陳鶴琴、張雪門等有識之士在尋求教育理論與實踐現(xiàn)代化、科學(xué)化、本土化過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分科課程追求統(tǒng)一、高效地傳遞知識,是全面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結(jié)果;改革開放以來,“幼兒園課程”概念的核心價值取向是以兒童為本位,“幼兒園課程”概念愈加豐富、多元。“幼兒園課程”概念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變遷的,社會文化背景對幼兒園課程概念的深化、發(fā)展起著或促進或限制的作用。
在高控制、高限制、高計劃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幼兒園課程”的概念相對單一,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實踐者的課程概念亦相對一致。如在分科課程模式下,幼兒園課程被理解為“教學(xué)計劃、學(xué)科、作業(yè)”。在實踐中,課程就是在一定的時間教給幼兒分門別類的學(xué)科知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了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而在開放的、寬松的、解放的、民主的社會背景中,“幼兒園課程”概念有了多元的表達。無論是政策文件本文中的描繪,還是學(xué)術(shù)界的理論探討,幼兒園課程被理解為是“以兒童為本位的”、促進兒童發(fā)展的、符合兒童生活和興趣的、適宜的、整體的、綜合的、生活化、游戲的、靈活的、有彈性的、生成的……在實踐中,涌現(xiàn)出多種課程模式,如游戲課程、生活課程、田野課程等。幼兒園課程概念越來越豐富,對幼兒園課程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入。由此可見,“幼兒園課程”概念的建構(gòu)有賴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
三、“幼兒園課程”概念變遷的歷史啟示
(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精神呼喚“以兒童為本位”的幼兒園課程
“幼兒園課程”概念及其在實踐中的體現(xiàn),是由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總體發(fā)展?fàn)顩r決定的,更由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時代精神決定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命題,指出要“辦好學(xué)前教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zhì)量的教育”。[43]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diào)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提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要站穩(wěn)人民立場”,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前進道路上,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44]“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精神,要求學(xué)前教育“以兒童為中心”;“公平而有質(zhì)量的學(xué)前教育”呼喚“以兒童為本位”學(xué)前課程——課程是教育的載體,“幼兒園課程”概念的落實決定教育的成效。要提高教育質(zhì)量,促進教育公平,就必須以兒童為本位,促進每一位兒童的成長與發(fā)展。
在“以兒童為本位”的基本價值取向的引領(lǐng)下,幼兒園課程必將向更“兒童”的方向發(fā)展:在當(dāng)前,幼兒園課程關(guān)注的核心是兒童,幼兒園課程最終是為了兒童的、屬于兒童、從兒童出發(fā)的。幼兒園課程要以兒童為基礎(chǔ),首先必須尊重和理解兒童,包括兒童的興趣與需要、兒童的精神與文化、兒童的生活與世界等。而兒童是復(fù)雜的、豐富的、鮮活的、流變的,因而較之傳遞知識,“以兒童為本位”的幼兒園課程具有復(fù)雜性、豐富性、靈活性和不確定性。
(二)重視實踐工作者“以兒童為本位”的課程概念的建構(gòu)
當(dāng)前,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幼兒園課程”概念充分彰顯了“以兒童為本位”的基本立場,但是在幼兒園實踐中,存在種種與“以兒童為本位”的課程概念相背離的現(xiàn)象,如幼兒園課程小學(xué)化、超前教育、課程超載等,產(chǎn)生問題的重要原因是實踐者持有的“幼兒園課程”概念存在偏差——幼兒園課程以傳遞知識為本位,課程是成人為兒童精心選擇和設(shè)計的、按照學(xué)科邏輯劃分的粗淺知識的集合。
觀念指導(dǎo)行為,錯誤的“幼兒園課程”概念,必然導(dǎo)向幼兒園課程錯誤的實踐。這表明:一方面,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課程概念表達了教育管理者和學(xué)術(shù)界對幼兒園課程的應(yīng)然狀態(tài)的認(rèn)識,它們會引領(lǐng)和影響實踐工作者的課程概念;另一方面,實踐工作者的課程概念直接影響幼兒園課程的落實,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課程概念,首先必須轉(zhuǎn)化為實踐工作者的課程概念,而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確保概念的落實。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實踐者的課程概念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過程,即幼兒園課程理論與實踐相互建構(gòu)的過程。這意味著要解決幼兒園課程的實踐問題,落實官方的、學(xué)術(shù)界的“以兒童為本位”的課程理念,就必須重視實踐者的“幼兒園課程”概念的建構(gòu)。
(三)“幼兒園課程”概念的發(fā)展與深化需要社會文化的支撐
歷史不是過去,而是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有意義的相互關(guān)系,具有開放的未來前景。[45]“幼兒園課程”概念的歷史告訴我們,“幼兒園課程”概念的進一步發(fā)展與深化需要更開放、更民主的社會環(huán)境的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社會、文化、經(jīng)濟大繁榮的背景中,我國學(xué)前教育理論和實踐出現(xiàn)了百花齊放的新局面,幼兒園課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課程模式上,從全國統(tǒng)一實施分科課程到形成百花齊放的課程模式;在課程目標(biāo)上,從以社會為本位到以兒童為本位;在課程內(nèi)容選擇上,從以知識為中心到以兒童的經(jīng)驗為中心;在課程組織實施上,從單一的集中授課到以游戲為基本活動,創(chuàng)造性地采用多種手段促進兒童發(fā)展……[46]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推進、思想文化的解放與繁榮是幼兒園課程發(fā)展的土壤,亦是幼兒園課程的發(fā)展進步,離不開社會環(huán)境的支持。
站在繼往開來、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新時代的起點上,學(xué)前教育質(zhì)量的提高有賴于高質(zhì)量的幼兒園課程,而幼兒園課程的進一步發(fā)展,有賴于社會提供更加完備的外部環(huán)境。
參考文獻:
[1]方維規(guī).關(guān)于概念史研究的幾種思考[J].史學(xué)理論研究,2020(02):151-156.
[2][3][36]方維規(guī).什么是概念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182,182,18.
[4]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xué)制演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93.
[5][9]中國學(xué)前教育史編寫組.中國學(xué)前教育史資料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03.
[6][10]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13,11.
[7][8]喻本伐,鄭剛.中國學(xué)前教育史料集成:第一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12-13,508.
[11]何曉夏、史靜寰.教會學(xué)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90.
[12][13][14][15]陳鶴琴.陳鶴琴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27,27,78,165.
[16][17][18][19][20][21][38]戴自俺.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M].北京: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24,178,339,126,343,474,1218-1219.
[22]王義高.蘇俄教育[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277.
[23]田正平,劉徽.課程理論研究六十年——基于概念史的研究[J].社會科學(xué)戰(zhàn),2009(11):9-15.
[24][25][28][42]中國學(xué)前教育研究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幼兒教育重要文獻匯編[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565,107,60-63,291.
[26][27]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草案)(1981年10月)[C]//中國學(xué)前教育研究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幼兒教育重要文獻匯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195,195.
[29]蔣雅俊.改革開放40年學(xué)前教育政策中的兒童觀變遷[J].學(xué)前教育研究,2019(03):12-20.
[30][31]幼兒園教育指導(dǎo)綱要(試行)(2001)[EB/OL].(2001-07-02)[2023-05-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0107/t20010702_81984.html.
[32]虞永平,張帥.從模仿借鑒到規(guī)范創(chuàng)新——新中國成立70年來幼兒園課程的發(fā)展[J].南京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06):34-48.
[33]邱學(xué)青,高妙.傳承與超越:從教學(xué)游戲化到課程游戲化[J].學(xué)前教育研究,2021(04):3-10.
[34]虞永平.課程游戲化的意義和實施路徑[J].早期教育(教師版),2015(03):4-7.
[35]程學(xué)琴.放手游戲 發(fā)現(xiàn)兒童[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19,27.
[37]陳鶴琴.陳鶴琴全集:第五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60.
[39]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M].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303.
[40]TIMO PANKAKOSKI. Conflict, context, concreteness: Koselleck and Schmitt on concepts[J]. Political Theory,2010,38(6):749-779.
[41]張宗麟.幼稚園的演變史[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27-28.
[43]習(xí)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
[44]習(xí)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jié)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2-10-25)[2023-03-14].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45]J?RN R?SEN. The horizon of history moved by modernity[J]. History and Theory,2021,60(4):74-81.
[46]蔣雅俊.新中國成立70年幼兒園課程的歷史變遷[J].課程·教材·教法,2019(16):48-55.
A Study on Conceptual History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China
JIANG Yajun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mong the official and the academic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areas has undergone the following changes: the goal of the curriculum has changed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has changed from mutual isolation and discipline to integration, wholeness and life?orientednes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ranges from indoctrination to play?based activities as well as creatively employ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he curriculum is developed from high pre?completion, high planning to kindergarten?based, personalized, and with generation and flexibility. The change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concept is a process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nstru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Official, academic curriculum concepts must ultimately be recognized and understoo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before they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ld?centeredness”, 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will surely develop in a more “child” direction.
Key word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conceptual history
(責(zé)任編輯:劉向輝)
*通信作者:蔣雅俊,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部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