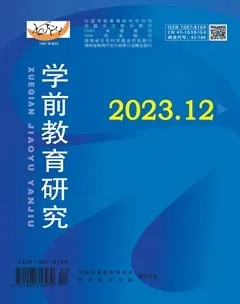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需求分析
孫曉軻 高雯吳鈺 朱爽爽 王曉旭



[摘 要] 提高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質量是當前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提升社會的生育意愿,就需要做好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持工作。當前我國農村地區0~3歲嬰幼兒照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還不完善,社會各界對農村家長的照護需求缺乏必要的關注和了解。本研究通過半結構化訪談對河南、江蘇、安徽三省33位農村0~3歲嬰幼兒家長的照護需求進行調查發現,農村家庭0~3歲嬰幼兒照護的支持需求主要體現在嬰幼兒養育支持、教育支持和條件性支持三個方面。進一步研究發現,農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對經濟、家長教育、心理健康、再就業等方面的條件性支持的需求更為強烈,對家庭內部的協同照護、鄰里支持等非正式支持更為偏愛,同時對心理健康的支持也有明顯的需求。為提升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質量,促進嬰幼兒身心健康協調以及家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強農村嬰幼兒照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引導婦聯、學校等社團組織和專業機構積極參與農村嬰幼兒照護服務,強化新型農村鄰里互助組織和互助文化建設。
[關鍵詞] 農村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照護支持需求
一、問題提出
家庭是支撐嬰幼兒生存與發展的首要環境。尤其在中國,傳統的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方式使得家庭在嬰幼兒照護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1]但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沖擊下,家庭在嬰幼兒照護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工作、經濟、社會競爭等方面的多重壓力。嬰幼兒時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家長在照料過程中經常會面臨睡眠不足、育兒技能缺乏、家庭關系緊張等問題的挑戰。當在照護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支持時,長時間的壓力就可能導致嬰幼兒家長出現心理健康問題,會使他們在嬰幼兒照料過程中變得更容易發怒和缺乏耐心。[2]而這種非常態的照護可能會影響嬰幼兒健康依戀關系的形成,并導致嬰幼兒各種行為問題的發生。[3]此外,家庭在獲取嬰幼兒照護資源方面遭遇的難度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育決策。當獲得高質量的嬰幼兒照護資源支持時,家庭更有可能決定再次生育。[4]反之,他們的幸福感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其生育意愿。[5]因此,給予嬰幼兒家庭必要的照護支持十分重要。
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是指在行為、認知、情感等多個方面為嬰幼兒撫養者及照料者提供適宜的幫助和指導,以緩解他們在養育過程中出現的無助感及其他照護壓力,從而使其更好地投入嬰幼兒照護及家庭生活。[6]其目的是更好地維護嬰幼兒生存環境,促進嬰幼兒身心健康發展,增強家庭養育的能力和韌性。這種支持可以來自社區、政府和社會,其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支持、經濟援助和早期干預服務等方面。[7]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需求因各自的經濟、家庭結構、文化背景等因素而異。低收入家庭往往更多地需要經濟援助、附加的醫療服務和教育資源,以滿足嬰幼兒的生存需要。相比之下,高收入家庭可能會尋求更多高質量的教育資源。[8]二胎、三胎家庭和獨生子女家庭在嬰幼兒照護的支持需求方面也存在差異,多胎家庭往往需要更集中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來安置和照顧孩子,更需要社區、鄰里或托育機構的幫助。[9]獨生子女家庭則更需要為孩子提供個性化的照護服務。[10]此外,文化水平較高的家長不只關心嬰幼兒的基礎安全、營養和健康照護,還重視優質早期教育機會和資源的獲得。[11][12]
相比城市家庭,農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方面面臨著更多問題,擔負著更大壓力。[13]一方面,農村家庭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為了滿足家庭生存需要,不少嬰幼兒父母進城務工,導致隔代教養現象普遍存在,祖輩在嬰幼兒的照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4]另一方面,我國農村嬰幼兒公共照護體系建設還不完善,在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面給予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持不多,嬰幼兒照護責任主要還是由農村家庭自身來承擔。[15]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需求未能得到合理的關注和有效滿足。在全面開放三孩政策的大背景下,關注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需求,為農村家庭提供有效的嬰幼兒照護支持,不僅是促進農村嬰幼兒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提升農村家庭生育意愿和育兒體驗的內在要求。當前學界對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支持關注不多,對于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需求的內在結構和具體內容還不十分清楚。厘清農村家庭0~3歲嬰幼兒照護需求并給予農村嬰幼兒家長合理的支持,不僅可以有效緩解農村家長的照護壓力,為農村嬰幼兒身心的健康成長創設良好的環境,還可以為政府建構農村嬰幼兒照護支持服務體系提供事實依據與方向,提升農村家庭的生育意愿,促進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訪談法探索農村家庭在0~3歲嬰幼兒照護方面的需求。研究圍繞農村家庭0~3歲嬰幼兒照護需求設定一系列開放式問題。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受訪者的家庭與養育情況、嬰幼兒照護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難、嬰幼兒照料與教育方面的需求、嬰幼兒照護公共服務享受情況等。為了更好地接近家長的真實想法,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針對每位受訪者的具體情況對提問內容進行了適當的調整,以便盡可能地全面挖掘農村嬰幼兒家長在照護過程中的支持需求。訪談時間為2022年7月8日至2023年2月1日,采用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每次訪談時長約40分鐘。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于方便取樣的原則,選擇了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的農村及城鄉接合部的33位0~3歲嬰幼兒家長為研究對象,具體分布為河南6個村、13人,江蘇4個村、9人,安徽4個村、11人。本研究將受訪者的篩選原則設置為:(1)在農村居住,有照護0~3歲嬰幼兒的經驗;(2)家長年齡、性別及職業具有一定跨度,以區分不同群體的家庭支持需求差異。(見表1)訪談完成后,研究將訪談錄音轉換成文字,共獲得96 855字的文本資料。研究隨機抽取30個樣本用于分析,留存3個樣本用于飽和度檢驗。
(三)數據處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中的程序化扎根理論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扎根理論又稱根基理論,是一種以質性研究為手段,通過有系統地收集和分析資料的研究歷程,從資料中衍生出理論的方法。[16]它最早于1967年由社會學家巴尼·格雷澤(Glaser)和安塞爾姆·施特勞斯(Strauss)提出,主要用于探究人們的行動和經驗背后的基本概念和關系。扎根理論流派有經典扎根理論、程序化扎根理論、建構型扎根理論三個流派,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論的三階段分析法,通過開放式登錄、關聯式登錄和核心式登錄三段程序,[17]對資料和數據進行不斷濃縮、歸納和分析,產生概念、范疇或關系并進行比較,直至達到理論飽和,最終提取出模式和關系,發展出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需求模型。
1. 開放編碼。
在開放編碼階段,研究對訪談資料進行了細致分解,利用Nvivo 12軟件進行記憶和反思,通過提問和比較完成文本資料的初步篩選。在這一過程中,研究發現并命名各種概念類別的屬性,并將其概念化。具體而言,本研究首先標記了與需求模型建構相關的390條原始語句,并在簡化和提煉后進行標簽貼附,尋找最合適的詞語加以命名和概念化(譯碼前綴為“A”)。(見表2)
2. 主軸編碼與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的主要目的是在所有已發現概念類屬中經過系統分析后選擇一個核心類屬,即分析各節點間的內在聯系。[18]在初步概念化之后,本研究共獲取嬰幼兒疾病防控、成長發育身體檢查與評估等59個初始概念。研究進一步對初始概念進行整合和序列化,形成了預防性健康護理、身心發育評估、食品與營養支持等17個初始范疇(譯碼前綴為“B”)。
選擇性編碼的主要任務是系統處理開放性編碼和關聯式編碼已發現的范疇之間的關系,選擇核心范疇和次要范疇。[19]通過對前期提煉出的17個具體范疇進行深度分析,本研究提煉出了7個主要范疇,具體包括嬰幼兒健康支持需求、嬰幼兒安全支持需求、嬰幼兒教育支持需求、經濟支持需求、家長教育支持需求、社交支持需求和心理健康支持需求。這些主要范疇從初始范疇中涌現,構建出一個概念網絡。(見表3)
3. 飽和度檢驗。
為檢驗資料分析是否完善,本研究利用剩下的3份訪談資料進行飽和度檢驗。按照三級編碼方式進行分析后,研究未發現新的概念與范疇,表明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已經飽和。研究進一步將編碼結果提交給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研討,亦未提出新的概念和范疇,表明本研究經過三級編碼得出的概念和范疇已經飽和。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圍繞三級編碼得出的7個主范疇進行分析,發現這7個主范疇可以劃分為3個不同的維度,且它們之間形成了特定的邏輯關系。其中由嬰幼兒健康支持需求和嬰幼兒安全支持需求構成的嬰幼兒生存支持需求是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的基礎性需求,其目標是確保嬰幼兒在成長過程中得到最基礎的照護和關心。嬰幼兒發展支持需求是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的進階性需求,它著眼于如何將嬰幼兒培養成有一個有情感、智力和社交能力的社會性個體。由經濟支持需求、家長教育支持需求、社交支持需求、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構成的嬰幼兒家庭照護條件性支持需求是滿足農村0~3歲嬰幼兒家庭照護的支撐性需求,涉及家庭在照護嬰幼兒時在各種具體情境下不同方面的需求,它是嬰幼兒實現健康成長的外在條件保障。以上三個維度形成了一個由宏觀到微觀的層次結構,共同構建了一個全面的農村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需求體系。(見圖1)
(一)嬰幼兒生存支持需求是家庭支持的基礎性需求
0~3歲是嬰幼兒生命中最為關鍵的成長時期,此時的他們還非常柔弱,其免疫系統發展尚不完善,更容易受到感染性疾病的侵襲,因此需要更多的護理和照顧。[20]在這一時期確保嬰幼兒的身體健康和營養對于其后續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發展十分重要。本研究顯示,不論調查對象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如何,農村家長首先關心的是嬰幼兒的醫療和營養問題,他們普遍期望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為孩子提供健康的成長環境,尤其是如何保證嬰幼兒的身體正常發育以及預防和應對嬰幼兒常見疾病成了家庭的首要關切。此外,農村家長強烈關注孩子的營養攝入與食品選擇,渴望從權威機構或專家那里獲得科學、實用的營養補充建議,其科學喂養意識有了很大的提升。
進一步分析發現,農村家庭的經濟狀況對其嬰幼兒生存支持需求有重要影響。對于那些經濟條件相對受限的家庭而言,由于難以負擔常規醫療檢查或在疾病爆發時及時獲得醫療援助,他們更加依賴公共醫療,以期獲得低成本甚至免費的醫療服務。這類家庭往往難以為嬰幼兒提供高質量和均衡的飲食,他們更多地依賴本地的食材和傳統的輔食制備方式,因此他們希望獲得政府提供的食品援助。“孩子從出生到現在,也沒吃過品牌的配方奶粉,舍不得買。輔食的話主要是喂孩子一些自制米糊或蔬菜泥,營養成分可能不夠全面。如果政府能夠提供一些高質量的嬰幼兒食品,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幫助!”(N10)與此相反,擁有較高家庭年收入的農村家庭往往更重視嬰幼兒的預防性健康護理,[21]并傾向于尋求專業的營養咨詢,[22]以確保孩子的健康發展。“像我工作穩定,經濟壓力也不大。我最擔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比如什么時候補充輔食,怎樣補充輔食才更合理,孩子吃哪些東西能起到最好的補充蛋白質、鈣的效果。”(N11)與此同時,這些家庭也會因頻繁的外出活動和社交而對公共母嬰設施有較高需求。[23]
在嬰幼兒安全維護方面,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和信息的流通,家庭對嬰幼兒安全的關注不再僅限于基本的物理安全,還涉及更為深入的社交和心理層面。隨著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家長們對嬰幼兒的心理安全問題更為敏感。然而,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尚淺,需求并不明確。相對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家長則更為期待增加嬰幼兒心理健康和早期干預服務。
(二)嬰幼兒發展支持需求是家庭支持的進階性需求
早期學習經驗對嬰幼兒的未來發展有重要意義,[24]此階段不僅要滿足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還要注重其認知、情感和社會性的發展。為家庭提供教育支持對于嬰幼兒的長期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農村地區。[25]與傳統農村家庭相比,現代農村家庭普遍更加重視對嬰幼兒的教育。研究普遍顯示,受收入增長、文化轉型和先進教育理念的影響,農村家長對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已經明顯上升,并且愿意為此投入更多的資源。[26]與此同時,農村家庭對高質量早期教育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長。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他們對孩子的早期教育有更高的期望,也希望得到更好的支持和服務。此外,農村家庭的教育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尤其是對于女孩的教育。[27]
研究顯示,農村家庭展現出了教育支持方面多元化的需求。首先,農村家庭對托育服務的需求包括全日制、半日制、臨時、緊急和過渡時期等不同形式,[28]農村家長需要靈活的選擇來適應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其次,受訪者對托育機構提供的課程資源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嬰幼兒的語言發展是家長最為關注的,好的語言環境可以提供更多的語言學習機會,但農村家庭往往缺少這樣的環境。在本研究中,部分家長更傾向于選擇那些可以提供全面發展機會的托育機構,有的家長開始認識到英語和科學技術對嬰幼兒的價值,并希望將其納入托育課程。再者,家長往往傾向于優先選擇那些有較好師資力量和學習環境的機構,即使面臨經濟壓力,許多家庭仍然強烈期望孩子獲得高質量的教育。此外,在家園合作方面,農村家庭盡管面臨諸如資源有限和遠距離交通等問題,但他們對學前教育的參與需求同樣強烈。[29]最后,服務費用仍是受訪者關切的重要問題之一。雖然家長都希望為孩子提供高質量的教育,但經濟壓力可能導致他們在教育質量和費用之間做出權衡。[30]對于多子女家庭來說,有限的經濟資源會限制他們在選擇托育服務時的空間,他們更關心如何在有限的預算內為孩子找到合適的托育場所。[31]但務農或務工家庭更注重托育服務的便利性和實用性,傾向于尋找能夠滿足其平衡工作時間和孩子照顧需求的托育服務,而不僅僅是教育質量,他們希望在工作和照顧孩子間找到平衡。
此外,還有部分農村家庭開始關注城鄉托育服務的優質均衡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農村家長對于城市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這種認知讓他們對城鄉間的教育差異有了更為深切的體驗,從而產生了對自己孩子未來是否能夠與城市孩子公平競爭的擔憂。他們期望政府和相關部門能夠更加注重這一問題,投入更多資源,努力縮小這種差距。如有家長就提出:“托育機構要像城里一樣,有一定的部門去監管,比如每個班里都能安裝監控,好讓家長了解孩子在托育機構的狀態。盡量要像城里一樣有多種模式的托育服務,像家庭式托育服務、普惠性托育服務,農村都很少。農村基本都是民辦的,收費相對較高一些,對年輕家長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N18)以上需求表明,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家長自身認識的不斷提高,農村家長對嬰幼兒的教養已經不再是養而不教,他們不僅關注嬰幼兒身體和心理的健全發育,同時也更為關注嬰幼兒在能力、個性品質等方面的成長,即他們對自己的子女有更高的發展期望。
(三)條件性支持需求是滿足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撐性需求
本研究顯示,農村嬰幼兒家庭在照護上最大的支持需求為條件性支持,這一部分條目占比最大。所謂條件性支持需求是指農村家庭為滿足嬰幼兒保教以及維系家庭自身可持續運轉而產生的對各種條件的需求,它既包含直接的經濟支持需求,也包含家長教育支持需求,還包含心理健康支持需求。這表明農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的條件基礎還較為薄弱。
家庭經濟條件、照護者的職業背景和家庭結構深刻影響著家庭對經濟支持的需求程度。首先,低收入家庭面臨的經濟壓力使他們更期望獲得更多的補貼,這種補貼既包含直接的經濟補貼,也包含營養、醫療等方面的專項補貼。“主要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壓力吧,現在養一個孩子太難了,生病了去醫院沒個幾百塊錢根本打不住。”(N21)反觀高收入家庭,因為擁有更好的經濟儲備,他們對外部的經濟支持需求度就更低。其次,職業背景決定了照護者對經濟支持的具體需求。由于工作不穩定,靈活就業或從事體力勞動的父母,往往對脫產照護孩子的補貼和其他形式的直接經濟支持有更大的需求。最后,家庭結構也是決定經濟支持需求的關鍵因素。隔代教養家庭和二胎且母親是全職主婦的家庭,往往更加依賴各類補貼和優惠,如祖輩照料補貼、生育補貼和托育補貼等。
家庭結構和育兒觀念的多樣化使不同家庭對家長教育的需求產生了差異。研究顯示,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或者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長對家長教育的需求程度普遍相對較高。這一部分家長希望能夠為自己的子女提供個性化的教育,因而對嬰幼兒語言發展指導、社會技能培育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我國農村還存在較大數量的留守兒童,祖輩是這一部分嬰幼兒的主要照護者。這一部分家長群體的育兒理念比較落后,育兒知識和技能比較匱乏,因此他們在育兒過程中對育兒理念、育兒方法指導等方面的需求就表現得更為強烈。
經濟狀況不僅影響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的物質條件配備,同時還影響著他們從其他社會群體獲取各種照護支持的能力。[32]經濟狀況更好的家庭更可能參與各種社會交往活動,并從中獲得信息、情感等方面的支持。[33]在本研究中,那些經濟相對更為困難的家庭更多地從實際需求出發,希望獲得家庭緊急應對服務以及就業指導和技能培訓,這充分體現了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為支持嬰幼兒生存與發展和維系家庭可持續發展而產生的內在張力,即促進農村嬰幼兒健康發展需要以相應的物質條件為支撐,物質條件的缺位會影響農村嬰幼兒身心健康發展需要的滿足。除經濟支持外,農村家長對各種靈活且充滿人文關懷的鄰里照護、鄰里與家庭情感支持等的需要都表現得十分迫切,適當的臨時看護和情感支持可以極大提升農村家長的照護和育兒體驗。“我們家是村里出了名的低保戶,現在的鄰居、親戚們眼里只有有錢人,我們這么窮別人根本不想看見,讓他們臨時幫忙照顧孩子太難了。如果能像以前那樣,有那種鄰里間互助式照護就好了。”(N4)但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那些具備一定身份或者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家長,如教師、村干部等,他們能夠更明確地表達自己的心理支持需求,而對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或者年紀較大的家長,則在一定程度上難以識別并表達自身在照護過程中的心理需求,造成了他們照護的無意識狀態或者內耗心理。
四、討論
(一)農村家庭對嬰幼兒照護中的條件性支持更為迫切
嬰幼兒的照護是一個兼顧嬰幼兒身心健康發展與家庭可持續發展的雙重過程,其中前者目標的有效達成有賴于后者的有效發展,農村家庭在經濟狀況、信息獲取、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改善可以極大地提升對嬰幼兒身心發展的促進水平。研究認為,經濟壓力通常是農村家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當家長能夠獲得有效的經濟支持時,其物質壓力的緩解可以使他們更好地支持嬰幼兒的發展。[34]教育指導則可顯著提高家長的照護和教養能力,減少兒童的行為和情感問題,并增強家長與兒童之間的關系。[35]社交支持可以作為家長育兒技能發展的重要資源,與外部社交網絡的聯系可以幫助家長更好地照顧嬰幼兒。[36]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對嬰幼兒發展有重要價值,當家庭成員獲得適當的心理支持時,他們更有可能為孩子提供一個穩定、積極的生存和發展環境。[37]在本研究中,農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對各種條件性支持表現得十分迫切,這進一步凸顯了農村家庭自身照護條件以及外部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問題。要進一步改善農村嬰幼兒的生存與發展狀況,以及提升農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照護體驗,就必須正視農村家庭的養育條件和養育環境問題。
在外出務工、鄉村振興等多種途徑的支撐下,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所享有的服務已得到極大的提升,農村家庭的生存與發展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嬰幼兒父母為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外出務工而導致的隔代教養、教養能力不足等問題仍普遍存在,農村嬰幼兒照護公共服務體系尚未有效建立、新型農村社會形態尚未發育完善等也影響著農村家庭外部嬰幼兒照護資源的獲取。一方面,得益于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家庭通常具備較為充裕的經濟資源,可以為嬰幼兒提供更為優質的生活、醫療和保教服務。但農村家庭多需要通過外出務工的方式來獲得經濟收入,這種方式具有穩定性低、流動性大等特點,收入難以保障,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農村家庭就難以為自己的孩子儲備充足的資源以供他們進一步改善生存和發展條件,因而當他們有更高的照護期望時,他們就期望從政府那里獲得諸如生育津貼、醫療補貼等公共服務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輕一代農村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育兒觀念的改善使得他們更關注自身在嬰幼兒教育方面支持的獲得。研究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兒童的健康和發展有密切關系,母親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兒童的營養狀況和免疫接種率都更高,[38]這樣的家庭更有可能為孩子提供一個有益的成長環境。[39]相對的,農村家長由于教育水平不足,遇到了更多的養育和教育挑戰,這種挑戰進一步轉化成了家長優化自身教養能力的動力。
與此同時,農村家長養育期望提升、信息鴻溝的縮小與農村嬰幼兒照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滯后之間的落差也提升了農村家長對各種外部支持的預期。由于地理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農村包含嬰幼兒照護在內的諸多社會公共服務建設都較為滯后,農村嬰幼兒照護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性都明顯低于城市。[40]盡管當前有關政策無差別地為所有家庭在生育和養育子女的過程中設置了多樣化的時間支持、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公益性育兒指導、育兒補貼、購房優惠等服務,但這些政策對農村家庭的適應性并不高。[41][42][43]此外,當前我國農村家庭也十分重視嬰幼兒的教育問題,其觀念和訴求已不再是養而不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指出,盡管許多國家都在努力提高農村的教育質量,但由于在資源分配、師資力量和設施條件等方面配置不足,農村學生所能享有的教育機會和能夠獲得的教育質量仍存在不足。[44]在嬰幼兒保教領域,當前我國的保教資源供給還不充足,有限的資源被優先滿足城市家庭和上層家庭,農村地區缺乏相應的托兒所、早教中心等教育資源,或者僅有的保教機構在師資、設備等方面的配置都處于低水平,公共托育服務不僅可及性和普惠性低,質量也不高。[45]這種高期望值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滯后之間的落差自然強化了農村家長對外部條件支持的預期,期望政府能夠為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提供時間、經濟、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的支持,他們期望與城市家庭獲得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持。
(二)農村家庭對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支持更為偏愛
盡管現代化和城市化正在快速地改變中國的家庭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子女的養育不僅是家事,也是國事。在農村地區,非正式的鄰里互助和社交關系仍是農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尋求的重要外部資源,鄰居、親戚等群體通常在農村嬰幼兒照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46]農村地區的居民之所以更傾向于依賴非正式的社會支持,這與其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資本特性有密切關聯。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社會資本是建立在相互認識和相互承認的基礎之上的,它強調的是社交關系和網絡的重要性。[47]在農村地區,社會資本的這種特性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農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長期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而固定的生活空間必然會強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從而形成比較穩定且相互信賴、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農村個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相互支持的心理基礎。農村地區的人際關系是基于群體信任的,當家庭內部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無法為家庭的嬰幼兒照護提供時間、場地和物質等方面的支持時,農村家庭就更傾向于尋求熟人的幫助,而這種幫助又不僅限于時間和物質條件等方面,它還為農村家長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的心理舒緩、情緒表達提供了一個適切的出口,使家長獲得心理和情感上的寬慰和支持。此外,農村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缺失進一步強化了農村家庭對非正式支持的需求。馬克·格蘭諾維特爾(Mark Granovette)的“弱聯系理論”認為,有些聯系在結構上可能顯得弱,但它們在提供支持和資源方面可能非常強。[48]在農村地區,居民往往具有較強的凝聚力,盡管鄰里照護或者親戚照護不能解決農村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的一些長期性、根本性問題,但其獲得的便利性可以很好地緩解農村家長的即時照護壓力。當正式的支持無法很好地解決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問題時,非正式的支持就成了農村家庭重要的尋求對象。
(三)農村家庭對心理健康支持的需求非常強烈
受限于農村地區獨特的生活環境以及嬰幼兒照護資源不足的現狀,照護者不僅身體上要承擔繁重的工作,同時在心理上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不確定性。有研究顯示,農村地區嬰幼兒的照護者抑郁癥的占比為13%~21%。[49]在農村地區,家庭在嬰幼兒照護中常因經濟壓力和社會環境壓力而承受不斷加劇的心理負擔。這種壓力并非來源于某一個方面,而是多重壓力的綜合效應。例如,農業生計的不確定性,不僅帶來經濟壓力,也影響了家長對未來的信心和穩定性。[50]農村地區教育和職業機會的缺乏使得家長對孩子的未來發展持有更大的期望,同時也對其產生更大的擔憂。[51]這種累計的壓力不只加重了照護者的精神負荷,還會對孩子的早期教育和發展構成障礙。
農村地區嬰幼兒照護者往往會因為育兒協作關系網絡的不健全而面臨著顯著的心理壓力。一方面,農村隔代教養家庭相對普遍,代際沖突比較突出。祖父母或其他長輩經常是嬰幼兒的主要照護者,他們既要處理家庭中的各種瑣事,還要扮演孫輩父母的角色,在照料他們飲食起居的同時還要擔負起教育責任,但文化水平不高、身體狀況差、孩子難管教等問題使得祖輩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面臨著持續的心理負擔。[52]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許多過去被認為是有效的育兒觀念和育兒方法現已被認為不科學,這些問題都加重了祖輩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由于父親的參與相對較少,母親作為嬰幼兒的主要照護者,常常處于一個相對無助的位置。在農村的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問題往往不被視為真正的健康問題,而被看作是小事或無大礙的煩躁情緒,這種認知會導致照護者心理健康被忽視或誤解。例如,產后的母親可能會經歷抑郁或焦慮,但這些情緒往往被視為產后常態而非真正的心理健康問題,從而得不到關注,導致她們的需求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解決。有研究發現,長時間的母親抑郁癥狀與嬰兒發育遲緩有關,抑郁狀態的母親在與嬰幼兒互動中會表現出“無反應照護”,[53]進而對嬰幼兒早期認知和社會情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面對農村家長在嬰幼兒照護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和心理支持需求問題,我們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改善這一局面。
五、建議
第一,政府要積極推進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在滿足農村嬰幼兒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同時,支持農村家庭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為農村嬰幼兒的健康檢查、身體發育評估、食品與安全提供設施、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以保障各項嬰幼兒照護支持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性;要加大對農村地區托育資源的供給,通過在公辦幼兒園內設置普惠性托育中心等方式來為農村家庭提供托育服務,并為貧困或者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相應的補貼或者其他福利支持。另一方面,政府要關注照護者養育技能的提升以及心理狀態的改善,有針對性地為農村家長提供嬰幼兒身體發育、心理發展、健康診斷、營養供給、教育等方面的宣傳或講座,不斷優化農村家長的育兒觀念和教養能力;通過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為農村家長提供心理咨詢服務,緩解他們在照護過程中的心理壓力;通過完善就業服務體系為農村家長提供就業方面的信息和政策支持,促進嬰幼兒家長,尤其是母親的再就業。
第二,鼓勵并引導婦聯、保健院等社團及專業組織參與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服務。農村0~3歲嬰幼兒照護家庭支持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具有政策性、系統性等特征,其建設和完善需要以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為依托,對農村家庭的滿足可能存在滯后性。對此,為強化對農村家庭的支持水平,政府在積極建構農村嬰幼兒照護公共服務體系的同時,也可以發動各級婦聯、婦幼保健院、各級各類學校等社團或專業組織,為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提供政策咨詢、知識普及和方法培訓,讓農村家庭獲得醫療、教育、心理咨詢、就業等方面的專業服務。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政策支持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工作,對積極參與農村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機構提供資金支持,給予稅收減免,優先選擇他們作為參與公共服務項目的合作伙伴。例如,政府可以鼓勵各類專業的醫療或教育機構參與農村嬰幼兒的早期教育活動,為農村嬰幼兒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的教育支持。
第三,推動鄰里社群組織與文化建設,加強對嬰幼兒照護者的心理與情感支持。鄰里關系和社區互助不僅是社交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還可為家長提供育兒支持,在其心理健康方面起到積極的緩沖作用。[54]為強化對農村嬰幼兒家長的心理和情感支持,村一級的群眾自治組織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組織身份,關注農村家庭的嬰幼兒照護情況,為家長提供各種嬰幼兒照護和教育服務,提升家長的照護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可以積極培育新型嬰幼兒照護組織和鄰里互助文化,鼓勵村民積極參與同村居民嬰幼兒的照護,通過提供臨時看護、經驗分享、心理疏導等方式來支持嬰幼兒照護工作,提升嬰幼兒家長的心理健康水平。
參考文獻:
[1]蔡迎旗,陳志其.家庭視域下我國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發展脈絡及其政策重構[J].中國教育學刊,2021(02):52-56.
[2]CRNIC K A, GAZE C, HOFFMAN C. Cumulative parenting stress across the preschool period: relations to m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 behaviour at age 5[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2005,14(2):117-132.
[3]ZEANAH C H, GLEASON M M. Annual research review: attachment disorders in early childhood clinical presentation, causes, correlates, and treatment[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2015,56(3):207-222.
[4]RINDFUSS R R, GUILKEY D K, KRAVDAL S P M.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fertility in norwa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0,36(4):725-748.
[5]BILLARI F C, PHILIPOV D, TESTA M R. Attitudes,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explain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bulgaria[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09,25(4):439-465.
[6]HOAGWOOD K E, CAVALERI M A, OLIN S S, et al. Family support i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 review and synthesis[J].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2010,13(1):1-45.
[7]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189-266.
[8]BRADLEY R H, CORWYN R 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2,53(1):371-399.
[9]CRAIG L, MULLAN K. How mothers and fathers share childcare: a cross?national time?use comparis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1,76(6):834-861.
[10]FALBO T, POSTON D L. The academic,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outcomes of only children in china[J]. Child Development,1993,64(1):18-35.
[11]尹春嵐,奚翔云,童梅玲,等.嬰幼兒家庭養育照護指導需求分析[J].中國兒童保健雜志,2023,31(1):32-36.
[12]王晶,童梅玲.嬰幼兒養育照護的框架和策略[J].中國兒童保健雜志,2020,28(9):993-996+1004.
[13]洪秀敏,朱文婷,陶鑫萌.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的家庭支持需求及群體差異——基于Kano模型的構建與分析[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151-160.
[14]鐘曉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議題轉換:從養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產家庭的隔代撫養與兒童照顧[J].探索與爭鳴,2017(07):81-87+96.
[15]張樂天.農村教育發展的支持政策:成效與問題[J].教育發展研究,2008(11):1-4.
[16]劉瑞瑞.師范生班級管理課程對其班級管理行為和班級管理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效果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9:29-30.
[17]程曉.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整合過程中機構間合作意愿影響因素研究[D].南昌:南昌大學,2020:14.
[18]周文輝.知識服務、價值共創與創新績效——基于扎根理論的多案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5,33(4):567-573+626.
[19]曾韋蜻,劉敏榕,陳振標.基于扎根理論的大學生創客服務需求模型構建及驗證[J].圖書情報工作,2019,63(15):68-76.
[20]LIU L, JOHNSON H L, COUSENS S,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auses of child mortality: an updated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2010 with time trends since 2000[J]. The Lancet,2012,379(9832):2151-2161.
[21]STARFIELD B, SHI L. The medical home, access to care, and insurance: a review of evidence[J]. Pediatrics,2004,113(5 Suppl):1493-1498.
[22]DARMON N, DREWNOWSKI A. Does social class predict diet qua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2008,87(5):1107-1117.
[23]EVANS G W, KANTROWITZ 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potenti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risk exposure[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2002,23(1):303-331.
[24]SHONKOFF J P, PHILLIPS D A.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M]. 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10-28.
[25]BLACK M M, WALKER S P, FERNALD L C H,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ming of age: science through the life course[J]. The Lancet,2017,389(10064):77-90.
[26]HANNUM E, PARK A. Educating chinas rural children for the 21st century[J]. Harvard China Review,2002,3(2):8-14.
[27]HANNUM E. Poverty and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villages, households, and girls and boys enrollment[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03,47(2):141-159.
[28]KAGAN S L, COHEN N E. Not by Chance: creating an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system[R]. New Haven: Bush Center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at Yale University,2017:21-42.
[29]COADY M R, COADY T J, NELSON A. Assessing the needs of immigrant, latino families and teachers in rural settings: building home?school partnerships[J]. NAB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2015,6(1):122-157.
[30]PHILLIPS D A, GORMLEY W T, LOWENSTEIN A E. Inside the pre?kindergarten door: classroom climate and instructional time allocation in tulsas pre?K program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9,24(3):213-228.
[31]DUNCAN G J, MAGNUSON K A. Can family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ccount for racial and ethnic test score gaps?[J]. The Future of Children,2005,15(1):35-54.
[32]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1-24.
[33]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6:241-258.
[34]GERSHOFF E T, ABER J L, RAVER C C, et al. Income is not enough: incorporating material hardship into models of income associations with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J]. Child Development,2007,78(1):70-95.
[35]SANDERS M R, KIRBY J N, TELLEGEN C L, et al. The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 multi?level system of parenting support[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14,34(4):337-357.
[36]BELSKY J. The determinants of parenting: a process model[J]. Child Development,1984,55(1):83-96.
[37]PARKE R D.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4(55):365-399.
[38]DESAI S, ALVA S. Maternal ed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is there a strong causal rela?tionship?[J]. Demography,1998,35(1):71-81.
[39]JANET C, ENRICO M. Mother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llege openings and longitudinal dat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4):1495-1532.
[40]EVANS D B, ETIENNE C. Health systems financing and the path to universal coverage[J].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88(6):402.
[41]侯佳偉,周博,梁宏.三孩政策實施初期廣東女性的生育意愿與托育服務、育兒假[J].南方人口,2022,37(03):39-52.
[42]MENG Q, YUAN J, JING L, et al. Mobility of primary health care workers in china[J].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2009,7(1):24.
[43]ZHANG X, FENG Z, ZHANG L. Analysis on the disparities of 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J]. Medicine and Society,2011,24(11):1-3.
[44]UNESCO. Education for people and planet: creating sustainable futures for all.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R].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16:36-129.
[45]康傳坤,趙書晨,李欣桐.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現狀、使用與效果[J].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23,35(3):75-85.
[46]CHEN F, SHORT S 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8,29(10):1379-1403.
[47]BOURDIEU P,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J]. The Forms of Capital,1986:241-258.
[48]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49]FILIPA C D, MARIE J P, AREMIS V, et al. Poor early childhood outcomes attributable to maternal depression in mexican women[J].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2017,20(4):561-568.
[50]JANVRY A D, SADOULET E. Income strategies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mexico: the role of off?farm activities[J]. World Development,2001,29(3):467-480.
[51]YUE A, SHI Y, CHANG F, et al.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intention to migrate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role of family and school factor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9,55:122-139.
[52]葉文穎.社會支持對農村祖輩隔代教養行為的影響[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23:66.
[53]WALKER P S, WACHS D T, GRANTHAM?MCGREGOR S, et al. Ine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early child development[J]. The Lancet,2011,378(9799):1325-1338.
[54]KAWACHI I, BERKMAN L F. Social ties and mental health[J]. Journal of Urban Health,2001,78(3):458-467.
Analysis of Family Support Needs for the Care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ged 0~3 in Rural Areas
SUN Xiaoke1, GAO Wenwuyu2, ZHU Shuangshuang3, WANG Xiaoxu3
(1Pinghu Normal School of Jiaxing College, Jiaxing 314001 China; 2Normal schoo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3Education Schoo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65 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 the birthrat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a fundamental policy of China at present. To elevate the societal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its essential to provide adequate support for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at home. Currently,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the care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ged 0~3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is not well?established, and various sectors lack the necessary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aregiving needs of rural parent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study surveyed the caregiving needs of 33 parents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ged 0~3 in the rural areas of Hena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It was found that support for caregiving in rural households mainly manifests in three areas: child?rearing support,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conditional assistance. Further research revealed that rural families have a stronger need for conditional assistance in terms of finance, parent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and reemployment during the caregiving process. They also have a preference for informal intra?family collaborative care and neighborhood support. Additionally, theres a noticeabl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upport.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in rural families and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usehold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in rural areas. They should also guide womens federations, schools, and other societal organizations, along with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are services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in rural areas and reinfor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rural neighborhood mutual assistance organizations and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family support, need for care support
(責任編輯:黎勇)
*基金項目:2022年江蘇省社科基金“共同富裕背景下蘇南地區城鄉學前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保障機制研究”(編號:22JYB012)
**通信作者:孫曉軻,嘉興學院平湖師范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