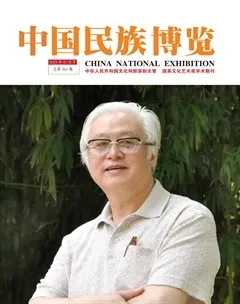淺議歷史考據學與地方史志編纂
【摘 要】地方志具有“存史、資政、育人”的功能,地方志必須全面真實地反映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發展情況,而對于存疑的內容,則必須重視歷史考據學方法,查找真相,成書于策,達到地方史志應有之作用。但在地方史志編纂過程中,尤其是現在,歷史考據學在地方史志編纂中并沒有得到運用,導致部分志書編纂質量存在很多問題,筆者覺得有必要再次探討歷史考據學對于地方史志編纂的重要作用,為第三輪志書的編纂做好鋪墊。
【關鍵詞】歷史考據學;地方史志;編纂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0—024—03
地方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周代《周禮》中就有地方志發展跡象,如清代章學誠曰:“州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見地方志發展歷史久遠,后經過不斷完善和發展,內容越來越豐富和詳實,成為中國獨有的歷史特色。現在新時代中國特色思想指導下,有了更加完善的結構和體例,因某些主客觀因素,地方史志編纂中往往忽略對歷史疑點的考證,某種程度上使志書失真,影響了志書質量,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歷史考據學的作用,以科學求實的態度,通過“細、真、嚴、實”的工作作風編纂好地方志書,為新時代的發展謀思路、開新局。
一、歷史考據學促就史志經典綻放
考據從字面意思來看就是考證與考究,以達到對人和物真相的了解。《史記·伯夷列傳》云:“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可見“考訂,即史料價值之估定也。”歷史考據是研究歷史的一種實證方法,它是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通過對搜集到的資料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鑒定和辨別,來斷定真偽,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描述到:“人們也早就知道,不可盲目地親信所有史料。人們早已有過這樣的經驗,發現為數不少的書籍偽造年代和出處,有些記載全是虛構的,甚至有些實物也不過是贗品。”[1]由考據衍生出考據學,成為一種嚴謹的治學方法,達到“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2]的目的。中國古代史學家充分運用考據學,創作了許多史學著作,如被魯迅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司馬遷在編寫這部書時,對自己所掌握的歷史資料充分考證,到過大禹召集部落開會的地方,去屈原去世的汨羅江,到曲阜考察孔子講學遺址,并詢問當地居民,考證第一手豐富資料。同時還忙于研讀歷史文獻和整理其父留下來的史料,經過幾十年的積淀,終于完成了這部流傳后世的佳作。南宋曾先之,其寫的《十八史略》中記載岳飛被害之事,通過考證寫下此言:兀術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清,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3]這就為后世提供了確鑿的歷史證據,即岳飛被害原因。被稱為清代考據學先河的顧炎武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清《四庫全書》編撰時,“訪求遺書,校讎中秘,其事往主有之。蓋其搜羅之富,評隲之評,為私家所不能隸,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奉購訪遺書之詔,奏陳四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著以補其余;三著錄校讎當并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4]從而使《四庫全書》成為流傳后世的經典子集。
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認真研究歷史,使歷史成就大放異彩,這一時期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呂思勉、范文瀾、侯外廬等,充分發揮考據學研究方法,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寫出了頗具地位的史學作品,如呂思勉《中國通史》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等史書,無一不滲透著考據學的方法,填補了中國史學上的空缺,成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瑰寶。
二、地方史志編纂中歷史考據學的發展狀況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告訴我們,要對事物敢于質疑,提出問題,然后親自實踐,達到“去偽存真,去粗存真”的目的。但現在某些地方志書的編纂,恰恰缺乏對歷史的探索與求證,導致志書編纂質量存在很多的問題,使其出版后難以服眾。
(一)地方志編纂中存在重文采輕考據的思想
地方志書每隔20年左右編纂一次,時間跨度大,對材料的搜集無疑是一項繁重的任務,動則幾百萬的材料需要和各單位溝通協調,形成材料,再進行剝絲抽繭,沒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絕非易事。面對這些材料,史志編纂人員僅僅細摳材料文字,看有沒有錯別字,語句通順不通順,事情合不合常理等等內容上的審閱,無形中就形成了文學上的糾錯,偏離了史志編纂中“重史事,求真相”的原則了,一定程度上導致志書傾向于文學色彩,背離志書編纂的初衷。反觀民國時期,當時由柳亞子擔任《上海市通志稿》主編時,就非常注重史志編纂的考證,其中一條就強調:“志稿必須突破慣例,用白話文撰寫,并且是系統研究的成果,而不僅僅是材料的堆砌。”[5]前人尚且如此,作為新時代方志人,我們應該繼承前人探究精神,充分發揮歷史考據學的治學方法,查真求實,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編纂新時代方志,切忌把方志編成材料的堆砌。
(二)地方史志編纂缺乏專業性歷史考據學人才,近而影響史志編纂質量
“秉筆直書”是對方志人的要求,而“直”就賦予了方志人要敢于探求真理,尋求真相,在編纂地方志書時要運用歷史考據學方法,考察歷史事件。劉知己提出史學家必有具有“三才”,即“才也、學也、識也”,“才”也就是史學編纂中的人才,正如他說“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可見,在史志編纂過程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視,尤其是重史志考證的人才。但現實是史志編纂人才匱乏,且年齡大者居多,思維跟不上社會發展步伐。要重視人才作用,積極挖掘史志編纂中史料考據人才,為史志編纂筑牢人才基礎,進一步做好三輪志書的啟動工作。
三、充分重視考據學在史志編纂中的運用,推動地方志編纂再上新臺階
作為延續中華文明發展的地方史志事業要緊跟歷史發展步伐,轉變思想觀念,充分發揮考據學在史志編纂中的作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編纂出高質量的精品佳作,為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助力,從而更好地定位史志行業的社會職責。
(一)史志編纂工作者樹立正確的史學觀,讓證據先行,把搜集證據作為史志編纂的基礎性工作
關于二輪志書出版的質量狀況或多或少有頗議,有的認為志書偏重文字性表述,缺乏考據資料支撐,參考價值不高;有的認為志書商業味濃厚,包裝精美,只追求經濟利益;有的認為志書成工作總結性志書,高大上、假空虛,嚴重脫離了志書的本質。王建議在《千錘萬鑿出“深山”》—淺易方志語言美一文中指出的:“二輪志書編纂中存在的問題有:大量使用論述性宣傳性總結性文體,空話、虛話、套話多,假話、大話、廢話也不少。”[6]地方志編纂者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史觀為指導方針,樹立正確的史學觀,李大釗說:“歷史觀者,實為人生的準據,欲得一正確的人生觀,必先得一正確的歷史觀。”[7]在史志編纂中,注重地方志某些事件的證據考察,用證據說服讀者,取信于讀者,才能編纂出更好作品,受益于后世。汶上縣第一輪志書編纂質量獲得高度好評,上世紀90年代,按照省市要求,編纂第一輪志書,當時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志書編纂者們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決心實事求是地編纂好這部志書(志書上限到商代以前,下限到1987年,歷史跨度長。),四五個人以驚人的意志,兵分幾路去國家和省市縣檔案館、圖書館、縣統計局等查閱資料,獲得第一手可信資料,反復審閱修訂,方才出版并獲得好評。所以,一部好的志書,必須充分重視證據的考察,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流芳百世。
(二)志書編纂者必須有質疑精神,有疑而糾,挖掘志書真相作為自身使命
志書編纂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作,志書編纂工作者必須對所搜集的志書進行整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保存真實合理的材料。在志書編纂過程中,對于幾百萬的志書資料,要進行鑒別取舍,更要有大膽質疑的工作風格,通過質疑而采取有效途徑搜集相關證據。明代學者戴震就敢于疑古,哪怕是圣人所言,在他十歲時,讀《大學章句》一文,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日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史學家顧頡剛也勇于“疑古”,打破舊有荒謬傳說,使歷代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失去了依據,編纂了著名的史學著作《古史辨》,成為考辨古史的佳作。[8]這說明古人尚且有疑古之精神,我們在志書編纂中更應該打破因循守舊之陋習,對志書資料中有疑問的地方積極有所為,才能編纂出令人信服的志書。這方面《廣州市志·民政志》[9]在記載市內一座清式建筑物名稱時就進行了質疑,這座建筑物到底是廣東錢局的建筑物還是普濟院的建筑物不能確定,由此進行考證,查閱了設計該建筑物同治《番禺縣志》,經印證該建筑物為普濟院,并將普濟院始建時間,地點、歷代演變情況等寫的明明白白記載入冊,也成為了后來資料查閱的有力證據。對志書資料中有疑問的地方卓力取證,方為史志人使命之要務。
(三)方志編纂者考證資料要多方查證,多措并舉,實事求是地讓證據說話,以事實服人
(1)充分利用信息化儲存條件,查找印證材料。信息化的迅速發展,為許多資料的儲存提供了便利條件,如關于自然災害的影像材料、經濟發展的圖片資料、優秀人物的視頻資料等都能處理之后長久儲存在硬盤里,方便查找取證。安徽歙縣1998年遭遇了50年一遇洪澇災害,當時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記錄了洪澇發生時的情況,影像資料清晰,在《歙縣志》自然災害方面就真實地記錄洪澇災害歷史,為后世提供了氣候方面的參考資料。
(2)重視志書編纂資料中事件親自參與者的作用。某種歷史事件中,親自參與者是最真實的歷史資料的發言者,也是最有利的證據說服者,因此,重視他們的作用是對史志編纂資料最好的見證。以《汶上縣志》編纂為例,在第一輪志書中涉及到抗戰時期該縣人民的抗日事跡時,其中有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件—永安寺起義,在編纂時對歷史資料記述不詳,就采訪了事件組織者劉啟文、曹志尚等人,[10]使這段歷史能夠完整記錄下來。
(3)充分發掘檔案館的儲藏作用,查找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檔案館收藏著很多歷史性的資料,在史志編纂中對一些模糊不清的歷史事件,可去檔案館查閱可靠性的資料。同樣,《汶上縣志》(1996年版)由于涉及編纂年限較長,在記述西周歷史時,就查閱了國家檔案館的相關資料,有力彌補了這段歷史在本縣的缺憾,也使本輪志書成為較有價值的地方史書。
總之,地方史書是一個地方發展的縮影,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在編纂過程中必須重視考據學的應用,讓考據先行,以考據服人,才能編纂出上乘佳作。
參考文獻:
[1]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2]陳其泰.新歷史考證學與史觀指導[J].中國史研究,2012(2).
[3]夏學杰.煩簡有當中國史[N].中華讀書報,2018—04—04.
[4]孟森.清史講義[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
[5]呂鮮林.新時代方志觀之探微——兼論新時代方志體例風格及內容特色[J].上海地方志,2020(3).
[6]王建議.千錘萬鑿出“深山”——淺議方志語言美[J].上海地方志,2020(3).
[7]李大釗.史學思想講義[A].李大釗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2020.
[9]廣州市地方志編委會,編.廣州市志[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1.
[10]汶上縣志編纂委員會.汶上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作者簡介:曹巧英(1980—),女,漢族,山東單縣人,本科,研究方向為地方史志編纂業務,擅長地方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