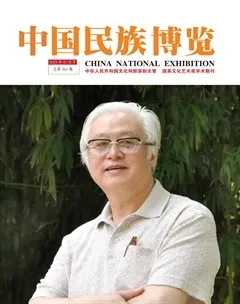音樂表演民族志分析
盧璐穎
【摘 要】文章圍繞音樂表演民族志進行分析,大致闡述其從“民族志”“表演民族志”到“音樂表演民族志”的演變過程。進一步討論其中的語境和身體敘事概念,結合國內音樂表演民族志的分析轉型變化,探究靜態文本與動態表演等研究角度,供參考。
【關鍵詞】音樂表演民族志;文本;語境
【中圖分類號】J6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0—103—03
引言
在民俗學領域“表演理論”的影響下,傳統民族音樂學研究角度也開始關注表演民族志,特別是音樂表演層面,依舊不再單一突出對樂譜架構的闡述。轉而把音樂文本構成動態嵌入實際表演場景中,加以審視分析。
一、音樂表演民族志的演變過程
(一)民族志
其本身是針對人及風俗習慣層面,討論文化和差異性的。在我國,“志”屬于動詞,代表記錄的意識,原意是“記載”。比如,地理志與天文志等。本質上和西方“民族志”有較大差別。但總而言之,民族志就是利用多個專業層面記錄和描述的科學。時至今日,民族志基本上可分成三個發展時期,一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在人類學領域,民族志的撰寫基本上是對已有信息的分析,比如《金枝》。二是從19世紀末開始,功能主義思想形成,倡導人類學家要走進現實,該階段形成了“科學民族志”,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采用了田野考察法。三是在“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下,逐漸產生“反思民族志”,并在后期的民族志寫作中,也發生的很多變化[1]。尤其是在20世紀的20年代之后,寫法更加多樣,并由原本的淺層解釋轉化成深層描述。
(二)表演民族志
“表演”原本就有不同的含義,一是在音樂會、戲劇以及其他形式中的演出行為;二是對于音樂以及作品中角色的演繹;三是實施某個動作或任務等。從西方藝術史的視角來看,“表演”能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吟誦者,相當于“神的傳話者”,把聽者、朗誦者與詩人集于一身。在此之后,理查·謝克納以戲劇和人類學的層面,認為是自我行動的范疇,具有客觀存在性。直到上世紀的60年代末期,民俗學研究中引入“表演”一詞,包含民俗實踐以及表演情境。在研究繼續深入中,80年代慢慢形成“表演民族志”。在2010年之后,對于該方面的研究側重于“后現代主義”寫作。
(三)音樂表演民族志
在“表演理論”不斷發展中,音樂表演民族志逐漸得到關注,相關研究有所增加。比如在1980年出版的《音樂表演民族志》,其應該是較早選擇此概念命名。斯通是促進音樂表演民族志的關鍵一人,表示音樂就是交流,表演者進行創作,和其他表演者一起動作,觀者則按照表演者的呈現進行回應,屬于雙向互動。在此以后,音樂表演民族志成為整合多種思想概念的一類民族志。從本世紀開始,國內民俗學領域才出現了“表演理論”以及“表演民族志”,同時也得到民族音樂學領域的關注。
二、音樂表演民族志中語境及身體敘事
(一)語境轉換
從音樂表演民族志的角度來看,語境決定了表演文本的形成,而表演場域空間形態,決定了表演內容,無論是即興互動,亦或有固定流程的民俗儀式,均注重在場語境下“互為主體”的形式,還有音樂文本形成語境,所以探討“語境”是有必要的。按照段寶林的觀點,民間文學表演就是一種創作的過程,很多作品都是即興產生,是表演者觸景生情的結果,例如唱詞和表演行為發生的場域環境有密切聯系。在20世紀中葉以后,西方民俗學分析形成兩個明顯的轉向,即由文本轉為語境、由靜態文本轉為動態表演與交流。由于語境的變化,會對表演文本和樂譜有巨大影響,而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影響到表演文本和過程的呈現。音樂表演民族志中,“語境”成為決定音樂表演結構產生和文化象征性出現過程的存在。這種強調語境的觀念,和民族音樂學相得益彰。
對于音樂表演來說,沒有重復的演出,每場表演均是全新的,這突出了文本自身的“新生性”特征,也可看作“去語境化”,突出表演腳本和臨場發揮的“沖突”,強調受到表演語境的作用產生的即興結果,也就是表演模式和“變式”的聯系[2]。表演民族志摒棄原本將樂譜文本作為研究中心的形式,關注表演文本構成的動態過程,以及不同語境下音樂文本的產生。從某個層面上來講,表演民族志注重“過程”,并非單純的樂譜文本,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模式,轉而朝著現場即興的表演部分,具有明顯的“后現代主義”特色。
按照“音樂學”的概念闡述,對音樂學的分析要從文化及社會環境層面的音樂家入手,包含社會學、文化、性別研究與語言學等。即便音樂表演作品內容及人員沒有變化,但因為語境的差異,特別是觀眾變化,均會使音樂表演文本有所調整。例如,我國民族音樂中的“彈詞”,即使是同一作品在一個舞臺上表演,由于與表演者互動的觀眾年齡段、教育經歷等差異,會引發在場表演文本結構變化。“還家源”儀式上,相關家庭和姓氏變化,“馬頭意者”和“盤王大歌”會做出調整。因此,音樂表演民族志不僅注重文本“程式化”的形成,還關注具體語境下,文本“模式化”的調整。
從民族音樂學視角來看音樂表演文本形成,只強調某個田野案例是不可取的,還需把表演語境下的音樂文本,放在“程式化”的行動架構中加以對比,也就是要考慮表演文本及語境變化。
(二)身體敘事
表演文本形成也是用身體敘事的過程,當前民族音樂學領域研究雖然深入到表演語境層次,但有關“身體敘事”對音樂表演過程的敘事情況影響,還要表演姿態變化對文本構成的影響等方面,還缺少深度分析。民族音樂學聚焦于表演理論,由音樂文本的靜態研究,轉而關注表演語境的音樂作品形成,同時也強調由樂譜研究和描述,轉為在場互動下的身體敘事。目前,部分學者發現了音樂表演姿態和文本形成之間的聯系。例如,演奏雙排鍵和管風琴時,要求手腳并用,并且要保持演奏姿態和身體狀態的協調感,既全面描述出演奏者的音樂表現力,又打開音樂表演的空間維度,這是由于演奏者身體姿態也屬于音樂表演的一部分。例如,指揮員的手勢及眼神,詮釋了音樂現場表演即時性,特別是樂譜和錄音文本的構成。
音樂表演民族志的分析,需要考慮表演姿態和文本形成,還有音聲符號的互動聯系。在表演者通過身體敘事中,持續產生音聲符號,而表演者本身的文化“角色”,會對表演文本形成的象征意義和敘事內容有較大影響。比如說,在儀式樂舞文本形成中,側重于通過身體敘事,音樂表演具有政治色彩和象征性。
總之,在音樂表演“身體敘事”的分析中,要考慮到表演姿態和樂譜構成、音聲文本生成的聯系[3]。表演姿態就是身體敘事過程的“符號”,延伸了表演空間維度,所以身體敘事不僅對音樂文本形態產生有影響,還拓展文化符號象征性的產生空間。比如在民俗儀式上,執行者通過身體詮釋美好的愿望,例如手訣、舞蹈。特別是即興類的表演,結合表演語境,開拓敘事空間的同時,還對象征性和音聲結構的形成“設置”框架。以表演民族志分析身體敘事,不僅涉及到錄音、樂譜等形式文本,還要考慮對于身體敘事的多層次表達、音樂文本象征性含義、社會化價值等形成的影響。
三、我國音樂表演民族志的轉型變化
(一)靜態音樂文本
在我國傳統音樂分析中,音樂文本是一項極具代表性的符號,但這反映出相關領域研究忽視了語境變化。按照楊民康學者對于我國音樂分析方法的劃分,基于樂譜的音樂文本形態學分析,就是其中的一種。在傳統民間音樂中,“聲音”是最受重視的符號,通過口傳心授形式積累下來的文本,經過實地調查記錄音樂表演作品,整理成樂譜。此類樂譜側重于彼時語境下表演情況和音樂表現。比如苗族的祭狗儀式一直在變化中,保存的影像資料,和如今看到的儀式及音樂文本會有出入,音樂分析不要僅考慮早期及當前的靜態表現,需從發展的角度看待。從此來看,以樂譜角度的研究方法,應當是國內傳統音樂分析中的較早方法,只停留在文本層面。而音樂文本分析需要結合表演藝術以及音樂形態,如創作背景與風格、曲式、織體、旋律、伴奏、和聲等,突出靜態音樂文本的同時,也要注重音樂表演及語境的“交流”。因此,研究靜態文本是有意義的,但不足之處在于缺少對“過程”的考量。
(二)動態表演文本
靜態樂譜和現場表演的轉變是在語境下完成,要考慮階段性表演和語境在各個時空中的動態轉化。例如,音樂家或戲劇家把樂譜與劇本表演呈現在觀眾面前,而在分析中就要考慮“腳本”和“表演”間的轉化。在民族音樂學范疇內,音樂表演民族志分析被“互文性”以及“符號學”所影響,注重音樂文本形成在各個階段的表現,即表演的前、中、后,實際上就是音樂作品由前期采集和文本創作,發展到文本詮釋,最終是觀眾對于文本的評價和理解。其中,文本詮釋便是音樂表演文本動態產生的環節[4]。
表演語境中包含人物、時間與空間等,涉及科學與文化、政治等眾多社會元素。語境會在時間流逝中持續變化,表演過后都會是“歷史”。所以,音樂表演分析中需要考慮所有語境下的文本,進行橫向對比。這樣既可以發現不同的表演形態,還可以觀察到表演文本變化趨勢,實現立足于表演的分析目的。
(三)可寫性文本
通過可寫性文本,能夠解釋音樂表演文本在動態中形成,而“可讀性”和“可寫性”不是完全對立的狀態,某些時候還有“共存”的關系。在將作者當成中心對文本形成進行分析,同樣關注相應語境,強調表演者和觀眾,亦或兩者之間形成文本的過程。例如,在少數民族某些節日中,會通過對歌的方式慶祝,該情景便具有可讀性與可寫性。對歌雙方會按照當前情景,也可能順著對方的問題進行演唱,曲調旋律一致。如果從符號學的層面來講,音樂應當是文化符號,人創作并賦予其特殊的象征意義。由于消費、體驗和生產的主體均是人,并且音樂風格和構成和人所處環境有較多聯系,所以民族音樂學既需分析音樂本身風格及形態,又應關注音樂具有的象征性功能。比如湘苗族侗族留存“四十八寨”,屬于村寨形式,長期以來慢慢構成文化圈。此處人們風俗習慣與語言均比較接近,村寨之間可以正常交流、互動,每逢重要節日還會一同慶祝。即使在傳統音樂腔調上會有差別,但闡述的意思基本明白。而在各類活動的交流下,各自的腔調也會被對方影響,出現混合或是使用對方腔調的情況,衍生出新的音樂形式。
總之,民族音樂學需考慮表演語境的可變性,以及人在其中的作用。如果忽略特殊的人際關系,表演者同樣會由于心理情緒改變,影響到即興表演。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內容相同的情況下,表演效果與觀眾反響始終不一致的現象,關鍵在于表演者對現場演繹“新生性”的作用。
(四)可讀性文本
其同樣也注重“人”,和可寫性文本的差異在于,強調受眾對文本的闡釋,換言之,各個年齡段、教育背景、社會經歷的受眾對相同音樂表演文本實際感受會有不同。在民族音樂表演領域,流傳著許多靜態文本資料,或是當地專家、傳承人整理編制,亦或相關學者為了課題研究而編撰,二者均將音樂表演內容記錄下來,但文本載體卻有不同,這可能是由于受眾差異引起的,受眾會選擇自己相對熟悉的形式闡釋和呈現。而以文本編撰者視角看來,音樂文本面向的受眾具有多樣化需要與理解力,所以需要結合音樂表演的實際目標調節文本內容[5]。文本無論是可寫性,或者可讀性,本質上依舊是動態形成和變化的過程。比如,前文提及的敬酒歌,由于表演地域與場合的變化,音樂文本便出現了多個調整形式,比如旋律和唱詞不變,調整節奏;留下關鍵詞,改編整體旋律等。該過程可以看作音樂表演具備“新生性”。
對于音樂表演研究來說,互文性、新生性等的特定定義,都說明了語境調整對表演動態的影響。總體而言,“表演理論”的發展轉變,集中在:“歷史民俗—當代民俗”“側重文本—側重語境”“集體—個人”“靜態文本—動態現場表演”等。
(五)研究發展方向
國內音樂表演民族志的分析,未來可繼續在表演和人兩個維度上考量。音樂表演過程中,“人”具有多重角色,但目前的音樂表演民族志一般側重于分析現場表演行為,未能注意到人際交往因素給表演帶來的影響。而人際交往則隱藏在社會生活中,從此層面來看,對于音樂表演民族志的分析,應當嘗試把音樂表演放在生活環境下,探究表演者和受眾的聯系,研究怎樣在人際交往層面上利用表演闡明觀點,同時受眾又怎樣捕捉訊息。另外,音樂表演民族志也要重視文本創作的文化空間背景,關注歷史傳承、地理人文等對文本帶來的影響作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引入了音樂表演民族志后,研究實踐促使觀察角度發生變化,總體上就是側重點從靜態延伸到動態,主體對象范圍在表演者的基礎上增加了受眾、其他參與者。目前,國內相關研究綜合了民族音樂學和符號學等多重理論,基本演化出理論邏輯,而且也在持續發展中,但依舊未形成系統化的完整研究脈絡和分析方法。
參考文獻:
[1]楊民康.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的學術走向與方法論意義——《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實例》教學與輔導之十三[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2(6).
[2]姚萌,張謙.綜藝節目中的想象空間與民族身份認同建構——基于《國家寶藏》的音樂表演文本分析[J].音樂與聲音研究,2022(2).
[3]楊民康.音樂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再思考——《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實例》教學與輔導之九[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2(2).
[4]余媛,趙書峰.從樂譜分析到以表演為中心的研究范式轉型:基于中國學者音樂表演民族志的分析與研究[J].藝術探索,2022(1).
[5]趙書峰,楊聲軍.語境·身體·互文·權力: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再思考[J].音樂研究,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