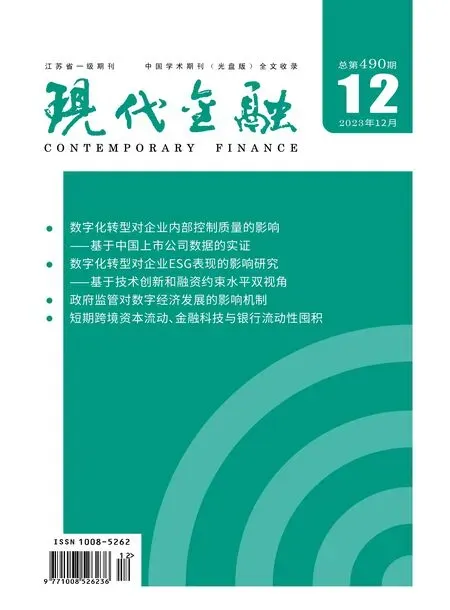短期跨境資本流動、金融科技與銀行流動性囤積
□ 王文江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持續推進金融業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雖然金融開放推動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的上升能夠優化產業結構(郭娜等,2023)、加強地區間的金融合作(費兆奇和劉康,2020)等。但由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同樣具有順周期性的特征,高頻率、大規模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會引起國內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對銀行業穩定性產生重大沖擊效應(顧海峰和謝疏影,2022),以至于銀行調整風險偏好,出現流動性囤積現象,致使整個金融體系內的信用供給端和需求端之間的流動性傳導渠道受阻(項后軍和周雄,2022)。對銀行而言,面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的上升,流動性囤積現象是銀行基于收益和風險的博弈,但對實體經濟而言,流動性囤積意味著商業銀行放貸意愿低下,實體企業從銀行獲取信貸支持難度上升(李建軍等,2023)。
在傳統的商業銀行經營時期,其業務模式通常呈現出粗放式擴張的狀態,客戶集中度較高(盛天翔等,2022),經營業務依賴于銀行內部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存款、貸款、信用卡、外匯和投資等傳統業務為主要收益來源。這些業務需要大量人力和分支機構的支持,因此投入的資金成本也相對高昂,且運營流程較為繁瑣、風險管理難以達標。所以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上升,造成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時,由于傳統銀行風險承擔能力較弱,且難以辨別企業真實財務水平(鄭錄軍等,2023),所以不得不降低風險偏好,調整信貸結構,流動性創造能力降低。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開始主動應用金融科技推動銀行數字化轉型,達到提質降本增效的目的,同時也為銀行流動性管理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Cheng and Qu,2020)。通過金融科技的賦能,商業銀行改變了以往單純以規模驅動利潤的經營模式(蔡岑等,2023),擴大戰略視野,提高對宏觀市場和地區客戶的敏感程度,降低經濟不確定性帶來的消極影響,在外部沖擊中發揮“穩定器”的作用(賈盾和韓昊哲,2023)。那么值得思考的是,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賦能作用能否緩解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的影響,發揮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功能。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目前少有研究將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銀行流動性囤積結合起來分析,探究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的背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因素;第二,本文將金融科技作為調節變量,探究金融科技能否緩解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并深入挖掘其中具體的調節機制,為銀行金融科技應用及發展方向提供可行性的理論支持;第三,考慮到不同性質銀行在面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時的應對措施不同,以及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渠道的多樣性,所以本文按照銀行性質和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渠道進行異質性分析,并且進一步運用面板分位數回歸的方法,探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科技應用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邊際效應規律。
二、影響機制與研究假設
具體來講,雖然跨境資本流入促進了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發展,非銀行融資渠道有所擴寬,但同樣加劇了企業高杠桿、高負債的財務狀況,企業投融資之間的不穩定鏈條難以持久,一旦遭遇國際市場震蕩、政策變動等外部沖擊,“明斯基時刻”必然接踵而來(茍琴和李興申,2023)。此時,大量跨境資本外逃引發資產價格斷崖式下跌,市場投資需求萎靡。其后伴隨市場恐慌情緒蔓延,引起資產大范圍無差別拋售。因此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過高時,銀行在預防性動機的驅動下,為了避免潛在的流動性危機問題,大規模吸收流動性資產、收縮信貸規模,導致流動性的過度囤積(李紅等,2023)。因此,市場投資者面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上升,可能導致趨同式市場預期,掀起境內資產市場的投機性炒作和資產配置調整浪潮,導致銀企信息不對稱程度擴大,企業違約概率攀升,導致銀行風險容忍度持續下降,跨境資本流入壓力推動的信貸擴張力度不足,跨境資本流出又導致銀行信貸收縮,使得銀行在整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階段出現流動性囤積現象(梁上坤和董青,2023)。
根據實物期權機制和信息不對稱理論,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提高了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對銀行而言,貸款等風險資產不可逆且流動性低,所以銀行會等待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下降,降低風險投資規模,最終出現“惜貸”“少貸”“難貸”等現象(郭娜等,2023)。但在金融科技的賦能下,商業銀行能夠通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手段增強信息搜集能力和分析篩選能力,降低銀企信息不確定性,并進一步強化了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能力和反欺詐能力,從而提高了銀行風險偏好,使銀行“敢放貸、愿放貸、能放貸”,推動銀行在利潤最大化的動機下主動開始信貸合理擴張,從而抑制跨境資本流出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的促進作用(龍海明和胡鳴,2023)。因此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上升加劇了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
假設2:金融科技通過提高銀行風險容忍度緩解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
除了銀行風險容忍度之外,信貸錯配同樣是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影響銀行流動性囤積的重要渠道,并且也是銀行金融科技應用緩解銀行流動性囤積的機制渠道。一方面,資本流入使得本國貨幣升值,且國內外利差的加劇使得大量國際投資者在國內進行套匯套利,國際熱錢的涌入使得負債端短期流動性大量聚集。負債端流動性急增使得銀行需要快速消化存款來釋放存款壓力,并且銀行需要提升資產質量來確保貸款回收率(顧海峰和卞雨晨,2022),但由于市場優質企業有限,難以消化過量存款,必然導致銀行業競爭加劇。在這種環境下,大量未涉及跨境資本業務的中小銀行也會受到市場信貸份額擠占,被動參與市場貸款價格競爭,導致貸款利率水平下降;另一方面,跨境資本流入強度上升帶動金融自由化環境,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競爭程度,銀行信貸收益不斷被壓縮(黃飛鳴等,2023)。因此銀行在粘性收益目標追逐下,開始調整信貸結構,逐步投資于短期證券市場,通過多種資管渠道認購債券獲得投機性收益,資產端流動性增加,短期存款和長期貸款之間的信貸錯配程度加劇,流動性囤積程度上升。
但在金融科技的賦能下,銀行能夠明顯擴大市場競爭力,能夠有效突破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市場投融資扭曲效應。銀行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來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客戶信息,對客戶習慣和潛在需求進行分析,將更多中小型客戶作為信貸服務對象,發掘更多潛在服務群體,提高貸款邊際收益(陳曉潔何廣文,2023)。并且銀行也可以同時應用金融科技來對市場競爭進行動態分析,借助建模工具對地區、行業和個體客戶等維度產品精準分析調整,實現市場邊界擴展、提高市場占有率,最終降低信貸錯配程度,緩解流動性囤積現象。因此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3:金融科技通過降低銀行信貸錯配程度從而緩解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
三、實證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樣本為216家商業銀行2011-2022年的面板數據,樣本銀行的資產總和占中國所有商業銀行總資產的95%以上。銀行層面數據和宏觀經濟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和國家統計局。
(二)模型設定
1.基準模型
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來分析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
其中,FKt為第t年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LHit為銀行i在t年份的流動性囤積水平,BANKit為銀行層面的微觀控制變量,MACROi為宏觀經濟層面的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用來控制部分不隨時間變化且難以觀測的銀行固定特征;εit為隨機干擾項。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是時間序列,因而不能直接納入時間固定效應來控制僅隨時間變化的宏觀環境調整,故參考張成思和劉貫春(2018)的做法,轉為添加宏觀層面控制變量來刻畫宏觀經濟環境變動。
2.調節效應模型
為了研究銀行金融科技應用在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銀行流動性囤積之間發揮的調節作用及其內在機制,本文構建如下模型進行分析:
模型(2)主要來分析金融科技的調節效應結果,模型(3)、(4)主要來分析具體金融科技發揮調節作用的內在機制。其中,FINTit為調節變量,意為銀行i在t年的金融科技應用水平,Mit為調節機制變量,其他變量含義與模型(1)一致,β2與λ2是解釋變量與金融科技的交互項系數,如果該系數與模型(1)或(3)中系數方向一致,則表明調節變量具有正向調節作用,不一致則表示調節變量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三)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LH)
本文基于Berger et al.(2022)、項后軍和周雄(2022)提出的流動性囤積測度方法,對銀行資產端、負債端相關科目進行賦權加總,測度我國銀行流動性囤積指標。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銀行流動性囤積規模=(0.5×流動性資產-0.5×非流動性資產)+(0.5×流動性負債)①銀行流動性囤積的詳細權重劃分參考郭娜等(2023)。
銀行流動性囤積占總資產比例(LH)=銀行流動性囤積規模/資產總額
2.解釋變量:短期跨境資本流動(FK)
傳統文獻采用國際資本流動凈額(韓乾等,2017)來表示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由于其為跨境資本流入與流出之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這種流動的強度。鑒于此,參照馬勇和王芳 ( 2018) ,采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賬戶”借貸方之和來衡量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并除以該指標的序列最大值將其標準化。同時,進一步引入“金融賬戶借方額/序列最大值”(FK_OUT)與“金融賬戶貸方額/序列最大值”(FK_IN),分別作為跨境資本流出強度和流入強度來考察不同種情況下跨境資本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
3.調節變量:銀行金融科技應用(FINT)
本文引用謝絢麗(2022)對于商業銀行金融科技指數的測定方法,將商業銀行數字化的過程分為戰略科技化、業務科技化和管理科技化三個維度,對其進行加權匯總構建銀行金融科技總指標,作為銀行金融科技的應用水平。具體指標構建方法見表1。

表1 金融科技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
4.機制變量:信貸錯配(LDR)、風險偏好(RWS)
本文使用銀行貸款和活期存款的比值作為銀行信貸錯配(LDR)的代理變量;使用風險加權資產對數值作為銀行風險偏好(RWS)代理變量。
5.控制變量
本文首先控制了銀行層面變量,包括收入成本比(CTI)、總資產周轉率(TAT)、不良貸款率(NPL)和資本充足率(CAR)。此外,由于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宏觀時間序列數據,回歸模型中無法納入時間固定效應,因此進一步控制地區及宏觀層面變量以期最大程度上緩解內生性問題。地區層面控制變量包括市場化指數(MARKET)、城鎮化率(URR)和就業率(ROEM);宏觀層面變量包括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PU)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各變量具體名稱和指標含義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定義與說明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3匯報了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回歸結果。第(1)列是未添加任何控制變量時,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回歸結果,后續幾列是添加控制變量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回歸結果。其中,第(2)列是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第(3)列是跨境資本流出強度;第(4)列是跨境資本流入強度。本文為了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每列回歸均控制了銀行個體固定效應。

表3 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
根據表3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整個國際資本流動的過程中,跨境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加劇了銀行流動性囤積程度。其實,從根本上講,在跨境資本流入時,銀行負債端流動性加劇,而且資本的流入為國內金融市場提供了資金,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外部融資壓力,使得企業對銀行信貸依賴程度下降,但由于此時企業資金來源多為短期借款,存在嚴重的“短借長投”行為,銀行基于對企業還款能力的擔憂也會略微收縮信貸規模。而當跨境資本外逃時,資產價格泡沫開始破滅,企業價值下滑時,銀行出于風險預防動機,會進一步大量持有流動性資產以應對可能到來的擠兌危機,銀行此時整體流動性水平出現顯著聚集現象,流動性囤積程度加深。
(二)調節機制檢驗
1.調節效應檢驗
前文理論分析及實證結果表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會提高銀行流動性囤積程度,而金融科技應用可以緩解這種促進程度,并且在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不同狀態中,銀行囤積動機和金融科技調節機理并不相同。因此為了進一步探討金融科技應用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具體調節機制,本文替換被解釋變量再次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表5所示。其中表4是金融科技應用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銀行流動性囤積的調節效應分析;表5是具體調節機制分析。

表4 針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的調節機制分析

表5 調節機制分析
由表4第(1)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銀行金融科技總指數和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的交乘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與主效應系數相反,說明金融科技確實可以有效抑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促進作用。驗證了本文假設2。并且第(2)(3)列跨境資本流入、跨境資本流出與金融科技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金融科技的賦能作用對跨境資本流入與流出均起作用。
表5第(1)(2)列顯示了基于銀行信貸錯配,金融科技對跨境資本流動的調節機制。結果顯示跨境資本流動對信貸錯配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金融科技和資本流動的交互項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應用能夠降低信貸錯配程度從而緩解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促進效應。其次第(3)(4)列顯示了基于銀行風險偏好,金融科技對跨境資本流動的調節機制,結果顯示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風險偏好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而金融科技和資本流動的交互項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應用能夠提高銀行風險偏好從而緩解跨境資本流出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促進效應。
(三)內生性處理
1.GMM動態面板分析
為了克服異方差與內生性問題對實證研究結果的影響,并考慮到銀行流動性囤積具有動態持續性,本文進一步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統GMM回歸進行實證檢驗, 以緩解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并檢驗前文結論的穩健性,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銀行流動性囤積一期滯后(L.LH)在各列中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銀行流動性囤積的確具有一定的序列相關性。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在考慮了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序列相關這一特征后,銀行金融科技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負向影響仍然存在,證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2.工具變量法
由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與銀行流動性囤積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來進行解決,首先借鑒顧海峰和于家珺(2019)的做法,使用美國經濟不確定性(USEPU)①本文使用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USEPU)作為工具變量,與控制變量做法相同,同樣是將對未來一期的月度不確定性數據算術平均得到年度值。作為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工具變量。一般而言,美國經濟不確定性能通過影響國際市場環境,進而影響我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美國經濟不確定性越強,國際市場環境就越差,國際投資者更樂意來我國進行投資交易,因此我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強度就越高,而美國經濟不確定性但又不會直接影響我國商業銀行具體決策,因此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和外生性假定。其次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反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又將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滯后一期值(L.FK)作為工具變量。對于銀行金融科技應用而言,移動電話用戶是銀行推廣數字產品的主要接受者,并且移動電話用戶數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地數字金融發展潛力(黃益平等,2021),所以商業銀行金融科技應用程度和銀行總部所在省份移動電話用戶數相關,但該指標是城市層面的環境特征,所以在控制宏觀變量后不會通過金融科技應用以外的渠道來影響商業銀行行為特征(梁方等,2022)。因此本文使用美國經濟不確定性,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滯后一期值和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滯后值與銀行總部所在省份移動電話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檢驗。
由表7可以看出,在使用工具變量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回歸系數仍然為正,與金融科技的交互項系數仍然顯著為負,說明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結果依然穩健。并且除此之外,本文還對弱工具變量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檢驗②Stock and Watson (2003) 給出弱工具變量判斷的一個經驗規則(rule of thumb),即如果第一階段的F統計量大于10, 則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檢驗結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以及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問題。

表7 工具變量法
(四)穩健性檢驗
1.替換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
為了進一步驗證文章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通過替換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銀行流動性囤積的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本文使用金融賬戶凈額與序列最大值之比(FK_T)作為跨境資本總流動的代理變量;其次,本文使用國際收支表金融賬戶借貸方之和與當年全國GDP之比(FK_GDP)作為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總強度的代理指標;另外,本文在國際收支表之外,使用地區對外開放程度(OPEN)即該地區外資企業與總企業比值,作為地區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代理指標;最后,本文考慮到流動性創造這一指標同樣能反映銀行流動性水平,一般而言銀行流動性創造能力越強,其流動性囤積程度就越低,因此本文構建流動性創造(LC)指標進行回歸,并將未使用資產總額進行標準化的流動性囤積總量(LNLH)再次作為流動性囤積程度的代理指標。
由表8可以看出,在更換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回歸系數仍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再次說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的促進作用,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8 穩健性檢驗
2.替換調節變量指標
由于本文對金融科技指標的構建是基于戰略緯度(FINT_S)、業務緯度(FINT_T)和管理緯度(FINT_A)三個層面來加權匯總的,并且三者相互聯系、相互發展,戰略金融科技化是銀行金融科技的基礎,業務科技化和管理科技化則是銀行戰略科技化的落地(謝絢麗和王詩卉,2022)。所以本文替換調節變量指標,分別對三個金融科技分指標進行回歸,從而驗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具體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

表9 替換調節變量指標
表9第(1)(2)(3)列銀行金融科技應用分指標和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交乘項回歸結果來看,其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銀行金融科技在各方面的應用均可以抑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促進作用,再次驗證了本文結論穩健性。
五、進一步分析
(一)銀行異質性分析
城商行作為中小銀行代表,在資產規模、攬儲能力以及客戶基本面等特征上,相較于股份制銀行和國有銀行而言劣勢明顯。首先,國有銀行規模較大,在業務、管理以及戰略等方面優勢明顯。其次,股份行也大多是跨區域經營,網點分布眾多,客戶規模也相對較多,創新動力強,并且股份行在經營上相對更有特色,如浙商銀行潛心探索小企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等特色業務;招商銀行的零售業務備受認可,目前又開始大力建設網絡交易銀行。因此在客戶規模和品牌效應上來看,股份銀行和國有銀行相較于城商行具有明顯優勢。另外從業務發展來看,雖然如南京銀行、北京銀行等城商行發展較快,但絕大多數地方銀行由于成立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務地方金融和中小企業發展,所以城商行很難擺脫地域的限制。而且跟各有特色的股份制銀行不同,城商行似乎也很難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業務。因此前文的實證結論可能因銀行性質的差異而存在異質性問題。因此本文將樣本銀行分為城商行、農商行、股份行和國有銀行四大類,從而分析不同種銀行間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作用效果差異。具體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銀行性質的異質性回歸結果
表10中的回歸結果顯示,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城商行的沖擊性最大,這主要是因為城商行一般以該地區客戶作為基本面,規模較小,抵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在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過程中,遭受風險擠兌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城商行相對會儲備大量流動性資產,從而導致流動性囤積水平上升。而國有銀行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回歸系數不明顯,說明在資本流動時,國有銀行并沒有出現流動性囤積現象,這可能是因為國有銀行規模最為龐大,在各地區都有客戶資源,并且信貸客戶多以國企和具備良好資質的上市企業為主,信貸資金具有保障,所以國有銀行通常并不擔心在市場投資的過程中出現流動性擠兌風險,況且國有銀行是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緩解企業融資難題的銀行主力,通常情況下對市場釋放大量流動性才是國有銀行常態。
(二)跨境資本渠道分析
由于國際收支的金融賬戶含有非儲備金融項目,以及非儲備金融下的直接投資項目和間接投資(證券投資)項目,所以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同樣分為直接投資主導的跨境資本和間接投資主導的跨境資本。在以往研究中,由于直接投資一般是股本投資,投資周期相對較長,流動性比較低,所以跨境資本直接投資往往會促進銀行盈利能力和風險抵抗能力(顧海峰和卞雨晨,2022),而間接投資則主要是投機性交易,一般以證券市場為主體,流動性較強,所以通常會降低銀行盈利穩定性。因此從理論上講,跨境資本直接投資并不會明顯促進銀行流動性囤積行為,而跨境資本間接投資則會明顯促進銀行流動性囤積行為。為此,本文接下來進一步檢驗不同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渠道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回歸結果由表11所示,其中第(1)列是非儲備金融(NRFK)的回歸結果,第(2)(3)列是直接投資(FDIR)和間接投資(FSEC)的回歸結果。

表11 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渠道分析
由表11可以看出,雖然跨境資本中非儲備金融(NRFK)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非儲備金融項目下的間接投資(FSEC)回歸系數同樣顯著為正,但直接投資(FDIR)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主要是由投機性資本引起的。這是因為投機資本的交易主體是證券市場,對市場資產價格的波動影響更加劇烈,投資交易強度的增加會造成金融市場短期興盛假象,推動企業過度進行風險投資,企業“短借長投”以及“脫實向虛”現象愈發嚴重;其次對銀行而言,間接投資交易周期較短,一般追求短線投機式交易,對國際金融周期變動情況更加敏感。當國內經濟上行時,投機資本大量涌入造成銀行負債端流動性臃腫,流動性錯配問題嚴重,并且加劇了銀行資產端的非信貸資產價值穩定性,而國內經濟上升趨勢放緩或國際經濟形勢出現變動后,投機資本開始大量撤資,銀行流動性缺口過大,從而出現擠兌危機,不得不賤賣資產來補充流動性。因此基于上述問題擔憂,當投機資本流動性強度上升時,銀行便開始大量儲備流動性資產來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造成流動性囤積程度上升。而對于直接投資引起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一般具有投資周期長、交易頻率低等特點,因此直接投資強度的上升會使銀行長期存款增加,降低銀行流動性錯配壓力。并且從實體經濟角度而言,直接投資為主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通常會帶來生產技術的溢出和轉移,有利于實體企業穩健發展,加快國內落后產業升級,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并不會抑制銀行信貸擴張行為。
(三)短期跨境資本流動與金融科技的邊際效應分析
本文進一步采用面板分位數回歸來探討當商業銀行流動性囤積處于不同水平時,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科技的作用是否存在差異,回歸結果如表12、13所示:
表12中回歸結果顯示了在不同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區別。從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流動性囤積在那個水平上,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回歸結果均顯著為正,說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是全體性的。但隨著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的上升,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程度逐漸降低,這大概是銀行流動性準備較為充分時,對于資本流動的反應程度比較低,并不會過于擔心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的負面沖擊。
表13分析了不同流動性囤積水平下金融科技的調節效果差異。回歸結果顯示,當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小于30%時,金融科技的調節效果不顯著,大于等于30%時,金融科技的調節效果開始顯著,并且調節程度逐漸上升。

表13 針對金融科技應用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從短期跨境資本流動視角出發,基于2010-2021年中國216家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現象的影響及其異質性特征,并分析了銀行金融科技應用所發揮的調節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第一,跨境資本流入強度、流出強度以及總流動強度的上升均顯著提高了銀行流動性囤積水平,信用供給端和融資需求端之間的流動性渠道難以通暢。這種影響在城商行中表現的更為明顯,對國有銀行不起作用;第二,銀行金融科技應用可以顯著降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主要通過增加利息收入、提高風險偏好以及降低信貸錯配程度和風險損失準備來緩解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第三,本文進一步分析了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渠道性質問題,發現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影響主要是基于投機性資本。此外分位數回歸顯示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存在邊際遞減效應,金融科技則存在條件邊際遞增效應。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針對對外開放、資本流動情況,政府應該合理有序地放開資本管制,建立高效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動態監管機制,并且設定針對跨境資本流出應設定科學的規模閥值,以抑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市場的集聚效應;第二,商業銀行應該借助金融科技的應用推動銀行數字化轉型,降低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銀行流動性囤積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銀行信用中介和信用創造功能;第三,由于對不同類型商業銀行而言,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其流動性囤積現象的作用程度也不同,因此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應進行差異化布局,如城商行要重點關注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情況,防范資本流動對市場風險的聚集,并且要大力發展金融科技,降低流動性囤積水平,從而既可以實現自身長期發展,也可以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助力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