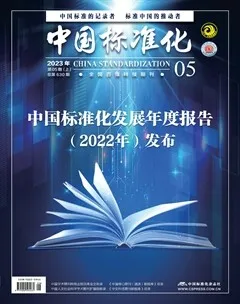論歐盟技術法規制度
摘 要:技術法規是規定技術要求的法律規范。歐盟技術法規的發展源于安全治理與區域一體化貿易治理的需求。圍繞這兩個根本目標,歐盟創新了“新方法”技術法規制度。歐盟“新方法”技術法規一改此前在文本中直接規定強制性技術要求的形式,采用間接引用、自愿遵守標準的靈活形式。為實現立法科學化與民主化,歐盟“新方法”技術法規制度使立法機關從標準化工作中脫身,對從事支持立法的標準化活動的組織施加民主要求,并通過委托制度和反對制度使標準化成果符合立法要求。歐盟技術法規制度為我國“建立法規引用標準制度”提供了比較法上的借鑒。
關鍵詞:技術法規,“新方法”,法治,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DOI編碼:10.3969/j.issn.1002-5944.2023.09.040
基金項目: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于法治、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技術法規研究”(項目編號:21&ZD192)資助。
O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of EU
CHEN Yuanyu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legal norms that specify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EU technical regulations stems from the need for governance of safety and regionally integrated trade. Based on these two fundamental goals, the EU has established the “New Approach” technical regul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technical regulation legislation. The EUs “New Approach” technical regulation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form of directly specifying mandatory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 the text to a fl exible form of indirect reference and 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 c and democratic legislation, the EUs “New Approach” technical regulation system frees the legislature from standardization work, imposes democratic requirements on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that support legislation, and restricts the standardization results through the delegation system and the opposition system to meet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regulations referring to standards.
Keywords: technical regulation, New Approach, rule of law, scientifi c legislation, democratic legislation
技術法規是規定技術要求的法律規范,是法律與標準融合的產物,以標準支撐法律的實施,對于治理與法治有重要意義。歐盟及其成員國在涉及科學技術領域立法時使用技術法規這一法律形式,圍繞技術法規形成了一系列制度,保障法治目標的實現。因此,本文對歐盟技術法規及其制度展開研究,以期為我國構建“法規引用標準制度”提供一些啟示。
1 歐盟技術法規發展的歷史
1.1 歐盟技術法規制定的動因
在歐盟各成員國,以“規定技術要求的法律規范”形式的技術法規早已有之。它是各國以法律而非政策形式,在涉及科學技術的領域提出規制要求,具體規定了某類產品或服務應當符合的特定技術要求,還可能涉及產品制造商或服務提供商未滿足相關技術要求的法律后果。例如,意大利1971年的立法要求燃氣設備滿足“最先進”的要求,經部長法令批準的UNI標準被視為符合這一條件[1]。又如,1987年法國關于擔保和售后服務合同書面證據的法律[1]。此外,奧地利政府1993年公布了包含大約80項標準的電工法規[1]。技術法規賦予了技術規范強制性,確立產品或服務質量的最低限度要求。技術法規有助于國家實現其治理目標,保護國民安全與健康、消費者保護、質量要求、保護環境、保護動植物生命與健康、減少成本提高生產率等等,是實現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然而,技術法規也可能成為技術性貿易壁壘,阻礙成員國之間產品與服務的自由流動。如果一定水平的技術標準能夠實現保護和治理目標,而一國技術法規卻選擇賦予更高水平或特別要求的技術標準以強制性,使得僅有該國本國生產商才能滿足要求獲得認證,而有意地將其他國家生產商拒之門外。此外,各國技術法規的不一致本身也會給國際貿易帶來較大不確定性。隨著全球化與歐盟一體化的發展,歐盟希望消除這樣的技術壁壘,實現貿易自由,讓消費者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選擇滿足安全要求且實惠的產品和服務。在歐盟層面制定技術法規,意在實現高水平保護與技術協調的域內治理。
為此,歐盟建立了一系列的技術法規制度或機制,其關鍵在于“協調”與“規范”。一方面,歐盟通過歐盟內部技術標準的協調一致,希望促使歐洲標準化成為區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主導力量。歐盟委員會認為,單一市場和歐洲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功取決于歐盟確保其內部和外部政策一致和互補的能力,應繼續推行其促進監管一致性的政策。而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歐盟建立一系列約束機制,保障歐盟技術法規的民主性、科學性與有效性。
1.2 歐盟成立以來舊方法、新方法的轉變
歐盟技術法規通過條例、指令、決定、建議和意見等形式實現內部市場技術協調,實現健康、安全、環境保護和消費者保護。歐盟在1985年形成了《關于技術協調和標準的新方法決議》(下稱《新方法決議》),較大地轉變了后來的歐盟技術法規形式,以此時間為界將歐盟的技術法規分為“舊方法”與“新方法”。1985年之前,歐盟委員會通過了與工業品和食品有關的大量指令,屬于“舊方法”。這些技術法規在正文或附件中直接規定了技術要求。例如大量技術要求內容被歐盟1970年《飼料添加劑指令》規定在附件中。《飼料添加劑指令》第3.1條要求成員國轉化該指令時應規定,“只有附件I中列出的那些添加劑才可以添加到飼料中,并且僅符合其中規定的要求。”附件I中就列出了飼料添加劑的名稱、化學方程式及描述,該飼料添加劑可用于的物種及其可用的最高年齡、最低與最高內容物含量濃度。例如附件I表格A.行列明,桿菌肽鋅這一種抗生素只能用于6個月以內的豬,并且其在全價飼料中的濃度不可超過20 mg/L。又如附件I表格I.行列明,所有含微量元素鐵的各種添加劑,該元素在全價飼料中的最大濃度不得超過1250 mg/L。同時,《飼料添加劑指令》正文中也規定有部分技術要求。其第3.7條就規定:“通過對第1款的部分廢除,成員國可在本指令通知后的5年內,提高本國境內的最大授權抗生素含量(附件I(A)),但E 709、E 711和E 712物質除外,具體如下:A. 奧蘭多霉素在全價飼料中的含量不超過25 mg/L……”
而相對于“舊方法”,“新方法”有以下突出的變化:
(1)技術法規從直接規定技術要求到間接引用標準。“舊方法”技術法規的特點在于技術法規直接規定技術內容細節,使得具體的技術內容成為法律的一部分,其優勢在于立法者可以通過立法程序全過程地控制標準化成果以使其符合立法者的預期立法要求。而“新方法”技術法規將不再規定技術內容的細節,而是規定技術法規對產品或服務提出的基本要求。《玩具安全指令》第10條第2款規定了基本要求:“玩具,包括其所含的化學品,在按預期或以可預見的方式使用時,不得危害使用者或第三方的安全或健康,同時考慮到兒童的行為。……”《玩具安全指令》附件Ⅱ則具體規定了物理機械性能、可燃性、化學性能、電性能、衛生、放射性等要求。盡管占據了八頁的篇幅,附件II規定的仍然是概括性要求,例如玩具機械性能要求是“玩具及其零件,如果是固定玩具,還包括它們的固定裝置,必須具有必要的機械強度,并在適當的情況下具有穩定性,以承受它們在使用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而不會斷裂或易于變形,從而造成人身傷害。”這樣的技術要求還不足以指示玩具生產商生產具有特定的強度和穩定性的玩具。技術法規及其附件中沒有如何生產產品的技術細節,這些內容則是以歐盟“實施決定”的形式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布協調標準清單。由此,技術要求從技術法規中剝離出來,成為了相對獨立的技術標準,不僅實現了立法文本的精簡,更便于技術要求增加、修訂、撤銷,畢竟隨著技術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是較為頻繁的工作。
(2)技術要求從強制性到自愿性。“舊方法”技術法規直接規定具體的技術要求,這些要求是強制性的,它在指令中經轉化為成員國法規,或者規定于歐盟條例中,生產商和服務商是必須遵守的。而“新方法”技術法規則通過引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布的協調標準來向公眾提供視同符合法規要求的技術要求細節,但它并不強制要求遵守這些協調標準。歐盟“新方法”技術法規通常規定視同符合條款,表明遵守協調標準,盡管具有推定符合法規的效力,但生產商仍然可選擇以其他方式證明產品符合法規條款和附件中規定的要求。例如《玩具安全指令》第13條“符合性推定”中規定,“符合協調標準或其部分(其引用已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布)的玩具,應被視為符合第10條和附件II所列標準或其部分所涵蓋的要求。”有別于“舊方法”技術規范的強制性,“新方法”允許法律適用者采取多種技術方式符合法規要求,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有利于鼓勵創新活力,增加法規適用的靈活性。然而,協調標準的自愿遵守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具有事實上的強制性,因為生產商往往不愿冒替代標準不被監管當局承認的額外風險[2]。
2 “新方法”制度的關鍵——保證法規與標準各自制定良好
相對于“舊方法”,“新方法”在技術法規的立法技術上作出了較大改變,增強了法規適用的靈活性和標準更新的及時性,而這一制度的關鍵在于使法規制定者和標準制定者各司其職,保證法規與標準能夠制定良好,以實現良法善治。
2.1 立法機關與標準化組織各司其職
立法部門缺乏技術標準的制定能力。技術標準對相關領域活動具有規范作用,是考慮最新科學、技術和經驗的成果,為相關領域的活動或其結果提供規則、指南或特性,追求技術上的“最佳秩序”[3]。而立法是通過規定社會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及其相互關系,實現民主、法治、秩序、自由、正義、效率、福利等法的價值[4]。標準制定與立法之間的這種差異帶來了專有知識、參與者與制定程序的截然不同。原有“舊方法”中,歐盟立法機關同時承擔了標準制定和立法的雙重工作,顯然是不恰當的。
更關鍵的是,歐盟立法機關在“舊方法”技術法規制定時,需要耗時費力地完成技術法規中技術要求的制定過程,法律規范和技術規范的制定獲得兩重程序批準。而標準化的過程往往較長,決定了整個法規的制定時間。有學者統計發現在1968年提出協調總體規劃至1983年的十五年期間,平均每年僅有10多條規定產品特定技術方面的指令被通過,這一制定速度被質疑能否解決歐盟各國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5]。
因此《新方法決議》“將定義產品技術特性的任務委托給標準”,形成一種獨特的公共與私人功能組合,在技術法規制定過程中,提出技術要求、標準化請求以及在《歐盟官方公報》上發布的行為均具有公共屬性,而制定技術標準草案則屬于私人屬性行為[6]。將立法與標準化在技術法規制定中“解耦”,歐盟委員會和理事會節約了立法的時間、提高了效率,同時提高了標準的質量。
2.2 標準制定良好以支持立法
在技術法規中,標準化支撐法律的實施,規定了法律義務該如何遵守的技術內容,作為判定行為是否違法的依據[7]。標準制定良好與否,也決定了技術法規實施效果如何。確保技術標準制定良好,就是要保證標準的技術水平先進、符合市場需求、保障安全健康、利益平衡、程序民主等。而標準化的關鍵在于標準化組織。
2.2.1 歐盟與歐洲標準化組織的緊密關系
受其歷史傳統的影響,歐洲標準化體系與其政府的關系比美國標準化體系與其政府的關系要緊密一些。這種關系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歐盟成員國或歐盟對標準化組織的承認。例如英國政府在《皇家憲章和附則》的皇家特許令正式承認英國標準協會(BSI)為其國家標準的唯一制定者。歐盟承繼了成員國在這一方面的傳統,在2012年《關于歐洲標準化的條例》(以下簡稱“《歐洲標準化條例》”)中認可了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和歐洲電工技術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三個歐洲標準化組織為歐洲標準的制定者。歐洲標準化組織CEN的成員包括許多其他標準化組織,例如歐洲標準化消費者代表協調協會(ANEC)、歐洲化學工業理事會(CEFIC)、歐洲醫療器械協會聯合會(EUCOMED)等,從而形成了一個等級化的標準化體系。有別于美國分散的標準化體系,歐盟標準化體系是以上述三大標準化組織為中心的,歐盟認可歐洲標準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國家標準作為監管標準,尤其是在健康和安全方面,避免了標準的沖突和重復工作。
二是國家對標準化組織的資助。美國標準化體系主要通過版權和會員費提供標準化活動經費,政府僅就有限的合作情況下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經費,而歐盟提供的經費是歐洲三大標準化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8]。《歐洲標準化條例》確立了歐盟政府為歐洲標準化組織提供資助的制度,這種資助不僅為了支持政府立法或政策的標準化活動,也為了支持執行歐洲標準化的一些基礎性和輔助性工作。除一般性資助外,接受標準化委托的歐洲標準化組織可以向歐盟委員會提出資金申請并得到撥款。
三是賦予標準化組織在體系內協調的權力。《歐洲標準化條例》形成了歐盟委員會、歐洲及國家標準化組織之間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停頓原則。要求在制定或批準協調標準階段,國家標準化機構不得在該歐洲標準領域發布與其不符的新的或修訂后的國家標準,且在發布新的協調標準后,所有與新制定的協調標準相沖突的國家標準均應在合理期限內被撤銷。通過停頓原則的規定,所制定的標準在較大程度上成為歐洲唯一可適用的標準。
四是歐盟政府對標準化活動的全程參與。《歐洲標準化條例》立法說明指出“在歐盟產品協調立法所涵蓋的領域,公共當局應參與標準制定的所有階段”。
2.2.2 歐盟對協調標準化活動的要求
基于歐盟與歐洲標準化體系的相對緊密的關系,歐盟委員會對歐洲標準化組織提出一系列要求,實踐歐盟“行政民主”的雙支柱——透明度與參與[6]。歐洲標準化組織應在每年度向歐盟委員會報告“為協調標準開發而開展的活動”,每年至少發布一次詳細的工作計劃,提供有關打算制定或修改的、正在制定或修改的以及在上一個工作計劃期間已采用的歐洲標準的信息。此外,有義務根據要求將任何歐洲標準草案至少以電子形式發送給其他歐洲標準化組織、國家標準化機構或歐盟委員會。
歐盟與歐洲標準化體系通過合作指南的方式確立了共同的政策目標,包括考慮公共利益以技術方案實現對立法的支持,確保可持續發展,具有高水平的安全和質量;還確立了標準化的基本原則要求,“雙方之間進行持久、公開和透明的對話是合作的根本基礎”。具體而言就是,公開透明,對所有利益負責,支持相關團體的參與并考慮其意見,確保各級與標準化組織之間的連貫性,及時和適當地回應不同部門、不同市場的需求,標準化可交付成果遵循透明度、可訪問性、開放性、效率、連貫性以及自愿工作和應用的原則。美國對法規引用的標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與參與方面也有類似的規定。美國《國家技術轉讓和進步法案》規定,除非與法律不一致或不切實際,美國聯邦政府制定行政法規應引用自愿共識標準。這個自愿共識標準的制定程序的原則是開放性、利益平衡、正當程序、申訴程序、共識(協商一致)。
為了實現行政民主的另一支柱——公眾參與,《歐洲標準化條例》確立了對代表利益相關方的組織參與歐洲標準化活動的資助制度。中小企業、消費者等利益群體由于時間精力有限、專業知識與組織能力缺乏、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難以在這樣需要專業的標準化活動中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維護自身利益。因而《歐洲標準化條例》規定其可以通過其附件III所列出的利益相關組織參與歐洲標準化組織的活動,并為這些組織參與標準化活動提供資助。
歐盟對標準化組織提出的這些要求能夠確保技術標準是以行政民主方式制定的,能夠獲得公眾的普遍認可,使引用其標準的技術法規更高效地實施。有學者認為,盡管存在一定的公開信息,但普通公民無法獲得關于這些技術委員會何時開會以及誰參與其中的信息,更不用說討論的結果和每個參與者的立場。公開透明、廣泛參與的要求沒有實際被滿足。此外,由于缺乏對于這些相關利益群體組織參與標準化權利的保障與救濟,公眾參與現狀不容樂觀[6]。但歐盟為技術法規所依賴標準化的民主參與和公眾監督提供了制度依據,仍然是值得學習借鑒的。
3 保證標準實現技術法規目標的歐盟制度創新
如果說上述制度與機制是為了確保法規與標準各自制定良好,那么歐盟關于標準化委托制度和反對制度則是為了確保協調標準符合歐盟技術法規的目的,即實現協調標準對技術法規的支撐。
3.1 標準化請求委托制度
歐盟委員會根據已經制定的法規的需要,向一個或多個歐洲標準化組織提出“標準化請求”的委托,請求歐洲標準化組織起草或修訂歐洲標準或其他歐洲標準化成果。通過請求委托制度,歐盟委員會向承擔標準化工作的組織說明歐盟技術法規的立法目的與具體標準化要求,以達到協調標準最終能夠支持技術法規實施的目的。歐盟委員會2011年第M484號標準化授權就將這一過程充分地展現了出來。歐盟委員會向CEN提出了修改《玩具安全指令》所引用的協調標準EN 71- 1:2005 +A9:2009“玩具安全 - 第 1 部分:機械和物理性能”關于某些水上玩具的技術內容。歐盟委員會在《玩具安全指令》附件II中提出技術要求為“5. 水上玩具的設計和制造必須考慮到玩具的推薦用途,盡可能減少玩具失去浮力和失去兒童支撐的風險。”該標準化授權文件中說明了歐盟委員會提出該授權是為了應對風漂移對水上玩具吹入深水的風險,這是此前協調標準并未考慮到的風險。歐盟委員會在該標準化授權中提出標準化的要求是“1) 確保標準將完全滿足指令2009/48/EC 的基本安全要求,特別是第10條和附件II 第 I.5 條。2) 確保考慮到下列對產品特性的要求。設計安全必須優先于通過說明來確保安全。- 符合預期和可預見用途的浮動穩定性;- 一個氣室失效后的最小浮力和剩余浮力。- 在使用過程中獲得保持支撐的方法(易于抓握);- 在傾覆的情況下輕松逃生,即避免任何形式的身體部位被困或纏住。3) 考慮委員會根據指令 2009/48/EC 發布的解釋性指南中對警告的要求,并確保根據預期和可預見的用途考慮警告和標記的耐久性。4) 包括一個附件,提供有關其條款與指令基本安全要求之間關系的信息,以便標準的用戶確定標準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符合基本安全要求的假設。”從這一細致的授權原因與工作說明來看,委托制度為歐洲標準如何滿足歐盟法律基本要求提供了指引。
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布特定技術法規對協調標準的引用之前,歐盟委員會還將評估歐洲標準化組織據此制定的協調標準是否符合標準化請求中的要求,這是涉及技術問題與法律目標是否匹配的評估,只有在擬定的協調標準符合要求的情況下才可公布[9]。委托書制度承擔著歐盟立法機關對標準化工作結果事前控制的功能,確保制定出的歐洲標準能有效地為歐盟法律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持。這是在高度制約和監管下的協調標準化[10]。
3.2 協調標準反對制度
除歐盟委員會外,成員國和由歐洲人民直選成員組成的歐洲議會也可以評估協調標準是否滿足根據相關歐盟技術法規中規定的要求。如果成員國或歐洲議會認為不能夠完全滿足立法要求,則將通知歐盟委員會并作出解釋。歐盟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在咨詢該技術法規相應的委員會或行業專家后,決定發布、不發布或限制性條件地發布,或是對已經發布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協調標準的引用進行保留、限制保留或撤銷。協調標準的反對制度是對標準化結果的事后審查,也是為了確保歐洲協調標準符合技術法規。然而歐盟技術法規并未賦予遵守協調標準即遵守法規的效力,而是“推定合規”,即符合協調標準推定符合法規的要求。這就意味著,協調標準在《歐盟官方公報》被公布引用之后,人們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對協調標準符合技術法規的要求提出質疑,兩者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正如上述2011年第M484號標準化授權指出的,由于在2009年《玩具安全指令》替代了1988年《玩具安全指令》后、CEN被授權修訂標準完成前,適用技術法規的玩具生產商需要修改企業所依賴的標準以遵守2009年新公布的《玩具安全指令》,即使當前《歐盟官方公報》公布引用的協調標準是舊標準。這些舊的協調標準中有許多不符合2009年《玩具安全指令》的地方,生產商不能以符合舊標準來證明其遵守了新指令。
4 歐盟技術法規制度之于法治的意義
4.1 技術法規間接引用標準的形式是立法科學化的表現
相較于歐盟“舊方法”在法規文本中直接規定技術標準內容,間接引用標準的“新方法”技術法規首先實現了文本的精簡,在節約了資源的同時便于人們對本已較為復雜的歐盟法律的理解與適用。其次,法律與標準的功能定位相對清晰。在歐盟法規中法律規范與技術規范之間的關系更為明確,技術標準規定技術要求的具體內容,而法律規范回歸規定權利義務本身,僅提出對技術的基本要求。人們在法律適用時也可以清晰地理解標準具體要求是對法規基本要求的細化,形成詳略兼宜的合規路徑。最后,技術法規間接引用標準附隨效果就是便于標準隨社會變化和技術更新而修訂,而不需要通過完整但卻耗時的立法程序。
4.2 技術法規引用標準保持自愿性,允許靈活方式遵守法律
技術法規規定了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所劃定的產品或服務所應滿足的最低要求。如果要求所有人按照規定具體技術內容的協調標準進行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必然會阻礙創新,使社會錯失技術進步的可能性。技術法規的形式允許以靈活方式遵守法律就是讓法治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尊重客觀規律的科學立法。
4.3 標準化與立法分離,立法提質提速
如上所述,歐洲標準化體系是等級的、協調的,以三大歐洲標準化組織及各國國家標準化組織為中心的。協調標準由一個或多個歐洲標準化組織制定,由各國國家標準化組織翻譯轉化為本國國家標準,以實現歐盟境內技術法規及其依照標準的實施的協調一致。由于《新方法決議》將歐盟立法機關原本承擔的標準化工作授權給該體系中心的標準化組織(即三大歐洲標準化組織CEN、CENELEC以及ETSI),從而減輕立法機關負擔。立法內容的集中與文本的精簡也帶來立法效率與質量的提高。
4.4 對協調標準化活動提出民主要求——透明度和參與
民主是法治的基石。基于歐盟與標準化組織的密切關系,歐盟在標準化條例、合作指南中均對標準化活動提出了透明度與公眾參與的要求,保證標準作為法規中的組成部分也能夠制定良好。
4.5 加強對標準化的合作與監督,使標準符合法規需求
歐盟要求歐洲標準化組織與歐盟信息互通、定期報告,加強了立法機關與標準化組織的合作;此外,委托制度與反對制度的建立保證歐洲標準只有在符合法規要求的情況下被公布作為支持法規的協調標準,才能產生相互協調、銜接良好的標準支撐法律的作用,以實現法治。
5 結 語
技術法規在我國普遍存在,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中均規定有技術要求。然而我國技術法規的制度是缺失的,關于如何更好地制定技術法規的學術研究仍然薄弱。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出 “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根本途徑。”為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中提出“建立法規引用標準制度”,我國技術法規制度構建也應朝著“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法治方向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歐盟技術法規制度將為我國技術法規的立法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與借鑒的樣本。
參考文獻
[1]SCHEPEL H , FALKE J , Legal aspects of standardis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C and EFTA volume 1 Comparative Report[M]. Belgium: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
[2]BREMER E S.American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private standards in public law[J]. Tulane Law Review, 2016, 325-370.
[3]白殿一,王益誼,等.標準化基礎[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20.
[4]張文顯.論法學范疇體系[J].江西社會科學, 2004(4).
[5]PELKMANS J.The new approach to technical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87(3), 249-270.
[6]ELIANTONIO M. Private Actors, public authorities and the relevance of public law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J]. European Public Law, 2018(3), 473–489.
[7]柳經緯.論標準對法律的支撐作用[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6):152-162.
[8]BU?THE T, MATTLI W. The new global rulers: the privatization of regul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9]聶愛軒.歐洲標準與歐盟法律的融合[J].法大研究生,2018(2): 195-213.
[10]SENDEN L. The constitutional fit of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put to the test[J].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017: 337-352.
作者簡介
陳媛媛,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民商法、標準化法。
(責任編輯:袁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