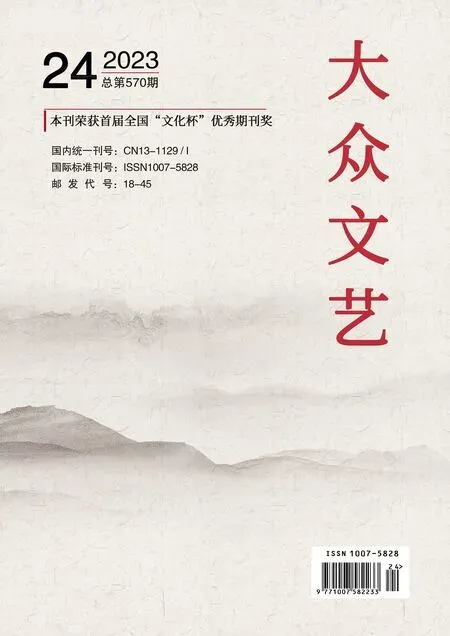人工智能視閾下的互動藝術核心課程建設*
——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為例
田 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江蘇南京 210000)
一、人工智能視閾下的互動藝術
1.從人工智能視野看藝術的流變
當下的藝術正處于以ChatGPT為代表的突破性人工智能產生的革命性藝術流變之中。實際上,我們需要更為宏觀的視野認知這場藝術領域的流變性。縱向上,追溯20世紀初藝術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近現代的藝術圖譜與其對應的觀念重構:約1916年至1960年的現代主義藝術是對傳統藝術形式的反叛,由現代主義思潮席卷而來,催生了動態雕塑、觀念藝術、激浪藝術、偶發藝術、行為藝術、大地藝術等多種結構性的藝術流派;約1960年至1983年的后現代主義藝術是對現代主義藝術的顛覆與反叛,解構了內容的意義與邏輯;而80年代末至今的藝術雖沒有公認的術語來描述,但無處不在的是藝術與技術的糾纏;如今,隨著大語言模型的出現,人工智能具備了更強的泛化和遷移能力。正如蔡新元教授所言“一切以技術為壁壘的行業終將走向終結”。人工智能已經在幾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領域超過了人類水平,具備了理解、邏輯推理、創作、情感等能力。這意味著奇點時刻降臨,意味著人類在廣袤的藝術領域里,藝術與技術糾纏時期正式落幕,意味著這場藝術敘事方式巨大變革的背后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藝術,推陳出新解決藝術領域探索的問題。既往的藝術領域認知系統與主體經驗已經難以適應當下的藝術發展趨向和要求。我們急需打破思維桎梏,重構一種適應當下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理論體系,來實現這場藝術流變的可能性。
2.互動藝術與后人類主義
互動藝術是一種由創作者制定規則,觀眾參與完成作品目標的藝術形式。互動藝術涵蓋了游戲藝術、互動影像裝置藝術、互動戲劇、互動舞蹈、互動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是由計算機信息技術催生而成的[1]。互動裝置藝術的出現標志著一場藝術形式的蛻變,基于人對虛擬和實體空間的感知,挑戰著藝術本體與社會思想。該空間包含物理范疇的空間(如形狀、大小、深度、方位等)、知覺范疇的空間(如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社會意識形態空間、審美空間等多個維度[2]。混合空間又集結成一個藝術場域,觀者的行動被當下的場域影響,與作品之間產生了行為與意識上的互動,這是一種場域的互動和轉化,互動裝置藝術通過這種形式完成了內容與情感的整體性表達。簡言之,互動裝置藝術是藝術探索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藝術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借助了材料、技術、影像等手段,創造了與以往藝術形式所迥異的新藝術范式。然而,它的核心表達仍然是受啟蒙運動影響的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理念,是人類意識形態由神本主義轉向人本主義的重要結果。
互動藝術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以信息技術為支撐,解構了當代語境下的人與物、空間建構以及藝術創造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哲學、社會學、物理學、心理學、生命科學等多種不同維度拓展了互動藝術的認知系統和創造規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人類生命在“人類學機器”的機制下越來越工具化、越來越貧乏。追溯馬克思資本主義異化勞動導致人的異化,思考阿甘本“生命政治”的轉向,人類已經敏銳地意識到生命是多重的,既可以是生物化學過程,也可以是社會-政治存在[3]。隨著生物技術對身體的改造、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及動植物的處境,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史前時代至今人對動物的馴化史,不得不思考人與機器、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人與他者、物質與非物質的關系及界限。在巨大的觀念沖擊中,主客體二元論得以消解,人本主義意識形態逐漸發生轉向,后人類主義呼之欲出。后人類將人類從慣性認知中抽離,人類主體性的基本假定發生了重大轉變,人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他者,群體意識中人類中心主義這一觀念的慣性表達宣告終結。后人類挑戰了人本主義思考人與萬物關系的傳統,人的優越性、獨特性與唯一性被打破,新的議題、新的倫理成為一種常態。作為后人類的我們如何用一種新的在場思考互動藝術?這為互動藝術的理論與實踐帶來了一條重要的探索分支。
二、人工智能視閾下的互動藝術課程建設的核心思路
縱觀現有知識體系,不難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規律,即專業領域的周期性,與之對應的是各行業的發展周期,其背后是以人類經濟發展為驅動的全球大型機器的運轉,現代教育系統為此存在。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建立依托于科技與媒體藝術的融合,互動藝術的互動性建立在技術、傳播媒體、文化之上。大語言模型帶來了技術的顛覆,在不斷迭代的人工智能面前,知識的應用,教學的方式,人才的培養如何智慧地進行戰略應變和價值定義,這成為未來藝術設計教育面臨的重大課題,為藝術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機。藝術家們不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解決技術難題,而是可以將精力投入藝術創作的內容表達上。這一轉變解決了以往由于時間稀缺造成的視閾狹隘等問題。隨著近年來全球化趨勢逆轉,我們不得不關注去全球化發展,數字媒體專業的建設必須以服務我國國家建設和行業發展需求為核心,互動藝術課程建設理應緊隨時代脈搏,緊密關注當下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核心課程的建設,需要考慮如何適應技術壁壘的打破,積極應對后人類主義思潮的轉向。
筆者認為,透過數字媒體藝術專業課程設置的表象,深入挖掘藝術本體與人類發展本質,立足于大語言模型的重大突破,著眼于未來數字藝術的可持續性發展,以數字藝術驅動國家文化建設是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的重要任務。而互動藝術核心課程建設需要以未來數字藝術發展為導向、以跨學科為視點,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藝術編程教育,培養掌握編程能力、后人文素養、創意思維和藝術創作能力的數字媒體藝術應用型人才。
三、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互動藝術課程的問題與對策
1.南航金城學院數字媒體藝術人才培養定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是一所綜合類應用型本科院校,數字媒體專業藝術專業基于學校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培養定位,以媒體藝術設計、數字影像設計、信息交互設計為培養方向,以遞進式人才培養模式,圍繞“一條主線,兩個強化,三個突出”展開。一條主線即培養現代信息技術背景下數字媒體藝術需求的寬口徑復合型人才為主線,兩個強化是指強化校內學習,校外實習,從而形成課內與課外融合,三個突出是指突出信息化場景下數字媒體藝術的特色,突出寬口徑數字媒體藝術崗位的復雜業務場景,突出應用型數字媒體藝術行業的適應性。
2.當前互動藝術課程建設問題
根據數字媒體行業的發展要求,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該專業現階段課程建設存在些許問題:其一,該專業以傳統數字媒體藝術人才培養為導向,著眼于教授藝術設計類課程,缺乏藝術編程教育。其二,學生花費大量時間長期訓練藝術技能,包含素描、色彩、各類計算機設計類軟件等,專注于藝術技能的訓練會讓學生忽視其他事物,陷入稀缺,而稀缺會導致管窺,學生的視野變得狹窄,只能透過“管子”的孔洞觀察藝術技能訓練,容易無視管外的一切。而互動藝術的創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可視化的編程能力,學生若是只將注意力傾注在藝術設計類理論課程及技能訓練上,學校沒有相關藝術編程帶領學生走出管窺之見。缺乏編程教育和長期進行藝術設計類訓練的雙重背景下,學生會因缺少了解產生編程學習的畏懼心理。稀缺和畏懼這兩大心理因素容易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難以跨越自身專業素養的局限,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行業需求,難以有效參與我國數字媒體專業建設,更難以應對國際競爭。其三,實驗室與設備的缺乏。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為學生提供了蘋果機房、攝影機、各類攝像頭、投影儀、追蹤器、影像傳感器、VR設備、建立了數字影像實驗室,但缺少3D打印機、金屬切割機、注塑機等。其四,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藝術編程教育改革問題。隨著大預言模型的迅速迭代,傳統的藝術編程教育已經無法應對時代的課題,我們不能照搬以往的經驗應對當下的挑戰,而要積極調整以適應新的態勢變化。
3.基于人工智能視閾下的互動藝術課程建設的優勢與對策
南航金城學院互動藝術課程建設的優勢在于學校內部擁有完善的信息技術類專業體系,這為互動藝術提供了寶貴的技術支持和資源基礎。然而,數字媒體藝術專業隸屬于藝術與傳媒學院,信息技術類專業隸屬于信息工程學院,兩者之間較為孤立,學生目前缺乏選修其他學院專業選修課的權限,校內專業間未形成健全的交叉教學探索,這限制了跨學院的合作交流。為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對策如下:其一,在校內建立密切合作的生態系統,開通跨學院選修課程權限,以“校、院、專業”三位一體建立合作機制,打通專業間的交叉課程建設,形成合作閉環,資源共享。通過這一合作模式,學院可以共同開設跨學科課程,探索項目教學、工作坊,通過合作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從不同領域獲得豐富的經驗,拓寬視野,增強綜合素養。其二,將人工智能助手引入互動藝術課程。這一舉措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編程語言,理解基本概念,熟悉語法規則,并掌握各種開發工具。有助于培養數字媒體藝術領域所需的創新應用型人才,更好地適應不斷發展的行業需求。其三,爭取經費購置所需設備,為跨學院工作坊、項目教學等提供有力的支撐。
四、以編程教育和后人文素養教育為核心的互動藝術課程建設
1.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藝術編程教育
互動藝術在技術上需要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基礎,通過傳感器、控制器、執行器來感應溫度、光線、距離、濕度、熱量、氣象等因素的變化[1],用編程語言引起互動行為,結合物質實體與社會文化思潮,通過有效選擇,完成帶有作品思想傾向的解構與建構,輸出視覺效果,闡述作品目標。由此可見,編程語言在互動藝術創作中尤為重要,常用的編程范式有命令式編程、聲明式編程、函數式編程、面向對象編程等。學生需要了解不同編程范式,適應不同的創作需求。國內外各藝術院校將編程語言納入藝術類專業課中,常用的新媒體藝術工具有Processing、Touch Designer、Arduino、Unity等。
然而,隨著大語言模型的迅速迭代,傳統的藝術編程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將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融入互動藝術創作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其一,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創建個性化學習平臺。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進度和興趣,定制教材、教學內容、練習等學習資源,協助學生有效的理解編程概念、提升編程技能,此外,平臺提供自動化調試和反饋,幫助學生快速發現并解決編程中的問題,糾正錯誤和改進代碼,從而更好地理解編程原理;其二,將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技術作為創作助手,開發情感識別系統,捕捉觀者情感狀態,如面部表情、肢體語言、聲音情感分析等。互動藝術作品根據觀者情感、肢體變化調整互動行為。學生通過利用這些技術為藝術作品提供新的創作思路和創意資源。技術壁壘終將被打破,死磕代碼應對不了未來的發展趨勢,唯有順勢而為,以變動應對發展,快速搭建新模式下的藝術編程教育,將人工智能融入互動藝術創作和編程教育方可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2.以綜合實踐類課程建設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
互動藝術課程建設強調藝術創作及互動性,需要學生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提升技能。在人才培養中,應意識到互動藝術中的編程教育、后人文素養教育和藝術創作之間的緊密聯系。而綜合實踐課程可貫穿藝術創作始終,致力于教授學生融會貫通的學習方法,掌握知識體系的煩冗,將獨立的知識點形成知識網絡,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專業需求、應對挑戰。綜合實踐課程應以項目驅動為核心,可涵蓋多個方面,包括以發光裝置為主的材料藝術表達,以VR、AR等媒介為基礎的互動藝術項目等。這些課程可以從編程、材料應用、設備操作、藝術表達等多層模塊進行解構,按階段訓練學生,增強他們的探索和實踐能力,培養跨學科思維。鼓勵學生積極探索和嘗試,與不同背景的同學共同工作,更好地應對日益復雜的互動藝術挑戰。倡導學生自主研究互動藝術,加強實踐能力,從而更深入的理解互動藝術領域。
3.基于后人類視閾下的后人文主義教育
人文素養教育著重培養學生的思想和品行,旨在將其內化為個體的人格、氣質、修養,引導學生正確處理人與場域的關系,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教育視閾。后人類主義站在生態危機、動植物處境、技術迅速擴張引發的倫理和道德挑戰之下,瓦解了傳統生物學意義上人的概念,擴展了人權話語和人類精神生命的討論,滋生出人類與非人類界限、生命形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世界觀和倫理主張,重審了人文主義教育學傳統。后人文主義教育標志著多元文化教育,是對人文教育的繼承、批判與反思,促進現代教育轉向萬物共生的教育視角,鼓勵學生深入思考文本、媒體和信息構建,是解決現代社會困境的可能性思路。
探討互動藝術核心課程問題,不可避免地提及數字媒體行業發展,行業發展的周期性又繞不開全球化進程中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技術、教育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一系列社會議題迫使人類社會正視人文教育的局限,舊的話語體系被不斷解構,后人文主義教育提供了一個有別于人文教育的思想框架,這種轉向需要克服思維的桎梏,重審現代人文主義教育體系,放下人類中心主義,重塑人與萬物的關系形態,走向萬物共生哲學思潮下的后人文主義。這種轉向意義深遠。
五、結語
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人工智能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人類知識體系的整體意識正在不斷加強,我們從專業的解構、建構到整合,跨學科概念的提出是將人類知識體系從單一過渡到多元的過程,個體的發展離不開國家這艘巨輪運轉的大方向,全球化趨勢收緊的背景下,各個專業的建構都需要立足于發展學的視角,打破固有思維的桎梏,注入新的活力,實現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可能。如今,各高校都在關注人工智能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我校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創辦時間晚,缺乏藝術編程教育,相比國內其他應用型本科院校而言,競爭力略顯薄弱,筆者認為互動藝術核心課程的建設應以編程教育、后人文素養教育、藝術設計教育為核心,整合現有藝術與信息技術類專業資源,以合作交流為導向,融合互動藝術綜合實踐類課程體系,培養適應時代的互動藝術創新應用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