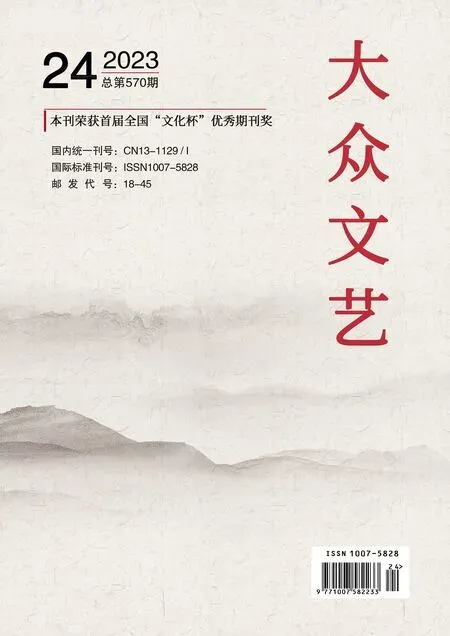先秦至南北朝:七夕節的起源、成型與發展
楊 宇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河南開封 475000)
一、相關研究評述
關于七夕節的起源,自20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過探討,筆者在此擇要列舉部分代表性成果。張君認為,七夕產生于戰國時期的楚國,脫胎于“漢之游女”的神話,織女的神性和七夕乞巧祈愿的習俗與楚地的少司命信仰關系密切。[1]吳天明認為,七夕文化源于夏人的原始宗教和夏代歷法,牛女傳說的本質是對華夏諸族青年男女七月七日夜祭祀先妣、月神、織女神時放縱野合習俗的反映。[2]劉學智、李路兵認為,牛女傳說和七夕早期節俗均產生于西漢初的長安,七月七日是因牛女傳說融入方成為“七夕”并作為一個紀念性節日而存在。[3]隆滟認為,七夕節的存在建立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其名稱和節俗都跟農耕習俗息息相關。[4]趙逵夫認為,七夕節誕生是受牛女傳說影響,而牛女傳說早在先秦就已經出現。[5]蕭放認為,七夕經歷了從兇時惡日到良辰吉日的歷史變化,這背后隱藏著古代社會民眾時間觀念的重大變遷,漢代以前七夕就已經出現,只是不一定在七月七日,可能在七月朔日。[6]劉宗迪認為,由于歷法不夠精確,七夕節在西漢末王莽時期之前日期并不固定,是東漢才固定為七月七日并因之成為一個節日,而七夕節所依托的織女崇拜則早在先秦就出現了。[7]以上研究從不同角度出發對七夕的起源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盡管在一些觀點上有出入,但基本有一個共識,即七夕節雖然大致在漢代才完全成型并正式成為一個節日,但早在漢代之前七夕文化及部分節日元素就已經存在。
關于兩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七夕節研究,根據主題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研究從民俗學、歷史學角度入手,重在對七夕發展歷程進行梳理和對七夕節俗進行考證與釋讀。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陳連山的《論七夕節的源流》、趙逵夫的《七夕節的歷史與七夕文化的乞巧內容》、蕭放的《七夕節俗的文化變遷》、劉宗迪的《七夕的歷史與神話》等等。這些論文論證充分、考證翔實,但大都主要論述漢代部分,關于魏晉南北朝的論述相對簡略。此外,山東大學馬瑩的碩士論文《北朝七夕風俗與西域文化》詳細考證了北朝七夕講武馳射的風俗之由來及其特殊性,彌補了學術界關于北朝七夕研究的空白。
另一類研究主要是從文學角度入手,以七夕詩歌、牛女傳說為主題進行的文學文本研究,且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的牛女傳說和詩歌中的七夕書寫。其中屬于學位論文且較有代表性的有青島大學王愛科的碩士論文《牽牛織女神話傳說與七夕節的起源》、中南民族大學邱綺的碩士論文《傳統七夕節演變歷程與現代轉型》等。學位論文以外,也有一些期刊論文值得關注,比如徐傳武的《漫話牛女神話的起源和演變》、鄭慧生的《先秦社會的小家庭制與牛郎織女故事的產生》、杜漢華與華漢文的兩篇同名論文《“牛郎織女”流變考》、劉宗迪的《七夕故事考》、趙逵夫的《牛女傳說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播與分化》與《由秦簡<日書>看牛女傳說在先秦時代的面貌》、傅功振和樊列武的《長安斗門牛郎織女傳說考證與民族文化內涵》、趙依的《“牽牛織女”傳說的起源與流變》等。以上論文均對這一時期的七夕節有所涉及,但皆非以七夕節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史料和文學文獻資料對隋唐以前的整個七夕節發展史做一個梳理,分階段論述七夕節從孕育到形成再到初步普及的整個歷史過程,并突出其在每個階段、每個時代的發展變化和主要特點,以期探明源流、從整體上把握七夕節的早期發展歷程。
二、秦漢之前:七夕節的起源與節日元素的孕育
一個節日的誕生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既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特殊的契機,又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七夕節雖然在漢代才正式成為一個節日,但是促使七夕節產生的文化元素早在秦漢之前的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七夕節的起源,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響:
第一,周秦之際,“農業革命”的發生確立了以耕織為中心的新的生產方式,并催生出日漸精密復雜的歷法體系。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傳播,鐵犁牛耕代替刀耕火種成為更先進的生產方式,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漸確立,與此同時,自西周起“一夫一妻”逐漸成為主流的婚姻模式和主要的家庭建構方式,單個家庭逐漸取代原始部落或族群等集體單位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組織單元,這種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革新徹底改變了周秦時期華夏先民的社會生活,使得中國古代先民們產生了新的更為復雜的生活需要,正是這些新的生活需要催生了封建社會日漸精密龐大的歷法系統和節日體系,七夕節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劉宗迪認為,節日的誕生有賴于天文學的進步和文字的使用,需要有成熟的歷法系統確立其日期,乞巧習俗和織女崇拜可能早在“觀象授時”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但七夕節遲至漢魏時期才正式誕生,這是更為發達的“按月計日法”代替“干支紀日法”因而把七夕確定在“七月七日”這一天的結果。[8]
第二,古老的星辰崇拜也對七夕節的形成和發展影響重大。一般認為,對七夕節來說影響巨大的牛女傳說便來源于原始先民的星辰崇拜,是先民將星辰形象化、擬人化以后產生的結果。這種星辰崇拜起于何時已難以考證,但不會晚于西周,因為牽牛、織女并列出現最早見于《詩經?小雅》中的《大東》篇。此外,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中也有關于二者的記錄。有學者據此以為牛女傳說大致產生于周代。比如蔣明智認為,西周時已有天孫織女與牛郎結合卻因違背天帝意志而為天河所阻隔、只能一年一度鵲橋相會的傳說,他明確指出這正是西周“一夫一妻專偶制”確立的結果。[9]在對秦簡《日書》進行考證后,趙逵夫認為牛女傳說“在戰國時代已大體形成同后代基本相同的情節,主要人物的身份特征也基本確定”。[10]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熊鈿認為,僅憑《詩經》和睡虎地秦簡中語焉不詳的片段記載無法證明牛女傳說在周秦時期便已形成,但是她也指出,就算《詩經》和秦簡并不能直接證明牛女傳說已經形成,二者對其形成過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因為二者關于星象的擬人化記載和情感化表達以及將“牽牛”“織女”并列對舉的做法,極易給人造成一種“門當戶對”的印象,激發人們的浪漫聯想。此外,星象本身也為民間故事的創作提供了素材。[11]
第三,先民對數字“七”的崇拜也值得注意。鐘年在梳理漢族及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后發現,在與女性相關的描述中數字“七”大量出現,鐘年據此認為是初民在觀察女性生理周期或生命發展節律后發現女性的基本生理現象往往與“七”有關,從而形成了對數字“七”的信仰。[12]這種信仰既然在神話中有所反映,毫無疑問,其早在文明初期就已經存在。而《黃帝內經》在“上古天真論”中確實存在這類說法:“女子七歲腎氣實,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13]該書對男女生理規律進行總結,認為女子每七年發生一次生理變化,男子則是八年。此外,關于數字“七”,萬建中認為,一般來說在中國傳統時間觀念里單月單日都是不吉利的、非兇即惡的,像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莫不如此,然而數字“七”則是時間觀念中的“一個圣數”,因而在單日里,只有逢“七”才具有吉祥的象征意義,而這種現象是在《莊子》《周易》等先秦典籍里已經有所體現的。[14]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對數字“七”已經產生了特殊的認識,這對七月七日在歷法體系中被凸顯出來無疑是有促進作用的。《太平御覽》中也確有“七月七日為良日”“七日為陽數”的記載。[15]可見數字“七”與眾不同的神圣性使得七月七并不像五月五、九月九一樣被視為惡日,而是一個吉日,其帶給民眾的情緒體驗和心理暗示也偏向積極或中性,后世七夕節祈福乞巧的主題和喜慶歡樂的氛圍可能就與先民對七月七的偏愛有關。不同的是,蕭放認為七夕節早期的節日主題也與“分離”“禁忌”有關,西漢中期以后才逐漸由兇趨吉。[16]筆者以為,這與數字“七”被視為圣數并不矛盾,或許正是因為數字“七”意義特殊,才促使七夕節很早就完成了由兇趨吉的轉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說法認為,七夕節在戰國時就已經出現。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明代。羅頎《物原》云:“楚懷王初置七夕。”[17]亦即七夕節可能在戰國末期的楚國就已經存在。但是這個說法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物原》一書雖為更訂北宋高承《事物紀原》而作,但是《事物紀原》全書并無這一說法,此說當為羅頎增補,除羅頎《物原》外,此說別無材料可供印證。二是羅頎為明代人,距離戰國遠甚,不知其材料出處。三是書中較多提及神話人物,有“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的說法,混雜神話與歷史。[18]因此,此說的真實性成疑,孤證不立,故而“楚懷王初置七夕”也只是一種可能,尚無足夠的材料支撐。
三、兩漢時期:七夕節的成型與相關傳說的發展
漢代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伴隨著政治統一和經濟繁榮,文化也出現了大發展。作為漢帝國的首都,長安的文化更是引領時代風潮,在漢代終于發展成一個正式節日的七夕節便誕生在漢都長安。漢代七夕節情況如下:
第一,西漢時,七月七日可能已具有了節日的屬性,至遲在東漢,七月七日已然成為一個節日。據筆者考證,“七夕”一詞可能最早出現在西漢。《西京雜記》中有“七夕穿針開襟樓”這一條目,這是現存古籍中關于“七夕”一詞的最早記載。此外,其書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俱以習之”[19],又引戚夫人侍女賈佩蘭之言云:“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受”[20]。這些記錄雖然簡略,但卻是現存古籍中關于七夕節俗的最早記錄,無疑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只是,《西京雜記》為西漢劉歆所作、東晉葛洪輯錄,成書時距離西漢已十分久遠。如所載屬實,則說明西漢初七月七日已然成為一個節日,有登樓穿針、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羈五色縷等多種節俗。不過,這僅限于皇宮之中,是宮廷中人的專屬活動。到了東漢,七夕節已正式誕生。據崔寔《四民月令》載:“(七月)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藥丸及蜀漆丸;曝經書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21]作麹即制酒,蜀漆丸據傳有給書或衣服防蟲蛀的功效,干糗即干糧、糧食,葸耳可制蠟燭。可見在東漢,七夕節已經有了釀制酒、做防蟲丸、曬經書、曬衣服、制干糧、采葸耳的節俗。這些記載是關于七夕已然成為一個節日的有力證明。
第二,牛女傳說也在漢代逐漸成形。司馬遷在《史記》中講解星宿時明確指出,“織女,天女孫也”[22],可見司馬遷時代有織女為天孫的神話流傳,司馬遷有所了解,只惜未詳加記述。但在東漢古詩《迢迢牽牛星》中,已有關于牛郎織女分隔銀河兩岸不得團圓的描寫。此外,東漢班固的《西都賦》也明確指出,在“昆明之池”旁,“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23]可見牽牛織女的形象已經形于建筑之中。由以上材料可知,至遲在東漢,牛女傳說就已經出現。只是此時,牛女傳說尚且還不能算作七夕節的傳說,二者尚處在各自獨立發展的階段。
第三,七夕節適應漢代人追求長生、仰慕仙道的需要,變成了一個具有神異色彩的節日。漢代人普遍渴望修仙得道、長生不老,他們將這種期待與七夕結合起來,演繹出一系列具有神奇色彩的傳說。據《太平御覽》載,《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中有關于漢武帝與西王母七夕相會的傳說,《列仙傳》中有關于王子喬七月七日駕鶴飛升、陶安公七月七日乘龍飛升的傳說,此外梁代文獻《荊楚歲時記》中也有關于竇太后七夕遭遇神跡的傳說。[24]從這些傳說可以看出,在漢代,七月七日被視為可以偶遇神跡、結交仙人、飛升得道的吉日。正如前述,牛女傳說雖在東漢已經存在,但尚未完全融入七夕節。而漢至南北朝文獻中記載的這些關于七夕奇遇的傳說,卻是真正屬于七夕節的傳說。另外,這些故事的主人公皆為貴族,可見七夕節此時還主要在上層社會流傳。
漢末三國歷時較短,史料有限,未能發現關于七夕節的記載。但曹丕《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25]的千古名句明確點出了牽牛織女,并以此比擬人間不得團圓的夫婦,很可能便是對牛女傳說的化用。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七夕節的發展與初步普及
魏晉南北朝時期,七夕節的發展情況則比較復雜。一方面,由于社會屢遭動蕩,民眾無法長期安居樂業,正常的社會生活難以持續進行,這必然對七夕節的發展和普及有所阻礙。但是另一方面,在兩漢的基礎上,這一時期七夕節也并非毫無進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至漢末魏晉,牛女傳說終于徹底融入七夕節。關于七夕節何時開始與牛女傳說發生聯系,學術界尚無定論。趙逵夫通過釋讀《周易》中《復卦》與《既濟卦》后指出,卦爻辭中“七日來復”“七日得”等描述與牛女傳說的情節符合,牛女傳說可能早在先秦就與七夕發生了聯系。[26]陳連山在對秦簡《日書》進行釋讀后也認為牛女傳說在先秦便與七夕關系密切,秦簡中牽牛織女結婚的日子大概在正月或七月。[27]蕭放認為七夕自漢武帝時期開始由兇日向吉日轉變,而漢武帝與西王母故事中青鳥的存在為漢代人將烏鵲引入牛女傳說發展出鵲橋相會的情節提供了依據,他進一步指出,七夕由兇到吉的轉變與牛女傳說的成熟是大致同步的,七夕這一轉變在漢魏初步完成,而牛女傳說也在漢魏基本成熟。[28]劉宗迪的觀點前文已有陳述,他在釋讀《夏小正》等文獻后認為織女崇拜及相關神話傳說先秦時已經出現。[29]綜合考量以上研究,可以發現雖然學者們對于牛女傳說與七夕建立聯系的具體時間意見不一,但基本都認為早在先秦時期二者就已有關聯,傳說與節日都經歷了一個由粗疏簡單而變得細密成熟的過程,而且基本同步。《淮南子》逸文中也有“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的記載。[30]但更直接的證據則是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該書在描述七夕節時,記載了某人乘浮槎見牛郎而客星犯牽牛、牽牛為娶織女借天帝錢下禮不還、漢竇太后少時于七月七日看織女而神光照室等三則傳說,并引用傅玄《擬天問》等典籍對“乞巧”的儀式流程進行了講述,這些記載都明確指出牛女是于七月七日相會、民眾有七月七日向織女乞巧的習俗。[31]由此可知,至遲在南北朝時期,牛女傳說已經徹底融入七夕節。
第二,在節俗形式方面,魏晉南北朝的七夕節繼承漢代并有所發展,魏晉士人佯狂傲世的風氣和南北朝士人詩酒風流的傳統均在七夕中有所表現。魏晉南北朝的七夕節繼承了漢代七夕的主要節俗,包括穿針、祈牛女、曬書、曬衣服等,并將之發揚光大,以至于留下了許多典故。比如《世說新語》中就記載了阮咸曬衣、郝隆曬書的故事,盡顯狂人風范。漢代七夕雖有穿針、祈牛女的節俗,但并未言明有乞巧,到了魏晉南北朝則非但明確提出乞巧,更發展出乞福、乞壽、乞子的新節俗,向牛女祈愿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據《太平御覽》引西晉周處《風土記》載,“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幾筵,設酒酺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此外,還要吃“湯餅”。[32]《荊楚歲時記》載:“是夕,婦人結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33]可見,漢代的穿針節俗被發揚光大,有七孔針,還以金、銀等貴金屬為針,奢靡浮華之風可見。此外,蛛絲乞巧此時也已經出現。晉張華《博物志》中甚至有關于海外島民“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沉海”的記載。[34]此說可能是對當時海外島民基于某種信仰而產生的人祭習俗之記載。
第三,在魏晉南北朝,七夕節較之漢代在上層社會更加盛行,在南朝民間和北朝也都有了一定的傳播。這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果說在漢代詩賦中七夕及牛女傳說只是偶爾出現的話,隨著魏晉南北朝詩歌創作的興盛,七夕題材已經頻繁出現在上層文人的詩文中。經筆者考證,魏文帝曹丕,西晉陸機、潘尼,南朝宋顏延之、謝靈運、謝惠連、謝莊、鮑照,南朝齊謝朓,南朝梁庾肩吾、劉孝儀,南朝陳江總等人,均有以七夕或牛女傳說為主題的詩歌流傳于世,如謝靈運《七夕詠牛女》詩等。而南朝梁君臣更把七夕作為御前創作的主題之一。南朝君王中,宋武帝、梁武帝、簡文帝、陳后主等人均有七夕詩傳世。這些詩人及其作品的存在標志著七夕節至少在當時的上層社會已經是頗為重要的節日,以至于那些達官貴人和文人墨客均要以七夕及牛女傳說為主題或素材進行詩文唱和,尤其是在七夕節這一天。此外,《太平御覽》引顧野王《輿地志》載,“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35],足見穿針之俗在南朝宮廷十分流行。
在南朝民間,七夕節及牛女傳說此時已經有了一定范圍的傳播。樂府民歌中已有關于牛女傳說的內容。《七日夜女歌九首》中有“春離隔寒暑,明秋暫一會。兩嘆別日長,雙情若饑渴”的詩句,全詩都圍繞牛女傳說展開,表達了對牛女一年一會的無奈和雙方的相思苦戀之情。[36]《月節折楊柳歌十三首》之《七月歌》更是明確點出牛郎織女:“織女游河邊,牛郎顧自嘆。一會復周年。折楊柳,攬結長命草,同心不相負。”[37]這兩首民歌均講述牛女故事,并明確指出牛女相會是發生在七月初秋時。
在北朝,七夕節也擁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逐漸被北朝貴族和文人所接受。這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受南朝七夕文化及游牧民族傳統影響,北朝發展出七月七日講武馳射的習俗,二是北朝文人也有寫作七夕詩的行為。據《魏書》載,北方拓跋氏政權素有七夕騎射的傳統,早在北魏追封的高祖、十六國代國君主拓跋什翼犍時就有“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為常”[38]的習俗。馬瑩指出,北魏拓跋氏堅持本族文化,將七夕講武馳射之風世代延續,以至于成為北朝定制,每年都必須舉行,形成了具有北朝特色的七夕節俗,成為史上僅有的一例。[39]此外,受南朝影響,北朝文人也有七夕詩流傳,比如北齊邢邵的《七夕詩》,其中“盈盈河水側,朝朝長嘆息”“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等句明顯是以織女為寫作對象。[40]這說明牛女傳說在北朝文壇也較為盛行,該詩哀婉凄美的風格更是明顯習自南朝宮體詩,南朝對北朝影響之深可見一斑。除邢邵外,現存的北朝七夕詩尚有魏收《七月七日登舜山詩》、溫子昇《搗衣詩》與庾信《七夕詩》及《七夕賦》等。魏詩主要抒發懷抱,內容與七夕無關。[41]溫詩中有“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等句,明指七夕。[42]庾信的《七夕賦》也有“睹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針鼻細而穿孔”等句,描述了七夕觀星、穿針的習俗。[43]
五、結語
七夕節從萌芽孕育到正式成型再到初步普及,每一步均跨越了漫長的歷史階段。通過系統梳理七夕節早期的演變歷史可以發現:古代七夕節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有到興的過程,其雖然在漢代才正式成型,但卻在秦漢之前便開始醞釀,是受多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七夕節的性質、主題及其早期節俗也都處于動態演變之中,七夕并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喜慶的、以乞巧為主要節俗的節日;七夕節的誕生與牛女傳說和織女崇拜有關聯,但其發生聯系的確切時間和內在的互動機制尚不確定,可以確定的是牛女傳說是在魏晉南北朝才徹底融入七夕節。
據此可以判定:七夕節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從一而終的所謂“傳統”,其節日性質、節日主題、節俗形式和節日傳說甚至節日日期都是在文明演進的歷史過程中動態演化出來的。七夕節早在魏晉時期就因牛女傳說而擁有了濃厚的愛情元素和浪漫色彩,其在當代向情人節轉化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據的,從樂府民歌和南北朝七夕詩中的七夕書寫可以發現,七夕節及牛女傳說早就建立了歌頌愛情、抒發相思的文學傳統,早就在人們心中打下了以男女情愛為作為節日主題的心理基礎,只是古代中國并無情人節這種說法,但是到了當代,部分民眾受西方情人節刺激和啟發把七夕節當作中國情人節也就順理成章了。
節日發展有它自己的邏輯線索和獨特的生命歷程,忽視節日的發展邏輯和文化基因去審視其動態演變是不客觀的。對節日演變過程和發展邏輯的揭示,無疑會對我們看待和處理當下及未來的現實問題有所幫助。對于七夕節來說,只有厘清其歷史源流和演變過程,方能理解其如何發展為當下的狀況。在這方面還有待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