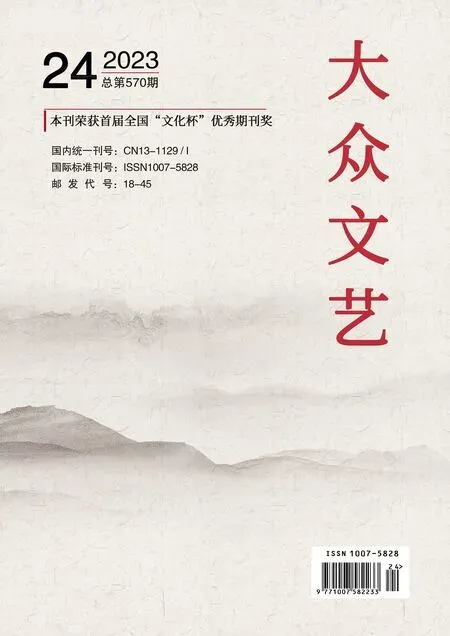《盜夢空間》的死亡-重生謎題解析與對創意寫作教學的啟示*
田 昊
(廣東工業大學,廣東廣州 510006)
上映于2010年的《盜夢空間》,一直被尊奉為經典燒腦神片。即便上映多年后,對該片的邏輯、細節、內涵等方面的討論仍然持續不斷。諾蘭導演以其慣有的打亂時空的非線性敘事,深入到人的無意識世界中,構建出多重夢境并與現實交織,確實讓不少觀眾迷惑又沉醉其中。《盜夢空間》這類刻意讓敘事變得錯綜復雜、預留多處符號隱喻,從而邀請觀眾參與解謎的電影,通常也被稱為謎題電影。大衛?波德威爾在《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中就從觀眾認知的角度將謎題敘事描述為:“拍片者創造出令人困惑的故事時間模式或因果關系,而相信觀眾可以通過重看電影找到線索……謎題電影就是要讓我們全神貫注于敘事形式的動態變化。”[1]沃倫?巴克蘭在《好萊塢謎題電影》中則從敘事的角度指出,“謎題電影的復雜敘事策略指的是非線性的環狀時間、碎片化的時空……裂隙、欺騙、迷宮般的結構、不確定的意義、不可靠的敘事者”[2]。謎題電影的復雜敘事策略契合了互聯網時代習慣碎片化時空、更愿主動參與并反復觀看故事的觀眾特征。于是,對數字化時代的故事書寫來說,便尤為重要。因此,對于謎題電影的敘事分析,不失為當下創意寫作教學中提升復雜性敘事思維與能力的必不可少一環,而《盜夢空間》無疑是其中頗為值得細細研讀和學習的范本電影。
一、二元特性與limbo困境
《盜夢空間》留給觀眾的謎題頗多,從觀眾角度來說,最意猶未盡的通常都會是影片設定的開放式結局——陀螺到底有沒有停下?但從創意寫作教學的視角出發,首先需要抓取的謎題卻是要從影片創作的緣起開始,也就是主人公在電影中需要解決怎樣的問題?在哪里解決問題?如何解決問題?這也是我們寫作故事時的前提。
看似復雜的《盜夢空間》,實際上嚴格遵循了好萊塢標準的英雄之旅的三幕劇結構,即接受召喚-試煉對抗-重生回歸的線性結構形式。這是一套源自美國神話學者約瑟夫?坎貝爾對神話中的英雄旅程總結基礎上的編劇模型,而神話本身跟人類無意識的心靈創造息息相關,所謂英雄之旅其實就是深入無意識的自我發現、自我療愈之旅。所以,在影片開始的“接受召喚”階段,人物所面對的問題一是外在的明確任務,二是內在的無意識需求。對于主人公Cobb來說,他接受了植入意念這一外在任務的召喚,目的是回家與孩子團聚,但影片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卻是Cobb因向妻子植入意念而導致妻子自殺所給他帶來的心靈創傷,只有解決這一問題,他才能擺脫夢境,回到現實。在英雄之旅的編劇模型中,最終解決英雄內在問題的場所被稱為“最深的洞穴”。“英雄站在了最深洞穴的最深處,面對著最大的挑戰和最大的敵人和最恐怖的敵人。這一時刻是事件的真正中心,約瑟夫?坎貝爾稱之為磨難。……磨難的小秘密在于:為了獲得新生,英雄必須死去。……他們十有八九會魔法般逃過死亡的劫難,實際地或象征性地重生,以便收獲假死所帶來的成果。最后他們終于通過了成為英雄的主要考驗。”[3]而《盜夢空間》中的這個“最深洞穴”就是limbo。從limbo開始解析,就算是抓住了該片創意的起點,也是我們解謎這部心靈療愈電影的重要入口。
1.什么是limbo?
天主教創造了limo這一術語,指地獄的最外邊境,人的靈魂暫時停泊的地方。在這里,靈魂得救就可以升天,否則將墮入地獄。在《盜夢空間》里,諾蘭導演借用了這一宗教詞并賦予其深層心理學的涵義,特指人類意識尚未生長出來的一片荒蕪即個人原初的無意識狀態。正如英雄之旅的編劇模型中,在“最深的洞穴”,英雄要做出死亡還是重生的兩難抉擇。limbo也需要被賦予這種二律背反的特質。所以,在寫作教學的影片分析環節中,首先可以引導學生列舉出limbo的二元特征。limbo具有有無相生的特征,無意識的活動能量在這里將尤為強大,而有意識的自我則變得微弱,意識若稍一松懈,就可能會墮入喪失記憶的無止境混沌中。死亡-重生這一命題在limbol里首先聯系著過去的記憶。limbo的夢境都是掉進去的人憑自己的記憶打造,如果沒有記憶入夢,那也許就將完全失去記憶,但記憶造夢,就容易讓人分不清現實與夢境,讓人擺脫不了夢境,正如Cobb的妻子。所以,實際上這兩種情況都可謂是死亡-重生的抉擇,同樣充滿著巨大的風險,而這體現在以不同方式進入limbo所帶來的人物不同的意識狀態。
2.如何進入limbo?
影片對此有兩種設定:一是某人在設定的某層夢境中死亡,但此時藥效未過,不能被喚醒回現實。這種情況最大的風險就是有可能在limbo中喪失掉以往的所有記憶。二是由女筑夢師Ariadne想到的方法:在設定的最深層夢境中,通過聯夢機再主動繼續向下進入。但與第一種情況不同的是,入夢者會帶著相對清醒的意識進入。死亡-重生命題在這里轉化為記憶與遺忘。于是,我們在影片里看到了人物在limbo里的不同意識狀態,電影也利用這種意識的二元差異,設計出讓觀眾迷惑的不同的limbo夢境。
3.不同limbo間如何共通?
影片尾聲部分的兩個不同limbo夢境分別是Cobb與妻子曾建立的城市世界和日本富商齋藤的海邊別墅空間。觀眾很容易誤認為這是兩層夢境,但這兩個夢境并不是上下層關系,而是limbo中的平行宇宙關系,夢者各自做著自己的夢。這個讓觀眾迷惑的設計,對于電影敘事者來說,卻是順理成章,因為之前已經預設了兩種進入limbo的方式以及進入之后的兩種不同意識狀態。而要搞清兩個limbo之間如何共通,則需要我們回看limbo的本質——在limbo里只有曾在里面的人留下的記憶碎片。Cobb和齋藤都將記憶鐫刻在了無意識的深處。被動進入limbo的齋藤被困在了夢里,但就是因為心中始終頑強地念及對Coob的承諾和那句“放手一搏,不讓自己年老時充滿遺憾”的宣言,即便記憶模糊,Cobb和Cobb曾經為他造的夢也成為他夢的素材。但對于主動進入,意識尚還清醒的Cobb來說,卻具有對夢境的選擇權。為了找到齋藤,Cobb必須抵制住他妻子投影的誘惑,主動選擇不再留在與Mal共同建造的世界里。只有在limbo里徹底地清除他跟妻子的那段記憶后,limbo里才會只存留齋藤的夢境,也就是讓放不下過去的那個我“死亡”后,Cobb才能重生一般地進入齋藤所構建的limbo夢境,進而與齋藤一起逃出limbo。這是影片未曾完全道明但卻深涵于自我療愈主題中的一個設定。
二、深層心理學與內在戲劇
支撐《盜夢空間》劇作復雜性的背后更有龐大的深層心理學理論。深層心理學是關于人類無意識的現代心理學理論,最重要的兩支分別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榮格的分析心理學,這兩支理論有機地融入了影片敘事中,對于豐富角色維度、提供復雜性沖突、塑造主客觀多重世界等方面來說都意義不凡。榮格就曾把人類無意識心靈轉變的過程稱為“內在戲劇。”[4]這種充滿極強主觀性的內在戲劇,總的來說就是為謎題電影增添了無意識的不可靠敘述維度。
1.自我與情結的對決
我們的分析思路同樣還是回到主人公面臨的深層問題上來,Cobb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治愈自己的心靈創傷,而深層心理學的情結理論為這一創傷在影片中賦予了人格化的象征——他妻子Mal在夢中的投影,這就是Cobb所面臨的最大對手。所謂情結,是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存在于無意識之內,由某種感情糾纏而形成的心理內容的集合,會妨礙通常的意識活動”[5]。情結之所以為情結,就是本身攜帶著巨大的情感能量。Cobb對過去痛苦的壓抑,使得Cobb一再沉溺于夢里,而壓抑只會讓內心的愧疚情結更強烈,于是,它才不斷地在無意識中以Mal的形象出來與自我作對,阻撓自我在現實中的行動,也就是要將自我重新拉回到逃避現實的夢境中去。這無疑也是死亡-重生命題的變奏。自我的壓抑與情結的反抗,就會出現兩個分裂的精神主體,壓抑是試圖殺死過去,于是在Cbob敘述創傷故事時,一定會有遮掩、隱瞞,而情結反抗則是試圖搶奪自我的主體地位,將試圖將潛抑于心的另一個我呈現出來。領悟這一二元性,也啟發我們在故事寫作中利用主體的分裂便可自然地去呈現敘述信息不可靠甚至互相矛盾之處,為觀眾增添解謎難度。
2.火車意象的創傷記憶
情結的形成來自往日的創傷,創傷記憶通常會跟一個揮之不去的心靈意象糾纏在一起。影片中,最為明顯的創傷當然是Cobb導致妻子自殺帶來的內疚,但對于謎題電影來說,一定會再設置一個暗藏的線索,而在《盜夢空間》里就巧妙地安排了另一場自殺,那就是Cobb與Mal為逃離夢境的臥軌。但在Cobb回憶敘述中的兩人臥軌,在影片中分別出現過年輕版和年老版。這該如何解釋?如按照Cobb的說法,他們在limbo生活了近50年,那年老版似乎應該才是真實發生過的。那年輕版是幻想出來的,還是曾經真的發生過呢?一個可追尋的線索是,他們當年是如何掉入limbo的?如大家所知,在夢境中死亡但未能喚醒回現實就會被動掉入其中。所以,如果年輕版曾經發生過,那這正是他們曾迷失limbo的原因,而在年輕時的夢境里選擇臥軌自殺,則可以視為是他們當年試圖將夢中夢探索至更深的好奇心使然。這條邏輯看來是成立的,而在電影中也有著強力的作證。
當Cobb服下Yusuf的超強鎮靜劑,立即便出現了妻子的臥軌場景,而緊接著的便是妻子的投影對他說:“你知道如何找到我”,“你知道該如何做?”這兩場景在夢里被剪輯在一起的意思不就是說,夢里自殺是再次找到妻子的方式,也就是讓自己沉浸在limbo里,從而把夢境當成現實,而當年他們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得以在夢里白頭偕老。所以,困擾Cobb的愧疚情結一直試圖誘惑著他永遠地回到limbo里。
3.自我與陰影整合的火車謎語
Cobb與妻子Mal選擇臥軌自殺的方式來逃離當下,但這逃離是回到現實或是進入更深的夢境,當事人其實都不能確認。正如兩人臥軌時所念誦的火車謎語中所說:
You're waiting for a train.
A train that'll take you far away.
You know where you hope this train will take you,but you can't know for sure.
Yet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ll be together.
“Because you'll be together”,這一句又是電影設置的讓人迷惑的不可靠敘述,按正常邏輯,不應是we'll be together嗎?但是,電影中的Mal基本上都是以Cobb的投影人物出現,并不是真的Mal。電影中總共出現過三次念誦火車謎語的場景。第一次是在Cobb打造的回憶電梯夢境里。第二次是Cobb面對Ariadne回憶Mal自殺的場景。第三次則是Cobb直面自己的愧疚情結,與投影人物對話時。所以,火車謎語的對白每一次其實都發生在他跟投影人物之間,將臺詞改為You而不是We,無疑是他揮之不去的渴望追隨妻子的幻想,但在夢里或者回憶里,需要另外一個類似上帝的超然聲音來安慰自己:“你們會在一起!”鑒于西方基督教的懺悔傳統,西方人的心理投射中,總是容易出現上帝的影子,一個凌駕于自己之上的聲音。這個聲音會對人的罪責做出回應,會讓人在罪感中與內心中不愿面對的內容直面對決。也就說只有遵從那個“you'll be together”的聲音,才能達成真正的心靈療愈。
You就是指Cobb跟自己的愧疚情結。情結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情結所奠基的意象,也是被冰凍的創傷記憶。無論是他倆的臥軌自殺還是Mal的跳樓自殺都構成了Cobb愧疚情結的首要意象,這也是被壓抑的個人無意識。而情結的另一要素則關聯到原型,所謂原型就是人類集體無意識中所共通的某種原行為模式的類型。愧疚情結的背后糾纏著的原型之一就是所謂陰影原型,“陰影就是這個人的意識沒能活出來的那一部分反面內容,對個人來說是難以認可的心理內容”[6]它是人類心中難以認可、拒絕接受的心理內容,一味地去壓抑它,便會反彈成一種自我否定的力量,但陰影不會被自我直接經驗,而是被投射在其他客體身上,正如影片中隨時出來阻撓正常行動的Mal。而當Cobb的自我直面自己的陰影投射時,陰影反過來再幫助自我重新反觀自我。Cobb終于在這limbo里敢于直面情結投影,終于敢于將對妻子植入意念的罪感,如同對著上帝懺悔一般袒露了出來,也就是承認了陰影就是自己的一部分。
實際上,我們并不能知道原型存在本身,而只是通過原型意象來把握。情結中的二元核心藉著把各種意象羅聚在它四周而成長,創痛記憶與各種原型糾纏一起而形成。所以,如果自我為了防止情結影響而強行將情結清除,那就容易與深處存在的原型內容形成斷裂,使得自我失去生命力,不能清除,那就是整合共生,這就回到火車謎語所說的“you'll be together”。
三、結語
一切的問題都“inception”于意識的最深層,該部電影的原名就是inception,而“盜夢空間”的譯名雖頗具票房吸引力,但“盜夢”卻極易讓人偏離對影片深層意味的把握。影片實際上并不是要盜取誰的夢,而是要在人的意識深處植入意念,只是這意念植入的突破口就在于人們內心深處所不愿面對的情結。《盜夢空間》的故事編寫,無疑也是一場操作細膩的心理治療,Cobb、Mal、Fischer乃至齋藤,每個人物都有自己壓抑的情結,都需要在心靈的深處重新面對,也就是都面臨著死亡-重生的命題。
我們通過分析死亡-重生這一內嵌于電影文本各個部分的命題,也領會到了該部影片無處不在的謎題創意思路。盡管導演和編劇在創作時,未必嚴格遵循著我們的分析邏輯,但通過將潛藏于創作無意識中的死亡-重生命題提取出來,對于模仿、學習、揣摩謎題創作來說卻可以讓我們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