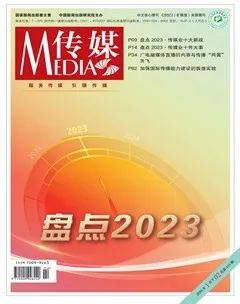“一帶一路”視野下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研究
梁睿 張睿婷
摘要: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邁進是我國當前重要的國家戰略。陜西民族音樂應借助“一帶一路”賦予的歷史機遇,積極克服內外部制約因素,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打造民族音樂品牌、打造“數字化”傳播空間及建構立體傳播體系,拓展和豐富民族音樂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提高陜西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力。
關鍵詞:“一帶一路” 陜西民族音樂 海外傳播
“一帶一路”是我國拓展改革發展新空間、發展新型國際關系、增進人類共同利益、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選擇。“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民心相通”在于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只有以文化先行帶動民心相通,才能夯實“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心理基礎,推進“一帶一路”的實施與可持續發展。陜西民族音樂融秦地民俗、民風、民性于一體,宏闊雄強、渾穆剛健,是陜西的一張重要文化名片。挖掘其文化內涵、美學價值,發揮其在人類情感表達與情感溝通中的作用,對于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促進沿線國家合作共贏,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溝通、文化融合是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要手段,而文化尤以音樂、影視作品等最易廣泛傳播。只有正確認識民族音樂海外傳播的作用和價值,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才更能影響并得到沿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更好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與發展。
1.利于實現“民心相通”。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順利推進的社會基礎,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根本歸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涵蓋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中東歐、北非等地區的60多個國家,不僅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多民族、多宗教,而且各國民族文化、政治立場、利益訴求、行為模式都存在巨大差別。目前,沿線一些國家對于“一帶一路”的倡議仍存在不同理解和顧慮。要消除這些顧慮,就要發揮文化的涵化、聚化、內化和轉化功能,消除偏見、化解歧見、匯聚力量,形成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共識。音樂作為一種全世界通用的人類情感藝術表達形式,“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無需特定翻譯就可以滿足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之間人群的交流,有利于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夯實中國與沿線各國“互聯互通”的心理基礎。
2.利于促進“國際合作”。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漢朝張騫出使西域開啟古絲綢之路以來,不同形式的文化就在絲路沿線各個民族、國家間相互傳播、相互融合,成為古絲綢之路沿線人民相親相交、相互融合的重要紐帶。“一帶一路”共建的內容涵蓋經濟、科技、金融、文化等各個方面,而這些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的基礎就在于文化,需要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遵循“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互鑒共榮”原則,推進優秀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使之成為政治、經貿、軍事、社會等各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潤滑劑”“催化劑”。而中國傳統民族音樂自身的傳承和傳播有利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領域的合作共贏、互利共榮。
3.利于提升文化軟實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傳播中華文化、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重要舉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海外的積極影響,主要是通過經典傳播途徑實現的。不論漢唐古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帶出去的不僅有精美的絲綢和瓷器,還有燦爛的中華文化和良好的國家形象。陜西民族音樂有著豐富而深厚的哲學、美學價值以及獨特的文化和音樂藝術魅力。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陜西民族音樂的“跨文化”傳播,讓世界感受立體、鮮活的陜西民族音樂文化,傳播中國好聲音,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對于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實現“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價值。
音樂的海外傳播固然利于提升國家軟實力,也有助于促進國際文化傳播與國際間的更多合作,但作為民族音樂,陜西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還是面對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多種因素的制約。
1.外部制約因素。“一帶一路”倡議是基于“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中國方案。目前,以中國為主導的“一帶一路”參與合作的國家已達到60多個,這些國家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性格取向等。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面臨著一定的外部制約:一是宗教文化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宗教種類齊全,不僅世界三大宗教匯聚此地,還有數不清的小型宗教。由于不同宗教之間的宗教制度和規范各不相同,各類宗教間的分歧、沖突從未中斷。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相互交織,成為制約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認同的重要因素。二是語言交流障礙。“一帶一路”覆蓋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多個地區,僅涉及的官方語言就高達40多種,各地區國家在文化上也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復雜的語言環境和文化差異是制約陜西民族音樂傳播的主要因素。但目前我國極為缺乏既了解文化傳播方式、文化傳播規律,又通曉小語種語言的復合型人才。三是文化排斥反應。文化排斥反應是與文化融合反應相對應的行為,兩者都是文化接觸中可能出現的反應。跨文化心理學學者約翰·貝利認為跨文化傳播過程分為融合、同化、隔離和邊緣化四種反應,隔離反應就是對移入國文化的排斥反應。從文化形成的角度來說,每一種文化都是在自身文化場域中形成的獨特“性情傾向系統”,這種獨特的“性情傾向系統”存在于與自身相一致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這種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對于外來文化具有天然排斥性。每個國家都有與自身文化場域相適應的“性情傾向系統”,很難接受外來藝術文化,這就導致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很難讓國外民眾產生認同感。同時,陜西民族音樂大多采用陜西方言表演,如經典曲目管弦樂《長安社火》,融合了高亢激昂的秦腔元素,鏗鏘有力、宏闊雄遠,但由于語言溝通障礙和審美習慣相異,可能讓外國受眾產生“看不懂、聽不懂、不想看”的問題,顯然不利于形成陜西民族音樂的海外認同。
2.內部制約因素。制約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海外傳播載體不足。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哈羅德·拉斯韋爾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必須依靠傳播才可以實現發展和傳承,更好的傳播方式以及傳播載體能夠更好地促進文化的發展。一直以來,陜西民族音樂的傳播往往是通過口傳心授和現場展示進行傳播和繼承,如“秦派二胡”、管弦樂《長安社火》、嗩吶獨奏《關中情》等具有獨特陜西風韻的傳統民族音樂曲目,主要以師徒傳授、現場展示和口口相傳為主要傳播、傳承方式。這種較為單一的傳播、傳承方式,在國際化、數字化背景下弊端日益凸顯,在流行音樂盛行的當下更有失傳的風險,更不用說在文化背景不同的異域了。在中國民族音樂文化國際話語權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這種傳播載體和傳播方式不利于陜西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二是跨文化傳播隊伍薄弱。人才資源是推動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的基礎,在60多個國家、40多種官方語言的復雜語言環境下,陜西民族音樂想要能夠遠播海外,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障礙,因此這需要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優秀翻譯人才。但目前民族音樂領域的從業者較多都是師承學習或民間教學,學徒大多缺乏跨文化傳播領域專業知識素養,具有專業跨文化傳播素養的綜合性人才往往又對民族音樂領域了解不夠深入。同時,專業的音樂人、媒體人、經紀人的欠缺也影響和制約了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三是音樂文化貿易尚未展開。近年來,我國涵蓋影視、動漫、體育、出版等形式文化的對外貿易量持續增長,但音樂文化對外貿易量占比極低。如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對外貿易年度報告從未將音樂文化產業單獨列出,這種情況直觀地說明了中國音樂海外傳播面臨著經貿短板。
“一帶一路”倡議給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陜西民族音樂應積極克服內外部制約因素,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打造民族音樂品牌、打造“數字化”傳播空間及建構立體傳播體系,拓展和豐富民族音樂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提高陜西民族音樂文化的海外傳播力。
1.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不僅能對外塑造良好國家形象,還可以將國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通過輸出轉化為文化認同。這有助于彌合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機、整合不同力量的作用。因而應明確陜西民族音樂溝通民心、化解分歧、促進合作中的傳播價值,應根據“一帶一路”拓展中國發展新空間、促進區域繁榮穩定,在建構“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以實現“民心相通”為根本宗旨,加強與其他國家在民族音樂上的交流與合作,引導“一帶一路”國家民眾認識、喜愛、學習陜西民族音樂,使陜西民族音樂發揮其“民心相通”中的文化溝通作用。
2.打造民族音樂品牌。中華民族的每一件傳世樂器、每一首經典曲目、每一段音樂典故、每一部音樂典籍都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密碼,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文化品牌。品牌是通過文化因素凝結而成的獨具特色的產品和企業形象、國家和民族形象,它是一種文化的靈魂、風格和氣質的文化外觀。應以現代視野審視和認知陜西民族音樂的獨特價值,立足全球化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民族音樂組織、曲目和人物,精心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文化品牌。
3.打造“數字化”傳播空間。打造“數字化”傳播空間,豐富民族音樂傳播形式,對于促進陜西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互聯網、移動媒體的廣泛應用和發展,依托互聯網、云音樂平臺打造“文化傳播+互聯網”的立體傳播空間,對于拓展陜西民族音樂傳播渠道、創新陜西民族音樂傳播方式、豐富陜西民族音樂傳播內容具有重要作用。陜西民族音樂企業、組織應將互聯網融入對外文化傳播方式中,將優秀曲目的音視頻通過互聯網、云音樂平臺向海外進行推送。如通過抖音海外版、網易云音樂海外版制作、傳播陜西民族音樂,以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陜西民族音樂的認同感,以民族音樂為文化傳播載體發揮“民心相通”的作用。
4.建構立體傳播體系。探索更加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傳播途徑,是實現陜西民族音樂海外快速傳播的基礎。一是通過文化層面的對外貿易實現民族音樂的對外傳播。通過發展海外音樂文化展演、民族音樂圖書、海外音像制品出版等文化貿易,實現陜西民族音樂深層次海外傳播。二是通過音樂類的院校間合作達到海外傳播的目的。很多精通民族音樂的中國音樂家在世界各地高校任教,為民族音樂在國外高校發展提供了師資條件和傳播基礎,如林萃青、石清照等在美國院校教授中國音樂。因而可以通過合作辦學、訪學及學術交流等手段,促進陜西民族音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傳播。三是鼓勵開辦民族音樂培訓班。各國人民認同民族音樂文化體系、樂于學習該民族音樂文化是民族音樂文化國際傳播的基礎。實際上,我國有很多音樂人在美、日、韓等國家開設音樂培訓班或進行私人家庭授課,對中國民族音樂的國際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建議政府設立專項資金,扶持、鼓勵中國海外音樂人宣傳和傳播我國民族音樂文化。
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的邁進,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對外傳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陜西民族音樂作為我國音樂的一個分支,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若要讓外界了解我國文化,就應借助“一帶一路”賦予的歷史機遇,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交流,借助國際間的交流機會,提升民族音樂的海外認同度,同時自身也要優化民族音樂內容、打造民族音樂品牌,讓世界認識和了解我國民族音樂,在打造“數字化”傳播空間時,也需要創新民族音樂的傳播形態,建構立體化的傳播體系,豐富民族音樂傳播途徑,讓民族音樂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使陜西民族音樂更好地借助“一帶一路”主題之義,發揮“民心相通”的作用,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添磚加瓦。
作者梁睿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張睿婷系河南師范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講師
本文系2019年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陜西紅色音樂國際化傳播平臺研究”(項目編號:2019K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夏婷,暢紅,羅暉.深化科技人文交流,共筑“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J].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7(04).
[2]李丹.構建“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的基礎條件與現實路徑[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06).
[3]向勇,李盡沙.融合與共生:“一帶一路”文化產業合作發展指數研究[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04).
[4]傅雨飛.“一帶一路”的文化包容機制:價值結構、阻力分布與路徑優化——基于結構功能主義方法的分析框架[J].江海學刊,2018(04).
[5]王鵬.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新時代“一帶一路”故事[J].一帶一路報道,2021(05).
[6]吳瑩,楊宜音,趙志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排斥反應[J].心理科學進展,2014(04).
[7]高一丹.在公共事件中強化和踐行傳媒的社會功能研究——對拉斯韋爾“傳播三功能說”的再認識[J].傳媒論壇,2020(20).
[8]李偉.“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差異性與包容性[J].人民論壇,2019(22).
[9]劉劍.體認多元文化視域下中華器樂之世界品牌[J].北方音樂,2019(13).
【編輯: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