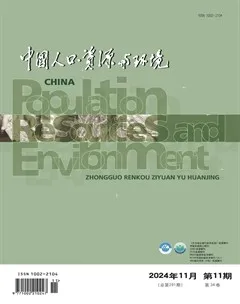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路徑證成
摘要 國際投資仲裁已成為氣候變化訴訟之外的一種新型氣候變化爭議解決方式。東道國氣候變化政策產生的經濟影響體現了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氣候法的互動,也使國際投資仲裁可以被用于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在實踐中,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案件主要存在調整環保措施與調整能源政策兩種類型,包括本訴與反訴兩種程序。在理論上,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存在實體性與程序性的正當性,符合投資條約中保護實體權利的要求與投資仲裁本身的程序要求。基于此,應當主動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投資仲裁的審理范圍,用足、用好既有的投資仲裁渠道,提升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效用。為促進全球資金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增強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能力,該研究從4個方面提出了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施路徑:①在法律解釋方面,重構條約解釋的路徑。例如,擴大對締約方條約義務的解釋、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的解釋以及對間接征收條款的解釋,并明確氣候變化協定與投資條約發生沖突時的優先效力與沖突規范的適用路徑。②在條約制定方面,改革投資條約的內容。例如,適當調整序言與投資保護條款的內容;在投資條約中明確否定氣候變化爭議屬于例外條款的范圍;在專門環境規制條款中規定氣候變化問題。③在平臺供給方面,繼續拓展國際投資仲裁平臺,充分利用全球性、區域性和商事性的投資仲裁平臺。④在機制實施方面,應當結合氣候變化爭議的特殊性,完善國際投資仲裁程序,提升投資仲裁的透明度、專業性和高效性。
關鍵詞 國際投資仲裁;氣候變化;國際氣候法;國際經濟法;投資條約;碳排放
中圖分類號 D996. 9;D996. 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11-0090-10 DOI:10. 12062/cpre. 20240722
氣候變化訴訟是實現1. 5 ℃全球溫控目標的法律工具,借此可以追究政府或公司應對氣候變化不力的責任。但氣候變化訴訟主要表現為國內訴訟,容易忽略氣候變化爭議解決機制多元化的特點,陷入過度能動司法的困境[1]。基于此,仲裁與調解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正成為解決氣候變化爭議更具競爭力的方式。氣候變化爭議是將氣候變化作為國際投資仲裁爭點的爭議,主要是與能源體系的轉型、碳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合同爭議,以及由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政策或國際氣候法所引發的、或與其相關的爭議[2]。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以下簡稱ICSID)已處理多起涉及氣候變化的投資爭議,投資者與東道國依《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以下簡稱《華盛頓公約》)將爭議交由ICSID進行投資仲裁,解決因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而產生的投資爭議[3]。例如,在Eco Oro 公司訴哥倫比亞案(ICSID Case No.ARB/16/41)中,仲裁庭支持了原告的主張,認為被告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對原告特許經營采取的管制措施,違反《加拿大與哥倫比亞自由貿易協定》第805條的投資者保護規定。同時,氣候變化問題既是環境問題,又是經濟問題[4]。各國為履行《巴黎協定》的承諾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會導致投資環境的變化,仲裁庭需要在投資仲裁程序中兼顧氣候責任與投資條約義務。例如,在Urbaser公司等訴阿根廷案(ICSID Case No. ARB/07/26)中,仲裁庭不僅審理本訴中基于雙邊投資條約的賠償請求,還審理反訴中關于投資者違反水權保護義務的賠償請求。國內外的研究與實踐表明:學術界對氣候變化爭議解決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氣候變化訴訟領域,忽略了對氣候變化爭議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探索;另外,國際上已有通過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相關實踐,但相關研究并不充分。鑒于此,本研究將系統梳理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踐,構建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施路徑。
1 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踐梳理
投資仲裁通常無法直接改變東道國的氣候變化應對措施,只能通過高額的索賠間接影響東道國的氣候法律規范,形成個案的溢出效應。國際投資仲裁是一種中立的糾紛解決機制,通過踐行個人與國家共同參與、公法與私法兼顧等理念,能有效應對涉及環境保護等公共政策的爭端[5]。目前,相關的準司法實踐不斷浮現,國際投資仲裁在氣候變化爭議的解決中承擔著不同的角色。
1. 1 程序類型:本訴與反訴的二元劃分
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依據提起仲裁主體的不同,可分為由投資者提起的本訴型投資仲裁與由東道國提起的反訴型投資仲裁兩類。在本訴型投資仲裁中,投資者請求損害賠償的原因或為東道國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導致其違背投資保護標準,或為東道國面對氣候變化的不作為導致其違反國際或國內的氣候保護義務;在反訴型投資仲裁中,作為本訴被告的東道國提交氣候保護的反訴,借助投資條約中的“綠色”投資條款要求投資者履行氣候保護的投資義務[6]。這種類型化區分體現了投資條約中投資條款與環境條款的相互作用:環境條款會在實質上對投資者權利造成限制,投資條款的最惠國待遇將會在事實上架空環境條款[7]。在投資條約中,投資者具有環境保護義務,東道國具有投資保護義務與環境保護義務,這些法律義務是本訴與反訴兩種程序的實體法基礎。例如,在Spence公司等訴哥斯達黎加案(ICSID Case No. UNCT/13/2)中,仲裁庭就對投資條約核心條款中的投資保護義務與環境保護義務進行分析,并認可了環境條款對投資條款的限制。
在本訴方面,投資者常以東道國違反投資保護義務或氣候保護義務為由提起國際投資仲裁。最為典型的就是外國投資者以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違反投資條款為由而主張損害賠償。具體包括非法征收、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和不完全履行投資保護義務等事由。在Lone Pine 公司訴加拿大案(ICSID Case No. UNCT/15/2)中,原告就因東道國的環保政策而被吊銷勘探石油和天然氣的許可證,進而以違反投資保護義務為由提出賠償。同時,在由于東道國未履行關于氣候變化的環境承諾而造成投資損害時,投資者也能將此爭議提交投資仲裁。目前雖無針對東道國違背氣候保護義務的實踐,但并不缺乏東道國未履行環保義務的實踐。在Peter A. Allard訴巴巴多斯案(PCA Case No. 2012-06)中,原告以東道國未履行國際環境法與國內環境法的環保義務而對其投資的自然保護區造成環境損害,以及對其投資形成間接征用等理由,請求東道國賠償損失。在反訴方面,基于仲裁裁決的執行優勢,東道國在投資者造成環境損害時也會通過投資仲裁來請求損害賠償。其中,東道國分別在Burlington 公司訴厄瓜多爾案(ICSID Case No. ARB/08/5)、Perenco 公司訴厄瓜多爾案(ICSID Case No. ARB/08/6)、David R. Aven 等訴哥斯達黎加案(ICSID Case No.UNCT/15/3)中提出反訴,以投資者違反東道國的環境法與投資合同義務為由,要求投資者對環境損害進行賠償。若氣候保護要求被明確寫入投資條約,投資者將具有保護氣候的義務,東道國也具有將投資者違反氣候保護義務的行為提交投資仲裁的程序請求權。
1. 2 案由類型:調整環保措施與調整能源政策
在實踐中,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主要是投資者因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而受到損害所提起的仲裁,屬于投資者保護自身在東道國投資利益的工具。國際投資協定應當保障各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者不得違反各國關于保護社會權利與環境的規定[8]。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行動或其他環境保護的國家行為,并非投資條約的直接規范對象;只有國家違反投資保護義務的行為,才是投資條約的直接規范對象。在此意義上,東道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只有在造成優惠國內生產者的保護主義或形成貿易壁壘等后果時,才會違背國際經濟法上的貿易自由化義務而具有非法性。以碳稅為例,東道國限制碳排放的應對氣候變化措施本身并不違法,但其若造成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或國民待遇原則,則會變為投資者可控訴的事由[9]。因此,投資者提起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的事實主張,仍以東道國違反投資保護義務為核心,主要涉及公平公正待遇原則或非法征收的問題。
以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為依據,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的實踐主要可劃分為調整環保措施型投資仲裁與調整能源政策型投資仲裁兩類。其中,Eco Oro公司訴哥倫比亞案與Windstream 公司訴加拿大案(PCA CaseNo. 2013-22)都是調整環保措施型投資仲裁的典型案例,屬于東道國基于環保理由而拒絕頒發許可證并影響投資者權益的情形。在前者,仲裁庭引入了國際氣候法的預警原則和比例原則幫助判斷間接征收問題,并以東道國未能為投資者提供穩定與可預期的法律規范為由,認定東道國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在后者,仲裁庭認為東道國停止離岸風力發電計劃的行為不屬于間接征收的行為,并因投資者未能充分舉證而未支持原告關于東道國違反不歧視原則與公平公正待遇原則的主張。同時,國際投資仲裁的實踐也表明,環保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應當以個案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結合環保措施的效果與目的、比例原則以及科學證據進行綜合考慮,以維護投資者對東道國保護投資的合法期待[10]。9REN公司訴西班牙案(ICSID Case No. ARB/15/15)和Eskosol 公司訴意大利案(ICSID Case No. ARB/15/50)都是調整能源政策型投資仲裁的實踐。二者都涉及氣候變化議題的關聯議題——可再生能源產業,投資者的權益也受國家能源政策的影響。在前者,仲裁庭強調可再生能源的特殊性,東道國需要保障投資人對可再生能源政策穩定性的合理期待,否則將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在后者,仲裁庭認為東道國提前終止激勵機制的行為并不違反投資保護義務,投資者“將來”的法律權利不屬于合理期待的范圍。同時,仲裁庭并未直接討論氣候變化議題,但能源政策本身已是東道國將氣候變化納入實質考量的結果,在“公平收益(fair return)”的認定中也不可避免地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解釋公平公正待遇原則的來源。
1. 3 實踐檢視:投資仲裁的需求與局限
現狀表明,氣候變化爭議對國際投資仲裁的需求依舊旺盛,相關實踐也在日益增長。氣候變化是一個系統性的法律問題,涉及政治、經濟和環境等方方面面,碳減排義務以及碳交易系統也與國際經貿息息相關[11]。在氣候變化議題中,碳減排行為的經濟成本和氣候變化政策目標之間相互影響,體現了該議題的復雜性。因此,《巴黎協定》等國際氣候條約為減少締約國對經濟影響的憂慮,允許締約國自主決定碳減排貢獻,導致國際氣候法缺乏法律的強制執行機制[12]。事實上,不同于《巴黎協定》的政治承諾,旨在保護全球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經濟法體系正在逐步加強,投資條約法與投資仲裁的強制性也隨之提升。其中,投資條約法對外國投資的保護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推動東道國經濟的綠色轉型,也可能阻礙東道國綠色經濟的發展。例如,通過對投資者進行全額補償使東道國承擔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所有成本,實質就是將氣候變化的成本負擔從排放者轉移到東道國[13]。但無論是何種影響,都將促進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數量與類型的增加。氣候變化問題,與其認為是法律問題,不如認為是經濟問題,國際投資仲裁也面臨投資保護與氣候保護的利益平衡問題。
當前,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宏觀上,當前實踐中的仲裁庭始終未對氣候變化問題能否適用投資仲裁機制進行正面回應。仲裁實務對投資仲裁本身是否適合解決氣候變化爭議保持著不約而同的沉默,也無任何仲裁裁決對投資仲裁與氣候變化的相容性發表意見。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法律定位仍不明確。在中觀上,當前實踐所涉及的氣候變化爭議具有間接性。其直接的法源是環境法與能源法,并非國際氣候法,國際氣候法和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并未被仲裁庭所考慮。相關案件既無與氣候科學直接相關的問題,例如全球變暖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的因果關系問題;又無與國際氣候法直接相關的問題,例如全球溫控目標以及國家自主貢獻承諾問題。這種關聯性使得此處的氣候變化只能符合最廣義的氣候變化的定義,最廣義的氣候變化不要求以氣候變化為主要爭點,只要求涉及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14]。在微觀上,投資仲裁在解決氣候變化爭議時,未能有效發揮其程序優勢。投資仲裁的法源是國際法,其功能是限制政府,但卻擁有與商事仲裁相同的爭端解決機制及優勢。遺憾的是,實踐中的投資仲裁仍存在程序拖延、效率低下和專業性薄弱等問題。
2 氣候變化爭議適用國際投資仲裁的正當性證成
氣候變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一是風險的廣泛性。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是控制碳排放與全球升溫,全球升溫不僅將會引起極端氣候和其他自然災害,還會加重空氣污染,對人類生命健康構成威脅。二是應對行動的全球性。氣候變化是需要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要求世界各國共同進行應對氣候變化的集體行動以減少碳排放,但各國氣候治理的具體目標和手段的不同導致責任分擔體系的失效[15]。氣候變化需要通過國際氣候法進行專門規范,減緩氣候變化的集體行動成果也由國際社會共享。三是議題的復合性。氣候變化屬于氣候科學問題,也屬于全球政治議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運作凸顯了氣候科學與政治共識的統合,為各國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合法、可靠的政策知識[16]。四是政策目標的預防性。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是為了預防全球升溫超出溫控目標,預防的手段是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此基礎上,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應從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兩個維度重塑正當性。
2. 1 實體層面:應對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
首先,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應從投資仲裁的制度目的予以證成。一方面,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并不會背離國際投資仲裁去政治化的制度初衷。投資仲裁的制度初衷是為雙邊投資協定的去政治化提供實現的方式,避免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的直接沖突。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行動計劃,只是一種自主貢獻承諾,并無國際法上的強制力。與氣候變化直接相關的碳排放權具有公法與私法的復合屬性,以配額的確定與分配為核心的第一階段屬于行政處理階段,以配額交易為核心的第二階段屬于民事合同階段[17]。這說明了氣候變化議題與國際投資保護在法律屬性方面都具有私法屬性,符合投資仲裁作為處理國家與私人之間糾紛的制度目的。另一方面,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符合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利益平衡要求。全球經濟利益的平衡是國際投資仲裁的追求目標,投資條約的主要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促進投資時將締約雙方的投資環境提升到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全球化標準[18]。與國際投資法類似,國際氣候法也是平衡國際社會多元主體利益后的產物。國際投資仲裁無須受傳統的束縛,可在投資協定中增加可持續發展理念等要求,也可在投資協定的目的條款中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內容。
其次,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需要從法律與政策的角度進行審查。應對氣候變化屬于非投資的國際義務,是涉及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等領域的國際義務。仲裁庭并不會直接提及東道國非投資的國際義務,但會通過自由裁量的方式適當減輕責任,要求東道國承擔因履行非投資國際義務造成損失的大部分。同時,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也應當與投資仲裁的法律或政策相聯系,具體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①氣候變化議題可以適用公平公正待遇原則。東道國調整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財務負擔將從東道國轉移至投資者,違反投資者的合理期待[19]。當前的國家實踐并未否定投資條約調整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權限,氣候變化議題也可以適用投資仲裁的法律[20]。②氣候變化議題可以適用征收條款。在碳排放政策下,在投資者投資了高碳產業后被要求退出時,東道國的行為將構成非法征收行為。例如,投資者可以依照《能源憲章條約》的規定,認為東道國調整能源產業政策的行為構成征收行為,通過提起投資仲裁請求東道國賠償損失[21]。③氣候變化議題可以適用保護傘條款。保護傘條款可以將有限的合同義務轉為條約義務。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碳減排與碳中和都屬于公共政策的目標,東道國涉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同行為屬于主權國家的行為,相關的合同義務構成條約義務[22]。
最后,投資條約或投資合同中應體現締約方將氣候變化爭議提交國際投資仲裁進行解決的仲裁合意。國際投資仲裁的本質是仲裁,爭端雙方的仲裁合意是其制度基石,這也是實體法意思自治原則的要求[23]。仲裁合意具有實體性意涵,體現了投資條約與投資合同中的雙方處置投資利益的共識。若投資者與東道國對氣候變化的可仲裁性進行明確約定,則氣候變化具有意定的可仲裁性;若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將氣候變化的可仲裁性寫入投資條約,則氣候變化具有法定的可仲裁性。無論是意定或法定的可仲裁性,對仲裁庭皆有約束力,可構成仲裁庭作出仲裁裁決的法律依據。締約方對于投資條約及投資合同的內容具有充足的解釋權,投資條約內容也可在投資合同中進行個別性安排與調整[24]。其中,東道國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具有雙重地位,即投資條約的締約國與投資仲裁糾紛的被告。前者涉及解釋條約的利益,后者涉及規避責任的利益。在此基礎上,東道國對于氣候變化的可仲裁性問題,可以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進行處理,并且影響仲裁庭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若氣候變化的可仲裁性未被締約方所明確規定,相關內容則需要由仲裁庭進行解釋。但只要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未被締約方所明確否定,在法律解釋上就可以承認締約方通過默示合意的方式認同氣候變化議題的可仲裁性。
2. 2 程序層面: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可適用性
在本訴程序中,東道國常在程序上以仲裁庭無管轄權為由進行抗辯,以此否定投資者提交投資仲裁事件的可仲裁性。投資仲裁的管轄權在實踐中具有擴張的趨勢,這是受到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投資爭議的管轄競合、投資者訴權的專屬性等因素影響的結果[25]。在此背景下,仲裁庭具有對氣候變化爭議的管轄權,由氣候變化所衍生的權益也將會成為投資條約的投資保護標的。
(1)氣候變化爭議符合國際投資法對于“投資”的定義。無論是“低碳”投資還是可再生能源投資等投資行為,都符合Salini測試的4個要件,即資源投入、持續時間、經營風險與經濟貢獻。氣候變化爭議所具有的經濟屬性使其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投資。
(2)氣候變化爭議影響投資仲裁案件的管轄。PatrickMitchell訴剛果民主共和國案(ICSID Case No. ARB/99/7)表明,一旦投資者未履行與氣候保護相關的環保責任,則將會被仲裁庭認為投資者對東道國經濟發展并無貢獻,進而否定其所尋求的保護屬于投資保護標的。仲裁庭通過強調投資者在環境保護、人權保護等領域的法律義務,對投資仲裁案件的管轄進行調整。
(3)環保領域投資仲裁案件的實踐間接肯定了仲裁庭對氣候變化爭議的管轄權。國際投資仲裁已處理數量頗豐的環保領域的投資仲裁案件,投資條款中逐步出現環境規制條款,注重對環境損害的預防[26]。氣候變化屬于廣義上的環境議題,仲裁庭具有對氣候變化型投資爭議作出裁決的權限。
(4)人權保障領域的投資仲裁實踐支持了仲裁庭對氣候變化爭議的管轄。投資仲裁已有與人權保障直接相關的實踐,涉及投資者自身的人權被東道國侵犯、東道國國民的人權被投資者侵犯和第三方的法庭之友提出人權訴求3種類型[27]。氣候變化應對措施與人權保障具有密切的關聯,應對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基本權利損害受到國內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救濟保障[28]。
在反訴程序中,東道國也常在投資仲裁中以投資者違反投資義務為由提起反訴的仲裁程序,向投資者進行索賠。在氣候變化爭議中,東道國能否提起反訴程序以矯正投資者違背氣候保護義務的不法行為是非常重要的程序性議題。反訴是有效追究投資者責任的重要手段,東道國可以通過反訴的方式制止投資者損害本國公共利益的行為和投資者侵犯本國公民人權的行為[ 29]。基于此,雖然東道國缺乏進行反訴的國際法支撐,但在利益平衡上應當承認反訴的正當性和投資者維護公共利益的法律義務。東道國也具有監督投資者履行國內法或國際法上氣候保護義務的責任。因此,新型的投資條約應將投資者義務條款進行擴展,要求投資者遵守東道國法律,也要求投資者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30]。以氣候變化爭議為由的反訴必須遵循投資仲裁反訴的程序性要求。
(1)反訴須具備同意的要件。國際主流觀點認為,若締約方并未特別表明同意反訴,則仲裁庭不具有對該反訴的管轄權[31]。同意的表現有4種:根據國際投資條約而確定同意反訴;當事人同意適用ICSID仲裁規則而視為同意反訴;由投資條約明確排除特定的反訴而推定允許其他類型的反訴;當事人達成單獨的反訴管轄權協議[32]。仲裁庭允許東道國在投資仲裁中提起反訴是一種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但也有相關實踐。在Urbaser公司等訴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承認對東道國以維護人權為由提起的反訴具有管轄權,理由是投資條約中的文字具有開放性,未明確排除東道國提起反訴的可能,進而推定締約方存在將反訴提交仲裁的默示合意。
(2)反訴須具備關聯性要件。這體現在法律上的連接與事實上的連接兩方面。法律上的連接尤為重要,單純事實上的連接通常無法滿足投資者本訴與東道國反訴之間密切聯系的要求。法律上的連接通常包括國際法連接與國內法連接兩方面。在國際法連接中,Urbaser公司等訴阿根廷案將投資條約連接到國際法上的投資者責任,并以此支持仲裁庭對反訴的管轄權;在國內法連接中,Burlington公司訴厄瓜多爾案則是仲裁庭經投資者同意后獲得了基于國內法提起反訴的管轄權。基于此,涉及氣候變化爭議的反訴同樣應當具有反訴的關聯性要件,但涉及氣候變化爭議的反訴的特殊之處在于法律上的連接。國際氣候法規范為其提供了更廣泛的法律連接點,使之更容易符合反訴管轄權的關聯性要求。
3 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實體路徑
溫室氣體排放對全球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都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具有不言自明的正當性。國際社會也在積極呼吁將投資條約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工具,并將減緩氣候變化納入投資條約的非經濟要素[33]。其中,國際投資仲裁并不能直接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卻具有間接推動氣候治理的功能。氣候變化爭議與投資仲裁的相容性應當關注由應對氣候變化所衍生出的經濟議題,這也是維持投資仲裁的政治正當性的保障。氣候變化規范具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內涵,投資仲裁的重心則是關注其經濟內涵,并將其與投資條約中的東道國義務相聯系,平衡氣候保護與投資保護兩種價值體系。
3. 1 法律解釋:重構法律適用的進路
氣候變化爭議作為投資仲裁的審理范圍,應當遵循國際經濟法的法律適用規則,對投資條約進行精細化的法律解釋。國際投資仲裁中的條約解釋重視《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以下簡稱《VCLT條約》)的解釋規則。這也是保障仲裁庭對投資條約核心條款的解釋具有一致性的前提,確保了仲裁裁決的合理性與可預期性。仲裁庭對氣候變化爭議的可仲裁性也需要遵循《VCLT條約》的解釋規則,在不修改現有投資條約規范內容的前提下,論證氣候變化爭議與投資條約的實質性聯系。氣候變化議題的全球性為投資者、東道國和法庭之友對仲裁庭通過法律解釋的方式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審理范圍提供了利益基礎。具體而言:東道國可以踐行自身的氣候政策;投資者可以進行綠色投資活動;法庭之友可以履行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能。
第一,借助《VCLT條約》第31條對締約方條約義務進行擴大解釋,提升氣候變化規范的影響力。仲裁庭必須從法律體系的角度考慮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都參與的國際條約內容,全面理解二者的國際條約義務。根據《VCLT條約》第31條第3款的規定,若投資條約的締約方皆為同一國際氣候條約的締約方,則仲裁庭有權將該國際氣候條約中的國家責任納入考慮,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審理范圍。同理,仲裁庭也可將《能源憲章條約》第26條第6款進行擴大解釋,將《巴黎協定》等國際氣候條約納入該款條文的涵蓋范疇,促進投資條約的解釋與國際氣候法要求的協調一致。由此,仲裁庭以《VCLT條約》第31條第3款為法律工具,可將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都參加的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條約視為國際投資爭端應當適用的國際法,并據此進行仲裁裁決。這種解釋方法能擴大國際氣候法的適用場景,并通過將其納入國際投資仲裁體系的方式,賦予其執行力。但是,若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具有排除適用國際氣候條約的明確共識,則不能采取此種解釋方法。
第二,借助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的法律解釋,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仲裁審理范圍。公平公正待遇原則是仲裁庭自由裁量權的又一來源,具有開放性與不可預測性,賦予仲裁庭將氣候變化議題納入審理范圍的權限。在《VCLT條約》未對該原則進行規定的情況下,仲裁庭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與各種情形進行綜合判斷。①仲裁庭可通過該原則來評價東道國的國內法規范,并與投資條約的解釋相聯系。如果東道國的國內法或司法實踐已有與氣候變化爭議直接相關的論述,則仲裁庭可援引這些論述來強化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角色定位。②這些論述也將構成投資者對東道國的合理期待,進而成為仲裁庭對投資條約予以解釋的依據。例如,若東道國長期存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要求以及始終強調相關的環境法原則,仲裁庭則可將其作為投資者的合理期待,進而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對投資條約的解釋。③仲裁庭在評估這種合理期待時,須審查投資人勤勉調查的義務。一旦投資者已履行勤勉調查義務,充分評估東道國投資環境的商業風險、政治風險和社會風險,超出投資者預見的東道國行為則是違反合理期待的行為。若投資者已對氣候變化政策與法規進行充分且必要的調查,仲裁庭在適用公平公正待遇原則時,可將氣候變化議題一并納入考慮。
第三,通過適用間接征收條款,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投資爭議的范疇并適用投資仲裁程序。在歐洲諸多可再生能源仲裁案中,投資者主張東道國變更可再生能源激勵機制的行為構成間接征收的行為,但并未獲得仲裁庭的支持[34]。仲裁庭以東道國采取的措施是出于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屬于重要的善意措施且符合東道國長期的法律傳統為由,否定構成間接征收的主張。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不應當僅立足于東道國的公共利益角度進行考慮,而應當依個案的具體情況認定事實,適用間接征收的法律。原則上,東道國為應對氣候變化而采取的措施,若構成對投資者的區別對待,就應認定為構成間接征收。如果投資協定已寫明,東道國基于氣候治理的需要所采取合法的善意措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差別待遇行為不構成間接征收,則不應認定相關措施構成間接征收[35]。只有遵循這種法律適用規則,由東道國明確應對氣候變化的善意措施是否屬于間接征收的行為,才能切實維護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平等地位。尤其是,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是東道國的義務,東道國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就應當在投資條約中明文規定,以滿足投資者對投資保護的合理期待。
此外,東道國所加入的氣候變化協定可能與投資條約相沖突,應當厘清規范沖突時的法律適用路徑。在投資條約與氣候變化協定發生沖突時,應當從強行法、事后法與特別法3個維度檢驗氣候變化規范的優先效力。在強行法維度,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公約本身屬于強行法規范[36],強行法規范的效力具有優先性。若東道國加入氣候變化協定,在投資保護規范與氣候變化規范沖突時,仲裁庭應優先適用氣候變化規范。若投資者母國加入氣候變化協定,氣候保護規范對投資者也具有法律適用的優先性。仲裁庭應將氣候變化協定締約國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理解為國際法上的單邊法律行為,其具有法律約束力,屬于國際投資仲裁的法律依據。在事后法維度,國際投資條約與氣候變化協定屬于不同主題,無法適用“事后法”優先原則。在特別法維度,國際投資條約的規定通常更為寬泛,而氣候變化協定中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規定更為具體。針對氣候變化問題,更具專門性的氣候變化協定符合“特別法”原則而應當被優先適用。
3. 2 條約制定:改革投資條約的內容
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直接依據是投資條約的實體性規定,這要求從條約制定的角度對投資條約的內容進行改革與擴充。目前,大部分投資條約并未規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部分新型投資條約雖然已規定可持續發展的內容,但相關條文主要是一種宣示性的條款,并不產生強制性的權利義務關系,無法對抗投資條約中的投資保護條款。基于此,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內容與氣候變化議題應當被寫入投資條約。
在宏觀上,氣候友好型的投資條約具有3個方面的要求。一是適用國際原則并明確投資者氣候保護的社會責任;二是關注各方對氣候保護的承諾問題并在投資條約中進行銜接;三是堅持可持續投資的理念并關注更廣泛的非經濟議題。其中,構建氣候友好型的投資條約具有兩種實現路徑:第一種路徑是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內容,第二種路徑是發展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具體路徑需要根據東道國的市場大小進行選擇。東道國的市場屬于大型市場時,第一種路徑雖會增加外國投資者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成本,但大型市場的投資價值依舊能吸引外國投資者;東道國的市場屬于小型市場時,需要采取第二種路徑吸引外國投資者。第一種路徑下的投資條約可以利用貿易規范達成氣候變化協議的目標,推進氣候保護政策的實施;第二種路徑下的投資條約可以減小貿易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
在微觀上,投資條約的具體條款也需要進行系統性調整,使相關條款與氣候變化議題相兼容。尤其是,應當將氣候變化納入投資條約的相關條款,推動投資條約朝著氣候友好型的方向改革。改革投資條約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氣候友好型的投資條約需要從序言規定與投資保護條款兩方面予以構建。①在序言規定中增加氣候變化的相關條款。國際條約的序言體現條約的目的與宗旨,具有補充解釋具體條款的作用。《VCLT條約》第31條第2款也明確規定,條約的解釋需要兼顧序言的內容。基于此,可考慮在投資條約的序言中引入《巴黎協定》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氣候法規范,并明確東道國與投資者在國際投資活動中遵守相關國際氣候法規范的義務與責任。②在具體條款中明確投資保護的實體標準。在投資準入門檻上,投資條約需要明確規定,投資者應當遵循東道國的氣候變化政策與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同時,東道國可根據自身議價能力的不同,適當調整審查力度,設置以碳排放為標準的階梯式準入條件規則。在公平公正待遇條款上,進一步明確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定,投資條約可通過排他性或列舉方式明文規定氣候變化問題上投資者合理期待的具體內容[37]。在間接征收條款上,投資條約應明確規定氣候變化爭議不構成間接征收的例外情形,東道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是否符合間接征收的定義應當通過投資條約中的條款進行明確;凡是不屬于投資條約中明確列出的間接征收的例外情況,相關行為在原則上都應當被認為構成間接征收的行為。
第二,投資條約應當明確否定氣候變化爭議屬于例外條款。氣候變化問題能否符合投資保護例外條款存在3種觀點,即反對成為例外條款、贊同成為例外條款與有限制地成為例外條款[38]。目前,尚未有投資條約明確將氣候變化問題作為投資保護的例外條款。因為,國際氣候法中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在重要性方面無法與國際法上的“安全閥”制度相提并論。《巴黎協定》的締約方所具有的義務,其實并非強制性的義務,主要是一種自主性與鼓勵性的安排[39]。氣候變化問題不應當成為例外條款符合相關國際法義務的非強制性特點,也有利于維持東道國與投資者之間的公平性。相反,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例外條款,對于外國投資者并不公平,也不符合將例外條款作為“安全閥”的制度目的。鑒于此,投資條約應當明確規定氣候變化爭議在原則上不構成投資保護的例外條款。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只有符合其他投資保護的例外條款,方構成排除適用投資條約的情形。
第三,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投資條約中專門的環境規制條款。當前投資條約中的專門環境規制條款并未直接規定氣候變化的內容,應當進行一定的變革。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為例,專門環境規制條款主要規定環境保護的目標、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的關系以及環境公約與該投資條約的關系,設立公眾參與、磋商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并未直接涉及氣候變化的內容[40]。對此,專門的環境規制條款應從兩方面明確當事人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法義務。從締約國的角度,需要在專門環境規制條款中增加締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權利與義務的內容。一是明確締約國具有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由的管制權,氣候變化議題構成締約國行使環境規制權的正當理由。二是明確締約國應積極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義務。締約國不得通過不完全履行或不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義務吸引外國投資,同時應積極履行氣候變化協定的義務、促進氣候友好型的投資和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從投資者的角度,需要在專門環境規制條款中明確投資者應對氣候變化的社會責任。具體而言,在實體法上,專門環境規制條款應要求外國投資者必須遵循東道國的法律,其中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一旦投資者不履行上述義務,則無法受到投資協定的保護。在程序法上,明確東道國有權以外國投資者違反有關氣候變化的東道國法律為由提出反訴。
4 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程序路徑
國際投資仲裁程序自身需要進行科學變革,以適應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特殊需求。這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在宏觀上,探索更加多元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投資仲裁平臺的供給機制;在微觀上,探索更為透明、高效和專業的投資仲裁運行機制。
4. 1 平臺供給:激發多元平臺的活力
首先,穩固全球性的投資仲裁平臺。ICSID是規則最健全的國際投資仲裁機構,但體制較為僵化,存在片面強調投資保護、裁決不具有可預測性和缺乏矯正機制等問題[41]。 ICSID仲裁作為一種投資仲裁工具,原則上仍須被接納為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手段。除非ICSID仲裁完全無法滿足東道國或投資者對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需求,否則不應當退出《華盛頓公約》;相反,應當積極推動ICSID仲裁機制的改革,促進仲裁庭回應當事人對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需求或期待。目前,ICSID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最大的障礙就是對“投資”內涵的解釋問題。在國際法學界,ICSID仲裁庭對投資的解釋主要存在2條路徑。一是意圖說的路徑。該路徑認為可以根據雙鑰匙孔原則對投資范圍進行擴張解釋,可以對爭議的原因背景進行整體性解釋,也可以從條約的有效性角度進行解釋。二是文本說的路徑。該路徑是將投資限定在Salini標準的范圍內,對具體要件進行嚴格的限縮解釋[42]。僅就氣候變化議題而言,需要積極推動仲裁庭采取意圖說的解釋路徑,使仲裁庭可審理氣候變化爭議成為ICSID仲裁機制的主流見解。
其次,探索區域性的投資仲裁平臺。若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皆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員國,這種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會提供相應的投資仲裁渠道。《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保留了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定,且將全球性的ICSID作為其仲裁平臺[43]。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RCEP)并未對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規定,也未設立專門的投資仲裁平臺[44]。RCEP未來可能的路徑之一就是采取《中-日-韓三邊投資協定》模式,只對投資仲裁進行框架性的設定,不對仲裁員、仲裁透明度等進行規定。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提供更大自由度的投資仲裁平臺,故氣候變化爭議中的雙方應當優先選擇這種更契合雙方經濟利益的投資仲裁平臺。其靈活性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允許雙方共同將調解程序作為投資仲裁的前置程序;二是允許雙方對具體的氣候變化爭議進行明確規定或排除;三是允許雙方繼續對投資仲裁進行上訴;等等。但這種投資仲裁平臺并不穩定,區域性協定的締約國應當深化相關合作,繼續健全相關規則。
最后,擴展商事化的投資仲裁平臺。投資仲裁的本質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仲裁,其核心是“去政治化”。在此背景下,涉及氣候變化爭議的投資仲裁也應當充分利用國際商事仲裁平臺。這種仲裁平臺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最高,氣候變化爭議的可仲裁性必須由當事人通過書面的方式進行確定。當前,國際商事仲裁并不排斥國家成為仲裁的一方當事人,通過國際商事仲裁平臺解決涉及氣候變化的投資爭議在仲裁規則方面也無障礙。國際商事仲裁在程序上的靈活性,也能為投資者與東道國提供更大的便利性與專業性。在現實中,國際商會仲裁院和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等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對國際投資仲裁的商事化已有豐富的實踐。基于此,在解決氣候變化爭議方面,國際投資仲裁應當與國際商事仲裁相互協作,利用國際商事仲裁平臺開展投資仲裁活動,對國際投資仲裁的商事化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
4. 2 機制實施:強化投資仲裁的優勢
其一,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要求建立一個更為透明、面向公眾的投資仲裁系統。傳統的國際投資仲裁在信任度方面存在仲裁透明度的問題與法庭之友參與仲裁的問題。氣候變化爭議對仲裁的透明度與法庭之友的參與要求更高。氣候變化問題還是一個復雜的氣候科學問題,僅依靠仲裁參與人提供的信息難免發生事實認知的錯誤。在仲裁的透明度方面,涉及氣候變化爭議的投資仲裁應以程序的全過程公開為原則,但在涉及國家利益時,東道國有權向仲裁庭申請不公開仲裁。具體而言,仲裁庭應及時公布涉及氣候變化爭議的仲裁案件信息;在開庭審理時,可提供網絡渠道以供社會公眾參與聽審,并及時公開仲裁裁決的結果。在法庭之友方面,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需要對第三方的參與更為包容。氣候變化議題具有公益性,第三方參與投資仲裁的基礎也是公益性。因此,在涉及氣候變化的投資爭議中,法庭之友需要被賦予更為實質性的程序參與機會,其中包括程序參與的便利化設計、仲裁庭對法庭之友意見的實質性審查等內容[45]。但為避免對仲裁程序的無意義干擾,對于不具有氣候科學專業知識或氣候保護公益背景的第三方,仲裁庭對其意見的審查應當更為謹慎。
其二,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需要提升仲裁的專業化水平。氣候變化問題具有突出的科學性與專業性特點,氣候變化的事實認定關系到溫室氣體排放的時間、數量及類型等不同因素,因果關系認定極為復雜[46]。仲裁庭在審理涉及氣候變化的投資爭議時,需要提升其專業化水平。一方面,仲裁員除了具備投資仲裁所要求的獨立性或公正性等職業道德外,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氣候科學知識。例如,相關仲裁員應當掌握全球變暖的科學知識,以促進仲裁庭全面了解氣候變化所涉及的科學、經濟與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仲裁庭在無法認定氣候科學的事實問題時,應主動引入專家證人以助其查明事實。這要求仲裁庭應制定一份專家證人名單,并賦予當事人在其中或另外選擇專家證人的權利。尤其是,需要結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所發布的有關氣候變化方面的報告,理解宏觀層面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厘清碳排放行為與氣候變化之間的因果關系[47]。此外,仲裁庭還應結合氣候變化議題與投資協定的專業性特點,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規則進行調整。若投資條約的保護范圍被限定在氣候友好型投資的范圍,則由投資者對氣候變化事項承擔舉證責任;若應對氣候變化措施適用投資條約的例外條款,則由東道國對氣候變化事項承擔舉證責任。
其三,氣候變化型投資仲裁需要實現仲裁程序的高效性,并健全投資仲裁的案件管理與集中審理機制。氣候變化爭議對于投資仲裁的便利性與高效性的要求更為迫切,同時,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也常被認為具有緊迫性。首先,仲裁庭應在投資仲裁程序中推行案件管理技術,以迅速解決涉及氣候變化問題的投資爭議。例如,在庭前進行程序性的聽證,明確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舉證要求,并在庭前會議上確定仲裁的時間安排,以及對投資爭議的焦點進行整理。其次,仲裁庭應盡可能地對氣候變化爭議進行集中審理。例如,集中進行事實與證據的調查,盡可能集中審理事實上、法律上以及證據上的爭議事項。最后,仲裁庭還應健全迅速解決氣候變化爭議的程序措施。例如,對于標的額在一定范圍內的仲裁案件,允許當事人選擇快速仲裁程序。又如,在仲裁程序中引入調解窗口,在不對仲裁造成程序延滯的情形下,允許雙方選擇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再如,完善緊急仲裁和仲裁臨時措施等機制,確保仲裁庭足以應對氣候變化爭議中的突發情形。
5 結 語
國際社會已對通過國際投資仲裁方式解決氣候變化爭議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實踐中,氣候變化爭議已成為國際投資仲裁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事實也證明,投資仲裁并不排斥對此類問題的解決。在理論上,將氣候變化爭議納入國際投資仲裁的審理范圍具有可行性,在國際投資仲裁的實體或程序的正當性方面也無阻礙。在國際投資仲裁與氣候變化爭議的互動中,投資保護與氣候保護并非不能協調。相反,二者都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都鼓勵和支持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無論是國際氣候法還是國際經濟法,都屬于全球治理的一種法律工具。這要求國際投資仲裁應當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衡量氣候變化議題,因投資產生的氣候變化爭議也應當被納入可仲裁的事項。未來,在《巴黎協定》所設定的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目標下,全球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將持續增加,通過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具有廣闊的現實需求。因此,通過國際投資仲裁解決氣候變化爭議已是箭在弦上,以積極開放的態度面對這種全球性趨勢,才是處理這一問題應當選擇的最優解。
參考文獻
[1] 高琪. 氣候變化應對類ESG 訴訟:對策與路徑[J]. 東方法學,
2023(4):165-177.
[2] ALOGNA I,BAKKER C,GAUCI J P.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M]. Leiden: Brill, 2021:15-17.
[3] 邊永民. 氣候變化訴訟的法律依據辨析[J]. 太平洋學報,2023,
31(3):94-106.
[4] SAND P H.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7,111(4):1074-1079.
[5] HAFNER-BURTON E M,PUIG S,VICTOR D G. Against secrecy:
the social cos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J].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7,42(2):279-343.
[6] GOUIFFèS L,ORDONEZ M. Climat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next big thing?[J]. Journal of energy amp; natural resources
law,2022,40(2):203-224.
[7] 趙玉意. 涉環境國際投資仲裁法律適用中規則選擇的困境與出
路:國際規則關系的維度[J]. 國際貿易問題,2019(1):147-159.
[8] CHOUDHURY B.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non?economic issues
[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20,53(1):1-77.
[9]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arbon
tariffs[J]. Harvard law review,2022,135(6):1640-1663.
[10] 張光. 論東道國的環境措施與間接征收:基于若干國際投資仲
裁案例的研究[J]. 法學論壇,2016,31(4):61-68.
[11] 馬忠法. 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技術轉讓法律制度研究[M]. 北
京:法律出版社,2014:228-230.
[12] TREAT S A. Fixing a broken system that promotes climate change
and depletion of global fisheries:WTO subsidy reform is just the
tip of the( melting) iceberg[J].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2019,
49(8):10755-10760.
[13] RESTREPO RODRíGUEZ T.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climate
change[M]. Cham: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2022:3-5.
[14] PEEL J, OSOFSKY H M.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J].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2020,16:21-38.
[15] BODANSKY D. Climate change:reversing the past and advancing
the future[J]. AJIL unbound,2021,115:80-85.
[16] 安德萬. 邊界組織: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的IPCC[J]. 自然辯證
法研究,2022,38(6):43-48.
[17] 魏慶坡. 碳排放權法律屬性定位的反思與制度完善:以雙階理
論為視角[J]. 法商研究,2023,40(4):17-30.
[18] CHOI W M.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aradig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7,10
(3):725-747.
[19] BOUTE A.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2,35(3):613-664.
[20] CONDON B J.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5,14(2):305-339.
[21] 劉禹,孔慶江. 碳排放政策的投資仲裁風險與因應[J]. 太平洋
學報,2022,30(4):44-56.
[22] 陳正健. 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理論與實踐[M]. 北京:當代
世界出版社,2019:179-180.
[23] 李賢森. 另辟蹊徑:我國Non?ICSID投資仲裁制度的建構與發
展[J]. 國際經濟法學刊,2023(2):87-106.
[24] DAVIES A. Investment law treaty interpretatio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legitimate expectations[J].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8,15(3):314-353.
[25] 徐樹. 國際投資仲裁庭管轄權擴張的路徑、成因及應對[J]. 清
華法學,2017,11(3):185-207.
[26] 趙玉意. 國際投資仲裁機構對涉環境國際爭端的管轄:主導與
協調[J]. 國際經貿探索,2017,33(9):99-112.
[27] 邊永民. 國際投資仲裁機構對涉及人權問題的投資糾紛的審
理[J]. 政法論叢,2020(2):25-36.
[28] 孫雪妍. 氣候風險下人權保障的司法類型化:法理探析及路徑
選擇[J]. 人權,2023(2):38-61.
[29] ISHIKAWA T. Counterclaim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 AJIL unbound,2019,113:33-37.
[30] 劉禹,莫漫漫,程玉. 投資仲裁下碳中和政策的爭端風險與應
對[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7):104-113.
[31] LING A. Adjudicating state counterclaims in ICSID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21,57(1):103-132.
[32] 桑遠棵. 國際投資仲裁中國家反訴的適用困境及其化解[J].
中國海商法研究,2023,34(1):102-112.
[33] 劉雪芹,黃世席. 國際氣候友好型投資爭端的解決與國家安全
例外抗辯[J]. 新疆社會科學,2022(3):113-123.
[34] 魏艷茹. 國際投資協議視野中的氣候治理[J]. 江西社會科學,
2021,41(9):193-200.
[35] 李俊然,趙俊娟. 國際投資協定與氣候變化協定的沖突與協
調:以國際投資協定的實體規則為視角[J]. 河北法學,2019,37
(7):130-142.
[36] CERVANTES M á M,ROEBEN V,SOLíS L 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as a jus cogens norm:some legal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ing evidence[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2022,52(5/6):
359-373.
[37] 梁丹妮,唐浩森.“雙碳”目標下的可再生能源投資仲裁研究:以
“投資者合理期待”為切入視角[J]. 武大國際法評論,2023,7
(4):119-140.
[38] 黃世席. 全球氣候治理與國際投資法的應對[J]. 國際法研究,
2017(2):12-31.
[39] 陳貽健.《巴黎協定》下國家自主貢獻的雙重義務模式[J]. 法
學研究,2023,45(5):206-224.
[40] 劉冰玉. 氣候治理投資安排:溯源、沿革與新路徑[J]. 法商研
究,2024,41(4):55-70.
[41] 余勁松. 投資條約仲裁制度改革的中國選擇[J]. 法商研究,
2022,39(1):59-70.
[42] 凌曄. ICSID仲裁裁決中“投資” 概念的界定[J]. 社會科學家,
2020(8):129-135.
[43] 張生. CPTPP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演進與中國的對策[J]. 國際
經貿探索,2018,34(12):95-106.
[44] 王彥志. RCEP投資章節:亞洲特色與全球意蘊[J]. 當代法學,
2021,35(2):44-58.
[45] 單菊銘. 法庭之友意見對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影響的實證研究:
基于ICSID案件的考察[J]. 國際法研究,2023(1):107-128.
[46] KELLER M,KAPOOR S.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civil liability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20,29(2):49-57.
[47] 林洧. 氣候變化訴訟的侵權事實認定:困境、架構與進路[J].
法治研究,2024(4):147-160.
(責任編輯:田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