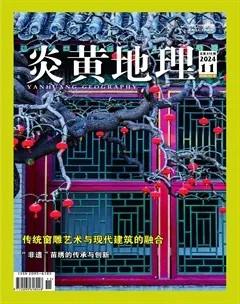西漢初年重農抑商政策考



文章結合重農抑商政策的普遍性與西漢初期的特殊性,探討西漢初年經濟社會發展及政策。文章首先闡述了重農抑商政策的起源、演變及困境,以及賈誼、晁錯等提供理論支撐,然后分析了重農政策與抑商手段,最后評估政策效果,如重農抑商政策的正負面影響。
西漢初年重農抑商政策產生的背景
西漢以前的重農抑商政策。中國作為農耕文明國家,重農抑商政策由來已久。在重農方面,《國語·周語》早有論述,“王事唯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從中不難看出周天子注重農耕,認為農耕是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線。在虢文公諫周宣王一文中記載:“夫民之大事在農,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此事導致“宣王料民于太原”,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局部人口普查,實質是強制征稅以充國庫和兵源。
西周時期實行“工商食官制”,周王室和諸侯國控制手工業者“百工”,其生活及生產由政府統一管理,產品專供貴族享用,不進入市場。官府設置專門官員管理手工業、商業及市場交易,這些職位世襲,從制度上抑制了商人崛起。
春秋戰國時期,重農抑商是變法改革的重要思想。許行、韓非、商鞅等提出“農本商末”。李悝是重農抑商的先驅,提出平糴法調節糧價。在司馬遷所著《史記·商君列傳》中也記載道:“僇力本業,舉以為收孥。”這也反映出商鞅認為農業是本業,商業是末業。《商君書·墾令》中,公孫鞅主張國家上層建筑服務經濟基礎,培養全心務農的新一代,視農業為政治首要。韓非子認為工商業者損害小農經濟,致社會不穩。秦始皇繼承重農抑商政策,為實現富農,派商人和罪犯戍邊、修建工程。
西漢初期社會經濟環境。公元202年,劉邦登基時,中原地區因戰爭和秦苛政而秩序混亂,經濟凋敝,上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狀況,下到人民不能果腹。如班固的《漢書》中記載:“秦時三萬余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西漢初年,人口流失普遍,經濟凋敝,財政赤字。為維護統治,漢高祖以黃老之學為指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漢文帝初開放資源利大商發展,導致商人哄抬物價。面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形勢,實施重農抑商政策,恢復了殘破的社會經濟,成為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
西漢前期重農抑商思想的發展。西漢初年,重農抑商思想在前代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如賈誼清楚地看到了西漢初年殘破的社會景象,提出了重農抑商政策的必要性。在政論《新書·憂民》中提道:“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同時賈誼也認為只有人民殷實、糧食富足才能使國家強盛,才能真正貫徹管子所提倡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能使國家強盛,符合周公的天下大同理念,讓各階層按周禮規范各盡其責。賈誼還在《治安策》中指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表明了他反對奢靡消費的主張,進一步完善了重農抑商思想。晁錯在《論貴粟疏》中指出:“民貧,則奸邪生……民如鳥獸。”他認為農民的災難源于天災、土地兼并及豪商破壞。當時人們轉向求富,政論家們緊急上書防思想走偏,為西漢初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農抑商的理論依據。
西漢前期重農抑商政策的具體表現
三十稅一。劉邦建漢后廢泰半之賦,行輕徭薄賦,田租減至十五稅一后改十一稅一。漢文帝再減佃租,田租減至三十稅一,持續12年至漢景帝時確立此政策,沿至東漢末。西漢初年還有口賦和算錢,口賦針對7~14歲兒童,每人每年20錢;算賦針對14~56歲成人,每人每年1算(120錢)。漢文帝將人頭稅降至每年40錢,算賦成為軍費來源,另征諸侯和地方官吏獻費。漢文帝、景帝減輕徭役,如將丁男每年一月更役改為每三年一次,并在公元前167年廢除戍卒令,利于農業發展。
頒布勸農詔書。漢代重視農業,帝王頒布勸農詔書,涉及多方面。西漢初期政府還重視農業技術教育,培養人民重視農業的習慣。《漢書·文帝紀》中記載,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這是帝王詔令首次肯定農業為西漢初年首要任務。漢文帝親自行籍田禮,皇后也種桑養蠶。在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又再次下詔書:“農,天下之本也,務莫大焉。”農業發展需增人力,漢文帝詔“免官奴婢為庶人”,強調農業重要性,此思想延及后世帝王。《漢書·景帝紀》中記載:“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文景二帝樹立勤勞耕種形象,鼓勵農業。他們頻發詔書,其中9道勸農,顯示對農業的重視,常自省效果。相比之下,商業被忽視。政府也征調人員培訓,推廣先進技術工具。
馬復令與貴粟政策。重農政策為西漢前期增收,主要用于對抗北匈奴。漢初對匈奴和親并賜予錢糧,漢文帝時行“馬復令”,鼓勵養馬以對抗匈奴。晁錯提出“貴粟政策”,讓人們用糧食買爵位或贖罪并將糧食運至長城沿線。這些政策助西漢經濟恢復,糧食產量提高,國家糧食儲備增加。
歸兵于農。西漢初,劉邦為安民樂業,下詔令士兵解甲歸田,按功績賜爵,并免其徭役。此舉促使士兵投身農業,以其集體之力推廣先進農耕,為國家創造財富。政府并行“徒民實邊”政策,引導人口從密集“狹鄉”遷往寬松“寬鄉”,以開墾更多土地。上述做法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抵抗外敵有益,但導致軍功地主、豪強興起,控制地方。如東漢末年豪強地主莊園可組建私人武裝,漢代選官制度如“辟除、征詔”等也助長了這一弊端。
興修水利。西漢初年國力不足,難以推廣灌溉技術。經文景之治至漢武帝初年,國力恢復,興修水利成為當務之急。漢武帝時修建150公里漕渠,后又建龍首渠,元鼎年間在鄭國渠基礎上開鑿六輔渠。水利設施修建便于灌溉,漢武帝在河西、酒泉、朔方、西河等新征服的地區用灌溉技術滋養農田。灌溉田地達10000公頃,糧食產量從每畝1石增至4石。興修水利不僅增糧,還保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
西漢初年重農抑商政策的措施
西漢初年,軍功地主轉變為商人囤積居奇、兼并土地,致人民破產,成為流民,影響社會穩定、勞役賦稅征收,且商人僭越等級制度。為此,西漢初期實行抑商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
漢高祖的重稅政策。西漢初年,帝王重農輕商,這與先秦貴粟思想及視商人為不穩階層有關。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凡編戶之民……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簡單來說,西漢初年商人富而欺壓百姓,漢高祖實施“賤商令”,取消高額農稅,對商人重稅、禁奢華、禁做官,限制其買地,旨在貶低商人地位,防止其成為封建地主。
漢惠帝時期禁止商人私人鑄錢。漢惠帝與呂后執政時期基本沿襲漢高祖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史記·平淮書》中記載:“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當時實行告緡令打擊驕奢工商業者。漢惠帝時之所以禁商人鑄錢,是因為允許私人鑄錢會增強地方勢力,不利中央。禁榷制度抑制商業,促人回歸農業,以重視農業。
漢武帝的抑商政策。文景之治后,經濟雖復蘇,但外有匈奴,內有諸侯矛盾加劇,貧富差距大。漢武帝為打擊商賈,公元前113年政府收回鑄幣權,減少商品交換困難。《史記·酷吏列傳》中記載:“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皆平作錢數。”漢武帝對平民和商人收稅,商人稅更重,平民有一輛車征收1算而商人加倍,其中船過5丈者也要加倍征收,平民的總資產稅是4000錢征收1算而商人是2000錢征收1算。除算緡政策外,漢武帝還頒布了告緡政策,鼓勵告發隱瞞財產者。元封元年,漢武帝實施均輸平準政策平抑物價,鹽鐵官營和酒類專營政策增加收入。這些政策打擊商人,平穩物價,增加財政收入,但鹽鐵官營也引發民憤。
重農抑商政策對西漢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的積極作用。人口增加。考量封建王朝強盛與否常看人口、財富的多寡。西漢初需增加勞動人口來發展農業,是因楚漢戰爭后人口達低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載:“天下初定,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大侯不過萬家。”西漢初年,人口蕭條,統治階級致力于恢復人口。漢高祖重農抑商、組織軍隊復員、輕徭薄賦,漢文帝、漢景帝繼續勸課農桑,實行三十稅一,頒布勸農詔書。到漢景帝晚年出現了“戶口亦息,列侯者大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的局面。再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局面。由此可見,人口顯著增加。
抑制土地兼并。從漢高祖到漢景帝雖強調抑商,但只是限制商人地位,未抹殺商業活力,反而給予支持。因統治者將輕徭薄賦與抑商政策結合,而導致漢武帝初年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這一點表明抑商政策還是值得肯定的。商人積累財富會導致義利關系轉變、等級僭越等問題。董仲舒提出限田建議后,度田事件顯示未有效控制豪強地主土地。西漢統治者通過賤商令、徒民實邊、重稅等政策打擊商人,抑制兼并,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重農抑商政策的負面影響。滋長小農意識。商鞅變法打破井田制,確立小農經濟,為封建王朝奠定基礎。重農抑商政策維護封建經濟,助經濟恢復,但導致保守、科技停滯,阻礙商品市場發展,且階級歧視影響商人形象。
資源爭奪頻繁。封建王朝初建時多行重農抑商政策以興盛王朝。但土地有限,人口增多后,失業農民變流民,被豪強控制,威脅中央。如漢光武帝“度田”遭反抗。多次此類事件會引發戰亂、改朝換代、人口減少、經濟凋敝,從而又開始新的輪回。封建統治階級未深刻意識到這點,今需以史為鑒思考“三農”問題。
官商主義盛行。官商依附性強,易受政府支持。封建社會雖抑商,但商業對國家強盛很重要,因此出現“禁榷”制度,即國家壟斷商業。官商主義導致產品質量低下,如漢武帝時期鹽鐵專營和酒類專賣。商人角色轉化,從軍功地主到豪強地主再到地方勢力,因統治者不懂權力下放,商人有機會左右政局。
西漢初年,統治者結合抑商、重農政策與農本、黃老思想,促進了社會經濟恢復與發展,出現文景之治等盛世,但后期政策固化,抑商手段隨中央集權加深而加強,從衣飾抑制到全方位打擊。重農抑商政策雖緩解財政、增加人口,支持了漢武帝抗匈,但對后世也產生負面影響,如官商主義導致產品質量問題。筆者認為,應靈活運用此政策于現代經濟發展,正確認識商業的地位,平衡農商。西漢初年實行此政策有必要,但如今需研究如何平衡農商,確保國民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