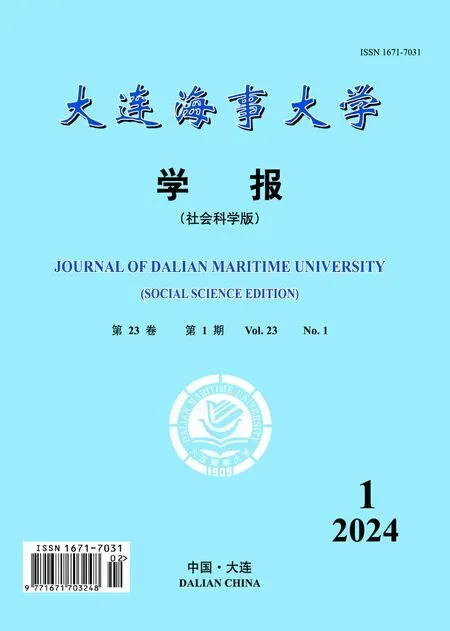中國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時空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高 鶴,宋雪亞
(1.中國黃金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2.大連海事大學 航運經濟與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一、引 言
人類健康與良好的生態環境息息相關,而全球氣候變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生態問題極大程度上威脅著人類健康。世界各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相應提出低碳行為措施,紛紛將國家的經濟發展轉變為以“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為特征的模式,中國更是向世界承諾努力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及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尤其是沿海城市憑借廉價資源、區位優勢、優惠政策,以全國1/10不到的面積和人口,創造出全國一半以上的經濟總量,成為全國和區域性的增長極,主導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命脈。然而中國沿海地區開發給沿海地區各城市環境帶來的負外部效應逐漸凸顯,人類健康和生存環境都受到了較大的危害。因此,分析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空間分布特征,探究沿海地區的能源碳排放變化特征的影響效應,有助于沿海地區經濟高速-能源低碳利用模式的開發,啟發沿海地區尋找適合自己的低碳發展道路,對減緩中國碳排放的壓力具有重大意義。
國內外學者使用各種空間技術對碳排放的時空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在碳排放的重心遷移方面,有學者發現中國碳排放的重心分布方向為東南方向,碳排放強度重心與經濟重心變動方向一致向西北方向遷移,其原因是碳排放強度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存在高度負相關關系,經濟重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碳排放強度重心向北移動[1-2]。在空間相關性分析方面,中國城市碳排放強度的空間相關性呈現出顯著聚集,城市碳排放空間集聚性增強的同時集聚水平在縮小[3],且中國東部地區碳排放總量高于西部地區碳排放總量[4]。在識別碳排放的影響因素方面,許多學者基于IPAT等式[5]和擴展STIRPAT模型[6]分析碳排放影響因素,發現中國的碳排放變化主要是由人口因素、經濟發展因素[7]、產業結構及能源強度[8]等因素引起的,且主要驅動碳排放的因素是經濟發展[9],主要抑制碳排放的因素是能源強度[10-11]。
綜上所述,碳排放問題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但現有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1)由于中國的碳排放體系并不完善,國家僅公布各省的碳排放數據,市級層面的碳排放數據很難得到準確的估算,因此我國學者大多數是從國家層面或者省級層面對碳排放進行研究;2)目前相關研究大部分使用單一方法探究能源碳排放空間分布狀態,同時從時間和空間上去分析碳排放的時空演變的研究較少;3)傳統因子分析模型分析相關性普遍存在共線性問題,雖然很多學者在研究中考慮使用添加控制變量等方法減弱因子共線性,但是通過該種方法探究的因子相關性往往存在較大誤差。因此,本文采用較為新穎的視角,以沿海地區113個地級以上城市為對象展開分析,研究對象從傳統的省級層面具體到市級層面,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綜合重心遷移模型和探索性空間數據模型對能源碳排放進行雙維度研究,并選擇地理探測模型探究沿海地區各城市能源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不僅能有效避免使用傳統因子分析模型存在的共線性問題,還能更準確地探測各影響因素對能源碳排放的影響程度,最終助力“雙碳”目標早日實現。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重心遷移模型
在重心遷移模型中,假設某地區由n個單元組成,其中第m個單元的中心坐標為(Xi,Yi),指標值為Ei,則該區域的重心坐標Ti(xi,yi)的計算公式如下:
(1)
(2)
本文中,Ei(i=1,2,…,113)為y沿海地區第i個城市某年份的碳排放總量。從第t年到第t+1年,該區域某屬性的重心移動距離的計算公式如下:
(3)
式中:C為常數,是把地理坐標單位(1°)轉化為平面距離(km)的系數,取值111.111。另外,為深入探究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在空間上的方向分布情況,本文還使用標準差橢圓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數據進行分析,具體方法參考文獻[12]。
2.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本文基于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數據,借助ArcGIS 10.8軟件,采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方法探究沿海地區的碳排放的空間集聚性和關聯性。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的核心是空間自相關的測度,主要包括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13]。全局空間自相關用來描述碳排放在研究區域內空間關聯性的總體特征,通常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Global Moran’s I)表示,計算公式為
(4)

局部空間自相關能夠對局部的空間聚集特征進行識別,本文采用局部空間自相關指數(Local Moran’s I)表示位于不同空間城市的高值集聚區和低值集聚區,其計算公式為
(5)
Ii為正值時,表示該區域單元周圍相似值(高值或低值)的空間集聚;Ii為負值時,則表示非相似值的空間集聚。采用LISA圖進行直觀展示,將具有顯著性的空間集聚單元劃分為“高-高集聚型”區域、“低-低集聚型”區域、“高-低集聚型”區域、“低-高集聚型”區域4類,其余為不顯著區域。
3.地理探測模型
地理探測器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個自變量對某個因變量有影響,那么自變量的空間分布和因變量的空間分布應該趨于一致[14]。參考已有研究,本文運用地理探測器方法中的因子探測及交互作用探測進行研究。因子探測主要用q值度量,其計算公式為
(6)

(二)數據來源
1.碳排放數據
本文選取沿海地區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等11個省份共113個地級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考慮到以化石能源為代表的傳統能源燃燒是能源碳排放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整合了2006—2020年沿海地區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氣和電力九類能源的消耗量,并依據各類能源的熱量轉換系數和碳排放系數計算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量。由于中國城市尺度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體系并不完善,各類能源的熱量轉換系數和碳排放系數參考已有文獻[18]。
2.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結合擴展的STIRPAT模型及現有研究,本文從規模結構、產業投資和能源強度等方面選取與碳排放聯系較為密切的7個指標,即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人口規模、土地城鎮化、能源強度、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1)經濟發展(X1),以人均GDP表示;2)產業結構(X2),以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表示;3)人口規模(X3),以年末總人口數量表示;4)土地城鎮化(X4),以建成區面積占行政區總面積的比例表示,城鎮化水平的衡量可以從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四個維度進行[19],為避免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本文重點使用土地城鎮化表征城鎮化水平對碳排放的影響;5)能源強度(X5),以地區能源消費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6)外商投資(X6),對外開放能有效優化國際資源配置,是提高我國國際合作與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且對外開放程度對工業碳排放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20-21],本文選取外商投資用以表征對外開放程度對碳排放的影響,以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表示;7)環境規制(X7),由于環境規制有力地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強度增長[22],且環境規制能通過抑制技術發展水平和調整產業結構等路徑間接作用碳排放[23-24],因此,本文參考任曉松等[25]的方法,環境規制數據由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SO2排放量及工業煙塵排放量計算得到。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07—2021年各城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
三、中國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時空格局演變特征分析
(一)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特征
本文選擇研究時期內等間隔年份和起始年份為代表年份(2006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為直觀展示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時空分布特征,采用ArcGIS軟件中的自然斷點法將2006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總量劃分為五個等級,并根據研究時期內實際演變數據進行相應的調整,最終將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劃分為以下五個等級:低度碳排放(0~500.00萬t)、較低度碳排放(500.01萬~1100.00萬t)、中度碳排放(1100.01萬~2500.00萬t)、較高度碳排放(2500.01萬~4000.00萬t)、高度碳排放(4000.01萬t及以上)。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總量分布特征如圖1所示。

整體來看,沿海地區在研究時期內時空演變規律顯著,即各城市能源碳排放總量逐年顯著增加,其中環渤海區域與長三角區域變化最大,而東南沿海區域、珠三角區域及西南沿海區域的變化較小。這可能與我國以環渤海和長三角地區為重化工業基地相關,重化工產業占比大,“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生產特點突出,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導致能源碳排放量大幅度上升;而東南沿海區域、珠三角區域和西南沿海區域是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前沿地帶,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節能減排工作做得相對較好,能源碳排放總量變化較小。
從局部空間分布上看,天津、上海和南京在較早年份就顯現出高度碳排放的特征,隨后在2020年高度碳排放區域增加了蘇州、杭州、寧波、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和欽州。對比各年份的碳排放分布圖,中度、較高度和高度碳排放三個等級的城市由2006年的20個逐漸增加至2020年的47個,能源碳排放的顯著增加對我國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的目標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能源碳排放的重心遷移及標準差橢圓分析
運用重心遷移模型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重心進行計算并利用標準差橢圓將計算數據可視化,可以直觀看到其在研究時期內在具體的研究區域上的空間重心位置點移動變化的特征,從而揭示時間段內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重心的空間動態移動變化規律,進而能夠測度沿海地區各城市能源碳排放在發展中的空間差異。本文采用ArcGIS軟件中的空間分析模塊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進行重心分析,得到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重心坐標、移動距離及方向,見表1。

由表1可知,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整體變動范圍為東經117.67°~118.11°、北緯31.73°~32.14°,重心總計遷移197.46 km,平均移動速度為13.16 km/年。從重心移動方向和距離看,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重心整體向西南方向移動,其空間移動軌跡可分為三個階段:1)2006—2009年向西南方向移動,相鄰年份間移動的距離為8.57 km~16.18 km,這一階段能源碳排放重心移動幅度較小,說明各城市能源碳排放變動相對均衡。2)2009—2013年向東北方向移動,該時期的重心移動恰好與2006—2009年抵消,因此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在2006—2013年間的變動相對穩定。3)2013—2020年向西南方向移動,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移動主要是該階段導致的,特別是2013—2014年與2019—2020年間重心移動距離高達32.70 km和39.97 km,表明沿海地區能源消耗在沿海南部城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較多。2013—2014年遷移原因可能是該時期我國正大力推進珠江三角洲建設為“粵港澳大灣區”且西南省份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分工;2019—2020年遷移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沿海北部城市在封城政策的影響下碳排放顯著減少。
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標準差橢圓分布情況如圖2所示,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標準差橢圓主要位于環渤海沿海區域、長三角沿海區域和東南沿海區域,標準差橢圓呈現“東北—西南”分布格局。在研究期內,標準差橢圓的面積明顯增大,說明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發展態勢并不穩定,空間差異性較為明顯。從半軸長度來看,長半軸長度由2006年1064.29 km擴大至2019年1091.87 km,短半軸長度由351.01 km擴大至374.84 km,說明沿海地區各城市的能源碳排放呈現空間發散的趨勢,總體上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重心偏向于南方,整體變化趨勢南方大于北方。

(三)基于ESDA的能源碳排放時空格局演變特征
1.能源碳排放時空格局演變總體特征
計算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全局自相關Moran’s I指數,結果見表2。表2中所有序列的全局Moran’s I指數的p值均小于顯著性水平0.01,通過顯著性檢驗,數據結果全部通過Z值檢驗,具有一定的統計學意義。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全局Moran’s I指數均大于0,集中于0.135~0.204之間,表明在研究期間沿海地區各城市之間能源碳排放呈現空間正相關,能源碳排放高度排放區域呈集聚狀態。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全局Moran’s I指數由2006年的0.135調整為2020年的0.166,呈現遞增趨勢,說明沿海地區各城市的能源碳排放空間相關性表現為不斷加強的趨勢。

2.能源碳排放時空格局演變局部特征
借助ArcGIS軟件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得出2006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局部空間自相關聚類,如圖3所示。由圖3可知:
1)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空間格局基本上保持穩定。蘇州、廣州、深圳和東莞從2006年以來就保持為“高-高集聚型”區域,即能源碳排放高值集聚區;在2015年上海、無錫、中山和佛山轉變為“高-高集聚型”區域,2020年南通由“低-高集聚型”區域轉向“高-高集聚型”區域;而中山在2020年從“高-高集聚型”區域轉向不顯著區域,排除數據誤差等原因,這可能是由于該地區的產業快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等原因使該地區出現集聚變化。
2)“低-低集聚型”區域在本文中的含義是能源碳排放低值集聚區域。在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演變過程中,顯著的“低-低集聚型”區域主要分布在西南沿海地區,如南寧、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欽州、貴港、玉林、百色、賀州、來賓和崇左;除西南沿海區域外,溫州、湛江、茂名和梅州也穩定于“低-低集聚”區域;到2020年“低-低集聚”區域包含溫州、南平、梅州、潮州、揭陽、汕頭、賀州、梧州、柳州和百色。
3)“高-低集聚型”僅出現在2006年的汕頭和2020年的欽州,其他年份均未出現“高-低集聚型”區域,而“低-高集聚型”區域穩定在廊坊、舟山、嘉興、湖州、鎮江和惠州等。

總的來說,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高-高集聚型”區域的時空變化顯著,呈現出逐漸擴張趨勢,而“低-低集聚”區域分布動態呈現緊縮趨勢,“高-低集聚型”和“低-高集聚型”區域的分布都較為穩定,表明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空間分布具有較強的空間集聚性,即空間集聚性顯著。
四、基于地理探測模型的能源碳排放影響因素分析
(一)因子探測結果分析
由于地理探測器軟件要求自變量為類型量,而本文中所研究的影響因子都為數值型連續變量,因此,在使用地理探測器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影響因子進行分析之前,首先利用ArcGIS軟件中的自然斷點法對自變量進行離散化處理。本文將各因素自然間斷為五個層級,隨后將離散化的自變量值代入GeoDetector軟件,得到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因子探測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2006—2020年,經濟發展、土地城鎮化、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具有顯著影響,而能源強度和人口規模對因變量的影響較弱,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產業結構對能源碳排放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由此可知,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單個影響因子主要是外商投資、土地城鎮化、經濟發展和環境規制,次要影響因子為人口規模和能源強度,產業結構并不是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原因。

(二)交互作用探測結果分析
交互作用探測主要是為了識別不同的因子交互是否會增加或減弱對能源碳排放的解釋力,本文使用地理探測器中的交互作用因子探測進一步探究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空間分異機理。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因子交互作用的結果見表4。從表4結果中發現:1)對比單因子探測和交互因子探測的結果,所有交互因子對能源碳排放空間分析的影響力都有明顯增強,說明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空間分異結果是由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人口規模、土地城鎮化、能源強度、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等多因素非線性耦合的結果;2)2006—2020年,經濟發展和土地城鎮化、經濟發展和外商投資、經濟發展和環境規制、土地城鎮化和外商投資以及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等交互因子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產生雙因子增強作用,除能源強度在部分年份具有雙因子增強效應外,其他交互因子均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產生非線性增強效應,表明經濟發展、土地城鎮化、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等關鍵交互因子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空間分異格局具有明顯的因子疊加效應。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數據,借助重心遷移模型和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型,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探究沿海地區各城市能源碳排放的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利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其空間分異的關鍵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第一,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時空演變規律整體顯著,各城市的能源碳排放總量逐年顯著增加,環渤海區域和長三角區域增加幅度較大,其余沿海城市增加幅度較小。能源碳排放重心整體向西南方向移動,標準差橢圓主要位于環渤海區域、長三角區域和東南沿海區域,其空間分布格局呈“東北—西南”方向。第二,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全局Moran’s I指數均為正數,各城市之間能源碳排放呈現空間正相關,“高-高集聚型”區域呈現出逐漸擴張趨勢,“低-低集聚型”區域呈現緊縮趨勢,“高-低集聚型”和“低-高集聚型”區域的分布都較為穩定,“高-低集聚型”僅出現在2006年的汕頭和2020年的欽州,其他年份均未出現“高-低集聚型”區域,而“低-高集聚型”區域穩定在廊坊、舟山、嘉興、湖州、鎮江和惠州等。第三,經濟發展、土地城鎮化、外商投資和環境規制等關鍵交互因子對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的空間分異格局具有明顯的因子疊加效應,其空間分異結果主要是由外商投資、土地城鎮化、經濟發展和環境規制引起,且影響程度逐漸減弱。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沿海地區各城市應實施差異化碳減排措施。沿海地區能源碳排放呈現出顯著的空間差異性,針對不同層級的碳排放,各級部門應通過不同側重點去制定和實施與該地區發展相符的碳減排措施。如高度碳排放、較高度碳排放及中度碳排放地區應將重心放在控制能源碳排放絕對量;低度碳排放和較低度碳排放區域應注重推廣和應用現有高新技術,引進更先進的技術,充分有效地利用沿海地區能源資源稟賦優勢,優化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第二,政府部門應當適當提高環境準入規制,對外商投資進行有選擇的引進和利用。環境規制是促進產業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適當提高環境準入規制,能夠有效引導沿海城市的龍頭企業將創新投入轉向環保技術投入。沿海地區各城市應該借助其區位優勢,加速對外貿易發展,將引資模式從單純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轉向有條件地選擇和利用外資,以此優化外資投入結構,引導外資更多地流向綠色環保型產業。
第三,沿海地區更應優化土地城鎮化、經濟發展和能源碳排放之間的耦合協同關系。規模結構、產業投資和能源強度各方面的影響因子對能源碳排放具有較為復雜的影響機制,處理好城鎮化、經濟發展與碳減排之間的關系,使土地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不僅能夠促進沿海地區實現低碳發展,還能推進落實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工作,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