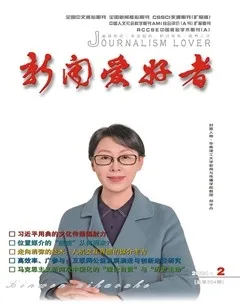視覺符號傳播視角下國潮創意的文化自信探究
熊錚錚 趙民濤
【摘要】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文化的表達形式正在經歷更新迭代,傳統文化在表現形式和視覺語言上都需要進一步創新。在傳統文化的表達與創新中,視覺符號給予受眾最直接、最有效的沖擊和體驗,對挖掘傳統文化、推動全新表達具有重要意義。以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為例,以視覺符號傳播理論為依據,探討節目創新表現中,傳統文化如何進行現代化轉變,提出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建議,讓人們更加關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關鍵詞】中國節日;文化自信;國潮;視覺符號傳播
2023年6月23日,河南廣播電視臺“中國節日”系列節目榮獲第28屆白玉蘭獎最佳綜藝節目,以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作為文本基礎,憑借其文化創新表現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當代表達的典范。“中國節日”系列節目將中華傳統文化的古典形象進行全新表達,引發了當代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熱烈討論,掀起了一股時尚的國潮風,在傳播中具有高度的文化穿透力,賦予了傳統文化新的表現形式以及由靜態到動態、由平面到立體、由守正到創新的文化語境。
一、轉化動力:視覺符號的創造性轉化
(一)視覺符號文本衍生出新的互文性生產實踐
所謂互文性,也叫做文本間性,可以理解為任何一個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其他文本的影響。如今,跨場域的“圖像和圖像”的互文結構在VR、AR、元宇宙等新媒介打造的沉浸式語境中得以出現。具體來說,“將他者圖像符號剝離原文本而納入新的文本表征體系并賦予特定的意義成為這一互文結構生成的要義所在”[1]。“端午奇妙游”的《定軍山》節目通過戲劇和電影畫面這一細節引入,將不同的畫面相結合,使受眾置身于形象的歷史場域之中。電影和戲劇中的畫面原本是節目《定軍山》文本之外的圖像,卻出現在節目之中,并且將“鼓槌”這一元素從中提取,以“鼓聲不停,傳承不止”的象征意義在舞臺上展開,這一符號的出場表達著父輩對年輕一代的囑托,此時的“鼓槌”也成為家族傳承的共振器,在演員反復的吟唱和眼神交流中,形象地呈現出家族傳承中不為人知的困難。由此可見,新的互文實踐給予文本新的文化內涵,賦予全新的審美價值,并在敘事效果上開辟了新的局面。
(二)具象符號概念介入中國故事樣本的隱性生成機制
在“中國故事”敘事模型的平面坐標中,對于橫縱坐標的歸屬,當今時代都設定了其對應的數值意義。首先,將話語實踐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在敘事坐標中橫向展開,同時用具象符號所生成的概念補充故事內涵的縱向坐標,這樣的作用機制應用于中華文化的時空語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講故事實際上是一種話語實踐,當某種符號對象被敘事者投入到其選擇的時空語境,便‘賦意了中國故事具體的內容特征。”[2]所以,在“中國故事”的平面坐標中,如果我們僅僅講故事,那么故事的文化內涵則略顯不足,尤其是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跨文化的輸出難免會出現“文化折扣”,在傳播中尋找共通的意義空間往往是有難度的。因此,通過將人們所熟悉和認同的具象符號引入中國故事樣本的隱形機制來增長故事軸距的縱向坐標,單一的故事文本通過具象符號文本等縱向指標的相互整合,形成具有獨特優勢的話語體系,諸如此類的縱向實踐在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得到廣泛應用。在“七夕奇妙游”《破陣樂》節目中,嘉峪關的雄壯威武、戚家軍的特殊武器破倭刀、戍邊清軍的嚴陣以待等各種具象符號的出場,讓觀眾聯想起一個個歷史故事,在縱坐標上完成了對橫坐標英雄人物故事敘事的補充。這樣的具象符號在中國故事的敘事坐標軸中開啟了中國故事的元講述,從基本的具象符號出發,故事情節能夠通過經典的視覺符號展開,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領航象征。
二、轉化探究:從“傳統文化”到“歌舞戲劇”的跨媒介探索
(一)春華秋實:“中國節日”系列節目文本中“中國符號”能指和所指的動態表達
能指和所指是符號學的關鍵術語,能指符號不要求信息傳達的準確性,相同的能指在不同文化語境下可能會有不同的所指。在“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服飾道具、舞美動作、舞臺呈現,這些節目大量地運用中國符號,其能指和所指的表達獨具匠心。“重陽奇妙游”的《釀秋》節目中,舞蹈演員的纖纖舞姿把“菊”的淡美演繹得栩栩如生。演員身著的裝束于肩、胸、腰、臀,服飾與人的結合將所指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以菊為載體展示出了中國美學的精神內涵以及中華女子的含蓄之美,菊的形象通過“釀”在舞蹈中得到了升華,意蘊得以深化,可謂“秋風清,秋月明,重陽用菊花釀了一個秋天,輕肌弱骨散幽葩,更將金蕊泛了流霞”。在舞美動作中,演員們在舞臺上“亦詩亦舞,亦動亦靜,剛柔并濟”,靈動的舞蹈動作將山水田園的人文精神賦予熒屏之中。在所指方面,傳統的重陽節與菊花這一意象緊緊聯系在一起,而節目《釀秋》正是以菊花為支點,用舞蹈動作表現其盛開、凋零、采集、釀造的全部過程,將菊花面對風霜歲月時的淡然與典雅之美展現出來,賦予菊花以生命的意義。同時,也增強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提高了社會凝聚力。
(二)百花齊放:“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伴隨文本的創新性輔助
符號文本的構建路徑需要大量的伴隨文本參與其中,根據文本間建立關系的方式和組成聯系的不同,伴隨文本分為前文本、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鏈文本、先后文本。“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伴隨文本,伴隨文本決定了文本生成與解釋的方式,對符號文本的表意過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符號接收與解釋,積極參與標志意義建構,直接影響標志意義解釋,并且隱藏在標志文本之后、文本之外和文本邊緣的就是標志的伴隨文本。”[3]
一個文化符號的生成,如果沒有前文本的參與,那么符號文本會與先前的文化產生割裂,成為讓人無法理解的符號。所以,前文本直接影響著符號的生成和理解。“七夕奇妙游”舞蹈節目《秀水伊人》展現了江南的風光美景,節目以“紅船哨兵”王會悟為人物線索,表面以柔美,實際卻是在展現南湖游船劃時代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場會議,表達了革命女青年心向陽光、內心堅韌的理想與追求。這些歷史文本都作為節目的前文本,我們可以發現,節目的靈感、故事情節設定、節目與節日文化的緊密連接,這些都有前文本的因素參與。
副文本在符號表意中起到關鍵作用,對“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的價值打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簪花仕女圖》《搗練圖》《明皇幸蜀圖》《千里江山圖》等這些家喻戶曉的畫作以及賈湖骨笛、武曌金簡、蓮鶴方壺、婦好鸮尊等博物館鎮館之寶作為“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的副文本,確保了“中國節日”的文化內涵和節目質量。
型文本在符號文本中起著歸類的作用,文本所屬的集群由型文本來劃分,影響著我們對符號文本的解讀以及期待。“中國節日”的系列節目大多以詩劇歌舞表演作為型文本將“中國節日”進行題材劃分,動作、音樂、服飾、道具、鏡頭、布景的有序組合在演員的表演下形成了動態的視覺符號文本。由于“中國節日”具有特定體裁,在對視覺符號文本進行創作的時候,就必須考慮這種文化性體裁的特點與要求,選擇相應的型文本。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憑借多個節目的爆火,已經形成了有其特定的風格、題材以及品牌價值的型文本模型,當“中國節日”系列節目出新,觀眾會主動選擇進入已經形成的型文本模型進行欣賞,同時這種已經具有品牌價值的型文本風格也在激起解碼者的閱讀期待。
元文本塑造符號文本的意義,符號文本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元文本來構建。盡管信息獲取的渠道不同,元文本的伴隨將符號文本的解釋范圍進行了很好的控制,使得譯碼者能夠順利理解符號文本。“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的相關報道以及海報的宣傳,為“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的詮釋范圍定下了區間,微博中各種節目的話題、評論引發全民參與,例如《2022中秋奇妙游》全媒體平臺進行推送,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多榜單熱搜上榜多次,其中節目“千里共嬋娟”相關熱搜引來了華春瑩點贊,“全球聯唱千里共嬋娟”在多平臺熱搜在榜。
(三)美不勝收:“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符號文本的雙軸關系
“兩個品牌或品牌與文化的結合實現文本陌生化,這實際上包含了一個選擇機制,而任何符號文本的構建都是符號雙軸的操作,品牌跨界形成的‘國潮符號文本亦是如此。”[4]這里的雙軸即組合軸和聚合軸,是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關系,前者考慮文本中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也可以看作構成整體的不同要素。后者更多關注的是構成文本的要素引發了人們的聯想。
在“中國節日”的符號文本中,制作方獨具慧眼,作為文本符號的編碼者,進行實際上的由縱到橫的運用。“清明奇妙游”中對《西園雅集圖》的內容進行選取,用新的形式演繹出文化潮流。《西園雅集圖》是宋代李公麟創作的水墨紙本畫,而在節目里選擇用新的“畫中有戲,戲中有畫”的方式進行呈現,就是制作方從縱聚合探尋橫組合的過程。而從觀眾的視角來看,雙軸運作則是由橫到縱的過程。作為解碼者,觀眾在節目中看到撫琴、調香、賞花、觀畫、弈棋、烹茶、聽風、飲酒、賞春玩樂等春日聚會活動里的視覺符號,這些是《西園雅集圖》文本中的橫組合,觀眾通過自身所具備的知識和文化素養,發揮一系列的聯想,這是從橫組合尋覓縱聚合的過程。另外,不同符號文本聚合軸的寬窄并不是一致的,有著寬幅和窄幅之分,聚合軸的寬窄直接影響著符號文本的風格。從“畫”到“戲”的轉化中,符號文本的聚合軸逐漸變寬。通過運用媒介技術,《西園雅集圖》這樣存在于文化中的“被動記憶”以單幕劇的形式表現出來,讓公眾自覺進行“主動記憶”,嘗試擺脫詩歌形式的“聚合軸夾裹”,進行“寬幅操作”。正是這種聚合軸逐漸變寬的演繹,增加了符號文本縱向的想象空間,在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割裂、重組、新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最終實踐:國潮在傳統文化表演中的演繹策略
(一)文化覺醒:符號修辭下的互動儀式激發個體情感能量
“符號修辭優化情感符號講述中國故事,嵌入傳播話語體系,在塑造國家形象的同時,象征著尋求中國情感的共鳴意義”。[5]通過符號互動來激發情感能量,需要建立由喚醒到共鳴的路徑。符號修辭可以作為由編碼者到譯碼者連接意義的機制,喚醒觀眾對文化的認同,因為符號文本的解釋項與符號修辭作用的內容具有共通的意義空間,都同樣能幫助譯碼者來更好地理解符號的意義。即使有著不一樣的文化背景,在符號修辭作用于符號文本的方式下,觀眾可以對文化符號產生情感能量,獲得情感共鳴,進而加入符號的互動儀式。
(二)科技賦能:時尚審美和媒介技術交相輝映
通過5G、VR、AR等這些技術的加持,現實與虛擬的融合讓傳統文化擁有全新的視聽場域,觀眾在場域中接收文化信息,擁有沉浸式體驗。“數字交互,身體在場”的數字人文交互給予觀眾全新的視聽感受。藝術與時尚相互轉化、相互融合,在科技的加持下鑄造全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審美實踐,從而以觀眾的視角提取新的藝術價值。
(三)國潮崛起:年輕語態的時空構建與青春力交互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青年群體在國潮文化構建和表達的過程中,賦予了文化在當代的身份認同和情感價值的新場域。可以說,青年群體的加入讓國潮在表達的主旋律上延伸為傳統與當代的結合和協作。在年輕化的語態時空中,當代青年與歷史文化、消費主義和新媒體空間的交互對話促進了國潮的發展。其中,歷史元素鑲嵌于國潮的內核,外在的表達形式則是時代創意的體現。如果想要協調好歷史元素和時代創意的合作,“青春力”的展現是提升國潮產品的重要路徑。
四、結語
國潮賦予傳統文化全新良好的表達契機,從視覺效果、中國話語體系以及媒介科技感這三個方面來看,國潮形象的品牌建構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系,國潮的發展得益于傳統文化和這三個方面產生的互動和協作。用中國符號講好中國故事,打造能夠傳播和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題材,以科技賦能為重要抓手,以年輕化表達為表現形式,以文化內涵和中國話語體系為精神源泉,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做好文化傳承,堅定文化自信。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海外社交媒體上的中國城市形象研究”(22BXW033);河南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品牌視覺符號傳播中的文化自信建構研究”(2021BXW02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張偉.符號互文、情境衍義與文化規約:當代視覺修辭的語境參數及其意指實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5):156-163.
[2]王昀,陳先紅.邁向全球治理語境的國家敘事:“講好中國故事”的互文敘事模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7):17-32+126.
[3]熊錚錚.伴隨文本對標志符號生成與解釋的影響:以奧運會徽為例[J].新聞大學,2016(6):125-134+152.
[4]蔣詩萍,周詩詩.論“國潮”品牌跨界的符號雙軸關系[J].符號與傳媒,2020(2):141-149..
[5]陳興,黃文虎.互動儀式鏈視閾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策略探析[J].新聞知識,2020(1):23-27.
作者簡介:熊錚錚,中原工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鄭州 450000);趙民濤,中原工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2022級碩士生(鄭州 450000)。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