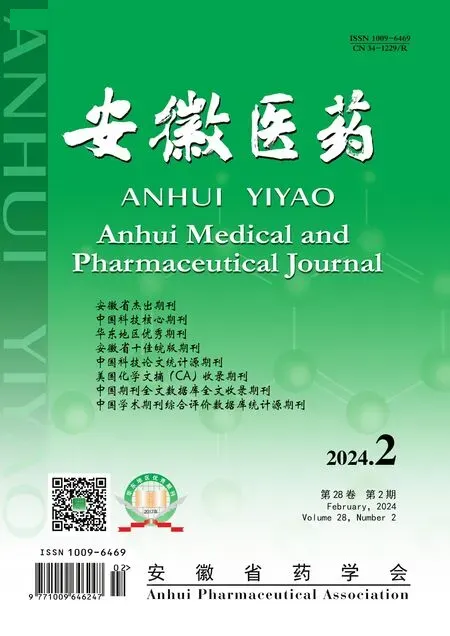兒童慢性肉芽腫病移植及基因治療研究進展
疏恒,葉同生,趙鈺瑋,戴立英,劉光輝
作者單位:安徽省兒童醫(yī)院新生兒科,安徽 合肥 230051
慢性肉芽腫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CGD)最早是在20 世紀50 年代被Janeway 發(fā)現(xiàn),由于編碼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oxidase complex,NADPH)氧化酶復合物亞單位的基因缺陷引起的吞噬細胞功能異常的原發(fā)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e deficiencies,PID)[1],遺傳方式有以蛋白gp91phox缺陷的X 連鎖隱性遺傳和以p47Phox缺陷為主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發(fā)病率約為 1/25 萬~1/13 萬,臨床可反復出現(xiàn)嚴重細菌或真菌感染威脅病兒生命,以及過度炎癥性疾病嚴重影響病兒生長發(fā)育及生活質量[2-3]。目前傳統(tǒng)預防及治療并沒有重大突破及更新,本文主要闡述近年來關于移植及基因治療相關的研究進展。
1 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
自 1977 年首例造血干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治療 CGD 成功,40多年來HSCT 已被認為是嚴重CGD 的治愈性方式,成功移植后幾乎可以達到無病存活[4-5]。最近一項多中心研究證實了這些觀察結果,3 年中位生存期為85.7%,無事件生存率(event free survival,EFS)為75.8%[6];當嵌合度超過90%,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病人癥狀也可以完全消失[7]。但因為移植同樣需要面臨供體短缺、預處理相關毒性、植入失敗、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和移植后感染等問題,且無法充分評估晚期影響,關于HSCT仍有爭論。
1.1 HSCT 移植時機及指征研究顯示經(jīng)過合理有效的傳統(tǒng)預防和治療,大約90%的CGD 病人將會存活到成年[8],部分研究也顯示移植和非移植病人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方面并無明顯差異[9],已經(jīng)不再盲目認為任何能獲得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 相合供者的CGD 病兒均應盡早進行HSCT,而是將是否能在發(fā)生器官損害前獲得比傳統(tǒng)治療更好效果作為移植適應證的核心原則,對于長期沒有曲霉菌病或結腸炎等并發(fā)癥的病兒來說,持續(xù)觀察和等待可能是更好的選擇[10]。來自一項跨度60多年的回顧性研究發(fā)現(xiàn)≤14歲時移植與移植相關生存率(transplant related survival,TRS)改善相關(HR=4.51;P=0.035),診斷后30年的存活率估計為65%[11],因此,建議對于所有HLA 配型≥9/10 的NADPH 氧化酶活性缺失的年輕CGD 病人才應該考慮進行HSCT,特別是小于14歲、無活動性并發(fā)癥的病人效果極好,而且確診后越早越好,8歲前更佳[9,11],2年OS可達90%以上[12],與傳統(tǒng)治療相比病兒生理及心理狀況顯著改善[11,13]。
1.2 如何選擇合適的供體找到合適的供體是HSCT 的前提條件。HSCT 的最理想供體是HLA 相合的同胞供體(matched sibling donor,MSD),OS 最高,移植失敗(graft failure,GF)、GVHD 和移植相關死亡率(transplant related mortality,TRM)的風險更低,但是總體來講這樣的供體不足30%[14],而我國可能還不到10%,其余的則需要一個替代的供體,那么在沒有MSD 的情況下,HLA 相合的非血緣供體(matched unrelated donor,MUD)是首選;而因為臍血更快的可獲得性以及更低的急慢性GVHD,通常用于急需移植的嬰兒或幼兒[15];因為HLA-單倍體相合的供體與更高的GF率、嚴重GVHD和免疫延遲重建風險相關,在以前被認為是在其他替代供體不可用時的最后手段,然而,隨著移植物操作策略的最新進展,如移植后環(huán)磷酰胺和選擇性去除T細胞受體,使其幾乎等同于來自其他替代供體的HSCT[16],我國唐湘鳳團隊運用單倍體HSCT 聯(lián)合第三方臍血移植治療CGD 及其他PID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植入成功率、供體嵌合度高、GVHD 發(fā)生率低,TRM 為11.9%,53/60 例無病存活,5 年的無失敗OS 和整體生存率分別為83.9%和88.1%[17],該方法既發(fā)揮了單倍體移植供體來源穩(wěn)定、造血和免疫重建快的特點,同時又發(fā)揮了臍帶血免疫調節(jié)、促進植入、降低排異的優(yōu)點,療效顯著,特別適合我國國情。而隨著HLA 分型技術、GVHD 預防和并發(fā)癥處理方面的進步,替代供體的HSCT也越來越安全和可行。
1.3 預處理的方式預處理是影響移植結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需綜合考慮病兒原發(fā)疾病、感染程度、供體類型及合并癥等因素,鑒于傳統(tǒng)的清髓性預處理(MAC)方案較大的毒副作用,特別是在嬰兒和兒童中可引起生長障礙、性腺功能障礙和繼發(fā)性惡性腫瘤等晚期副作用,近年研究表明降低強度/ 降低毒性的預處理方案(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RIC/reduced toxicity conditioning,RTC)對CGD 病人(包括IBD 病人)是安全有效的,已成為降低TRM 和晚期不良事件的首選[18-19],在非惡性疾病中已證實可提高兒童 HSCT 生存率,特別是對于合并嚴重程度感染的病人時,即使出現(xiàn)混合嵌合體,也并不影響OS和EFS[20],但對于出現(xiàn)混合嵌合體的女性CGD 攜帶者仍還需進行長期隨訪,以評估自身免疫疾病的可能性[21],目前已被歐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學會(european society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EBMT)/歐洲免疫缺陷學會(european society for immunodeficiencies,ESID)指南推薦的RIC 方案由氟達拉濱和烷化劑組成,如環(huán)磷酰胺、塞替派和曲奧舒凡等[18],但因清髓效應不徹底,也需同時面臨混合嵌合及植入失敗的風險,因此對于具有較高GF 風險的病人,MAC 的療效優(yōu)于RIC[22]。當然預處理方式的選擇和供體類型也密切相關,EBMT/ESID 指南建議對于臍帶血或單倍體相合的供體建議采用MAC,其他供體來源則采用RIC/RTC 的預處理方案。國內因以單倍體相合供體為多,且缺乏一些新藥如Alemtuzumab 和Treosulfan,主要還是采用MAC方案,病兒不僅能耐受預處理,也能獲得穩(wěn)定的完全嵌合體[17]。
1.4 GF 的預防HSCT 術后良好的結果取決于對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移植物衰竭的預防(包括骨髓供體嵌合體下降至10 %以下,以及GVHD)[23]。作為最嚴重的并發(fā)癥,防治GVHD 至關重要,尤其是對于單倍體及無關供者的移植,目前采用的方法有體外去T 細胞、回輸干細胞后給予環(huán)磷酰胺、血清療法(抗胸腺細胞球蛋白、抗淋巴細胞球蛋白和抗CD52單克隆抗體阿侖單抗)及低劑量輻射[24],有學者在此基礎上聯(lián)合富含內調節(jié)T淋巴細胞和間充質干細胞的臍血,研究發(fā)現(xiàn)它們在防治GVHD 中發(fā)揮重要作用[25];另外對于其他免疫缺陷疾病目前已采取一種新型的選擇性去T 細胞(TCRαβ T 細胞)的HSCT應用于PID,留存TCRγδ T 細胞、NK 細胞、樹突狀細胞、調節(jié)性T 細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6-27],成為后期研究的一個方向。
2 基因治療
自體基因治療(gene therapy,GT)作為一種新的治療方式,因可避免GVHD 和其他同種異體反應性并發(fā)癥[28-29],以及降低預處理方案的復雜性,在沒有遺傳毒性證據(jù)及供體的情況下,成為更有前途的治療方式。
GT 的臨床試驗始于1900 年末,起初由γ-逆轉錄病毒為載體,但不幸的是因為持續(xù)的增強子活性引導了原癌基因的插入激活,導致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征的發(fā)生,或只是顯示短期的臨床收益,自2000年以來,設計了一種具有嵌合內部啟動子的自失活慢病毒載體[30],該啟動子優(yōu)先驅動gp91phox在吞噬細胞中表達,利用富含HSC 和祖細胞的自體CD34+治療X 連鎖CGD,69 例病人隨訪中表現(xiàn)出穩(wěn)定的載體拷貝數(shù)和持久的氧化酶活性[28],基于這一有希望的結果,F(xiàn)DA 已于2020 年1 月授予這種基因治療藥物(OTL-102)指定用于治療X 連鎖CGD。盡管載體研究有所突破,但基于傳統(tǒng)基因治療帶來了不可避免的插入突變風險,新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則可以在離體或體內細胞上介導基因添加、切除、校正和其他高度靶向的基因組修飾,通過位點特異性核酸內切酶如鋅指核酸酶、轉錄激活因子樣效應核酸酶或CRISPR/Cas9 核酸酶進行的基因編輯顯示了巨大的潛力。通過核酸內切酶誘導的雙鏈斷裂(doublestranded break,DSB)的產生來啟動靶向DNA 改變,但因鋅指核酸酶或轉錄激活因子樣效應核酸酶需要為每個新的DNA 靶標設計一對特定的核酸酶[31-32],加上CGD病人基因突變的獨特性,需要為每位病人單獨設計,增加了實際應用難度及成本,而其中CRISPR/Cas9核酸酶最具發(fā)展前景[33],CRISPR/Cas9 核酸酶由一個設計好的單向引導的RNA 的指引下與感興趣的靶位點互補,可以實現(xiàn)有效的DSB,其通過導致插入或缺失的非同源末端連接途徑或允許供體DNA 摻入的同源定向修復途徑進行修復[34],并已經(jīng)被研究證實[35-36]。使用靶向基因編輯技術對來自CGD 病人的誘導多能干細胞或祖細胞進行同源定向基因修復的臨床前研究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分化的中性粒細胞中NADPH 氧化酶基因表達及其活性的功能性恢復[37],但目前該領域仍有許多挑戰(zhàn)需要克服,包括來自細胞的來源和培養(yǎng)、核酸酶和校正模板的遞送、脫靶基因組編輯的基因毒性、核酸酶活性和基因校正的效率,對核酸酶的免疫反應、移植物衰竭以及高昂的價格[33,38]。預期效果如何,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以達到臨床應用的目標。
3 小結
有效的感染預防方案和積極的干預措施的發(fā)展大大改善了CGD 病兒預后。我們認為,HSCT 治療因個體化,提供給沒有其他治療方案且患有嚴重感染和/或自身炎癥并發(fā)癥的年輕、高危CGD 病人,對于沒有匹配供體的高危CGD 病人應該開展更多單倍體相合的HSCT和GT的前瞻性試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