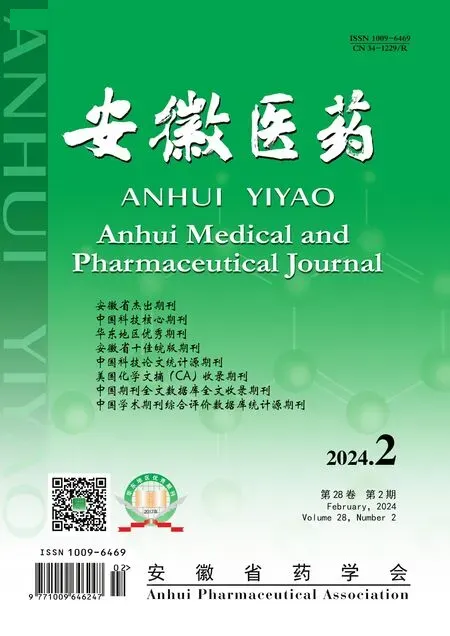生物靶向制劑與高T2型哮喘
何苗,王翎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全科醫學科,江蘇 蘇州 215006
哮喘是一種異質性疾病,其本質為慢性氣道炎癥,表現為氣喘、咳嗽、呼吸困難和胸悶等癥狀[1],大多數患有哮喘的成人和兒童可以通過使用吸入性皮質類固醇(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和長效支氣管舒張劑很好地控制,但嚴重哮喘病人(占全球哮喘病人人口的5%~10%)仍需輔助生物制劑治療[2],我國哮喘總體控制水平尚不理想,根據全球哮喘倡議(GINA)定義的哮喘控制水平分級,我國城區哮喘總體控制率為28.5%[3]。目前多種生物靶向藥的研發迎來了哮喘個性化治療的新時代,掌握其臨床應用及最新進展對提升我國哮喘控制水平意義重大。
1 T2型哮喘病理生理學
哮喘最早提出分為兩種內型:高T2 型和低T2型。高T2 型哮喘由Th2 細胞因子、嗜酸性粒細胞(eosinophils,EOS)、警報蛋白和免疫球蛋白E(IgE)驅動,機體接觸刺激物后會被樹突狀細胞等抗原提呈細胞攝取加工產生白細胞介素(IL)-4,并反過來作用T 輔助細胞分化成Th2 細胞,分泌IL-4、IL-5 及IL-13 等細胞因子,誘導B 細胞產生特異性IgE(sIgE)觸發肥大細胞脫顆粒[4]。警報蛋白包括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IL-25 和IL-33,其中IL-25 和IL-33 主要激活Ⅱ型固有淋巴樣細胞(ILC2s),TSLP 還啟動抗原提呈細胞激活T、B 細胞來促進2 型免疫。大量證據表明,ILC2s 在氣道組織中含量尤其高,產生的IL-5 和IL-13 是活化Th2 細胞的10 倍,在增強氣道的2 型反應方面起關鍵早期作用[5]。因此,ILC2s 和Th2 細胞是增強T2 炎癥的關鍵來源,故目前“2 型”哮喘而非“Th2”型被廣泛關注。
低T2型哮喘的機制仍然知之甚少,可能涉及輔助性T細胞,Th17細胞和干擾素γ(IFN-γ)的失調[6]。目前雖然有針對低T2型哮喘的新興生物療法,但這種類型的總體鑒定和使用生物標志物來監測治療反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在本綜述中,我們將重點介紹生物靶向制劑對高T2型哮喘的治療。
2 T2型哮喘炎癥生物標志物
個性化醫療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是應用生物標志物對病人進行分層,理想情況下,生物標志物可能是病理生理治療靶點本身,在設計和實施高效經濟的臨床試驗中至關重要。呼出氣一氧化氮(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IgE、痰液和血液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及血清骨膜蛋白(serum periostin)都是T2炎癥的重要生物標志物,可以幫助預測哮喘對生物制劑治療的應答反應[1,4]。
常規測量血清中游離IgE 可以預測對奧馬珠單抗(Omalizumab,Xolair)治療無應答的病人,但一旦治療開始測量血清IgE 反映的是奧馬珠單抗-IgE 復合物,因此治療期間的血清IgE 不是對奧馬珠單抗治療反應的預測指標[7]。血清IgE 不能預測對抗IL-5 藥物的反應,mepolizumab 的有效性與基線IgE無關[1]。但有研究表明dupilumab 可降低過敏性和非過敏性哮喘病人的血清總IgE,并降低過敏性哮喘病人的過敏原特異性IgE[8],提示我們對IgE 的探索仍遠未完成。
痰嗜酸性粒細胞的表達被認為是診斷T2 型哮喘的金標準,可在細胞水平上提供有關氣道狀態的信息。然而痰液是一種難以分析的生物標本,且在大多數臨床中心很難檢驗。相較而言,更易獲得的血EOS 是預測除奧馬珠單抗外所有目前可用于嚴重哮喘生物制劑治療效果的最成熟的生物標志物[1]。Ortega 等[9]的二次分析顯示,mepolizumab 在較高基線的血EOS 和更頻繁惡化的病人中顯示出更強的臨床療效。然而血EOS 增多并不能統一預測治療反應,在一項共納入872 例采用奧馬珠單抗治療嚴重過敏性哮喘病人(SAA)的研究中顯示[10]:SAA 病人對奧馬珠單抗反應不隨血EOS 計數而變化,提示奧馬珠單抗在“高”和“低”嗜酸性粒細胞組中的治療效果相似。一項前瞻性研究也顯示,無論治療前血EOS 及FeNO 如何,奧馬珠單抗都能顯著減少哮喘的急性發作[11]。這表明某些低生物標志物亞組的病人也可以從生物靶向治療中受益。
血清骨膜蛋白是支氣管上皮細胞響應IL-4/IL-13而分泌的細胞外基質蛋白,與調節黏液生成和氣道重塑有關,可用于篩選病人能否進行抗IL-13治療,且測定相較于FeNO 和嗜酸性粒細胞更穩定,日本相關研究顯示基線血清膜蛋白水平可以預測奧馬珠單抗治療反應[12]。在抗IL-4α 治療中,高血清骨膜素組在接受lebrikizumab 和dupilumab 治療時,哮喘急性加重和肺功能緩解更明顯[13]。
一項來自歐洲多中心研究支持使用尿白三烯E4(LTE4)和前列腺素D2(PGD2)代謝物作為潛在的生物標志物來指導哮喘的分子表型[14]。二肽基肽酶-4(DPP-4)水平較高病人的肺功能和健康狀況對tralokinumab 治療表現出更好改善[15],已被提議作為抗IL-13 治療的候選預測生物標志物,未來的研究應評估額外的生物標志物。總之,這些標志物的升高可能表明治療反應性并進一步指導哮喘分層,這將允許臨床醫生選擇性地使用生物制劑,并最終為個性化醫療提供路線圖。
3 高T2型哮喘生物制劑靶向治療
3.1 抗IGE 抗體奧馬珠單抗是首個被批準治療哮喘的生物制劑,通過阻止IgE 與其在肥大細胞、抗原呈遞細胞和其他炎癥細胞上的高親和力FcεRⅠ受體結合,特異性結合游離IgE 并阻斷過敏級聯反應。奧馬珠單抗治療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地研究的證實,其應用減少了醫療資源的使用,顯著減少吸入性(ICS)及口服(OCS)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劑量,改善哮喘癥狀及肺功能、提高生活質量、減少住院率[11],還抑制促炎細胞因子和TGF-β的產生,從而預防氣道纖維化,顯著降低氣道壁厚度[16]。此外其對阿司匹林加重呼吸道疾病(AERD)、過敏性支氣管肺曲霉病(ABPA)、哮喘COPD 重疊綜合征(ACOS)也有較好療效[17]。常見的不良事件包括藥物注射部位的局部反應、鼻咽炎、頭痛、上呼吸道感染和鼻竇炎,長期使用奧馬珠單抗不會增加出現惡性腫瘤的風險[18]。
利格珠單抗(Ligelizumab,QGE031)是人源化的IgG1 抗體,其結合IgE 比omalizumab 有更高的親和力,在體內模型中抑制FcεRI 依賴性過敏反應更有效,但在抑制FcεRⅡ/CD23 介導的IgE 信號傳導方面效果不如omalizumab[19],且在2 期試驗中顯示并未顯著改善哮喘ACQ-7 評分,未能證明療效優于安慰劑和omalizumab[20]。
3.2 抗IL-5/IL-5R 抗體IL-5 是嗜酸性粒細胞增殖、遷移、活化的主要調節因子,導致氣道平滑肌收縮、氣道重塑和黏液生成增加,成為哮喘的主要藥理靶點之一。抗IL-5 治療是嚴重嗜酸性粒細胞增多哮喘病人的首選,目前開發的三種抗IL-5 藥物均可將嚴重嗜酸粒細胞性哮喘病人的哮喘惡化率降低約50%, 減少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21]。
美泊利單抗(Mepolizumab,Nucala):是第一種被批準的一種人源化IgG1 單克隆抗IL-5 抗體。一項涵蓋19 個國家的多中心、 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3b 期試驗(MUSCA)中[22]:mepolizumab 在嗜酸性粒細胞升高的哮喘病人中可以減少哮喘發作、改善哮喘控制(SGRQ)評分和全身性糖皮質激素使用。雖然一些研究顯示FEV1 有所改善,但2017 年Cochrane[21]回顧顯示與安慰劑相比并未發現使用mepolizumab對肺功能有任何臨床意義的改善。
瑞利珠單抗(Reslizumab,Cinqair):是一種人源化IgG4 單克隆抗體,阻止IL-5 與其受體α 的結合。在Castro等[23]3期試驗中,對于吸入高劑量ICS未得到充分控制的病人,血EOS≥400 U/mL 時,reslizumab使肺功能和癥狀有所改善,但這些影響在嗜酸性粒細胞水平較低時不顯著。3 期研究的事后分析表明,reslizumab可能有助于減少伴有鼻息肉病的慢性鼻竇炎病人的哮喘惡化[24]。
苯那利珠單抗(Benralizumab):是一種針對IL-5α 亞基的IgG1 單克隆抗體。匯總分析顯示,無論血EOS 基線如何,benralizumab 都能緩解哮喘急性加重,但肺功能和哮喘相關問卷評分的改善僅在較高嗜酸性粒細胞亞組中顯著[21]。一項為期28 周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benralizumab 使病人口服皮質類固醇使用量減少75%,每8 周給藥能使哮喘年急性發作率比安慰劑減少70%,52%接受治療的病人能夠完全戒斷口服皮質類固醇[25]。
目前三種IL-5 拮抗劑都有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使用IL-5 抑制劑觀察到的最嚴重的不良反應是過敏反應,有文獻表明嗜酸性粒細胞數量減少可能會增加某些黏膜癌的風險[26]。其次,嗜酸性粒細胞在維持脂肪組織代謝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長期抑制嗜酸性粒細胞可能會導致肥胖和代謝功能障礙,包括胰島素抵抗[4]。我們需要對接受抗IL-5治療的病人長期隨訪以解決這些潛在風險。
3.3 抗IL-4/IL-13 抗體IL-4 和IL-13 都利用共同的IL-4Rɑ鏈通過轉錄因子信號傳感器和轉錄6激活子(STAT6)的磷酸化和激活來啟動信號傳導,IL-4和IL-13 促進杯狀細胞過度表達,增加黏液分泌以及氣道高反應性。
目前抗IL-13 生物制劑的臨床試驗療效大多不理想,其中Lebrikizumab是一種人源化IgG4抗體,干擾IL-13 與IL-4rα 的結合,2 期試驗顯示在基線高血清骨膜蛋白水平的病人中,哮喘急性加重率和FEV1 改善更明顯,然而在兩項重復的3 期實驗中,生物標志物高組(血清骨膜蛋白≥50 ng/L 或血EOS≥300個/微升)的病人對lebrikizumab 治療效果未顯示出一致性,且FEV1 雖顯示輕微改善但哮喘相關評分沒有差異[27]。另外Tralokinumab(CAT-354)在3期試驗中顯示其未能減少嚴重哮喘病人口服皮質類固醇的劑量,ACQ-6 和AQLQ 評分無明顯改善[28]。在GSK679586 的2 期研究中,對使用了最大推薦劑量ICS 治療仍無效的重度哮喘病人,附加GSK679586 治療未能證明有ACQ-7 評分和FEV1 的改善,且治療前后IgE 水平和血EOS 基本保持不變[29]。 雖然單獨阻斷IL-13 尚未被證明對治療哮喘有效,但IL-4和IL-13的雙重阻斷顯示出希望。
已經開發的兩種針對IL-4Rα 的單克隆抗體,其中AMG-317 顯示出相對較差的藥代動力學,并且在中重度哮喘病人的臨床試驗中沒有顯示出療效。杜普利單抗(Dupilumab,Dupixent)是目前唯一獲得FDA 批準的靶向IL-4Rα 的人單克隆抗體,可減少哮喘急性加重率,改善FEV1 和ACQ-5 評分[8],此外,dupilumab 在改善支氣管高反應性方面比IL-5 抑制劑有更顯著的作用,并能降低FeNO、IgE 等2型炎癥生物標志物水平,但有研究結果表示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升高[30], 因為IL-4/IL-13 阻斷機制可能不是抑制嗜酸性粒細胞分化,而是通過阻止嗜酸性粒細胞從血液中招募到組織中[31]。Dupilumab 還被FDA批準用于中重度特應性皮炎(AD)和鼻息肉病[32]。
3.4 抗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抗體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SLP)是一種上皮細胞衍生的細胞因子,與氣道炎癥的發生和持續存在有關,可以通過成纖維細胞增加膠原蛋白的產生和氣道平滑肌的增殖來潛在地促進氣道重塑[33]。Tezepelumab是一種特異性結合TSLP 的人IgG2λ 單克隆抗體。2期臨床研究顯示,無論Th2細胞因子和FeNO狀態如何,與安慰劑相比,tezepelumab 能顯著改善肺功能和嚴重哮喘病人的結局[34]。有研究觀察到低T2 和高T2生物標志物亞組中,tezepelumab治療都可降低哮喘基線加重率[35],表明其對低T2炎癥的病人具有潛在益處。目前暫沒有觀察到tezepelumab 對大氣道或小氣道重塑結局的影響,未來的長期研究可能會提供其對氣道結構和功能的廣泛益處的證據。
3.5 T2 哮喘潛在靶點和藥物隨著對哮喘免疫發病機制認識程度的提高,已經確定了其他炎癥途徑作為治療靶點,并且正在開發新的生物制劑。IL-9在過敏性哮喘的病理發生中具有介導作用,但抗IL-9 制劑MEDI-528 在2 期試驗顯示,未得到控制的哮喘病人第13 周的ACQ-6 評分沒有受到MEDI-528治療的顯著影響[36],仍需進一步探索。IL-27由活化的抗原呈遞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可以抑制Th2 細胞的分化以及ILC2細胞的增殖,研究顯示哮喘小鼠模型中預防性施用IL-27 可以緩解肺部Th2 炎癥環境以及改善氣道重塑[37],因此IL-27 有望成為哮喘免疫治療的新靶點。IL-33 通過刺激IL-13 從ILC2和肥大細胞釋放來誘導氣道高反應性,IL-33 與TSLP 合作促進2 型炎癥,已有研究表明抗IL-33 抗體REGN3500 能夠改善對嚴重哮喘的控制,但其治療效果并未優于dupilumab[38]。前列素D2(PGD2)是T2 哮喘的關鍵遞質之一,主要由肥大細胞產生。Fevipiprant 是一種非單克隆抗體的口服藥物,可阻斷前列腺素D2 與其受體(CRTH2)的結合,這種受體通常在Th2 細胞上表達,因此有望在高T2 型哮喘病人中起作用。然而臨床試驗顯示其似乎只對FEV1 略有改善,類似于白三烯受體拮抗劑[39-40]。作為口服藥物,fevipiprant 相對容易給藥,但治療哮喘的潛力并不確定,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4 總結
奧馬珠單抗作為第一個被用于哮喘治療的靶向生物制劑,使T2 型哮喘病人的轉歸得到了改善。從那時起,針對2 型炎癥的生物學方法成為一種新的有前景的個性化藥物。哮喘生物制劑在這一領域的進展不僅有助于更好地診斷和靶向治療,還將為需要解決的基礎研究問題提供反饋。目前何時停止生物制劑的治療沒有既定的指南,對治療反應的生物標志物的探索仍不全面,很多生物制劑的開發也尚不完善,在未來幾年中我們應該努力解決上述問題,更好地掌握哮喘的表型及內型,這將有助于指導最佳治療和監測治療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