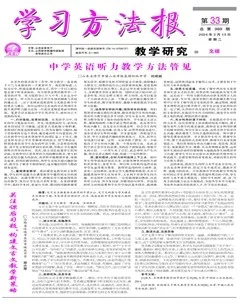初中語文大單元教學中學生思維能力培養策略探究
劉麗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指出,學生語文核心素養是文化自信和語言運用、思維能力、審美創造的綜合體現。其中思維能力主要包括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辯證思維和創造思維。基于此,在語文教學中,我努力實踐,不斷探索,嘗試著以大單元教學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一、創設教學情境,激發聯想想象,培養學生形象思維
課標指出,應“創設豐富多樣的學習情境”,“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在題為《慷慨激昂誦詩篇》的大單元教學中,我選擇了初中語文教材中的《黃河頌》《海燕》《沁園春·雪》,以及課外李白的《將進酒》重組單元進行教學。利用網絡視頻、課件等創設了情境,以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我把《海燕》的配樂朗誦帶進課堂,突現的炸雷、尖叫的海燕,加上交響樂的烘托,讓學生如臨其境:在烏云和大海之間,在那一觸即發的形勢下,海燕在搏擊,海燕在堅守,海燕在渴望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就這樣學生通過文圖的轉換,完成了形象思維的培養。而黃河的視頻讓從未見過黃河的學生見識了什么叫氣勢磅礴、什么叫勇不可擋,輔以解放軍強渡黃河解放南京的的視頻,波瀾壯闊的自然圖畫和撼天動地的戰斗場面相得益彰,學生自然就理解了“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將要學習你的榜樣,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的情感。講解《沁園春·雪》時,我進行視頻剪輯,詞的上片我配用千里冰封的視頻,漫天飛雪、銀裝素裹、晶瑩蒼茫。下片播放朗誦視頻,“毛澤東”昂首佇立,慷慨激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氣概已不用言說,學生的想象思維得以激發。然后我讓學生自行設計配樂朗誦李白的《將進酒》或其他喜歡的詩篇。學生很快找到了合適的音樂以及視頻,學生們紛紛化身為李白,只見講臺上的男生,慷慨激昂:“天生我材必有應,千金散盡還復來。”此時他已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個鮮衣怒馬的少年,正義無反顧地朝著自己的理想進發。如此創設教學情境,學生的想象力被激發,也培養了學生的形象思維。
二、創建思維導圖,完善知識構建,培養學生邏輯思維
思維導圖是一種可視化的圖表,能夠還原大腦的思考和產生想法的過程,通過捕捉和表達發散性思維,對大腦內部進程進行可視化呈現。例如,在《品詩情,會畫意》大單元教學中,我選擇了先教《使至塞上》;蘇軾評王維“詩中有畫”,請結合“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一句做出分析。我提示學生可以從畫的角度,也就是美術的角度去思考。美術素養高的學生發現了詩中的“直”和“圓”兩個字,具有線條美。接著,又有學生由此得到啟發,發現了隱含在景物中的色彩美。我又引導學生,注意體悟作者要傳達的其他美感,學生的呈現可圈可點,邏輯思維得到了發展。
三、量化學習遷移,舉一而后反三,培養學生創造思維
學習遷移也稱訓練遷移,指一種學習對另一種學習的影響,或者習得經驗對完成其他活動的影響,即“觸類旁通”“舉一反三”。遷移對于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學生在完成了思維導圖、習得了心得知識之后開展小組合作,依思維導圖探究“詩中有畫”這一特色在其他詩句中的體現。如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李白的“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杜牧的“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劉長卿的“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等。圍繞“詩中有畫”這一主題,從王維到其他詩人,從課內到課外,相關詩句先從數量上保證,然后從線條美、色彩美、意境美、層次美四個維度制訂評價標準,對探究結果進行量化評價,學生如果能從其他維度創造性賞析,會得到創新加分。這樣,不僅夯實了已構建的知識體系,更能培養學生的遷移能力、創造能力。
四、深化文本解讀,見現象明本質,培養學生辯證思維
辯證思維是用聯系的、發展的、一分為二的觀點去認識事物、認識世界、認識社會的一種思維方式。這要求我們在研究問題時注意事物之間的整體與部分、原因與結果、量變與質變、現象與本質、共性與個性等等關系。它能使我們認識全面,見解獨特,立論深刻,論證周密。因此,深化文本解讀,見現象,明本質,培養學生的辯證思維很有必要。例如,在《見字如面同喜樂》的大單元教學中,我選擇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記》,蘇軾的《記承天寺夜游》,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四篇文章。以“樂”為主題,探究四位先賢的憂樂觀。柳宗元被貶永州,寄情山水,本想讓大自然排遣他被貶的落寞,見到小石潭,他因景而樂,但又因環境太凄清,觸發貶謫之情,轉樂為悲。他的樂是基于他自身際遇的憂樂,是“小我”的樂。蘇軾同樣遭貶,無聊之際想到了好友張懷民,月下與友散步,兩人之間的樂,是一種別人無法啟及的閑人之樂、豁達之樂、友人之樂。歐陽修被貶滁州,憑一己之力將滁州治理好,閑暇時期,與民同游,設宴酣飲,他的樂是樂人之樂,與民同樂,與前兩位相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而范仲淹不愧“正公”名號,胸懷天下,以天下之樂為樂,先憂后樂。其胸懷是前面三人所不能及的,是“大我”的樂,“大我”的樂是建立在犧牲“小我”的基礎上的。通過深度的文本解讀,對比探究,見現象明本質:雖都是喜樂,但從柳宗元到范仲淹,“憂樂”已發生了質的飛躍,其表現出來的胸懷、抱負更是不同。這樣,深化文本解讀,見現象明本質,培養了學生的辯證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