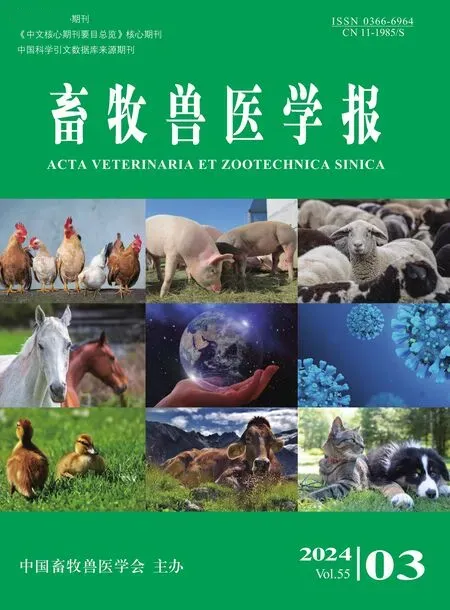冷熱應激對肉牛生理指標及基因表達影響的研究進展
王 瀟,張 昊,欒慶江,李 慧,楊 鼎,王婷月,田 菁,趙 濛,陳 陸,田如剛*
(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科學院,呼和浩特 010031)
應激反應是指動物在受到外界頻率較大,持續時間較長(或短但變化劇烈)的刺激時,機體內環境穩定性、生理指標等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機體健康程度的一種反應,產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極端溫度、運輸和轉場等方面[1],而由外界溫度變化產生的冷熱應激,是諸多應激反應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可從多個方面對機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在肉牛產業中,飼養環節既是基礎部分,又是最重要的環節,而在飼養過程中產生的冷熱應激,可對肉牛的能量代謝產生影響并降低群體健康狀況。已有研究發現,在熱應激狀態下肉牛群體的采食量、生長效率較非應激狀態普遍降低[2-3],而嚴重的冷應激也會對干物質攝入量(DMI)和耗水量產生負面影響[4]。總之,冷熱應激可從生產效能、存活率、繁殖率等多個方面造成經濟損失,進而影響肉牛產業的發展。所以,如何降低冷熱應激對機體產生的影響,改善肉牛冷熱應激情況下的健康狀況,是肉牛產業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在動物體內,生理生化和免疫指標可表征機體的生理功能狀況與健康程度。在應激狀態下,動物個體的內環境穩定性會發生變化,進而造成血液生理生化和免疫指標較非應激狀態下出現顯著差異[5]。本文從冷熱應激的評判標準和產生地域入手,基于冷熱應激的產生機制,對冷熱應激下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的肉牛血液內分泌、免疫、抗氧化等生理生化指標變化情況進行概述,挖掘對冷熱應激起到調控作用的基因和調控因子,討論并展望了緩解肉牛冷熱應激的可行性方法,從而為促進我國肉牛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1 冷熱應激的評判標準及調控機理
1.1 肉牛冷熱應激的評判標準
外界溫度變化是否對機體產生冷熱應激的辨別標準包括溫濕度指數(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THI)和綜合氣候指數(comprehensive climatic index,CCI)等[6-7]。
THI可基于溫度和濕度評價肉牛機體應激狀況,其計算公式為THI=(Td + Tw) + 40.6(Td為干球溫度;Tw為濕球溫度),當THI<72時,肉牛群體為無應激狀態;當THI>72時,可分為輕度(72~79)、中度(79~88)和嚴重熱應激(大于88)3個程度。不同程度的高溫高濕氣候可導致肉牛的自身散熱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進而產生非特異性的生理防御應答,并導致熱應激的產生[6,8]。
而CCI的評價方法,除了考慮溫度和濕度,還將風速和陽光輻射度考慮在內,在評價冷應激時,更具有說服意義[4]。此外,風寒指數(wind chill index,WCI)和熱負荷指數(heat load index,HLI)也可分別用來評判冷、熱應激[9]。
1.2 冷熱應激出現的范圍
冷應激根據環境低溫程度和機體暴露在寒冷氣候的時長,可進一步分為急性冷應激和慢性冷應激2種類型[10],這2種冷應激均會對肉牛群體的健康情況產生影響。我國大部分地區屬于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受到西伯利亞冷氣團的控制,氣候寒冷,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赤峰市、通遼市、錫林郭勒盟等地,以及新疆、黑龍江、吉林等一些緯度可達北緯45°左右的重要肉牛養殖地區,冬天的室外溫度會降至-20 ℃以下,部分地區甚至可達-30 ℃~-40 ℃,不同品種的肉牛在此環境下,均會產生冷應激現象。而在國外如加拿大阿爾巴塔省、安大略省,以及美國俄亥俄州五大湖附近等同緯度的部分地區,冬季極端低溫和頻繁出現的暴風雪也可導致肉牛群體出現冷應激狀況,而在更高緯度的加拿大北部的魁北克省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緯度可達50°以上,極端溫度會降至更低,且一天內暴露在極冷環境下的時間更長,造成的冷應激現象較低緯度地區就更為嚴重。
肉牛群體熱應激現象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夏季均會出現。主要分布在北緯30°附近及以南的四川、重慶、云南河谷以及長江中下游平原等地,這些地區夏季的平均溫度均可達到30 ℃左右,濕度可達70%以上,且持續時間可達20 d以上,長時間的高溫高濕可對肉牛機體內環境產生影響,進而產生熱應激。而在赤道附近如東南亞的印度北方邦、中央邦等地區,以及非洲尼日利亞等國家的部分地區,這些地區年平均氣溫更高,且濕度更大,熱應激現象常年都會出現,嚴重制約了當地肉牛產業的發展。
1.3 冷熱應激的調控機理
機體在受到外界刺激產生應激后,可通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hypothalamus-pituitary-thyroid axis,HPT)和交感神經-腎上腺髓質軸(sympathetico-adrenomedullary,SAM)對應激進行調節[11-13]。
由HPA軸組成的調節系統為機體最主要的應激響應和調節系統[14],其作用機制為下丘腦接受到外界刺激后,產生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CRH可刺激垂體前葉產生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ACTH可促進腎上腺皮質產生更多的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GC),GC可提高機體肝糖原的異生作用,降低細胞因子的表達量,進而維持機體內環境穩定[15](圖1)。

圖1 HPA軸調節冷、熱應激的機制Fig.1 The mechanism of HPA axis regulating cold and heat stress
HPT軸作用機制為在機體受到外界刺激產生應激后,下丘腦釋放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TRH),TRH可刺激垂體產生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TSH可作用于甲狀腺調控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T3)和四碘甲狀腺原氨酸(thyroxine,T4)激素的分泌水平[16-17],而T3和T4可調節細胞對糖原的利用,進而達到調節機體機能、改善應激狀況的目的(圖2)。此外,血液中的血清素可通過調節SAM軸對肉牛的冷、熱應激產生影響[18]。

圖2 HPT軸調節冷、熱應激的機制Fig.2 The mechanism of HPT axis regulating cold and heat stress
2 冷熱應激對肉牛血液生理生化指標的影響
2.1 冷熱應激對肉牛血液內分泌相關指標變化的影響
當外界溫度刺激導致機體產生冷熱應激后,體內的交感神經系統可降低生殖系統和腎上腺系統的血流量,增加腦部、心臟和肌肉的血流量,從而緩解機體的應激情況,達到維持機體內環境穩定的目的[19]。這種途徑可通過機體內HPA軸和HPT軸的調節完成,與之相關的激素表達量也隨之發生變化。
在冷應激對肉牛血液內分泌相關指標影響的研究中,陳浩等[16]通過比對秋季和冬季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地區蒙古母牛血清中T3、T4、ACTH、GH、GC等激素指標,發現在冬季冷應激情況下,蒙古牛血清中ACTH、GC、T3、T4的含量顯著升高,表明蒙古牛可通過HPA軸和HPT軸增強機體的糖原異生作用,從而提高機體對低溫環境的抵抗力和適應性。此外,同一地區的西門塔爾牛在冷應激情況下與非冷應激情況相比,ACTH和GC的含量也會顯著增高,表明西門塔爾牛也可通過HPA軸緩解冷應激[20],此外,已有研究發現荷斯坦牛在寒冷的環境下也可通過HPA軸調控冷應激[21]。
熱應激同樣會引起到血液內分泌指標的改變。蒙古牛和西門塔爾牛在發生熱應激時,體內的T3、T4、ACTH、GC含量較熱應激恢復期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20,22-23],表明這2個品種的肉牛均可通過降低體內代謝的方法緩解熱應激。羅宗剛等[24]檢測不同品種的雜交肉牛熱應激后的內分泌指標,發現熱應激情況下的紅西本肉牛T4值顯著低于其它群體,且部分體征指標較其它雜交群體和純種群體相比趨于正常,表明此類雜交牛對熱應激有更強的適應性,既肉牛品種與冷熱應激之間可能存在一定聯系。此外,Johnson和Vanjonack[25]研究發現,在31~35 ℃下的熱應激時期,荷斯坦牛的甲狀腺活動情況顯著低于16.8 ℃的非應激時期,表明荷斯坦牛也可通過降低體內代謝率的方法減少產熱,從而增加機體對炎熱環境的適應性。
2.2 冷熱應激對肉牛血液抗氧化相關指標變化的影響
動物機體在產生冷熱應激時,會導致體內產生大量自由基,這些自由基導致細胞內脂質過氧化物改變,進而產生氧化應激反應[26]。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是機體內重要的抗氧化酶,可通過清除體內多余的超氧陰離子自由基達到阻止細胞損傷的目的[27-28]。此外,由脂質過氧化物反應產生的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也與機體抗氧化程度存在密切聯系[29],而總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T-AOC)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等指標的值也可反映機體的抗氧化能力水平[30]。
一般情況下,冷應激會造成不同年齡段肉牛血清中SOD和GSH-Px含量下降,MDA和T-AOC含量上升[31]。孟祥坤等[32]研究了慢性冷應激對西門塔爾雜交犢牛的影響,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并發現犢牛月齡越大,其對溫度變化的適應越好。
熱應激研究方面,鄭海英等[33]對在夏季科爾沁肉牛的抗氧化指標進行檢測,發現在夏季熱應激情況下,科爾沁肉牛血液中SOD、T-AOC、GSH-Px含量較春季非應激情況下降,但MDA含量上升,表明機體為維持內環境穩定,SOD等大部分抗氧化酶被大量消耗,且發生脂質反應,從而導致MDA含量增加。此外,科爾沁肉牛與同地區的科爾沁牛相比,熱應激時SOD、T-AOC、GSH-Px等抗氧化指標要明顯偏高,表明科爾沁肉牛有更強的熱應激適應性。也有研究發現,蒙古牛與西門塔爾牛和安格斯牛相比,具有更強的免疫性能和抗氧化性能[34-35]。以上研究可表明,熱應激對抗氧化指標影響與肉牛品種有關,黃德均等[36]對紅安格斯牛和其它肉牛雜交品種的研究也證實了該結果,而Tejaswi等[37]通過對印度不同品種瘤牛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結論。
2.3 冷熱應激對肉牛血液免疫相關指標變化的影響
動物機體在受到外界冷熱刺激后,體內的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G(IgG)等表達量上升,起到調節機體的作用,但過度的冷熱應激會導致血清中IgA、IgM、IgG含量下降,從而導致免疫機能的下降。此外,機體在受到冷熱應激時,體內的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 TLR)可產生抗原呈遞細胞,這些細胞可對機體固有的免疫應答產生關鍵調控,進而導致TLR2和TLR4、IL2和IL4等調控因子釋放出預炎癥因子,引起宿主的免疫反應[38-39]。
冷應激主要影響的免疫指標包括IL-2、IL-4、IgG[40]。Ebrahimi和Towhidi[41]通過對比西門塔爾牛、三河牛和荷斯坦牛在冷應激下免疫指標的變化,發現3個品種肉牛血液中IL-2、IL-4、IgG的含量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格日樂其木格[10]的研究也發現冬季冷應激時期的西門塔爾母牛較秋季非應激時候相比,IL-2、IgG指標變化顯著,二者均證實了冷應激可對肉牛機體的免疫性能產生影響。
熱應激方面,Bharati等[42]的研究發現塔帕卡牛在經過短期熱應激刺激后其血液內TLR2、TLR4、IL2和IL4的含量較非熱應激時均出現明顯上升,表明這些指標與熱應激存在密切關系。但是陳浩等[22]通過對熱應激狀況下西門塔爾牛的研究發現,其IL-2的表達量與非熱應激情況下相比含量顯著下降,IL-4無明顯變化,IL-6的表達量顯著上升,此外,IgA、IgM和IgG等球蛋白含量也出現下降,表明與塔帕卡牛相比,熱應激對西門塔爾牛的免疫系統造成的影響更為顯著,且不同品種的牛在熱應激下IL2和IL4的表達量之間存在差異性[43]。
3 冷熱應激相關調控基因及分子機制
冷熱應激的分子調控受到多個基因的共同調節,在這些基因中,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HSPs)作為一個大的基因家族,在維護機體內環境穩定、抵御冷熱應激影響時發揮著重要作用[44-45]。目前,國內外已有許多關于HSPs家族相關基因的研究,這些研究可為挖掘調控冷熱應激的關鍵基因及其分子機制提供參考依據[46]。
HSPs家族基因最早發現于果蠅體內,主要功能包括體內蛋白質的折疊、運輸和組裝等。其中,HSP70基因作為家族的代表性成員,是機體對冷熱應激調節作用的分子標志物[47],并在調控冷熱應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表現為當機體受到外界冷熱應激時,體內的HSF被蛋白激酶磷酸化,并形成三聚體,這些HSF三聚體復合物進入細胞核并與HSP70基因啟動子區域的熱休克元件(HSE)結合,使得機體內HSP70 mRNA的表達量上調[48],高表達的HSP70 mRNA隨后被轉錄并離開細胞核進入細胞質合成HSP70等熱休克蛋白,這些蛋白可輔助異常的蛋白質恢復其構象,還可激活抗細胞凋亡信號通路,從而降低機體受到的應激損害[49](圖3)。在機體內,HSP70基因的表達存在時空差異性[50],隨著冷熱應激的加重,體內細胞受損或壞死,氧化應激反應出現,此時胞內的HSP70蛋白釋放到機體內,從而引起免疫系統的迅速反應[51],達到調節冷熱應激的效果,但是這種調節有一定限度,過度的冷熱應激可使HSP70基因表達量下降,進而導致機體功能受損[52]。

圖3 體內HSP70基因的調控機制[53]Fig.3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HSP70 gene in vivo
HSP70家族包含HSPA1A、HSPA1B、HSPA6、HSPA7、HSPA8等8個以上的基因,其中HSPA1A、HSPA1B屬于誘導型基因,可在外界刺激的情況下實現誘導表達[54-55]。白丹丹等[56]以三河牛為研究對象,對HSP70家族的基因開展研究,發現受到冷熱應激時,三河牛血液淋巴細胞中的HSPA1A、HSPA1B內表達量較非應激時顯著上升,李瑋等[57-58]的研究也獲得了同樣的結果。Kumar等[59]對印度瘤牛開展了研究,也發現與春季相比,夏季和冬季HSPA1A、HSPA1B基因的表達量顯著升高,Behl等[60]也獲得了相同的結果[61],且耐熱性越好的品種表達量變化越顯著。
已有研究報道,HSP70的SNP差異可影響到其表達量的高低,進而對肉牛機體冷熱應激的產生和調控造成影響。在三河牛體內,HSP70基因啟動子上游的SNP差異可影響其表達活性,進而影響到冷應激時體內T3、T4指標的變化[62]。印度塔帕卡牛HSP70基因的多態性與其耐熱性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具有AA基因型的個體較具有BB和AB基因型個體的耐熱性強,該位點A等位基因的頻率可作為此品種肉牛耐熱性的檢測指標之一[63]。甘佳等[64]研究了蜀宣花牛、荷斯坦牛和娟荷雜交牛HSP70基因在熱應激下的表達情況和個體間的SNP差異,發現HSP70基因存在3個SNPs位點,這些SNP位點可影響HSP70基因的表達量從而使蜀宣花牛對熱應激有更好的耐受性。此外,利木贊牛、比利時藍牛和不同品種的瘤牛在HSP70基因啟動子和上游區域也存在基因多態性,導致其擁有不同的冷熱應激耐受性,表明HSP70基因多態性可受到品種差異的影響[65-66]。從以上研究可以推斷出,HSP70基因在受到冷熱應激時的高表達對維持機體正常功能和細胞內穩態具有重要作用,且不同品種間的SNP位點差異可對其表達量高低產生影響,進而造成不同品種肉牛耐冷熱應激能力的差異[67]。這些位點的基因多態性可作為肉牛抗冷熱應激的分子標記,用于肉牛分子育種和相關基因芯片的開發工作[68]。
HSP基因大家族的其它基因也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肉牛對冷熱應激的耐受力。如HSP90基因家族表達的蛋白可通過對TLR2/TLR4和IL2/IL6的影響調節反芻動物的熱應激[69-70],而在肉牛體內,HSP90家族的HSP90β與HSP70位于同一染色體上[46],可對HSP70家族基因的表達起到調控作用。在尼日利亞婆羅門牛體內,位于HSP90第三個外顯子上的SNP差異對其熱應激的耐受力影響顯著[53]。HSF1作為一類調控因子,也可調控熱休克蛋白的表達[71]。此外,不同品種肉牛micro RNA的表達差異,也可對熱應激蛋白的表達起到調控作用,進而影響其冷熱應激耐受能力[72]。
除了HSP家族的基因,其它家族的基因也可對肉牛的冷熱應激產生調控。Tian等[73]用全基因組測序的方法研究了65頭紅安格斯牛和45頭蒙古牛對冷熱應激的適應情況,最終篩選出TRPM8、NMUR1、PRKAA2、SMTNL2、OXR1等多個可能與冷應激相關的基因。Jia等[74]對安格斯牛和印度瘤牛的MYO1A基因開展了研究,發現安格斯牛與印度瘤牛相比,隨著緯度由北向南的變化,MYO1A上有4個SNPs位點發生突變,并證明了這些突變均與熱應激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些與細胞修復相關的基因也可對冷熱應激起到調節作用,EIF2AK4基因已被證實能夠通過限制p53因子的表達水平和轉錄活性從而降低因冷熱應激導致的細胞氧化造成的損傷[75-76],而Edea等[77]通過全基因組掃描的方法也發現該基因可能與牛的適應性存在一定聯系。此外,DGAT1、PPP1R16A、SOD1、FOXH1、PRLH、PLEC等基因在山羊、奶牛等物種中做為機體調節冷熱應激的候選基因已被證實[78-80],但在肉牛體內的研究有待進一步驗證。
4 討論與展望
肉牛機體在受到外界冷熱應激刺激后,可作用于HPA、HPT、SAM等途徑,此時機體處于應激狀態,T3、T4、ACTH、GH、GC等血液內分泌相關指標,SOD、MDA、T-AOC、GSH-Px等抗氧化相關指標,IgA、IgM、IgG、IL2、IL4等免疫相關指標會產生變化,造成機體產生不良反應,進而影響到肉牛的健康程度,降低生產效率。目前,可通過調節飼喂方式和分子育種改良的方法,提高肉牛機體對冷熱應激的適應性,從而降低相關損失。
已有研究證明,補充飼料添加劑和改變飼喂方式可調節機體內免疫應答,進而達到降低冷熱應激嚴重程度的目的。李進春和何振富等[81-82]分別通過補充酒糟和復合酶菌制劑的方法,提高了西門塔爾牛IgA、IgG和IL2等免疫指標的表達量,可從飼料添加劑角度為降低冷熱應激提供參考,而在不同季節有針對性地改變飼養管理方式也可以緩解冷熱應激,降低相關損失[83]。
不同品種肉牛表現出對冷熱應激不同的耐受力,這種耐受力的調控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性狀,受到多個基因的共同影響,其中HSP70基因家族的基因在肉牛冷熱應激的分子調控中起到重要作用,且這些基因在不同肉牛品種中存在SNP差異,進而導致不同品種肉牛冷熱應激耐受力的差異性。此外,HSP90家族的部分基因和HSF1等調控因子也可對肉牛的冷熱應激耐受性產生影響,而HSP70、HSP90-α和HSP90-β等基因在綿羊、山羊等偶蹄動物的冷熱應激調節中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69]。對這些基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挖掘和探索與冷熱應激適應性相關的分子因子及調控機制,從而進一步改良肉牛對惡劣環境氣候的耐受性。生產實際中,可通過極進雜交或導入雜交等方法完成對冷熱應激耐受力較差肉牛群體的遺傳改良。
目前,國外已有許多研究采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的方法將內分泌、抗氧化、免疫指標等表型數據和基因型進行關聯分析,進一步挖掘出與冷熱應激相關的候選調控基因[84-86],但GWAS方法在我國肉牛冷熱應激的研究中報道較少,后期可基于GWAS方法挖掘我國特有肉牛品種中與冷熱應激等抗逆性相關的候選基因,并將這些基因作為分子標記位點,開發相應的基因芯片,并采用全基因組選擇(genomic selection,GS)的方法找到優秀個體,通過雜交的方式構建具有優良抗逆性狀的肉牛群體,從而產生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