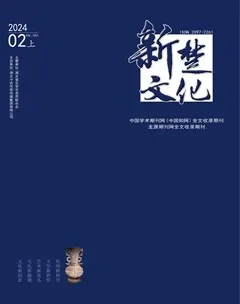試論跨文化傳播中的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

【摘要】中國古代文論在千年的積淀與發(fā)展中早已形成一套獨(dú)有體系和核心術(shù)語,術(shù)語的譯介直接影響中國古典文藝精神的表達(dá)。“感物”作為中國文藝審美創(chuàng)造和審美體驗(yàn)的發(fā)生之學(xué)在中國古典文藝?yán)碚撝兄陵P(guān)重要,但在英語世界中的傳播與研究并不算豐富。綜觀英語世界對于“感物”一詞的英譯,“感”所蘊(yùn)含的主客體交互意義以及“物”的豐富性很難同時(shí)得到準(zhǔn)確傳達(dá)。可見,術(shù)語英譯的缺憾往往造成中國文藝精神的誤讀。因此,要做好中國古代文論的跨文化傳播還需綜合采納開放闡釋、優(yōu)化術(shù)語邏輯梳理、融合跨學(xué)科、文化比較視野等傳播策略。
【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跨文化傳播;感物
【中圖分類號(hào)】H059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7-2261(2024)04-0064-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4.020
在本民族視閾內(nèi),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術(shù)語研究,其實(shí)始終賡續(xù)不斷,例如“神”“韻”“味”等文論術(shù)語都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歷史,并在發(fā)展中擁有了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和衍生。現(xiàn)代學(xué)者們也圍繞著術(shù)語的發(fā)展脈絡(luò)、內(nèi)涵意蘊(yùn)、現(xiàn)代價(jià)值等方面產(chǎn)出了十分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從跨文化傳播的視角出發(fā),中國古代文論的跨文化傳播仍處于初始狀態(tài),“東西方各國主流文學(xué)理論界都還是以西方文論為主,中國古典文論尚未進(jìn)入他們的視野。”[1]因此,在推進(jìn)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時(shí)代要求下,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的跨文化傳播關(guān)乎中國古典文藝在世界上話語體系建構(gòu)。當(dāng)前的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的跨文化傳播需要不斷地廣泛地拓展、網(wǎng)羅傳播內(nèi)容,平衡打開接受度和挖掘深度之間的關(guān)系,以達(dá)到探索中國古代文論“走出去”的方法和路徑的目的。
一、“術(shù)語”——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重點(diǎn)與難點(diǎn)
從詩詞歌賦到書法繪畫,中國的古典文學(xué)、藝術(shù)始終令人神往不已,然而要真正實(shí)現(xiàn)對于一種文化的文學(xué)藝術(shù)的把握就必須具備該文化在文學(xué)藝術(shù)審美創(chuàng)造、審美體驗(yàn)等方面的理論知識(shí)。受中國文化特質(zhì)的影響,“中國理論對事物的把握也隨之分為兩種各有側(cè)重的方式:精煉性詞組和類似性感受。”[2]這種極為凝練的詞匯、詞組即是中國文藝美學(xué)的獨(dú)特術(shù)語。因此,中國美學(xué)在理論上的本質(zhì)特色,決定了對中國古代文學(xué)藝術(shù)、對中國古典美學(xué)精神的把握不可避免地要從“術(shù)語”出發(fā),要實(shí)現(xiàn)對于中國古代文學(xué)藝術(shù)的跨文化傳播,就必須要做好理論術(shù)語的傳播。
然而,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語言抽象且意義復(fù)雜,加上言說方式自由,對于異質(zhì)文化中的人來說,理解難度大。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xué)思想讀本》一書的《導(dǎo)言》所說:“一種文學(xué)思想傳統(tǒng)式由一套詞語即‘術(shù)語構(gòu)成的,這些詞語有它們的悠久歷史、復(fù)雜的回響和影響力。”[3]把握一種文化中的術(shù)語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中國古代文論的術(shù)語又有其獨(dú)特的復(fù)雜特點(diǎn),使得這套“中國理論話語”更加難以理解。
首先,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基本以中國古代哲學(xué)、思想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范疇為根基,如道、氣、性、情、志、神、韻等,由這些范疇而產(chǎn)生了意涵多樣的術(shù)語,如詩言志、詩緣情、文以載道等。但這些范疇本身也并沒有唯一正確的指向,如黨圣元先生在《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和體系》一文中所說“中國古代文論范疇在理論指向和闡釋方面具有多功能性。”比如“氣”這一范疇既指向天地自然之氣,又指向個(gè)人的精神氣質(zhì),還指向藝術(shù)作品的審美因素,那么對基于“氣”這一范疇所產(chǎn)生的“文氣”概念的理解則也應(yīng)豐富多樣。由于范疇的“理論指向和闡釋方面的多功能性”,文論術(shù)語的內(nèi)涵也十分豐富深刻。
另外,黨先生還指出“傳統(tǒng)文論概念范疇之間往往相互滲透、相互溝通,因而在理論視域方面體現(xiàn)出交融互攝、旁通統(tǒng)貫、相浹相洽的特點(diǎn)。”這種范疇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自然也使得文論術(shù)語之間呈現(xiàn)出關(guān)聯(lián)性,比如“情”與“志”相關(guān)聯(lián),那么“詩言志”與“詩緣情”則具備著關(guān)聯(lián)性,既進(jìn)一步豐富了文論術(shù)語的內(nèi)涵,同時(shí)又加大了對于文論術(shù)語的理解難度。并且,這些關(guān)聯(lián)范疇的組合又會(huì)產(chǎn)生新的范疇,比如“意”與“象”的組合產(chǎn)生了“意象”這個(gè)新的范疇。“中國古代文論范疇具有較廣的內(nèi)容涵蓋面和闡釋界域,因此衍生性極強(qiáng),一個(gè)核心范疇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范疇,子范疇再導(dǎo)引出下一級范疇,范疇衍生概念,概念派生命題,生生不已,乃至無窮。”[4]文論術(shù)語也在這種范疇的不斷衍生中發(fā)展,彼此相關(guān)而又相異。因此,“術(shù)語”就成為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極關(guān)鍵、極復(fù)雜的部分。
二、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之“感物”
“文學(xué)理論譯介過程中無法回避術(shù)語翻譯問題,術(shù)語翻譯的恰當(dāng)與否直接影響到讀者對一種思想體系的理解”[5]。中西方從根本上來說看待世界整體的方式便不同,因此所產(chǎn)生的哲學(xué)、文化基本概念也就不同。這種從宇宙模式到文化精神到文藝存在形態(tài)再到文藝?yán)碚撎厣系牟煌沟弥形魑膶W(xué)、文藝、文化之間存在著艱難的理解壁壘,也使得中國古代文藝?yán)碚撔g(shù)語的豐富含義無法用另一種語言被完全地表達(dá)出來。以中國古代文藝?yán)碚撝袠O為重要的“感物”一詞來說,其在跨文化傳播中就存在著內(nèi)蘊(yùn)的誤讀與失落。
“感物”一詞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dòng),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dòng),故形之于聲。”也就是說音樂的產(chǎn)生是“感于物”的結(jié)果,在這里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樂記》雖是討論音樂理論,但其揭示的卻是中國的古典文藝精神、美學(xué)精神。那么,“感”與“物”分別應(yīng)作何理解呢?這個(gè)問題的答案在歷代文學(xué)、文藝乃至哲學(xué)思想中出現(xiàn)了不斷的豐富。
在先秦時(shí)期,儒家之感是一種有意識(shí)有目的意向性活動(dòng),而所“感”之物則是與道德、人倫、王道教化等關(guān)聯(lián)的社會(huì)之物以及自然之物。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從《詩大序》中儒家文藝精神認(rèn)為,人感于物,而物亦感與人,這種“感”的雙向交互性也是一直貫穿“感物”的核心。而道家之感,則是人在摒除了一切意向之后,在一片虛空澄明中與天地自然、宇宙大道無限交融的狀態(tài),而所感之物則最初是與宇宙大道關(guān)聯(lián)著的天地自然,而當(dāng)真正進(jìn)入虛靜狀態(tài)之中后,便是物我兩忘,無物無我。雖然“感物”一詞在先秦時(shí)期并沒有得到定型,但其身兼儒道思想的特質(zhì)卻是在先秦時(shí)期得到啟蒙。在西漢時(shí)期,黃老之學(xué)盛行,中國的氣化宇宙被強(qiáng)調(diào),人與天地萬物皆秉氣而存,因此人物相感,則是氣之貫通,感的身體之感受在此得到強(qiáng)調(diào)。而董仲舒重釋“天人合一”的概念,“感”則又顯現(xiàn)出一種具有神秘的通靈意義的感應(yīng),而所感之物則是具備神秘力量的天。班固又提出感時(shí)、感事,則此感又成為一種意向性活動(dòng),特指通向歷史過往的感懷,而所感之物,則重在強(qiáng)調(diào)人世與人事。至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人的自我意識(shí)覺醒,審美意識(shí)覺醒,人之感具有了其獨(dú)立價(jià)值,而物亦有其獨(dú)立價(jià)值,“感物”一詞不僅正式出現(xiàn)了,且其內(nèi)涵也基本得到了定型。從嵇、阮的音樂感物美學(xué),到衛(wèi)恒、宗炳、謝赫的書畫感物美學(xué),再到陸機(jī)、劉勰、鐘嶸的文學(xué)感物美學(xué),這時(shí)的“感”身兼人的身體之感與心靈之感,而所感之物則是與時(shí)間空間、永恒規(guī)律相關(guān)的且被審美化了的自然之物。至此,“感物”的內(nèi)涵基本確定了。而后唐宋明清又就“感物”的不同方面進(jìn)行了極致地拓展,發(fā)展出感興、觀物、妙悟、格物、情景等理論,雖與“感物”原本之意有很大不同,但內(nèi)里仍是“感物”的精神。
因此,總結(jié)“感物”一詞在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精神發(fā)展中不斷豐富的概念可以發(fā)現(xiàn),“感物”之感既是物質(zhì)性的身體的感受,也是精神性的活動(dòng),更是從物質(zhì)身體;其作為精神性的活動(dòng),既可以是有著明確意向性的,也可以是非自覺的、無目的的;既是理性的感思、感想,也是感性的感受、感傷,更是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感懷,是人的靈魂、精神審美化之后呈現(xiàn)出來的藝術(shù)精神。而所感之物,是抽象的儒家之道,也是至高的道家之道,是道在具體事物中顯現(xiàn)的“理”,是人最本真的“心”;是中國獨(dú)特的物質(zhì)之氣,是具備神秘力量的天;是與儒家追求的至仁的“王道”相關(guān)聯(lián)的社會(huì)倫理現(xiàn)實(shí),是與道家至高無上的道相關(guān)聯(lián)的天地宇宙;是歷史、現(xiàn)實(shí)中的人事物,是關(guān)聯(lián)著無窮的時(shí)間的四時(shí)景象,也是關(guān)聯(lián)著無垠空間的自然風(fēng)物……
三、從術(shù)語英譯看“感物”的被理解與被誤解
由于“感物”的概念往往不以“感物”一詞的形式出現(xiàn),這也給作為文論術(shù)語的“感物”傳播帶來了困難。譬如《禮記》所說為“感于物而動(dòng)”,鐘嶸在《詩品》中的表述為“氣之動(dòng)物,物之感人”,只有劉勰在其《文心雕龍》的《明詩》篇及《物色》篇中明確寫作“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人感物,聯(lián)類無窮”。故而,要考察作為文論術(shù)語的“感物”的跨文化傳播,還是必須依托《文心雕龍》的譯介。
本文根據(jù)表1中的四種翻譯,“感物”之“感”的翻譯,核心詞有兩個(gè),stir和respond。stir這個(gè)詞有擾動(dòng)、鼓動(dòng)之義,可以說帶有一些情感上的激烈性和負(fù)面意味,與劉勰所強(qiáng)調(diào)的感,應(yīng)是充盈情感的積極與豐滿,而并非帶來情緒上的激動(dòng),故而stir一詞并不貼切。respond雖然沒有stir那種激烈的意味,但同樣沒有傳達(dá)出中國之“感”的交互性,即“人感于物,而物亦感于人”。
“物”的翻譯比較多樣化,宇文所安[6]譯作 physical things,這個(gè)翻譯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物的物質(zhì)性,失去了中國文藝極為重視的物的神的層面。施友忠[8]將《明詩》篇中的“物”譯作 external objects,將《物色》篇中的“物”譯作things,本文認(rèn)為things的翻譯更加妥當(dāng)。首先,中國之物并不是一個(gè)單純的物體或客體,而是指宇宙、哲學(xué)層面的物,是充滿生命之氣的物。因此用objects反不及用things,另外external的強(qiáng)調(diào)更是將“物”局限了,感物之物是一定與人的心、情、意相通的,并不是完全的外物。黃兆杰[7]和楊國斌[9]都是基于原文思想進(jìn)行的翻譯,劉勰在兩篇文章中的所言及的物其實(shí)側(cè)重不同。《明詩》篇中重在強(qiáng)調(diào)詩人有感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自然、人事而抒發(fā)自己的情志,而《物色》篇?jiǎng)t主要強(qiáng)調(diào)人對自然之物的感受。因此,黃兆杰分別將“物”譯作the world outside和the things of nature,楊國斌的翻譯則是environment和the natural world,但總的來說,黃譯所選用的詞內(nèi)涵更加豐富,更能契合劉勰原意。但是如果要將“感物”視為一個(gè)固定術(shù)語,則這兩個(gè)翻譯則又有失精當(dāng)。
另外,由教育部、語委等多部委聯(lián)合發(fā)起的中華思想文化術(shù)語工程,其工程成果中華思想文化術(shù)語庫中也收錄有感物一詞。在中華思想文化術(shù)語庫中,感物被譯作Sensed Externalities。sense是較respond和stir更接近于中國之感,體現(xiàn)出了“感物”所身兼的感官活動(dòng)以及精神活動(dòng)的意味,并且sense傳達(dá)出了主體不僅是被動(dòng)而感,也有主動(dòng)感知的層面。然而以externalities來表達(dá)“物”,則又落入了局限。
綜觀現(xiàn)有的翻譯,對于“感物”一詞,各學(xué)者的理解各有不同,導(dǎo)致其翻譯對于“感物”的表達(dá)各有側(cè)重,也各有不足,而本文認(rèn)為將“感物”譯為sense things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也還差強(qiáng)人意。從語言學(xué)的角度來說,中國詞語的多義性本身就造成了理解的困難,又加上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質(zhì)要求用絕對精練的語言來表達(dá)豐富的含義,更使得術(shù)語的內(nèi)涵似乎無所不包又模糊不清,對于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來說,要弄清古代文藝?yán)碚撔g(shù)語的真正含義尚且困難重重,在進(jìn)行術(shù)語的跨文化傳播中出現(xiàn)的誤解與意義缺失也是在所難免。
四、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的跨文化傳播策略思考——以“感物”為例
中國古代文論術(shù)語的龐大數(shù)量決定了古代文論的跨文化傳播最好先從辭書的編纂、詞庫的整理開始,這也正是目前學(xué)界正在開展的工作。但是,無論是辭書還是詞庫畢竟仍是工具書性質(zhì),對于文論問題的深入探究畢竟鞭長莫及。因此,要繼續(xù)推動(dòng)中國古代文論的跨文化傳播不應(yīng)止于辭書,在某種程度上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反辭書的階段。即放棄對于一錘定音的標(biāo)準(zhǔn)的譯注的追求,適當(dāng)?shù)叵蚨嘣U釋以及闡釋歷史開放,使其能夠呈現(xiàn)出術(shù)語背后的理論精神。
中國的文化精神和理論言說特點(diǎn)也決定了中國文論術(shù)語的指涉多樣性、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和不斷衍生性,因此不同時(shí)代的文論術(shù)語之間其實(shí)是有著關(guān)聯(lián)性和衍生脈絡(luò)的。以“感物”為例,其承自先秦儒道思想,與“興”“虛靜”“心齋”等有所關(guān)聯(lián),又下啟唐代的“思與神會(huì)”“神與物游”,開拓出宋代的“觀物”“妙悟”等。因此,若能通過整理術(shù)語之間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術(shù)語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衍生關(guān)系,勾勒出術(shù)語的大致發(fā)展脈絡(luò)會(huì)更加有助于對于術(shù)語的理解。
另一個(gè)很重要的方面是在術(shù)語傳播中融入跨學(xué)科視角以及文化比較的視角。比如解釋“感物”,如果單從中國古典文藝精神出發(fā)進(jìn)行解釋或許存在著接受困難的問題。但是將之與西方人類學(xué)中的“互滲”概念進(jìn)行關(guān)聯(lián),或許就能夠使得一部分受眾明白“感物”的思維和意蘊(yùn)。
五、結(jié)語
推動(dòng)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譯介、傳播、闡釋,激活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論的現(xiàn)代性與世界性,加強(qiáng)中國古代文論與世界文論的互動(dòng),為世界文學(xué)批評提供中國理論與中國方法。如能做好中國古典文藝?yán)碚撔g(shù)語的跨文化傳播便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使跨文化者于一詞之內(nèi)透視中國古代文論的魅力。至于如何在術(shù)語研究層面取得突破,探索出中國古代文論的海外傳播與接受的路徑、方法與策略,仍然長路漫漫,有待不懈求索。
參考文獻(xiàn):
[1]張杰.擴(kuò)大古典文論海外傳播影響力[N].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22-05-13(002).
[2]張法.中西美學(xué)與文化精神[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20:44.
[3]宇文所安.中國文學(xué)思想讀本[M].王柏華,陶慶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17.
[4]黨圣元.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和體系[J].文學(xué)評論,1997(01):15-25.
[5]魏瑾.中國傳統(tǒng)文論術(shù)語的民族文化特征與譯介策略[J].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11(01):114-119.
[6]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7]Siu-kit Wong,Allan chung-hang lo,Kwong-tai Lam.tans.Literary Design[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9.
[8]Shih Vincent Yu-chung,trans.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15.
[9]Guobin Yang,trans.Dragon-Carving and Literary Min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作者簡介:
李官麗(1997-),女,漢族,四川內(nèi)江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國際漢語教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