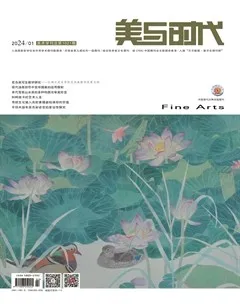范寬山水畫藝術(shù)風(fēng)格賞析
摘 要:宋代繪畫是我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高峰。宋一改唐濃麗精工之風(fēng),以秀雅精致為主要特點(diǎn),畫意重點(diǎn)突出人與自然相合之境。這與宋代對(duì)前朝藝術(shù)風(fēng)格的批判和對(duì)天人合一理想的追求息息相關(guān)。范寬,北宋山水畫家,其《溪山行旅圖》被稱為北宋“第一神品”,風(fēng)格真切確實(shí),畫面可見崇山峻嶺壯闊雄偉、氣勢宏大之態(tài)。范寬既以“中峰鼎立”的構(gòu)圖方式彰顯著北宋文人對(duì)“中正”的追求,又立足“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之取向,體現(xiàn)了北宋文人與自然、與天合一的理想。
關(guān)鍵詞:范寬;《溪山行旅圖》;中正;天人合一
中國山水畫中“最雄偉的一座山”——《溪山行旅圖》,是北宋畫家范寬的代表作品。此圖為雙拼絹本,淡設(shè)色,以多變的筆墨及皴法描繪了溪山的峰巒疊嶂,瀑布縱流,旅人風(fēng)塵仆仆,表現(xiàn)出了山、水、人的動(dòng)靜結(jié)合之美。本文以“六法”為標(biāo)準(zhǔn)賞析范寬作品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并基于其作品探見北宋文人的審美理想。
一、范寬其人及師承
范寬,別名中正,字中立,出生于華原(今陜西銅川耀州區(qū)),是宋代著名的“北派”山水畫大師。盡管歷史中并未明確記載范寬的生卒年份,但據(jù)畫史記載,他大約在五代后漢乾祐年間出生,且在宋仁宗天圣年間(1023—1031年)年依然健在,主要活躍在北宋前期。范寬以他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深刻的人文內(nèi)涵,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一位大師。
據(jù)史料記載,范寬先后師承于荊浩和李成。李成作品傳世絕少,難見二人之間風(fēng)格傳承。據(jù)說丹徒僧房有一幅山水畫,與荊浩畫風(fēng)相似,畫中瀑水邊題字“華原范寬”,后人認(rèn)為這是范寬年少時(shí)所作,具有荊浩“善寫云中山頂,四面峻厚”的構(gòu)圖傳統(tǒng)。范寬善畫山水,能自出新意,《宣和畫譜》著錄當(dāng)時(shí)宮廷收藏他的作品達(dá)五十八件,米芾在《畫史》中提到見范寬真跡三十件。由于年代久遠(yuǎn),現(xiàn)存有《溪山行旅圖》《雪景寒林圖》《雪山蕭寺圖》等。
二、范寬作品內(nèi)容
《溪山行旅圖》被譽(yù)為“宋畫第一”。畫作為絹本,淺設(shè)色,現(xiàn)藏于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畫卷縱206.3厘米,橫103.3厘米。近觀此畫,最能體會(huì)到何謂高山。遠(yuǎn)景是懸崖峭壁,山體高聳,近景是突兀巨巖,前后景錯(cuò)落有致,使人仿若置身山間小路之上,走在其間,只要抬頭仰看,便可見到山就在頭上。山澗還有瀑布縱落,大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之氣勢,又見瀑布末尾呈分流之態(tài),雖未能盡見山石,卻也能想象峭壁之間的犬牙交錯(cuò)。畫面右側(cè),一隊(duì)商旅緩緩走進(jìn)了人們的視野,人、馬均呈現(xiàn)前傾姿勢,馬前蹄彎曲,可見前行之態(tài),且著墨濃淡不一。山間霧氣蒙蒙,沙飛石走。山、水、人三種元素應(yīng)和,動(dòng)中有靜,靜中有動(dòng),詩情畫意在一動(dòng)一靜中顯現(xiàn)出來。
除《溪山行旅圖》外,范寬的《雪山蕭寺圖》也甚為出名。該圖立軸,絹本,淡設(shè)色,縱182.4厘米,橫108.2厘米,現(xiàn)藏于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此圖無款印,詩塘有王鐸順治六年(1649年)上巳觀識(shí)。這幅畫作堪稱巧妙絕倫,它以細(xì)膩的筆觸描繪出白雪皚皚的群山深谷,以及山頂上寒樹叢生的景象。畫中的古剎、寒泉及行旅錯(cuò)落有致地布置在山澗中,讓人仿佛置身于一個(gè)神秘而又靜謐的世界。畫中以水墨渲染出陰沉的天空,山石的皴筆不多,但氣象雄渾,完美地展示了范寬“寫山真骨”“與山傳神”的精湛技藝。畫上還鈐有清嘉慶諸璽,詩塘上有北宋王詵題跋的贊譽(yù)之辭:“博大奇奧,氣骨玄邈,用荊關(guān)董巨,運(yùn)之一機(jī),而靈韻雄邁,允為古今第一。”這幅畫作不僅讓人領(lǐng)略了范寬精湛的繪畫技藝,更讓人感受到了中國古代山水畫的無窮魅力。
《臨流獨(dú)坐圖》是范寬又一表現(xiàn)層巒疊嶂、千巖萬壑的巨制,縱166.1厘米,橫106.3厘米。深郁的山坳間騰起浮動(dòng)的云霧,吐吞變滅。光影的晦明變化間,房屋人家或隱或顯,樹與山石形態(tài)各異,峰巒錯(cuò)落之間還有泠泠瀑布。水之柔滋養(yǎng)著山之剛,樹之蔥郁又同石之孤堅(jiān)交相輝映,在霧氣的襯托之下,加強(qiáng)了觀者忘身于萬山之中的感覺,不由引人遐想。若居其間,則成天端坐,放眼四望均是自然景觀,樂山樂水樂人家,見雪見霧見自然。
三、范寬山水畫藝術(shù)風(fēng)格評(píng)析
《圖畫見聞志》這樣評(píng)價(jià)范寬之作:“畫山水唯營丘李成、長安關(guān)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跱,百代標(biāo)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xùn)、荊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xué)者,如翟院深、劉永、紀(jì)真之輩,難繼后塵。夫氣象蕭疏,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jiān)凝,雜木豐茂,臺(tái)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guān)氏之風(fēng)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qiáng),搶筆俱均,人屋皆質(zhì)者,范氏之作也。”此評(píng)價(jià)可謂極高。
自南齊謝赫在其畫論《畫品》中提出“六法”,并得到中國畫家、學(xué)者們的普遍認(rèn)同后,“六法”便成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和審美理想。
“骨法用筆”是筆法的標(biāo)準(zhǔn)。“骨法”一詞最初是一個(gè)相貌學(xué)概念,后來成為人們觀察人物身份和特征的語言。繪畫評(píng)論中用“骨”字,始于顧愷之,用來描述畫中人物骨感外表所體現(xiàn)的身份和氣質(zhì)。到了謝赫所處的時(shí)代,“骨法”的含義逐漸轉(zhuǎn)向骨力、力量美,即筆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繪畫對(duì)象需要依靠線條的準(zhǔn)確性、力量感和變化來表達(dá)結(jié)構(gòu)、姿勢和表情,因此謝赫借用“骨法”來形容畫筆的藝術(shù)性。簡單來說,繪畫中運(yùn)用“骨法”來表現(xiàn)人物的氣質(zhì)和情感,通過準(zhǔn)確的線條和力量感,表現(xiàn)人物的結(jié)構(gòu)、姿態(tài)和表情。范寬的作品多為山水畫,因此若以“骨法”論其筆法,當(dāng)多言其筆力之強(qiáng)。以《溪山行旅圖》來看,山勢走向,樹木彎曲,石頭的聚集與分散均可見清晰線條,棱角分明,甚至在表現(xiàn)行旅馬隊(duì)與山間自然狀況(霧氣或是沙塵)時(shí),雖有墨濃淡之別,但未見線條模糊之象。
“應(yīng)物象性”是指畫家的描繪要與所反映的對(duì)象形似。這一點(diǎn)的要求正好區(qū)別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與西方繪畫。范寬的繪畫作品雖有其個(gè)人精神之顯現(xiàn),但也未超出山水本色。如其《臨流獨(dú)坐圖》,山中雪夜,本應(yīng)目難視物,但畫面之中房屋瓦舍,樹木群石,甚至是遠(yuǎn)山之間的瀑布均有體現(xiàn)。可見,創(chuàng)作此畫時(shí),范寬應(yīng)加入了想象,但因“胸有成竹”,故而無一物偏離其本身形態(tài),甚至可見物之氣韻。
“隨類賦彩”指的是繪畫中的著色技巧。賦是施、布色的意思,隨類是隨著物象的自然狀態(tài)。在繪畫中,根據(jù)物體的自然色彩進(jìn)行著色。比如,山水畫中的草本和木本等物象可以按照相同色調(diào)處理,也可以按照季節(jié)分類。同時(shí),也可以根據(jù)需要改變客觀物象的色彩,以符合畫家的主觀意愿。范寬的山水畫追求造化之象,因此并未著以彩色。以《溪山行旅圖》為例,在色彩運(yùn)用之上范寬以墨色為主,凸顯背景環(huán)境與物體顏色的差異主要依賴于絹色與墨色的對(duì)沖。其以“雨點(diǎn)皴”畫法,使墨色多集中于山頭之上,而在樹葉的表現(xiàn)上選用了“積墨”的方式。兩相結(jié)合,畫面層次豐富,墨感濃淡分布有序,既突出“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色彩之感,又彰顯出物體本身的狀態(tài),不因真實(shí)而寡淡,也不因著墨而虛幻。
“經(jīng)營位置”指的是作品構(gòu)圖。其中,“經(jīng)營”原指營造、建筑、位置或指物象的地位或指安排配置的動(dòng)作,“位置”則表示為作品中人、物所占之位。范寬作品就整體而言為山水景物之作,卻也并非全然為景。作品中,人、物安置亦有其特色,與周圍之景相協(xié)調(diào)。無論是《溪山行旅圖》,還是《臨流獨(dú)坐圖》,均可見與雄大山景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比的人物安排——人物之小與山景之壯闊盡入畫中。
“傳移模寫”是指臨摹作品的過程。其中,“傳”指的是傳遞、流布或遞送;“模”指的是法度或模仿;“寫”也有模仿之意。整體而言,“傳移模寫”就是通過模仿和學(xué)習(xí),來掌握和理解藝術(shù)作品的過程。此法主要用于說明繪畫作品與“造化”之間的關(guān)系。范寬作品雖多為寫實(shí),但與具體事物之間還是有些差距的。就《溪山行旅圖》來看,溪山位于陜西境內(nèi),其山連綿,因雅丹地貌的影響雖有犬牙相錯(cuò)之態(tài),但也難有格外突出的某一山頭。而在作品之中,前景之山與后景之山落差巨大,范寬如此處理,當(dāng)有其見山之時(shí)心境之由。
“六法”除以上具體五法之外,還有“氣韻生動(dòng)”之法,且此法為前五法之總轄。
兩宋時(shí)期,由于社會(huì)風(fēng)氣的轉(zhuǎn)向,宋代的藝術(shù)格外注重氣韻,“風(fēng)雅”是宋時(shí)文人最高的美學(xué)理想。不同于魏晉的道法自然,兩宋對(duì)自然的追求側(cè)重于“合理”。又因宋儒對(duì)“理”的詮釋,令“理”與“持敬”的不動(dòng)心狀態(tài)和天道的生生不息相互糾纏,所以兩宋時(shí)期繪畫作品體現(xiàn)的氣韻多以穩(wěn)重、安定、素凈、動(dòng)靜有序?yàn)樘攸c(diǎn)。
觀范寬之作,《溪山行旅圖》主體部分為巍峨高山,山勢險(xiǎn)峻,并由于前景后景落差巨大,給人以壓迫之感,但又因山間有行旅、瀑布這些動(dòng)態(tài)的對(duì)象,減少了靜態(tài)山石帶給觀賞者的壓迫感,進(jìn)而既保證了畫面的穩(wěn)重,又留下足以喘息之地。
除此之外,留白亦是氣韻生動(dòng)的來源之一。《臨流獨(dú)坐圖》畫面之中山體錯(cuò)落,排布更密,但最遠(yuǎn)處的山與紙張邊緣留有較大空間,削弱了高山帶來的窒息之感;前山后山之間也留有空白,不僅為霧氣提供了流動(dòng)空間,也間隔開山與山之間的距離,得以使氣充盈回環(huán);近處樹木與石頭集中于一條線之上,除此之外的空間里未有大面積的物體,空白區(qū)域廣闊,以觀賞者視角帶入想象時(shí),不會(huì)感覺到山路逼仄而產(chǎn)生畏懼心理。
看回《溪山行旅圖》,該作雖氣勢宏大,但畫面中虛實(shí)關(guān)系處理得恰到好處。山路之上馬隊(duì)前行,馬的著墨有深有淺,如此處理,令畫面如有生命,可見風(fēng)動(dòng)。且,范寬在創(chuàng)作之時(shí),將山做了切實(shí)處理,水與霧則以留白的方式渲染動(dòng)向,從而做到了山為實(shí),水為虛。“畫面前部即近山和遠(yuǎn)山之間的一片虛空云氣是整幅畫的點(diǎn)睛之筆,也是氣韻生動(dòng)的關(guān)鍵所在。這片云氣空白既自然地分開畫面上下兩個(gè)部分,也拉開了遠(yuǎn)近的空間。”[1]
范寬之作與“六法”高度契合,也正因如此,其《溪山行旅圖》被視為中國山水畫中“最雄偉的一座山”,擁有“故宮《蒙娜麗莎》”的美譽(yù),為北宋的山水畫樹立了典范[2]。
四、從范寬作品看北宋文人的審美理想
(一)中正
范寬的繪畫風(fēng)格沉穩(wěn)大氣,《溪山行旅圖》《雪山蕭寺圖》《臨流獨(dú)坐圖》均呈現(xiàn)出“中峰鼎立”的構(gòu)圖方式,而這一構(gòu)圖方式正體現(xiàn)了其對(duì)中正境界的追求。
中庸是儒家關(guān)于個(gè)人修養(yǎng)與社會(huì)治理的基本價(jià)值理論。《論語·雍也》有載:“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3]可見,是儒家所追求與秉持的一種臻至完美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或行為規(guī)范。
宋代,是儒學(xué)的中興時(shí)期,對(duì)儒家價(jià)值觀的認(rèn)可使得兩宋文人將對(duì)儒家傳統(tǒng)命題的思考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對(duì)于繪畫來說,心中之念必將落于紙上。
“中峰鼎立”式構(gòu)圖不僅是范寬個(gè)人的繪畫特點(diǎn),還是北宋山水畫中常見的構(gòu)圖方式。觀察畫面正中央的山峰,可以看到左右各有一條垂直線,上面是水平線,下面則是一條留白的水平線,這四條線框出一個(gè)長方形,便形成“中峰鼎立”[4]。《溪山行旅圖》中,畫面中心的山峰高聳,較矮的山體環(huán)繞周圍,形成錯(cuò)落之感。如此構(gòu)圖不僅是“守一”的彰顯,也是對(duì)“中庸之道”的發(fā)揮,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四書章句集注》)[5]。
(二)天人合一
范寬曾有感悟:“吾與其師于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于物者,未若師諸心。”遂常流連于終南山、太華山等山林之間,危坐終日,體會(huì)自然。因此,其作品之中不僅有山水,亦有其本心。
《雪山蕭寺圖》中寺廟林立,僧人挑擔(dān);《溪山行旅圖》中行旅風(fēng)塵,諸馬曲蹄;《臨流獨(dú)坐圖》中山霧迷漫,臨流撫琴。無論是哪一幅作品,都能見其中有天地,有山水,有人。如此,天人合一之境躍然筆下。
北宋文人表現(xiàn)出與自然合二為一,將心交于天理的態(tài)勢。佛、道的影響,重建儒道的時(shí)代追求,促使北宋文人思考自然,思考人道與天道的關(guān)系,思考如何以人道合于天道。有別于魏晉玄學(xué)之風(fēng)下文人的寄情山水、逃避禮教,北宋文人對(duì)自然的態(tài)度更偏向于認(rèn)識(shí)自然、利用自然。他們致力于尋找自然的本質(zhì),建立自然與人的關(guān)系,促使人文社會(huì)同自然產(chǎn)生聯(lián)系,重新解釋儒家禮教。這種積極入世的思想很好地體現(xiàn)在了北宋的書畫作品之中。徐悲鴻高度贊揚(yáng)《溪山行旅圖》,稱此作“大氣磅礴,沉雄高古,誠辟易萬人之作”,“章法突兀,使人咋舌”。由此可見,北宋人治藝之精。而北宋人治藝之精正在于他們對(duì)“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繪畫畫意的踐履,更在于他們對(duì)天人合一審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參考文獻(xiàn):
[1]林永潮.《溪山行旅圖》布局之氣韻[J].福建藝術(shù),2021(12):28-29.
[2]魏慧慧.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的美學(xué)意境[J].西夏研究,2022(1):96-99.
[3]論語[M].陳曉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74-75.
[4]徐力.從范寬畫作“中峰鼎立”看北宋文人中正精神[J].美術(shù)教育研究,2023(3):10-12.
[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19.
作者簡介:
任美霖,中國計(jì)量大學(xué)人文與外語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學(xué)、禮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