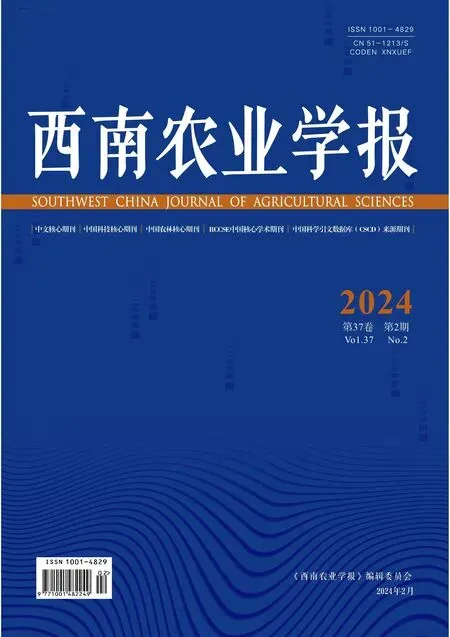不同覆膜處理下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響應特征
王正強,張政兵,李清昊,李耀明,楊 平,楊藝帥,譚 琳
(1. 湖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長沙 410128;2. 湖南省植保植檢站,長沙 410006;3. 津市市農業農村局,湖南 常德 415400)
【研究意義】藠頭(AlliumchinenseG.Don)又名薤、蕎頭,百合科蔥屬植物,一種藥食兩用資源,是目前所有農副產品中為數不多的復合型功能食品,被譽為“菜中靈芝”[1-2],湖南省津市市白衣鎮更是被冠以“中國藠果之鄉”的美譽。但隨著種植年限的增加,藠頭的病害問題逐年加重,尤其是根腐病[3]、炭疽病[4]等真菌性病害的發生,嚴重影響著藠頭的產量和品質。農用地膜是現代農業的重要生產資料,覆膜措施具有防病、抗蟲、抑制雜草生長等作用,還具有促進作物生長發育、提高作物產量等優勢[5]。土壤微生物作為土壤生物區系中最重要的功能組分,其數量、種類及多樣性在土壤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6-7]、提高植物的抗病蟲害能力[8]、促進植物的生長發育及生產力[9]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對土壤環境變化非常敏感,因而被認為是衡量土壤健康的重要生物學指標[10]。【前人研究進展】地膜覆蓋提供了特殊的土壤生態環境,改變了土壤理化性質,而土壤微生物能對土壤生態機制變化和環境脅迫作出反應,導致其群落結構及生態功能發生改變[11-12]。婁俊鑫等[13]在煙田土壤中覆蓋黑色地膜后發現,地膜不影響真菌群落的多樣性,但顯著影響其群落結構及生態功能。而Huang等[14]在玉米地覆蓋無色透明地膜后,顯著影響了真菌群落的多樣性及群落組成。劉岳飛[15]還發現,銀色地膜能顯著改變辣椒土壤真菌群落的類型和結構。可以看出,地膜顏色也是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的重要因素。針對藠頭作物的生產,已有學者提出使用地膜覆蓋并結合高溫曝曬能有效預防土傳病害、地下害蟲及雜草生長,且對藠頭生產具有明顯的增產效果[16-18],但不同覆膜處理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影響仍未可知。【本研究切入點】土壤真菌作為農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土壤病害的發生和抑制密切相關[19],且在有機物的分解和養分循環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20-21],但土壤真菌對人為干擾比較敏感,不同管理措施對土壤真菌群落結構和多樣性具有較大影響[22]。為促進藠頭健康生產,深入了解覆膜處理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結構及功能的影響很有必要。【擬解決的關鍵問題】以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為研究對象,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并結合功能預測、分子生態網絡等方法探討其真菌群落結構與功能對不同覆膜處理的響應特征,以期為不同顏色地膜的選擇及地膜覆蓋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影響提供參考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田概況
試驗在津市市白衣鎮紅光村進行(111°52′ E,29°24′ N),試驗地為旱田壤土,肥力中等,前作為藠頭,該地海拔44 m。
1.2 試驗設計
試驗設3個處理,每個處理重復3次,共9個小區,每小區面積為30 m2。于2021年9月16日分別覆蓋0.06 mm厚普通透明地膜(Normal plastic mulch,NPM)、0.06 mm厚藍色地膜(Blue plastic mulch,BPM),以不覆膜地塊(CK)作對照。兩種地膜材質均為聚乙烯(PE),其中普通地膜(透光率95%)產自山東省鄆城一鳴塑業有限公司,藍色地膜(透光率80%)產自江蘇省宿遷恒華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藠頭播前各試驗區統一施用復合肥(N 26%、P2O510%、K2O 16%)600 kg/hm2作基肥,于10月1日完成種植,次年3月20日施尿素(N ≥ 46%)250 kg/hm2作追肥。除草、病蟲害防治等田間管理同當地一致。
1.3 樣品采集
于2022年6月1日在藠頭收獲期利用五點取樣法分別對各處理進行土壤樣品采集,具體方法為每個處理設置5個取樣點,每個取樣點隨機選取10株藠頭,為避免土壤樣品單一,5株藠頭根際土壤并到一個自封袋,每個處理10份,共30份。將各處理所取樣品帶回實驗室,-80 ℃冰箱保存。
1.4 DNA測序
參照FastDNA?SPIN Kit for Soil(MP,USA)土壤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的步驟提取各根際土壤樣品DNA,DNA濃度和純度利用NanoDrop 2000進行檢測,利用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DNA提取質量。使用引物ITS1 F(5’-ACTTGGTCATTTAGAGGAAGTAA-3’)和ITS2 R(5’-BGCTGCGTTCTTCAT CGATGC-3’)對18S rRNA基因的ITS-1可變區進行PCR擴增[23]。使用2%瓊脂糖凝膠回收PCR產物,利用AxyPrep DNA Gel Extraction Kit(Axygen,USA)試劑盒進一步純化回收后,委托廣東美格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Illumina高通量測序。
1.5 序列預處理
將所有原始數據以FASTQ格式以及樣本對應的Barcode信息上傳到Galaxy分析平臺上(http://mem.rcees.ac.cn:8080)進行分析[24]。使用Trim Primer將正反向引物去除。通過FLASH將正反向序列進行拼接[25]。使用Btrim[26]步驟去除由FLASH拼接后序列中的低質量區域后,對序列進行篩選和修剪。用UPARSE方法按97%相似度進行OTU歸類,生成原始OTU表,并對原始表進行重抽,使每個樣品序列數相同,用重抽后OTU進行后期統計分析[27-28]。
1.6 生態與統計分析
通過RDP分類數據庫對OTU進行注釋。計算樣本間的Bary Curtis距離,再進行非度量多維尺度NMDS(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分析,為驗證不同覆膜處理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之間群落結構是否有顯著差異,通過相似性分析(ANOSIM)、多響應置換過程分析(MRPP)以及置換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3種方法進行不相似性檢驗(Dissimilarity test)。使用FUNGuild數據庫分析不同覆膜處理條件下的真菌功能類群[29-30],將Resample OTU表上傳到INAP分析平臺上(http://mem.rcees.ac.cn:8081)進行分析[31]。基于Spearman相關性構建分子生態網絡,基于隨機矩陣理論設置合適的閾值,利用Gephi對微生物網絡可視化處理,并進行拓撲參數的計算。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覆膜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多樣性分析
通過高通量測序分析,從30個樣本中共獲得2 696 172個有效序列,并從這些序列中識別出5054個OTU。將3個處理根際土壤樣品的OTUs分布進行韋恩圖分析,由圖1可知,CK、NPM、BPM處理根際土壤樣品中真菌的OTU豐度分別為342、385、338個,而三者共有的OTU為113個,占OTU總數的2.24%;NPM處理的OTU豐度相比CK增加12.57%,而BPM處理的OTU豐度相比CK降低1.17%;CK、NPM、BPM處理中特有的真菌OTU分別為147、203和156個,分別占各自總數的42.98%、52.73%和46.15%,且NPM、BPM處理特有的OTU數分別是CK的1.38和1.06倍。

CK:未覆膜處理;NPM:普通地膜處理;BPM:藍色地膜處理。下同。CK: Control treatment; NPM: Normal plastic mulch treatment; BPM: Blue plastic mulch treatment. The same as below.圖1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OTUs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fungal OTUs of A.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根據Richness指數結果(圖2-a)可知,所有樣本的Richness多樣性指數為435~760,且CK和BPM處理的根際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水平差異顯著(P<0.05)。進一步分析不同處理下土壤真菌群落的β多樣性,基于Bray-Curtis距離,利用NMDS方法對根際土壤真菌群落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圖2-b),不同處理下的真菌群落分化格局明顯。隨后進行不相似檢驗分析驗證,結果表明(表1),CK和NPM、BPM處理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下同),且NPM和BPM間也存在顯著性差異,從而證明覆膜處理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β-多樣性具有顯著影響。

a:Richness指數分析;b:基于Bray-Curtis距離的NMDS。不同字母表示顯著差異(P<0.05)。a: Richness index analysis; b: NMDS based on Bary-Curtis distanc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圖2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α與β多樣性分析Fig.2 α and β diversity analyses 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1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差異性分析Table 1 Dissimilarity test 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2.2 不同覆膜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物種組成
由圖3-a可知,CK、NPM、BPM處理根際土壤真菌區系在門水平上主要由子囊菌門(Ascomycota)和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組成,二者含量在各處理中均達70%以上。進一步分析組間差異可以發現,不同覆膜處理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相對豐度有一定影響,NPM處理與CK相比,子囊菌門增加16.76%,擔子菌門和壺菌門(Chytridiomycota)分別降低19.60%、3.46%;BPM處理與CK相比,子囊菌門增加26.61%,擔子菌門和壺菌門分別降低17.73%、3.60%。

圖3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在門水平(a)和屬水平上(b)的相對豐度Fig.3 Relative abundance of fungal community at phylum (a) and genus (b) levels of A.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由圖3-b可知,除未分類菌屬(Unclassified)在各處理根際土壤真菌區系中占一定比例外,CK優勢菌屬為腐質霉屬(Humicola,7.72%)、杯革菌屬(Cotylidia,9.78%)、Neottiosporina(4.29%);NPM處理優勢菌屬為半內果菌屬(Hamigera,5.38%)、腐質霉屬(Humicola,8.41%)、籃狀菌屬(Talaromyces,5.58%)、曲霉屬(Aspergillus,4.57%)、錐毛殼屬(Coniochaeta,5.54%);BPM處理優勢菌屬為半內果菌屬(24.74%)、腐質霉屬(4.93%)、籃狀菌屬(9.27%)、曲霉屬(7.96%)、鬼傘屬(Coprinellus,6.41%),可以看出不同覆膜處理導致真菌群落在門水平和屬水平上的比例變化。
由圖4可以看出,曲霉屬、半內果菌屬、籃狀菌屬、被孢霉屬(Mortierella)、鬼傘屬、木霉屬(Trichoderma)在BPM處理中豐度較高,杯革菌屬(Cotylidia)和Neottiosporina在CK中豐度較高,錐毛殼屬(Coniochaeta)和枝孢霉屬(Cladosporium)在NPM處理中豐度較高。由此可見,同一菌屬在不同處理條件下豐度存在差異;對各處理進行聚類發現,CK和NPM處理的土壤真菌群落結構和組成較為相似,與BPM差異較大。

圖4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主要真菌菌屬熱圖Fig.4 Heatmap of the main fungal genera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2.3 不同覆膜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分子生態網絡
為研究不同覆膜處理對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影響,利用INAP分析平臺,采用相同閾值0.81構建分子生態網絡(圖5),其冪定律均>0.8,且各拓撲參數大于隨機網絡的相應數值(表2),可進一步分析。

表2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分子生態網絡及隨機網絡拓撲屬性Table 2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molecular ecological network and random network 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1個節點代表1個OTU,且節點大小與連接數呈正比。不同顏色區分不同模塊,小于5分子的模塊中的節點為灰色。A node represents an OTU, and the node siz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connections. Different colors distinguish different modules, and the nodes in modules smaller than 5 molecules are gray.圖5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分子生態網絡Fig.5 Molecular ecological network 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由3個不同覆膜處理下根際土壤真菌分子生態網絡的拓撲參數比較分析可知,節點數、邊數、平均度及平均聚類系數呈現為BPM 在共現網絡中,可以根據節點在模塊內的連通度(Zi)與模塊間的連通度(Pi)識別群落的的關鍵物種,而節點屬性類型一般分為4類:模塊樞紐(Zi>2.5,Pi<0.62)、網絡樞紐(Zi>2.5,Pi>0.62)、外圍節點(Zi<2.5,Pi<0.62)、連接節點(Zi<2.5,Pi>0.62)。在本研究中所構建的3個分子生態網絡中(圖6),大部分節點是外圍節點,主要與模塊內的節點相連,連接數很少,均無網絡樞紐節點。在CK處理中,有3個模塊樞紐節點(OTU_154、OTU_138、OTU_40),2個連接節點(OTU_97、OTU_181);在NPM處理中,均為外圍節點;在BPM處理中,有1個模塊樞紐節點(OTU_2164)。進一步對共現網落中起重要作用的節點進行注釋,發現在CK根際土壤中的主要關鍵物種為散囊菌目(Eurotiales)、毀絲霉屬(Myceliophthora)等;在BPM根際土壤中的主要關鍵物種為Neosetophomarosarum。可見,隨著生態環境的改變,關鍵物種也發生著顯著變化。 圖6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Zi-Pi圖Fig.6 Zi-Pi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采用FUNGuild平臺對藠頭不同覆膜處理根際土壤真菌群落進行功能預測分析,結果發現,樣本共涉及腐生型(Saprotroph)、病原型(Pathotroph)、病原-腐生-共生型(Pathotroph-Saprotroph-Symbiotroph)、病原-腐生型(Pathotroph-Saprotroph)、共生型(Symbiotroph)、腐生-共生型(Saprotroph-Symbiotroph)、病原-共生型(Pathotroph-Symbiotroph)7種生態營養模式。本研究以相對豐度超過10%的功能菌群進行作圖分析(圖7-a),結果顯示,腐生型(Saprotroph)、病原型(Pathotroph)、病原-腐生-共生型(Pathotroph-Saprotroph-Symbiotroph)3種功能菌群在CK和NPM處理中占比均超過10%,其相對豐度分別為46.26%、13.86%、11.53%和47.07%、13.92%、12.82%,而在BPM處理中相對豐度超過10%的功能菌群為腐生型(Saprotroph,48.44%)和病原型(Pathotroph,15.40%)。 a:營養型分類;b:Guild詳細分類。a: Trophic mode; b: Guide detailed classification.圖7 不同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FUNGuild功能分類Fig.7 FUNGuild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of fungal community of A. chinense rhizosphere soil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對各樣品菌群進行了詳細的物種生態功能預測分類,并以相對豐度超過3%的菌群進行作圖(7-b),可以看到,不同覆膜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已鑒定出的主要生態功能菌群是未定義腐生菌(Undefined Saprotroph),在CK、NPM、BPM處理中的占比分別為33.49%、33.15%、35.64%,其次是植物病原型(Plant Pathogen),其相對豐度依次為8.26%、8.42%、10.21%。 覆膜措施具有防治病蟲草害、增溫調溫、保墑提墑等多種綜合效應,能在作物的產量和品質上發揮重要作用[32],但覆膜處理改變了土壤微環境,進而對土壤微生物活性及群落結構造成一定影響[33]。Tian等[34]在黍種植田中覆蓋透明地膜后顯著降低了土壤真菌群落多樣性,改變了真菌群落組成及關鍵類群。Dong等[35]在玉米地中覆蓋透明地膜顯著提高了真菌群落多樣性和豐富度。而宋健等[36]發現,藍色地膜對韭菜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結構造成一定影響,對其多樣性影響不大。在本試驗中,覆膜處理造成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多樣性降低,并對β-多樣性(Bray-Curtis距離)具有顯著影響,該結果與Liu等[37]的研究結果相似。Liu等[37]認為,由于真菌對有氧環境的偏好,覆蓋會造成局部厭氧環境,從而導致真菌群落發生變化和豐富度下降,且胡志娥等[38]研究發現,覆膜處理雖然降低了土壤真菌群落多樣性,但并不意味著土壤功能性的降低,其土壤氮磷等養分含量仍受其多樣性的顯著影響。在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種群中,有70%以上的真菌來自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這與其他農田或草地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結構研究相似[39-42]。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位于真菌進化樹的頂端[43],它們不僅是有機質的主要分解者,而且參與根際氮素循環,對植物生長發育起著重要重用[39,44]。在屬水平上,腐質霉屬、籃狀菌屬、曲霉屬等菌群的相對豐度在覆膜處理后顯著提升,已有研究表明,這幾種真菌類群是自然界重要的分解者,可降解植物木質纖維素,增加土壤腐殖質,還具有較強的溶磷能力,使植物能更好地利用土壤中的磷元素[45-47];另一方面,半內果菌屬菌群的含量在覆膜處理后也呈上升趨勢,研究報道該菌群是一種耐熱性霉菌,常在食品加工階段引起食品污染[48],而這將可能給藠頭的實際生產帶來潛在風險。 生態網絡已成為揭示不同環境條件下微生物物種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手段[49],網絡的拓撲特征可以反映微生物之間的連通性和相互作用的水平[50]。關鍵物種的存在或消失可能會導致群落的結構與功能發生一系列變化[51]。本研究發現,對藠田進行不同覆膜處理后,造成了NPM和BPM處理在網絡中的節點數和連接數減少以及平均度和平均聚集系數降低,從而降低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的網絡復雜性,這與胡志娥等[38]對覆膜下農田土壤真菌群落響應一致,且Tian等[34]認為地膜覆蓋下微生物α多樣性的降低是造成微生物網絡簡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雖然不同覆膜處理降低了網絡的復雜性,但其模塊化指數均呈上升趨勢,表現為BPM>NPM>CK,研究表明,模塊化指數表征系統抵抗外界干擾的能力,其值越大,系統穩定性越高[52]。此外,在本研究中,不同覆膜處理下的真菌生態網絡中的模塊樞紐節點和連接節點差異明顯,在CK中,主要關鍵物種為散囊菌目(Eurotiales)、毀絲霉屬(Myceliophthora)等。研究報道,散囊菌目中存在著一些高效的纖維素降解菌,在碳轉化循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53];還有研究發現大多毀絲霉屬真菌是嗜熱真菌,能產生熱穩定的酶,具有較強的降解能力[54]。在NPM處理中沒有出現關鍵物種;在BPM處理中只出現1個關鍵物種為Neosetophomarosarum,該物種隸屬子囊菌門(Ascomycota)、新刺毛莖點霉屬(Neosetophoma),由Perera等[55]分離并命名,目前,該菌的研究報道并不多,其生物學功能還有待進一步挖掘。綜上,不同覆膜處理下真菌網絡中關鍵核心物種的改變,可能與覆膜后改變了真菌群落結構,導致真菌類群為適應環境變化而采取多樣化的生態策略有關。 不同覆膜處理改變藠頭根際土壤真菌群落結構的同時,也改變了其生態功能,從而對宿主和環境產生不同的影響。研究發現,部分真菌會隨著土壤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身的營養類型,以抵抗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56-57]。基于FUNGuild功能預測結果可以發現,腐生型真菌在各處理中的相對豐度表現為CK 在本試驗中,覆膜處理降低了真菌群落的多樣性,富集了相對豐度更高的腐質霉屬、籃狀菌屬、曲霉屬等有益真菌菌群,而有益菌群在藍色地膜處理下更為富集;覆膜處理還使根際土壤的真菌分子生態網絡變得簡化,但覆膜處理后的模塊化程度更高,表明覆膜后真菌群落對外部環境的抵抗能力也相對提高,其中藍色地膜較普通地膜表現更優越;試驗進一步對各處理的真菌群落進行功能預測,結果發現,覆膜處理增加了腐生型功能菌群的相對豐度,而該功能型菌群在藍色地膜下占比更高,更利于有機物的分解和養分循環。此外,在本試驗的測產結果中,未覆膜處理藠頭總產量為267.9 kg,普通地膜處理總產量為283.2 kg,藍色地膜處理總產量為359.7 kg,普通地膜及藍色地膜處理相比對照分別增產5.7%和34.3%,與本試驗結論相吻合。因此,推測覆膜處理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可能是藠頭增產的重要因素。在實際生產中,覆膜處理在一定程度上雖能促進作物生長,增產增收,但覆膜措施也可能帶來潛在風險,如病原型功能菌群顯著提升,還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并加入限制。
2.4 不同覆膜處理藠頭根際土壤真菌功能預測

3 討 論
4 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