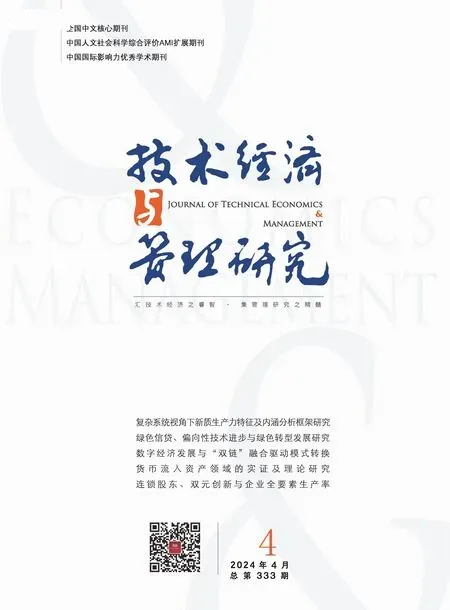數字服務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
——基于我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徐向慧
(1.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北京 100029;2.鄭州科技學院財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64)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技術創新不僅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處于核心地位,而且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性支撐。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2—2023》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國家創新指數在世界范圍內排名第10 位,較上年提升3 位,是唯一進入前15 名的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中國在技術創新領域已取得突破性進展。然而,受創新成果轉化不暢[1]、關鍵技術缺乏[2]等原因影響,企業創新面臨對新興技術領域的掌控力度偏低、創新資源協同運作不暢等梗阻,成為阻礙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現實壁壘。所謂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意指通過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提高國家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以此打造創新型國家。在步入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關鍵時期,如何進一步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已成為當前學術界研究重點。
作為全球服務貿易體系的重要支撐,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有效加快信息交互,降低信息搜索成本與創新試錯成本,促進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依托數字化技術可加速全球產業鏈與創新鏈整合優化,強化各國高端產業互聯互通。這可以有效降低創新活動的不對稱性以及技術應用不確定性,以此提高創新產出回報率,釋放創新潛能,助推企業技術持續創新[3]。另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借助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促使產品研發設計、開發制造等環節向集約化方向轉變。這不僅可以實現供需匹配精準化,還可有效催生大量創新資源,為提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注入資源動能。由此可以推斷,數字服務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存在密切聯系,但二者間的內在機理仍需進一步展開分析。
現階段,學術界關于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一是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直接效應。許晨曦等(2023)認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創新可持續性具有正向推動作用[4]。李健等(2018)表示,經營期望落差可正向提升企業創新可持續性[5]。二是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間接效應。李健等(2017)發現,企業實際績效可正向放大對企業持續創新的負向影響[6]。樂怡婷等(2017)認為,高管過度自信會弱化高管持股對企業持續創新的正向推動作用[7]。
當前,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已在學術界研究中形成較為成熟的模式與體系,大致分為探索數字貿易網絡的衡量方式與中國在數字貿易網絡中的位置兩種,均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一,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衡量方式。趙文霞(2022)以包含節點與節點關系社會關系網絡衡量全球數字服務貿易網絡[8]。呂延方等(2021)使用網絡節點數與邊數測算數字貿易網絡規模特征,借助密度、平均路徑與平均度測度網絡聯系密度,以聚類系數表征網絡聚集效應,以此衡量數字服務貿易網絡[9]。其二,中國在數字貿易網絡中的位置。劉震等(2023)發現,隨著全球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嵌入度的提高,中國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地位逐步提升[10]。而溫湖煒等(2021)則認為,中國在全球數字服務貿易網絡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但近年來逐漸呈現顯著核心區域靠近的趨勢[11]。
梳理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已有研究分別就企業技術持續創新與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展開大量研究,為研究奠定良好基礎,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方面,尚未有文獻深入探究數字服務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二者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鮮有文獻從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助力研發要素流動視角出發,探究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作用機制。和已有研究相比,文章可能存在的創新性貢獻在于:第一,聚焦數字服務貿易網絡探究其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效應,并從知識產權保護與研發要素流動視角剖析全球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間接作用,為相關研究提供有力補充。第二,借助動態調節效應,實證檢驗在知識產權保護、研發要素流動、技術差距、對外直接投資門檻影響下,數字服務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非線性特征。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服務貿易網絡憑借共享性、開放性特征,通過現代通信與信息技術切實提高中國技術創新質量與創新規模,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有效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質量。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突破時空限制,推動知識、數據等內容沿貿易鏈條跨區域、跨產業流動,以此加速企業持續性知識技術的轉移、擴散與溢出。進一步激勵企業通過學習、模仿網絡上關鍵技術,突破原有的技術發展瓶頸[12],助力企業技術創新質量升級,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另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切實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規模。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不斷推動技術創新向集約化發展轉型,助力企業明晰自身與其他企業的前沿技術差距,以此激發企業創新活力[13],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規模,推動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具有正向推動作用。
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促進研發要素流動兩種途徑,間接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間接提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有效破除國家、地區發展限制,打破傳統貿易時空屬性,拓寬知識產權保護邊界,倒逼知識產權保護效率提升。知識產權保護通過提高侵權成本、強化創新成果保護,持續降低創新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知識外溢與創新風險,從而激勵企業自主開展高質量創新活動,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
另一方面,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促進研發要素流動,間接推動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數字貿易網絡借助無紙貿易、電子簽字、電子發票等方式,有效簡化研發要素跨境流動程序,降低研發要素流動時間成本,提高研發要素流動速度。研發要素流動本身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可有效整合空間中閑置、分散的創新資源,不斷促進創新知識跨區域傳播與交流,推動各創新主體研發合作,從而催生出新產品、新工藝與新方法,以此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綜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數字貿易服務網絡可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促進研發要素流動,間接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
三、研究設計
1. 模型構建
(1) 基準回歸模型
為深入考察數字貿易服務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直接影響,構建如下雙重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i 表示企業,t 代表年份,Gtis 代表企業技術持續創新,Gdstn 指代數字服務貿易網絡,X 表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凈利率(Sub)、企業年齡(Age)與現金持有水平(Chl)。β0表示截距項,β1為全球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估計系數,μi與λt依次表示時間固定效應與個體固定效應,εit代表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誤差項。
(2) 中介效應模型
為探究全球數字貿易服務網絡對企業技術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參考Baron&Kenny(1986)[14]的研究思路,在模型(1)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并依次使用逐步回歸法、Bootstrap 檢驗法以及Sobel 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驗證,具體模型如下:
上式中,Mit代表中介變量,包括研發要素流動與知識產權保護。在回歸模型中,重點考察系數β1、γ1、δ1與δ2的大小與方向。
2. 指標選取與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企業技術持續創新(Ctis)
創新活動包含技術研發投入、人力資本投入、戰略目標制定等方面,這就意味著企業的無形資產增量可有效表征創新活動持續產出。因此,使用企業無形資產增量與企業年度初期資產總額的比重測度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水平。
(2) 解釋變量:數字服務貿易網絡(Gdstn)
使用企業進出口市場與國家嵌入位置的比值測度企業在數字服務貿易網絡中的嵌入中心性、聯系強度與解耦洞,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c 表示中國,f 表示除中國以外的國家,degreeft(degreect)、strft(strct)與sthft(sthct)依次表示t年f 國嵌入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中心性、聯系強度與結構洞指標;eft與mft表示t年企業i 向f 國的出口、進口數字服務產品總額;oiet、oimt與oict表示t年企業i 的數字服務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國內銷售額占三者之和的比重。與sthft依次代表企業依托出口空間布局嵌入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中心性、聯系強度與結構洞指標;依次表示企業依托進口空間布局嵌入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中心性、聯系強度與結構洞指標。
(3) 中介變量
研發要素流動(Ifl)包括R&D 人員與R&D 資本流動,下面分別對兩個要素流動進行測算。一方面,引入引力模型測算各地區R&D 人員流動。具體表達式為:
模型(7)中,pfsij表示由i 企業流入j 企業的創新人員數量;代表i、j 兩企業間地理直線距離,Mi指代i 企業涵蓋R&D 人員范圍;wageij代表企業全部就業人員的工資;houseij代表商業住宅平均銷售價格。
另一方面,構建如下模型測算R&D 資本流動:
模型(8)、(9)中,cfrij代表由i 企業向j 企業流入的R&D 資本存量;Ki表示i 企業擁有的R&D 資本存量;rateij代表企業創新過程中平均利潤水平;marketij表示金融業市場指數。R&D 資本流動引力變量為企業平均利潤差值-金融發展水平。
知識產權保護(Ipr),使用各地專利授權數與全國專利授權總數之比測度知識產權立法強度;選取當年各地專利糾紛結案總數與全國專利糾紛立案數之比測度知識產權執法強度,并采用熵值法確定上述兩個指標權重,以衡量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4) 控制變量
為盡可能避免因一系列變量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思路,加入如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以公司總資產取對數表示;總資產凈利率(Sub),以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測度;企業年齡(Age),以企業成立時間起到樣本年限的時間差測度;現金持有水平(Chl),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總資產衡量。
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選取2012—2022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深入考察數字服務貿易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為保證數據可得性、科學性,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首先,剔除ST、*ST、PT 等被特別處理或者現已退市的企業。其次,剔除連續3年內主營業務發生重大變化的企業。最后,去除主要數據指標嚴重缺失的樣本。最終文章得到11574 個觀測值。為消除利群變量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影響,對所有變量進行上下1%縮尾處理。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企業年鑒》 《中國工業企業統計年鑒》、北大法寶法律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Wind 數據庫、中經網與國家統計局網站。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 直接影響效應檢驗
(1) 基準回歸檢驗
構建雙重固定效應模型,驗證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因果關系,具體結果如表1 列(1)所示。可以知悉,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服務貿易可切實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假設H1 得證。

表1 基準回歸結果檢驗
為探究數字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提升作用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依照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全部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東北與西部地區進行區域異質性檢驗,具體結果如表1 列(2)~列(5)所示。觀察表中數據可以知悉,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呈現“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格局。
2. 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 內生性檢驗
為排除內生性對研究結果造成的影響,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探究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具體地,選擇數字服務貿易網絡的二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研究結果如表2 列(1)所示。數據顯示,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在1%置信區間上顯著為正。在排除內生性問題后,研究結果依舊具有穩健性。

表2 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2) 穩健性檢驗
為證明研究結論具有可靠性,使用創新研發投入替換無形資產增量,重新代入模型(1)中進行驗證,具體結果如表2 列(2)所示。可以知悉,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上述結果具有穩健性。
3. 間接影響效應檢驗
為探究知識產權保護與研發要素流動在數字服務貿易網絡與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中的關系,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3 列(1)~列(3)報告了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由列(1)數據可知,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影響系數為0.685,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切實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在1%置信區間上顯著為正,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可切實推動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但是對比列(1)與列(3)數據可以發現,影響系數有所下降,仍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在數字服務貿易網絡促進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中發揮中介效應。假設H2 得到初步證實。
表3 列(4)~列(6)列示了研發要素流動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由列(4)數據可知,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研發要素流動的影響系數為0.671,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助力研發要素流動。從列(4)數據可以發現,研發要素流動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547,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證明研發要素流動可切實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但在加入研發要素流動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可持續雖有所下降,但仍通過Sobel 檢驗,意味著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助力研發要素流動,間接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至此,假設H2 得到完全驗證。
五、進一步討論
1. 模型設定
文章為深入考察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動態調節作用機制,構建如下所示雙面板門檻模型:
其中,I(·)代表門檻指定函數,Q 表示門檻變量,包括知識產權保護(Ipr)、研發要素流動(Ifl),η 為門檻值,其余變量與上文一致。
2. 門檻效應檢驗及結果分析
通過自舉法重復抽樣500 次,探究各個變量門檻存在性,以此確定門檻個數以及模型具體形式,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知識產權保護、研發要素流動均通過雙門檻檢驗。

表4 門檻存在性檢驗
表5 報告了門檻效應的檢驗結果。列(1)列示以知識產權保護為調節變量時的回歸結果。由結果可以知悉,當知識產權保護跨過第一門檻值0.745 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有所增大,從0.485 上升為0.496,當知識產權保護跨過第二個門檻值0.512 時,這一影響系數增大,同時對應的標準誤也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而逐漸增大。列(2)列示了以研發要素流動作為調節變量的研究結果。當研發要素流動水平偏低時,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當研發要素流動越過第一個門檻值5.247 時,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推動作用顯著為正,但僅通過10%顯著性檢驗。當研發要素流動系數大于6.478 時,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影響系數上升至0.475,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這意味著研發要素流動到達一定門檻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賦能作用方可顯現。

表5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1. 研究結論
選取2012—2022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深度考察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直接效應、傳導機制與動態調節效應。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有效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第二,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推動作用存在顯著區域異質性。第三,中介效應檢驗發現,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促進研發要素流動兩條路徑,間接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第四,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對企業技術持續創新的賦能作用,受到知識產權保護、研發要素流動的影響且呈現非線性特征。
2. 政策建議
第一,提高數字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水平。研究結論表明,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有效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因此,政府部門應緊抓這一契機,持續擴大數字服務貿易對外開放領域,進一步促進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具體而言,政府部門可通過打破數字領域的行政壟斷,消除國有、私營和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差異,以此改善服務業企業的營商環境。這可有效破除數字信息技術服務的進入壁壘,助力社會資本滲透至應用型技術研發活動中,為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注入資本動能。
第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機制。基于研究結論,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間接促進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據此,政府部門應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機制,通過知識產權保護為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提供制度支持。具體地,政府部門可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審查注冊登記政策調整機制,借助審查動態管理機制等手段,有效避免錯登、漏登現象出現,以此保護企業原創性技術創新權益,助力企業技術持續創新。
第三,發揮研發要素協同配置效應。研究結論認為,數字服務貿易網絡可通過促進研發要素流動,間接推動企業技術持續創新。因此,政府部門應采取針對性措施,通過發揮要素協同配置效應,有效賦能企業技術持續創新。一方面,政府部門應積極制定國外高端人才認定標準,通過為境外人才提供出入境、停留居等便利條件,進一步吸引境外人才加入企業,為促進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注入人才動能。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加快構建數據要素市場,通過建立健全數字資源清單管理制度,有效界定數據要素歸屬權,實施開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標準與措施,為企業技術持續創新注入數據要素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