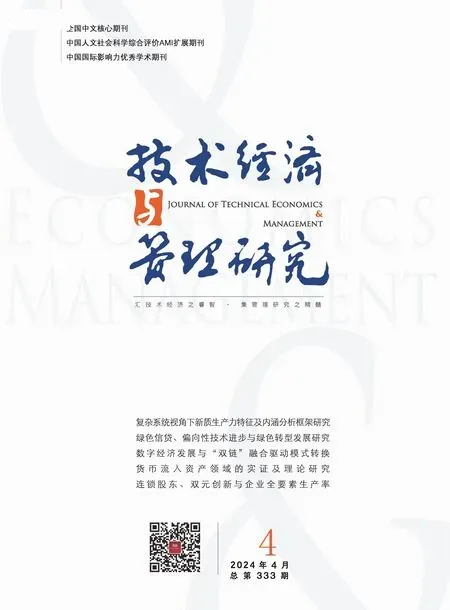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測度與時空演化
蔡清龍
(1.中國礦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2.江蘇財經職業技術學院金融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十四五”規劃提出,我國總體發展目標是:“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可見,加快建設農業現代化,賦能農業強國建設仍是我國長期關注的內容[1]。
現階段,生產資源浪費、農業轉型困難等問題頻發,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糧食產量與居民需求難以匹配、國民生計難以維系,嚴重制約了農業產業可持續發展[2]。農業經濟作為國家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發展格局中處于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提升農業經濟韌性,發揮農業產業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作用,是推進農業產業現代化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動能[3]。有鑒于此,科學測度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研究農業經濟韌性的區域差異及時空演化特征,對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賦能農業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有關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研究可分為測度和影響因素兩個方面。有關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測度,蔣輝(2022)研究指出中國農業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省際關聯特征[4]。李久林等(2022)使用PSR 模型對安徽省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進行測度,認為現階段安徽省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表現出顯著提升態勢[5]。有關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影響因素,Zhou J 等(2023)發現,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能夠顯著提升農業經濟韌性[6]。唐瑩和陳夢涵(2023)研究發現,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對提高農業經濟韌性水平[7]。
梳理上述文獻可以發現,現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測度及影響因素層面,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空間關聯的相關研究較少。但是,研究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分布格局并明確其區域關聯性,對于提升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文章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使用熵值法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和區域差異進行測度,為縮小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差距提供理論基礎。第二,使用莫蘭指數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進一步探析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分布特征,以推動其協同發展。第三,基于經濟收斂理論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收斂性進行分析,以期為縮小農業經濟韌性區域差異提供有效助益。
二、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指標體系構建
1.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評價指標
為更精確、更全面地分析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首先,在構建指標時應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及數據可得性原則[8-10]。其次,在構建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指標體系之前,需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的主要內容及基礎內涵進行進一步探討,明確指標體系構建思路,為文章實證檢驗奠定良好基礎。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提升能夠憑借做好風險防御、調節經濟結構、推動科技創新等方式,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是推動我國農業強國建設的重要動能[11-13]。因此,在構建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指標體系時,應將防控、調節、創新作為重點刻畫內容,多維度闡釋農業經濟韌性的基礎內涵與重要性,以精確衡量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最后,基于前文所述,從抵抗能力、調節能力、創新能力三個維度構建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指標體系[14-16],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 數據來源與說明
選取2013—2022年我國30 個省份(除西藏及港澳臺地區) 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主要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農業年鑒》 《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中國糧食年鑒》 《中國林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中國環境統計年鑒》 《中國保險年鑒》 《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年鑒》、中經網、國泰安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使用插值法補齊。
三、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測度方法
為客觀、精確、統一衡量指標,需進一步對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進行賦權處理。因此,選熵值法對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具體方法如下:
第一,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原始數據展開標準化處理,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Xij′與Xij分別指代標準化處理后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指標值和第i年第j 個指標的原始值;max{Xj}與min{Xj}分別表示全部研究年份中j 指標的最大值及最小值。
(1) 復合地基承載力驗算[6-8]。由JCCAD計算得出:基底壓力標準值Pk=450 kPa;計算車庫等效覆土深度d=1.25 m,深度修正的基礎埋深d=3.75 m,有效重度取值15 kN/m3。
第四,對指標的信息熵冗余度進行測算,可得fj=1-ej。
計算出第j 個權重后,Sij=yjXij′表示第i年j 指標的評分值。
四、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綜合指數測度及結果分析
使用熵值法對2013—2022年中國30 個省份的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進行測算,得出綜合評價指數,并進行排序與對比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由表中數據可知,從全國層面來看,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均值從2013年的0.190 上升至2022年的0.349,年均增長率達6.346%,整體呈現出良好發展態勢。從省級層面來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高于全國綜合平均水平(0.251)的省份共有14 個。其中,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最高的地區為山東,最低的地區為寧夏,二者指數相差3.201 倍,表明各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較大差距。

表2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綜合評價
五、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空演化與收斂性分析
1. 研究方法
(1) 莫蘭指數
現有文獻顯示,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存在空間異質性[17]。因此,文章利用莫蘭指數對各區域間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分布特點進行分析,該指數大小處于[-1,1]之間。具體模型如下:
式(3)、式(4)分別為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n 代表區域總數,zi表示i 區域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指數,zˉ指代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均值,wij為相鄰省份的空間權重矩陣。
(2) 經濟收斂理論
根據前文分析可知,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空間差異。為分析這種差異是否會隨著時間推移擴散或收斂,參考已有研究,對四大區域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依次做σ 收斂、絕對β 收斂及條件β 收斂分析。
第一,中國農業經濟韌性的σ 收斂。σ 收斂能夠檢驗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離差變化,當離差變小,區域間離散程度也隨之降低,說明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存在σ 收斂,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Sn,t指代n 省t 時期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為全部省份t 時期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的平均水平;σt為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相對差異程度,當σt+T<σt時,說明各省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離散系數會隨時間逐步縮小,證實σ 收斂存在。
第二,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絕對β 收斂。絕對β 收斂主要分析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較低地區是否具有較高增長率,進而追趕較高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地區發展速度,反映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增長率與初始水平是否具有負相關性,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驗證,具體模型如下:
第三,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條件β 收斂。考慮到不同個體在地區可能存在一定差異,文章使用條件β 收斂對不同區域間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是否會向自身穩態水平收斂展開測度,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α0表示不同區域的穩態條件;β 為回歸系數;當β 顯著為負時,說明存在β 條件收斂,即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會向自身穩態水平收斂。
2. 結果與分析
(1)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間演變
根據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探討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布局及區域差異。此外,借鑒任建華和雷宏振(2022)[18]的研究思路,將區域人均播種規模的中位數作為劃分我國小規模種植區域與大規模種植區的標準,并進一步研究我國不同規模種植區的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空演變。其中,人均播種規模使用土地播種面積與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比值測度[19]。
一是四大區域。四大區域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間演變趨勢如圖1 所示。觀察可知,四大區域與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整體均呈現出上升趨勢。其中,2013—2022年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表現出持續增長態勢,且在2020年呈現出大幅增長趨勢。2022年四大區域的農業經濟韌性水平仍呈現出中部地區最高、東部地區次之、東北地區再次、西部地區最后的態勢,且東北與西部地區明顯低于其他地區,與中部地區相比差異較大,說明我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

圖1 四大區域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時間演變
二是不同規模種植區。圖2 為不同規模種植區的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間演變趨勢。觀察發現,我國不同規模種植區的農業經濟韌性平均水平整體上表現為平穩上升趨勢。其中,大規模種植區經濟韌性水平大于小規模種植區,且遠高于全國水平,說明大規模種植區仍是推動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圖2 不同規模種植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時間演變
(2)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空間分布
根據各省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可知(篇幅限制,圖已省略),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均大于0,說明其呈現出空間正相關性,且整體表現出波動上升態勢。需要說明的是,雖然2017—2019年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略有降低,但仍然能夠證明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較強空間集聚現象,并于2022年達到0.346 的最高值,表明這一年省際空間相關性最強。
表3 為2013—2022年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局部莫蘭指數的空間分布情況。列(1)~列(4)分別為高—高型地區(H—H)、低—高型地區(L—H)、低—低型地區(L—L)、高—低型地區(H—L)。可以發現,呈現出L—H 型集聚特征的省份主要分布于東北與西部地區省份相對較多,中部與東部地區省份較少;呈現出H—H 型集聚特征的省份主要分布于東部及中部地區;表現為H—L 型集聚特征的省份多分布于西部地區;而北京、上海這類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多呈現出L—L型集聚特征;此外,青海、甘肅這類地理位置偏遠且自然條件對農業發展有一定掣肘的西部地區省份也表現為L—L 型集聚特征。綜上,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表現出顯著空間相關性。

表3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局部莫蘭指數分布情況
(3)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收斂性分析
一是σ 收斂。根據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在全國及四大區域中的標準差(篇幅限制,已省略) 結果可知,以全國范圍為視角,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從2014年起呈現出顯著發散態勢,并于2017—2019年時表現出短暫的階段性收斂狀態,但從2020年開始繼續呈現出持續發散狀態。這意味著在樣本期內,全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仍能夠在整體上表現出發散狀態。以四大區域為視角,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在四大區域的發散程度與全國的發散趨勢存在極高相似性,說明在研究期間,中國農業經濟韌性不存在顯著σ 收斂。值得注意的是,東部、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存在較大的區域內部差異。其中,東北地區在大多數時期均表現為低發散狀態,且內部差異最小。東部地區的內部差異略大于東北地區,小于中西部地區,并呈現出波動上升與階段性收斂的相互交替態勢;中部地區的區域內差異在2016年達到最高點,并于2017年開始呈現出收斂態勢。西部地區的區域內差異在2018年時,由相對平穩逐漸轉換為持續上升趨勢。
二是絕對β 收斂。表4 為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絕對β 收斂分析結果。觀察發現,全國范圍與東北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絕對β 收斂結果均顯著為負,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及西部地區系數顯著性相較東北地區更低。說明除全國整體及東北地區外,其他區域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較高地區的增長率更高。也就是說,即使這些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出現收斂態勢,也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穩定追趕狀態。而東北地區的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一定落后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態勢。

表4 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的絕對β 收斂分析結果
六、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文章選取2013—2022年我國30 個省份面板數據,使用多種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時空分布與收斂性特性展開研究。結果顯示,其一,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表現出逐漸提升趨勢,具體呈中部地區最高、東部地區次之、東北地區再次、西部地區最后的發展格局。其二,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其中,西部地區集聚特征多表現為L—L 型,東部、中部地區多為H—H 型和L—H 型集聚。其三,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在全國及四大區域均存在條件β 收斂,但不存在顯著σ 收斂,且東北地區具有絕對β 收斂。
2. 建議
第一,推動農業產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業經濟提質增效。研究表明,大規模種植區是推動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提升的關鍵助力。因此,各地政府應加強農業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進而推動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提升。政府部門可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化技術構建氣候觀測系統、水利澆灌系統、要素分配系統等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擴大種植區數字規模,提高風險防御水平,推動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持續不斷的提升。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農業發展規劃,縮小農業經濟發展差距。上文研究結果表明,全國及四大區域均存在條件β 收斂,說明各地區因區域異質性表現出不同的穩態水平。故此,政府部門應針對不同地區農業現有基礎制定不同發展規劃,提高各地區適應調節能力,賦能各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提升。針對中部及東部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較高省份,相關政府部門應著重打造囊括生產、研發、運輸、安全等方面的農業綜合發展園區,加強農業產業工業化、數字化、自動化程度,提高農業產業適應調節水平,賦能農業經濟韌性水平進一步提升。針對東北及西部地區農業經濟韌性水平較低的省份,政府部門應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吸收中部與東部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利用當地特色因地制宜發展農業周邊產業,建設農業產業園區,縮小區域差距,進一步賦能各區域農業經濟協同發展。
第三,打造農業經濟共享空間布局,賦能農業經濟協同發展。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農業經濟韌性水平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能夠對周邊省份產生影響。因此,政府部門應加速農業創新技術攻關,利用5G 技術、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打通省際交流渠道,充分發揮H—H 型地區的引領作用,向周邊地區展開合作與交流。同時,有關地區還可向鄰近省份輸送優質人才、創新技術等資源,提高周邊地區農業創新技術發展水平,帶動周邊地區農業經濟發展,推動周邊地區向H—H 型地區邁進,進而賦能農業經濟韌性水平持續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