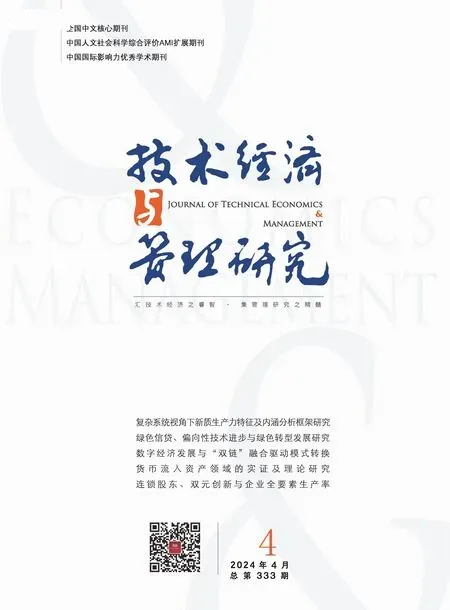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創業活躍度與共同富裕
董楊子
(河北地質大學創新創業教育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31)
一、引言
適逢國際局勢動蕩加劇與全球經濟復蘇不確定性交匯,兩極分化嚴重[1]、貧富懸殊[2]、社會階層固化[3]等問題并存,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攔路虎”。就當前形勢來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亦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但尚需注意,受創新動能與人才供給不足等多層因素制約,共同富裕推動進程受阻[4]。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以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基石,以“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為根本路向,推動創新成果全員共享,并通過完善多主體價值共創利益分配機制,助力推進共同富裕。同時,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可發揮人才與創新資源集聚效應,優化地區創業環境,推動創業項目成果轉化,提升創業活躍度。這能夠盤活地區生產資源,促進就業,實現財富創造與積累,促進共同富裕。
現有研究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展開探討:第一,共同富裕影響因素。就金融層面而言,張金林等(2022)研究認為,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推進共同富裕,其中創業活躍度是數字普惠金融推動共同富裕建設的重要機制[5]。譚燕芝與施偉琦(2023)認為,數字普惠金融與其三重子維度均可對共同富裕產生顯著推動效應[6]。就城鄉均等發展而言,韓建雨與儲海濤(2023)研究發現,新型城鎮化能夠通過集聚效應與創業活躍度有效促進共同富裕,且伴隨創業活躍度上升,新型城鎮化的賦能效應隨之增強[7]。
第二,創業活躍度驅動效應。王軼與劉蕾(2022)研究認為,農民工高質量返鄉創業是促進農民增收、縮小農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可通過培養企業家精神、發展數字技術等途徑實現共同富裕[8]。林嵩等(2023)研究發現,縣域產業活動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為共同富裕提供可行路徑[9]。呂重陽等(2023)研究認為,數字創新創業對共同富裕的作用整體呈“U”型特征[10]。
第三,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影響效應。白潔與李萬明(2022)研究發現,創新型城市建設可正向驅動城市創業,對鄰近城市發揮擴散效應,對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城市具有負向虹吸效應,其中營商環境優化發揮中介作用[11]。白俊紅等(2022)研究認為,創新驅動政策以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為主要抓手,賦能城市創業活躍度提升,且該影響效應在具備地理區位優勢與高行政等級地區作用更為顯著[12]。
鑒于此,文章嘗試從如下層面進行突破:第一,將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創業活躍度與共同富裕置于統一研究框架,豐富現有研究視角。第二,以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不同層面影響作用為依據,嘗試將創業活躍度分為“新創企業成才”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以雙維視角深入探析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與空間溢出效應,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與共同富裕
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以促進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機制創新為基本遵循,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為切入點,促進共同富裕。具體而言,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能夠增強城市創新導向,推動中試平臺建設,促進各類公共資源開放,引導企業整合優勢資源,打造高能級城市創新平臺。在政策導向指引下,企業瞄準人工智能、區塊鏈與大數據等新賽道,持續加大技術研發與儀器設備購置投入,促進顛覆式技術創新,在信息網絡、先進制造業與能源資源領域取得重大突破[13]。于此情形下,技術創新以多點突破與融合互動促進新興產業興起,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助力現代生產要素傳遞與轉化,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形成產業結構升級長效驅動機制。進一步地,產業結構升級可提高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水平,均衡區際產業布局,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共同富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推進共同富裕。
2. 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創業活躍度與共同富裕
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以打造自主創新創業高地為價值旨歸,向各界投資與創業者釋放利好信號,提高創業活躍度,增加社會層面就業機會,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動共同富裕。既有研究指出,創業活躍度能夠通過新創企業成長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進行考察[14]。因此,圍繞新創企業成長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論述創業活躍度在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發揮的中介作用。就新創企業成長而言,受規模較小、起步資金不足、信貸水平偏低等因素掣肘,新創企業成長與發展速度相對較慢。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可加快推進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促使銀行與金融機構快速評估信貸人資信狀況,緩解新創企業融資約束,賦能新創企業成長,激發市場活力,提升城市自身及相關利益群體的收入水平和財富總量,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就社會人群創業傾向而言,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可為創新要素供給與社會創新氛圍提供制度保障,增強創新創業項目孵化力度,優化創新創業生態。值此契機,社會人群創業傾向得以增強,可有效減少低收入群體,提高中高收入群體比重,縮小貧富差距[15],促進共同富裕。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提高創業活躍度,賦能共同富裕。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1. 模型構建
(1) 漸進雙重差分模型
為精準識別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借鑒馬茜等(2022)[16]的思路,將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以政策實施效果評估作為因果檢驗依據。考慮到該政策為分批次多時點批復,構建如下漸進雙重差分模型:
上式中,i 與t 分別為城市與年份;Mit表示共同富裕,分別運用發展性(Develop)與共享性(Share)指代;policyit代表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α1為截距項,Controlsit指代控制變量集合;μi指城市固定效應;δ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即隨機誤差項。
(2) 機制檢驗模型
為深入探究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研究運用Ⅳ-2SLS 法,實證檢驗創業活躍度在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與共同富裕間的傳導機制,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Eait表示創業活躍度,分別通過新創企業成長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度量;λ1反映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于城際創業活躍度的作用;γ1代表創業活躍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其余變量設定同模型(1)。
(3) 空間杜賓雙重差方模型
鑒于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具有較強外部特征,可能對周邊地區共同富裕發揮作用,文章將空間計量模型與雙重差分模型相結合,放寬雙重差分模型中實驗組不會影響控制組樣板的原假設,構建如下模型:
式中,ρ 代表被解釋變量空間滯后系數;β1為創新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區共同富裕的回歸系數;θ1表示創新城市試點政策對鄰近地區共同富裕的估計系數;W 指代反映城市間創業活躍度關系的空間權重矩陣,由后續修正引力模型得出,其余變量設定同式(1)。
2.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 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Cp)
共同富裕的本質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與人類共同進步,確保全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于數據可得性,在深入剖析共同富裕時代特征與內在涵義的基礎上,從發展性(Develop)與共享性(Share)角度出發,構建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為規避多項指標重疊與主觀賦權等問題,運用熵值法對各項指標賦權,最終得出共同富裕發展指數,如表1 所示。

表1 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
(2) 解釋變量: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policy)
采用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虛擬變量表示,若在研究期內某一城市被評選為“創新型城市”,設定policy在評選當年及之后年份的取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
(3) 機制變量:創業活躍度(Ea)
參照林嵩與劉小元(2013)的研究[17],將創業活躍度劃分為新創企業成長(Growth)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Intention)。就新創企業成長而言,使用城市樣本中新創企業固定資產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股利增長率等指標衡量。構建李克特量表,綜合上述衡量指標,分別使用1~5 指代成長速度慢、成長速度較慢、成長速度適中、成長速度快、成長速度較快五個等級,最終得出新創企業成長量表。研究結果顯示,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9,說明量表具有較高信度,取量表評分均值作為新創企業成長觀測值。就社會人群創業傾向而言,設定多維評價體系,運用面板熵權TOPSIS 法綜合評價社會人群創業傾向,如表2 所示。

表2 社會人群創業傾向指標評價體系
(4) 控制變量
為排除其他因素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選取城市特征層面控制變量如下:對外開放水平(Open),使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表示;創新能力(Innovation),運用地區每萬人擁有發明專利授權數量衡量;產業結構(Industry),采用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指代;政府規模(Scale),通過地區公共財政支出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表示;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c),使用5G 基站建設數量衡量。
(5) 數據來源
選取2006—2021年中國284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其中包含103 個創新型城市,181 個非創新型城市。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信息源自《建設創新型城市工作指引》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官網;樣本數據主要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 《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部分缺失數值使用插值法補齊。
四、實證分析
1. 基準回歸分析
為檢驗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作用,使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展開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列(1)、列(2)為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發展性的影響效應;列(3)、列(4)為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共享性的估計結果。數據顯示,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發展性與共享性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假設H1 初步得證。同時,使用多期多個體倍分法對政策實施效果展開進一步論證。由表3 末行數據可知,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仍對共同富裕發展性與共享性產生正向影響,說明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2. 異質性分析
事實上,城市間創新要素稟賦、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差異,可能使得創新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異質性。因此,對上述三者展開深入分析,并構建調節效應模型如下:
上式中,Vit為情境特征變量,包含創新要素稟賦(Factor)、信息產業發展水平(IT industry)。其中,借鑒既有研究經驗,創新要素稟賦使用城市資本存量與年末就業人數乘積的對數值衡量;信息產業發展水平通過信息產業增加值與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值之比表示。
(1) 創新要素稟賦
創新要素稟賦不僅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先決條件,亦是均衡區際創新要素流動與配置的有力抓手。因此,文章將創新要素稟賦納入異質性分析,探究在不同創新要素稟賦條件下,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賦能作用,結果如表4 列(1)、列(2)所示。數據顯示,在創新要素稟賦的調節作用下,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正向影響顯著提升,說明前述推論正確。

表4 異質性分析結果
(2) 信息產業發展水平
受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差異化影響,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可能存在異質性。因此,立足信息產業發展水平,探討其在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存在的異質性特征,如表4 列(3)、列(4)所示。結果表明,信息產業發展水平提升有利于增強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發展性的賦能效應。
3. 穩健性檢驗
一方面,使用傾向評分匹配法,依據控制變量展開樣本匹配,在傾向得分匹配的基礎上,使用模型(1)進行雙重差分估計。另一方面,在引入省域控制變量的基礎上,設置省份固定效應、省份與時間趨勢交互效應,用以緩解結果波動。在經過上述穩健性檢驗后,“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能夠帶動共同富裕”這一結論仍成立。
五、影響機制分析
研究使用雙重差分(DID)與工具變量法(Ⅳ-2SLS)識別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見表5),從而有效規避中介效應模型誤用、忽視機制變量內生性等問題。使用創業者人均流動性資本(iv)作為工具變量。
在表5 列(1)與列(5)中,分別將新創企業成長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作為被解釋變量展開機制分析。列(1)、列(5)結果顯示,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創業活躍度子維度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能夠切實推動創業活躍度的雙重子維度提升。列(2)~列(4)與列(6)~列(8)分別列示新創企業成長與社會人群創業傾向對共同富裕的回歸結果。可知,前述二者均對共同富裕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分析列(2)與列(6)Ⅳ-2SLS 法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可知,Ⅳ-2SLS 法均已通過相關檢驗,且iv 估計系數均與創業活躍度呈顯著正相關,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要求。列(3)、列(4)、列(7)、列(8)結果顯示,創業活躍度可顯著驅動共同富裕,表明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通過創業活躍度促進共同富裕這一傳導路徑成立,即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新創企業成長、社會人群創業傾向→共同富裕傳導機制得以證實,假設H2 成立。

表5 影響機制檢驗結果
六、空間溢出效應檢驗
1. 空間效應分析
選用空間杜賓模型展開空間效應檢驗,同時考慮到空間計量模型中的點估計系數分析結果可能存在偏誤,在模型(4)的基礎上運用偏微分法分解空間效應,結果如表6 所示。數據表明,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本地區共同富裕發揮助力作用,該結論與前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此外,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鄰接地區共同富裕水平同樣存在正向空間溢出作用。也就是說,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正向影響可產生由本地到鄰近地區的外溢效應。

表6 空間效應檢驗結果
2. 區位特征異質性
從地理角度分析,胡煥庸線為適宜人類生存地區分界線,可反映地區人口集聚情況、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引入胡煥庸線將我國分為胡煥庸線以東地區與以西地區,深入分析區位特征異質性,結果如表7 所示。分析表中直接效應數據可知,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影響效應更為顯著。就空間溢出效應而言,胡煥庸線以東地區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鄰近地區共同富裕的賦能效應存在正向空間溢出;胡煥庸線以西地區該驅動效應的空間溢出作用不顯著。

表7 區位特征異質性檢驗結果
七、結論與建議
文章以創業活躍度為切入點,對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與共同富裕間的關系展開探討,得出如下結論: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是共同富裕發展性與共享性提升的重要助力,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在創新要素稟賦、信息產業發展水平較高地區,創新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更強勁;在創業活躍度較高地區,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賦能效應存在正向空間溢出作用。此外,區位特征異質性估計結果顯示,在胡煥庸線以東地區,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共同富裕的帶動效應更顯著。
基于前述結論,提出如下針對性建議:
第一,打造科技創新高地。一方面,健全多元主體創新制度。各級部門應建立健全多元主體創新機制,引入研發機構,設立國家級實驗中心,吸引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加入創新孵化平臺,大力打造創新策源地。同時,階梯式布局“創新項目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科技園區”科技創新發展平臺矩陣,加速推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激發創新活力。有關部門應大力推行項目經費包干制、首席專家組閣制與科技項目攻關揭榜制,打造“鼓勵創新”“包容失敗”社會新風尚,提高創新成果轉化率,放大對共同富裕的賦能效應。
第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一方面,提高數字技術賦能效應。各級政府部門需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速固定寬帶、5G 普及與應用,構建數字公共服務平臺,擴大優質服務資源可及性,推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多元供給。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引導作用,提供公私合營、特許經營、資金補貼、貸款與擔保政策紅利,吸引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參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賦能共同富裕。
第三,因地制宜優化收入分配機制。一方面,胡煥庸線以東地區應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例,調整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通過土地與資本要素收益權與使用權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促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胡煥庸線以西地區地廣人稀,需以土地收益為初次分配有力抓手,健全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擴大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規模,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空間,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為共同富裕提供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