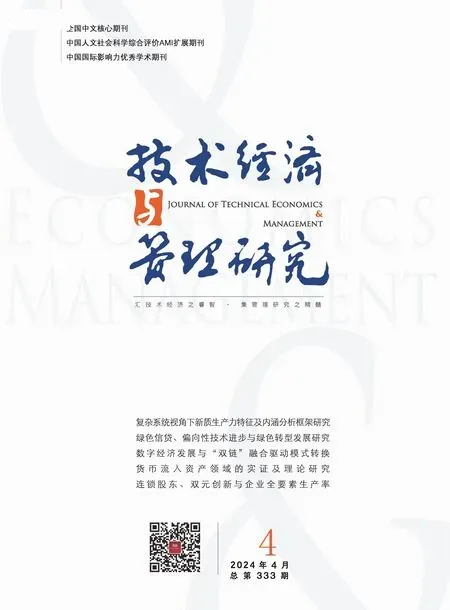都市圈規劃建設的演化邏輯、面臨挑戰及推進方略
張雙悅
(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134)
都市圈作為城市群建設、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抓手,改革開放以來備受黨中央、國務院和政府規劃及學術界的關注。尤其是自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2022) 之后,學術界對于都市圈建設展開了廣泛而又深入的討論。基于此,文章重點從五年規劃的視角對都市圈建設的演化邏輯、面臨的挑戰和推進方略進行探討。
一、都市圈規劃建設的歷史邏輯
雖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篇章,但從政府五年規劃(計劃) 的視角看,可以梳理出城鄉發展及城市建設史。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2)〔下文均簡稱為“xx”規劃(計劃)〕首次提出“特大城市和部分有條件的大城市,要有計劃地建設衛星城鎮。”從都市圈的視角看,這里提及的“建設衛星城鎮”本身就是在為都市圈建設打基礎。也正因為此,早在20 世紀80年代中后期,諸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特大和大城市均有意識地加快了衛星城鎮的建設。在此基礎上,“七五”計劃(1986)提出要依托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經濟區網絡”。若將“城市網絡”理解為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強化城市及城鎮之間的聯系,進而形成“金字塔”式或者扁平化黏性區域的話,那么,這本身也是在為都市圈建設做鋪墊。“八五”計劃(1991)進一步提出“城市發展要堅持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這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要逐步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的歷史淵源和基礎。
繼黨的十四大(1992)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九五”計劃(1996)首次提出“環渤海經濟圈”。無論是經濟區域的建設,還是經濟帶和經濟圈的建設,均有賴于經濟增長極——城鎮及城鎮體系的建設。如果將任何一個都市圈所涉及的城鎮看作是一個小微型“城鎮體系”,那么,關于都市圈建設的思路和架構在此時已經基本形成。
“十五”計劃(2001)中提出“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城鎮密集區有序發展”“依托亞歐大陸橋、長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線及中心城市……促進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長江上游經濟帶和南(寧) 貴(陽) 昆(明) 經濟區”的思想。這里提出的“城鎮密集區”“經濟帶”“經濟區”等概念,無不體現出未來將通過諸多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也正因為此,“十一五”規劃(2006)第一次提出“新城市群”建設。由此可見,“城市群”概念的提出先于“都市圈”概念,同時,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不是目的,旨在依托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經濟帶建設,逐步形成區域協調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框架。
在前述“兩橫兩縱”經濟帶建設的基礎上,“十二五”規劃(2011)提出逐步“構建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以軸線上若干城市群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區和城市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不僅如此,在該規劃中還首次提出要加快“武漢城市圈”建設。這意味著在暫時不具備都市圈、城市群建設條件的地區,特別是中部、西部地區,可以率先加快城市圈建設,待條件成熟時,再向都市圈的方向邁進。之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提出“都市圈”概念,并指出“特大城市要適當疏散經濟功能和其他功能……加強與周邊城鎮基礎設施連接和公共服務共享,推進中心城區功能向一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體發展的都市圈。”
至此可以發現,“兩橫三縱”經濟帶之網絡節點規劃的思路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城市網絡—城鎮體系—城鎮密集區—城市群—城市圈—都市圈—中小型城市。都市圈在其中為承上啟下的核心層次。
二、都市圈規劃建設的現實邏輯
“十三五”規劃(2016)提出“適當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強化與周邊城鎮高效通勤和一體發展,促進形成都市圈”。從而為加快縱橫交錯的經濟帶建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筑牢根基。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9年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不僅對都市圈的內涵、范圍、定位等再一次進行了高度概括,而且對其建設的內容、重點和方向給予了規劃指引。此后的“十四五”規劃(2021)進一步提出“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的新思想。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建設“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其對于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的內蒙古、寧夏、山西、陜西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促進制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 (2021),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2021),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均從產業轉移、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暢通循環、強化市場基礎制度、建設現代流通網絡等視角,為加快現代化都市圈建設提供了指導意見。
綜上所述,都市圈的現代化建設,不僅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承載新發展理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且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
三、都市圈建設面臨的挑戰
1. 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核心城市經濟實力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明顯,輻射帶動能力差
核心城市作為都市圈范圍內的“領頭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經濟實力的強弱,直接決定著產業的聚集和輻射能力,且表現為與周邊城市和國內外的聯系度。由表1 可見,處于西部地區的南寧市和處于中部地區的太原市,其市轄區人均GDP 分別為北京市的39.67%和51.13%;從西部地區的成都市來看,其市轄區人均GDP 也僅為北京市的57.98%;在東北地區,哈爾濱市的市轄區人均GDP 僅僅為長春市的56.78%;在中部地區,太原市的市轄區人均GDP 亦僅僅為合肥市的62.29%;從東部地區內部看,同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區的石家莊市,其市轄區人均GDP 僅為北京市的37.72%。由此可見,東部地區都市圈范圍內的核心城市,其聚集和輻射能力要大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因此,對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而言,其加快都市圈建設的重點任務就是通過產業聚集來壯大核心城市的經濟實力,并輻射帶動周邊城市及地區的發展。

表1 2021年我國29 個都市圈核心城市市轄區GDP 總量及人均GDP
2. 部分城市人口收縮現象明顯,制約了都市圈建設的進程
加快都市圈建設,既需要提升核心城市的經濟實力,也需要中小城市錨定發展,協同發力。但從現實方面看,城市收縮成為制約都市圈建設的短板。以2015年為基期,地區人口統計為基數,將2021年與2015年的數據進行比較后發現:中部地區(40 個)、東北地區(70 個)、東部地區(19 個)、西北地區(36 個)、西南地區(18 個) 城市出現城市收縮現象。其中,東北地區城市收縮現象最為嚴重,西北地區次之,中部地區亦不容忽視(見表2)。在市場經濟和人口城鎮化的條件下,雖然人口的跨城市或區域流動屬于大勢所趨,但核心城市及中小城市在五到十年內如果出現長周期人口收縮,一方面證明其競爭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則更重要的就是不利于都市圈、城市群和經濟帶建設,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表2 全國收縮型城市(含縣級市) 城市數量 (單位:個)
3.都市圈空間布局呈現東密西疏、南強北弱的格局
若將都市圈的發展類型分為成熟期、成長期、發育期、萌芽期四種,并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省份劃分為南方地區,那么南方地區的都市圈為16 個,且多處在成熟期和成長期,北方地區僅有13 個都市圈,且多處在發育期和萌芽期。同時,從人均GDP 方面看(見表1),南寧市市轄區的人均GDP 僅為上海市市轄區的41.98%;即使與中部地區的鄭州市市轄區人均GDP 相比,也僅為其59.65%,差距明顯(見表3)。由此可見,都市圈的空間分布格局總體上呈現出東密西疏、南強北弱的格局。

表3 29 個都市圈空間布局
四、都市圈建設的推進方略
加快都市圈建設,事關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來應通過建立都市圈聯盟機制,依托于城市群、經濟帶建設和鄉村振興規劃和法律,以及省際交界區經濟區建設,尤其應依托于東北全面振興、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等規劃或實施意見,加快都市圈建設。
1. 建立都市圈聯盟,磋商解決一體化進程中的若干重大問題
對于“一小時交通圈”,學術界尚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因為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總是在發生著變化,比如就鐵路而言,最初為普通鐵路,后來伴隨著高鐵、城際、地鐵,及數字經濟、物流、快遞的發展,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城市及區域之間的“時間”概念,拓展了地域的空間。與此同時,都市圈的時空范圍也可能發生變化。因此,應盡快成立都市圈聯盟,共同磋商解決一體化進程中的問題。著重解決城市及城鄉功能定位與功能分區、城鄉融合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分工及融合、產業園區及產業鏈供應鏈建設、市場一體化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數字化都市圈建設、人口的就近城鎮化等重大問題,加快都市圈建設,從而為城市群、經濟區和經濟帶建設鋪平道路。
2. 依托于“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建設規劃,加快都市圈建設
繼“十三五規劃”(2016)明確提出“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之后,“十四五規劃”(2021)再次提出:“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打造遼寧沿海經濟帶”“支持淮河、漢江生態經濟帶上下游合作聯動發展”“以沿海經濟帶為支撐,深化與周邊國家涉海合作”。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十大報告(2022)提出的“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重大戰略,均突出強調了中國將通過“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建設,加快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來,中國都市圈建設重點應該放在長江、隴海蘭新(尤其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珠江—西江和沿海、京哈京廣、包昆三橫三縱的區域,適時加快西部沿邊和北部沿邊經濟帶建設,逐步形成“四橫四縱”、規模不等、層次分明、城鄉融合、布局合理、聯系緊密、協調發展、綠色發展的都市圈新發展格局。
3.依托于省際交界區建設,夯實都市圈建設的基礎
關于省際交界區,學術界亦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標準。但無論是從人口密度,還是從人均GDP 方面考察,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省際交界區經濟區的建設水平均要低于東部地區及全國平均水平(曾冰,2017)。因此,依托于省際交界區城市,加快核心城市建設,逐步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最終形成跨越省際邊界的都市圈。從目前來看,可以考慮先在具有代表性的省際交界區,如蘇浙滬、蘇魯豫皖(淮海經濟區)、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合作區) 等交界區選擇人口規模達到300 萬的城市,進行城市圈或小微型都市圈建設,待取得一定經驗后在其他區域推廣。爭取在“十五五”時期形成跨越省級行政區邊界,特色明顯、帶動能力強的若干城市圈、小微型都市圈和大中型都市圈,從而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及實現高質量發展鋪平道路。
4. 加快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小微型都市圈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對外開放
表3 所列示的29 個都市圈均為大中型都市圈,從其定位看,也可以分別稱其為國際化、全國性和區域性的都市圈。盡管其為經濟帶建設創造了條件,但從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的視角看,尤其是對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而言,其作用發揮還比較有限。因此,“十四五”后期及未來,在做大做強已有都市圈的基礎上,建議這三類地區對于經濟實力排在全國前100 位的城市,先是進行城市圈建設,即以市轄區為核心,“一小時通勤圈”為半徑,與周邊縣城、小城鎮及特色小鎮形成產業融合、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均等、生態共建共享的圈域命運共同體,進而向小微型都市圈方向發展。最終形成城鄉融合、城城包容、圈圈分工、一體化發展、“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及次級經濟帶相互交織的新發展格局。
5. 依托于都市圈建設,加快城鄉融合發展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事關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因此,加快都市圈建設,尤其是在目前實行市管縣和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城鄉融合發展這一現實問題也應引起足夠重視。也正因為此,都市圈建設,絕不是簡單的城、城互動,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生態共保、產業的分工合作和公共服務均等,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依托于中心城區、衛星城鎮、縣城關鎮、特色小鎮建設,加快城鄉一體及一二產業的融合發展。故此,“十四五”后期及未來,建議以大、中、小型都市圈及城市圈建設為核心,持續推進戶籍人口城鎮化,加快城鄉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市場一體化進程,補齊小城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短板;鼓勵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金融機構設立都市圈建設專項基金,支持城鄉融合發展及試驗區建設;“促進城鄉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支持城市資本下鄉,加快農村集貿市場和特色小鎮建設;規劃建設城際、市域(郊) 鐵路,推進中心、城市核心“軌道交通向周邊城鎮合理延伸”(國家發展改革委,2020),實現大中小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縣城、小城鎮和特色小鎮及鄉村之間無縫對接,最終形成都市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及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6. 加快數字經濟建設步伐,助力都市圈建設
加快數字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既是新發展階段實現中國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根本,也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路徑所在,更是都市圈建設的內涵所在。因此,建議在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2021)、中央網信辦等10 部門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 的基礎上,加快制定數字產業及數字經濟都市圈規劃,就數字化基礎設施、云網協同和算網融合發展、數據要素市場體系、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產業化水平、數字化公共服務、產業園區和產業集群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互聯網+政務服務”、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數字城鄉融合發展和數據安全保障水平等作出具體規劃,最終形成數字化都市圈,為城鄉融合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