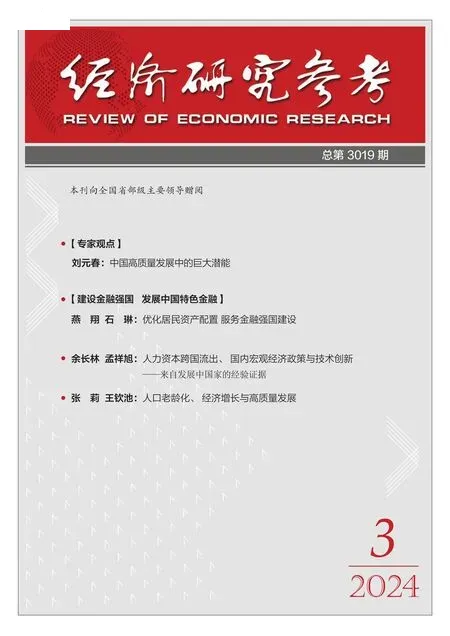優化居民資產配置 服務金融強國建設
燕 翔 石 琳
2024年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居民部門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民財富的重要持有方,其資產結構的特征深刻影響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優化居民資產配置對于金融體系高效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和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尤其是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等的構建,為居民資產的增值和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本文從金融體系中的居民部門出發,研究如何通過優化居民資產配置,促進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服務金融強國建設。
一、優化居民資產配置對建設金融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在金融強國的政策指導下,近年來有關居民資產配置的討論逐漸增多。首先,從增長模式看,中國經濟正逐步從傳統的金融地產驅動向新質生產力驅動的新發展模式轉變。映射到居民資產端,現階段中國居民資產配置仍以房地產為主(李鳳等,2016;Lu et al.,2020),后地產時代其結構如何演進、哪些資產會逐步取代房地產地位,受到各界普遍關注。其次,從國際經驗看,居民消費不僅是收入的函數,同樣受資產端的財富效應影響。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收入相對資產的比重大概率下降,而金融資產的比例隨之提升,從而為居民部門創造新的財富來源,并直接刺激需求(Poterba,2000;Di Maggio et al.,2020)。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目前中國居民消費仍然取決于收入,資產多元化程度和風險資產占比偏低,使資產的財富效應相對不突出(張屹山等,2015)。最后,從共同富裕視角看,由于資本的回報率超過勞動回報率,使財富層面的不平等遠超過收入層面不平等(Piketty,2014;遲巍和蔡許許,2012),如何在繼續做大居民資產蛋糕的同時推動分配合理化,是共同富裕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因而居民資產的增值及合理分配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結合政策脈絡和已有文獻看,優化居民資產配置對于服務金融強國建設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發揮財富效應刺激內需、防范金融風險三個方面。
(一)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近年來,國家對居民資產配置較為關注,相關政策主要體現在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提到,健全各類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并提出推動資本市場規范健康發展。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增加居民投資收益。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
就理論意義而言,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讓居民通過土地、資本等各類要素及房地產、金融等各類市場獲取收益,為居民收入創造新的來源。當前,中國居民資產中房地產占比處于世界較高水平,但對金融資產尤其是權益型資產的配置比重較低。而與房地產相比,金融市場的普惠性更強,后續有望成為居民資產增值的主要來源。
(二)更好發揮財富效應,助力居民消費
居民資產的財富效應是經濟學界經久不衰的議題,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的生命周期理論(Ando &Modigliani,1963)。而20世紀90年代歐美股票市場持續上漲,帶動居民消費明顯提升,再度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從已有文獻看,大部分研究均發現居民資產與消費存在正向和顯著的長期關系(Ludvigson &Steindel,1999;Poterba,2000;Fernandez-Corugedo et al.,2003)。而從理論機制上,居民資產主要通過直接財富效應、共同因果關系和抵押渠道三方面作用到消費(Paiella,2009)。其中,直接財富效應是指資產價格上漲增加家庭財富,通過放松預算約束來增加消費;共同因果關系是指資產和消費增加是由共同的宏觀經濟因素驅動,如若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看好,則資產價格和當前消費均可能受益;抵押渠道主要體現在房地產等實物資產,其可以作為抵押品,放松(或收緊)信貸約束來影響消費。
國內學者同樣對資產與消費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部分研究認為居民資產對消費存在明顯的直接財富和抵押作用(南永清等,2020),但也有觀點認為與收入相比,房地產、金融資產等對消費的影響相對有限(萬曉莉等,2017;李濤和陳斌開,2014;張屹山等,2015)。總體上看,中國居民資產對消費具有一定的財富作用,但相對歐美而言并不突出,一方面源于金融資產中無風險資產比重較高、財富效應發揮有限,另一方面總資產中房地產占比偏高,房地產在帶來財富效應的同時,對消費等同樣存在擠出效應。
(三)提升多元化配置比例,防范金融風險
當前中國居民資產結構單一化問題較為突出,體現在房地產占比較高,金融資產中現金及存款等無風險資產占比偏高。房地產占比偏高,使居民資產受房地產市場影響較大,房價漲跌直接關系萬億老百姓的“錢袋子”。由于房地產天然金融屬性,其在發展過程中也帶來了居民的高杠桿問題(王靜,2023),且對居民消費存在一定擠出效應(孟憲春和張屹山,2021)。金融資產中無風險資產占比較高,雖然使居民對金融資產的敞口波動率較小,但偏保守的配置同樣也犧牲了多元化資產配置帶來的收益率提升。因此,推動居民資產配置優化,提高金融資產等其他類型資產比例,可以從微觀層面增強家庭資產的穩定性,宏觀層面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周弘等,2018)。
二、中國居民資產配置的主要特征與發展趨勢
與歐美相比,國內對居民資產負債表的統計相對不完善,現有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宏觀數據出發構建居民資產負債表,如中國人民銀行編制的2004~2010年資產負債表,社科院編制的2000~2019年居民資產負債表(李揚等,2020),許偉和傅雄廣(2022)編制的1978~2019年居民資產負債表等;另一類研究運用家庭微觀調查數據進行測算,如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的《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Lu等(2020)等運用CHFS數據得到中國居民資產情況,并與歐洲、美國的微觀調查數據結果進行國際比較。其中社科院的核算數據在市場研究中被廣泛運用,因此本文采用社科院口徑數據,并借鑒其方法將測算更新至2023年。(1)社科院并未披露部分細項的核算方法,因此本文更新的測算結果可能存在一定誤差,但不影響文章主要結論。
根據社科院的口徑,居民資產由非金融資產(固定資產)和金融資產組成,非金融資產包括住房資產(城鎮住房、農村住房)、汽車資產、農村居民生產性固定資產,金融資產包括通貨(現金)、存款、保險準備金、證券投資基金份額、股票及股權、債券、貸款共計7項。通過分析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居民資產配置主要呈現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居民資產增速總體跑贏GDP和收入增速
如圖1所示,2001~2023年,居民資產快速增長,其增速顯著跑贏GDP名義增速和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增速。2001~2023年居民總資產、名義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復合增速分別為14.2%、11.6%、11.3%,居民財富的積累速度超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居民資產也由2000年底的約32萬億元增加至2023年的近700萬億元,與GDP的相對比重由3.2提升至5.4。(2)正文中2001~2019年的居民資產相關數據來自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2020~2023年數據為作者參考社科院方法手動更新,下文如無特殊說明均同。與此同時,居民資產增速呈現出典型的順經濟周期特征,2013年經濟增速放緩后,居民資產增速同樣下滑,而2022年以來受新冠疫情疤痕效應影響疊加房地產、股票市場低迷,居民資產增速明顯跑輸名義GDP增速,但整體仍然實現正增長。究其原因,居民資產端的三大敞口——房地產、股票及股權、現金及存款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其中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直接受到經濟和金融周期作用,而現金及存款很大程度來源于居民收入增長。

圖1 2001~2023年中國居民總資產、名義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情況資料來源:居民總資產數據來自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GDP名義增速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可支配收入增速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其中2001~2021年的數據采用住戶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增速,2022~2023年的數據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近似替代。
如圖2所示,金融資產增速領先非金融資產,2001~2023年基金、保險、股票復合增速位居各類資產前三。2001~2023年,按資產規模復合增長率計算,金融資產增速(16.0%)領先居民總資產增速(14.2%)和住房資產增速(12.3%),其中金融資產中基金增速(29.5%)、保險增速(21.7%)、股票及股權增速(17.1%)位列各類資產前三,反映近20年來金融市場快速增長,金融深化明顯提升。以股票和基金市場為例,A股總市值由2001年的4.4萬億元提升至2023年的77.8萬億元、復合增速14%,證券投資基金總凈值由2001年的818億元提升至2023年的27.27萬億元、復合增速30%,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資產受居民認可度和觸及度大幅提升,而通貨(9.5%)、債券(4.4%)增速排名靠后,反映居民風險偏好有所提升。

圖2 2001~2023年中國居民各類資產復合增速資料來源: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及作者自行測算。
(二)房地產仍然是最重要資產
從居民資產結構看,如表1所示,房地產比例占居民資產比重邊際下滑但仍是居民部門最重要資產,金融資產占居民資產比重邊際提升。2000~2023年,非金融資產(固定資產)占比從56.9%下降至39.1%,金融資產占比從43.1%提升至60.9%。其中,非金融資產主要為房地產,即使到2023年占總資產比重降至35.3%,也仍然是居民資產最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他口徑下房地產占比更高,如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城鎮住戶調查中住房資產占比為59.1%,(3)央行調查:10%家庭資產占比近半 少數家庭資不抵債[EB/OL].人民網,2020-04-25.Lu等(2020)運用2017年CHFS微觀調查測算的結果為73.5%。但無論是何種口徑,房地產是居民資產中最重要組成部分是不爭的事實,且明顯高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固定資產中汽車占總資產比重由2000年的1.8%提升至2023年的3.2%,主要源于國內汽車保有量大幅提升,由2004年的2742萬輛增長至2023年的3.36億輛。而從對居民總資產的貢獻度視角看,2000~2023年居民總資產增長中,房地產貢獻度排名第一(34.5%),排名第二的為現金及存款(27.1%),股票及股權位居第三(25.7%),同樣說明房地產在居民資產中發揮關鍵作用。

表1 中國居民部門資產結構拆分 單位:%
居民房地產占比較高,源于實際需求和財富效應的共同推動。一方面,21世紀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帶動居民住房需求大幅提升。2000~2020年中國城鎮人口從4.6億人增加至9億人,商品房銷售面積從2000年的1.7億平方米提升至2021年的峰值18億平萬米附近。(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另一方面,房價的持續上行使其作為資產的超額收益大幅提升,2005~2023年一線城市房地產年化收益率為10.6%,甚至高于同期滬深300收益(8.8%)。但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以來隨著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房地產銷售額和房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跌,使居民房產財富受到沖擊。截至2023年底,居民房產價值相較2021年底下降7.9%,而同期總資產仍然增長1.4%,居民房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也由2020年的45%降至39.1%,是居民資產最主要拖累項。(5)資料來源:人口和商品房銷售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收益率數據來自Wind。
(三)金融資產以無風險資產為主
從金融資產內部視角看,無風險資產占金融資產比重仍然偏高,反映出居民風險偏好較低。2000~2023年,現金及存款占金融資產比重由57%降至44%,股票及股權、基金、保險準備金相應占比分別從33%、0.7%、1.5%提升至41.3%、8.9%、4.6%,反映出隨著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有所提升,明顯增加對含權類產品配置。但總體看,現金存款等無風險資產占比仍然偏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的調查口徑,城鎮居民資產負債表中,無風險金融資產占金融資產比重達53.9%,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持有率(99.6%)也顯著高于風險金融資產(59.6%)。若按照本文沿用的社科院口徑,截至2023年股票及股權占金融資產比重為41.3%,已經處于相對較高水平,但股票及股權中超70%為未上市公司股權,流動性較弱,與歐美相比上市公司股票占比仍然偏低。以美國為例,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股票類資產占居民總資產比重高達25%,與房地產相當。(6)資料來源:美聯儲官網。
與全球相比,中國居民儲蓄率偏高、資產多元化相對欠缺。由于資產負債表的橫向對比可能受統計口徑影響,我們可以從儲蓄率指標切入進行研究。如圖3所示,截至2022年底,根據世界銀行的口徑,中國儲蓄率(總儲蓄占GDP比重)為46%,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和日本(28.7%)、歐盟(25.0%)、美國(18.1%),在與中國人均GDP接近的國家中也遙遙領先。儲蓄率偏高,背后映射出中國居民資產多元化比重較低,一方面與投資者教育、金融素養培訓等相對缺位有關,另一方面在社保水平相對偏低的情況下居民預防式儲蓄動機較強,而股票市場波動率過大、財富效應偏差也是居民對風險資產配置不足的重要原因。

圖3 全球各國儲蓄率對比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新冠疫情以來居民風險偏好更趨保守,無風險資產占比明顯提升。尤其是2021年以來,居民現金及存款配置明顯提升。2020~2023年,居民資產中現金及存款占金融資產比重由38%提升至44%,而2000~2019年其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相應地,股票及股權占金融資產比重由46%降至41%。居民風險偏好趨于保守、大幅增加儲蓄的背后,一方面源于新冠疫情以來居民收入增速邊際下滑、對未來收入預期不確定性增加,預防式儲蓄需求提升;另一方面源于2021年以來房地產、股票資產均經歷明顯下跌,風險資產的財富效應偏差,使居民大量增加無風險資產配置。以中國人民銀行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為例,截至2022年底,儲戶中選擇“更多儲蓄”占比上升至61.8%,2023年以來隨著經濟溫和修復而邊際下滑,但整體處于歷史偏高位置,居民風險偏好仍有待回升。
三、他山之石:海外居民資產配置的經驗
從國際視野看,發達經濟體在居民資產配置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值得國內審視,其中美國、瑞典、日本的案例較為典型。美國作為全球金融最發達市場,居民對權益資產配置全球領先;瑞典作為北歐國家的代表,儲蓄率在歐洲處于極低水平但股票投資比例在歐洲領先;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居民資產配置轉向保守,房地產占比逐步下降但儲蓄存款比重提升,但2013年后隨著日本經濟和日股復蘇,權益資產配置比例邊際提升。
(一)美國:權益資產配置全球領先
美國作為全球金融最發達的市場,居民對金融資產尤其是權益類資產的配置比重在全球領先。根據美聯儲的居民資產負債表數據,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金融資產、非金融資產占居民總資產比重分別為65.6%、34.4%,其中房地產占比由1970年的20%波動提升至2023年的27%,股票占比從16%提升至25%,儲蓄占比則由12%降至10%。如圖4所示,與歐洲、日本橫向對比看,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美國、歐洲、日本金融資產比重分別為39.4%、21.0%、11.0%,現金存款比重分別為12.6%、35.5%、54.2%,美國居民權益配置比重大幅領先歐洲和日本。根據美聯儲的數據,從各類資產的增長情況看,1970~2023年按資產規模復合增速排名為股票(8.3%)>債券(7.9%)>房地產(7.8%)>儲蓄(6.9%)>耐用消費品(6.4%)>非公司型企業權益(6.3%)>養老金(6.2%)。股票和債券類資產增速領跑,其中股票對居民資產增值貢獻(25.4%)僅次于房地產(26.8%)。

圖4 歐洲、美國、日本居民金融資產結構拆分資料來源:日本銀行。
美股較好的財富效應疊加養老金大規模入市,使美國居民對金融資產尤其是權益類資產的配置在全球領先。1972~2023年,以標普500全收益衡量的美股取得10.7%的年化收益率,(7)資料來源:Global Financial Data。領先黃金、美債、大宗商品及其他主要經濟體股票,且在風險收益比上優于美歐及新興市場,從而給居民帶來了良好的財富效應。而美股的發展,源于企業盈利、估值抬升和股息紅利回購的共同貢獻,其中企業盈利是關鍵。1988~2019年,標普500全收益指數年化收益率為10.6%,其中企業盈利增長、股息紅利回購、估值抬升貢獻分別為7.2%、2.5%、1.0%。(8)資料來源:Bloomberg。另外,20世紀70年代以來養老金計劃的推出,使美國居民間接參與股市比例大幅提升,也為美股提供了可觀的增量資金。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陸續推出第三支柱養老金賬號,并對給付確定制(defined benefit,DB)、繳費確定制(defined contribution,DC)等養老金計劃提供稅收遞延和優惠政策,帶動養老金規模大幅擴張。根據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CI)統計,截至2022年底,美國養老金規模(三支柱合計)超37萬億美元,占金融資產的比重近三成。在資產配置上,美國養老金中權益類投向占比近四成,成為居民參與股市的又一重要渠道,同時為美股提供了大量中長期資金。
(二)瑞典:福利國家+養老金入市,權益比例歐洲領先
瑞典作為北歐國家代表,較低儲蓄率及較高的權益配置比重,是其居民資產配置最重要特征,權益配置比例在歐洲領先。金融資產結構上,根據歐洲基金和資產管理協會(EFAMA)的數據,如圖5所示,截至2019年底,瑞典儲蓄占金融資產比重為19.4%,僅高于丹麥(18.9%)和荷蘭(17.9%),在歐洲處于偏低水平;相應地,股票占居民金融資產比重為11.0%,僅低于芬蘭(19.5%),在歐洲處于領先水平。如果按居民總資產口徑核算,參考Kozina等(2021)的研究,2015~2018年瑞典房地產(土地和房屋合計)占總資產比重為43.3%,現金及存款占比為11.1%,均顯著低于歐洲平均水平(63.8%、16.4%),而股票及基金、保險及養老金占比分別為37.7%、30.0%,同期歐洲平均水平分別為15.2%、16.9%,金融資產尤其是含權類產品配置比例大幅領先。

圖5 2019年瑞典儲蓄和股票占居民金融資產比重資料來源:EFAMA。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了瑞典居民預防式儲蓄動機,有更多激勵投入風險資產配置。在自然資源稟賦豐裕、居民人均財富可觀的基礎上,瑞典很早就進行福利國家建設,1938年瑞典國內簽署“薩爾茨約巴登協議”,就勞動雙方的初次分配進行協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其建設福利國家進程加快,主要體現為高稅收+高福利的政策組合。稅收層面,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稅收負擔普遍較重,除個人所得稅累進且稅率較高外,在資本利得稅、公司稅、遺產稅、房產稅等方面力度同樣較強。而在福利層面,瑞典在全民醫保、義務教育、失業福利等領域均對普通群眾實行較大力度的補貼。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瑞典社保支出(不含醫療)占GDP比重為19.5%,處于世界范圍內偏高水平。完善的社保體系下,北歐國家預防式儲蓄的需求相對較小、儲蓄占比偏低,瑞典同樣也不例外。
建立起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金制度,并大規模投資權益市場,為居民間接參與權益投資提供渠道。1913年瑞典就已建立養老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相繼推出基本養老金(FP)和補充養老金制度(ATP),覆蓋全體居民。1998年為解決養老金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瑞典開始對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形成以保障養老金、名義賬戶制養老金、實賬累計制養老金為主的多支柱體系,其中名義賬戶制養老金由四大國民養老基金管理(AP1-AP4),投資范圍包括權益、固收、私募股權、另類資產在內較為廣泛的各類資產,實賬累計制由瑞典養老金管理局統一管理并提供多種投資組合供居民選擇。截至2020年,名義賬戶制下的四大國民養老基金投資權益占比在40%以上,且大部分投資于海外市場、分散化布局,取得了年化7%以上的收益率。(9)資料來源:AP1-AP4年報。養老金制度的完善及大規模入市取得的良好收益,使養老金成為瑞典居民間接參與股票市場的重要工具。歐洲基金和資產管理協會(EFAMA)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養老金占瑞典居民金融資產比重為43.6%,遠高于歐洲國家平均比重(25.7%)。
(三)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居民資產配置偏保守
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房地產占居民資產配置大幅下降,但現金和存款比例大幅提升,居民資產配置較為保守。1994~2022年,日本金融資產占比從44.2%提升至62.7%,相應地非金融資產占比從55.8%降至37.3%。(10)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官網。其中,達到非金融資產比例大幅下滑,主要源于房地產占比的明顯收縮。1991年日本樓市正式見頂回落,開始將近20年的下行周期。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東京房價指數在1990年10月達到248.3的歷史高點,到2009年4月降至92.6,降幅達63%,2013年后伴隨日本經濟回暖、房地產市場邊際回暖,但仍遠未達到1990年的巔峰水平。如圖6所示,體現在居民資產上,房地產占比從1994年的53%降至2022年的34%。與之相對應,金融資產的大幅提升主要源于現金及存款的貢獻,其占總資產比重從21.7%上升至34.5%,成為居民資產中最重要構成。股權及投資基金比重在2012年之前變化較小,圍繞6%波動。總體看,日本在后地產時代居民資產配置偏保守,主要源于日本經濟在1990~2012年陷入“失去的二十年”,需求不足導致經濟長期處于通縮區間,GDP實際增速由泡沫經濟期間的4.9%降至2000~2012年的0.8%。日股同樣表現低迷,1990~2012年復合收益為-4%,而同期美股年化收益為8.6%。(11)資料來源:GDP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日美股數據來自Wind。

圖6 日本居民部門資產結構拆分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官網;原始數據未公布居民房地產資產數據,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按比例折合成住房資產,再加上土地資產近似得到房地產資產。
2013年以來日本經濟邊際回暖,帶動居民風險偏好和權益資產配置比例提升。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臺后,推行“安倍經濟學”政策,包括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被稱為“三支箭”,希望通過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匯率貶值,帶動日本經濟回升擺脫通貨緊縮。盡管政策成本存在爭議,但從結果看確實帶動了日本經濟溫和復蘇。從實際增速看,2013年開始日本實際GDP增速多數時候運行在潛在GDP增速以上。對于日股而言,2013年后經歷了持續回升的過程,Wind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2月下旬,日經225較2013年初累計上漲276%,且突破1989年底的歷史高點。受益于宏觀經濟轉暖和股市財富效應提升,日本居民風險偏好回升,股權及投資基金占金融資產比重從2012年的6.3%提升至9.1%。但總體看,日本居民權益資產配比較歐美仍然偏低。為此,日本政府于2024年1月將2014年實行的小額投資免稅制度(NISA)轉型為新NISA,新規定取消了對NISA免稅持有期限的限制,并大幅提升投資限額,投資類型也由限定為投資信托擴展為股票及股票類投資信托。新NISA制度建立,有望加速居民金融資產從儲蓄向股市流入,為日股提供可觀的增量資金。
四、政策建議
(一)推動長期資金入市,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
A股財富效應偏差是國內居民股票投資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而缺乏長期資金扮演著關鍵角色。從復合收益率看,國內A股復合收益率與美股接近。Wind數據顯示,2005~2023年,滬深300全收益和標普500總回報的復合收益率接近(9%)。但與美股投資者相比,A股投資者投資體驗不佳、財富效應較差,使金融資產尤其是股票類資產在居民資產中占比偏低。究其原因,A股波動率相對較大,一方面與上市公司重融資輕分紅和回購有關,另一方面源于A股市場仍以個人投資者為主,機構投資者尤其是長期資金相對欠缺。未來,權益類資產要想在居民資產增值中扮演更重要角色,長期資金入市是關鍵。
從全球經驗看,長期資金入市對于熨平市場波動、增厚市場收益發揮關鍵作用,同時也能間接提升居民入市比例。2004年以來,中國養老金、保險公司、社保基金等長線資金規模穩步上升,但橫向對比看依然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以養老金為例,根據OECD數據,截至2022年底國內養老金資產規模為4097億美元,占GDP比重為2.3%,遠遠低于美國(98.3%)、英國(117.0%)、日本(31.3%)。從各類長期資金對A股配置看,目前中國中長期資金持股占比不足6%,持股比例偏低。截至2021年底,美國、日本、英國養老金資產配置中權益資產占比分別為36.4%、9.3%、29.0%(OECD口徑),而瑞典養老金權益配置比例更是超過40%。與成熟市場相比,國內長期資金仍有較大發展空間。2023年8月底,證監會召開機構投資者座談會,提出養老金、保險資金等各類中長期資金與資本市場互相促進、協同發展。2024年3月6日,證監會主席吳清在兩會答記者問中明確提到,市場上長錢短錢都是需要的,但是更缺的是長錢,同樣缺的是長期主義,也需要堅持價值投資、理性投資、長期投資的理念。未來,養老金、保險資金等中長期資金加快發展權益投資正當其時,或將迎來政策層面的持續催化,后續進展值得期待。
(二)做好普惠金融,豐富居民金融產品選擇
推動居民資產配置優化,尤其是從房地產和儲蓄存款向權益資產轉移,需要做好普惠金融工作,豐富居民金融產品選擇,并提升居民金融素養。
普惠金融在金融資產的供給上體現為豐富居民金融產品選擇,加快發展個人養老金、企業年金,并提供多元化的基金和保險產品。現階段,在政策支持和數字化金融的推動下,國內貸款端的普惠性推動較快,普惠貸款、小微貸款覆蓋度較廣,但資產端的普惠性和可得性仍有待加強。后續證券、基金、保險等各類型金融機構應當根據居民的收入層次、年齡結構、投資目標、風險偏好等特征,提供個性化、專業化的投資產品及組合。另外,養老金作為發達經濟體居民資產配置的重要途徑,在國內發展仍相對滯后,體現為第一支柱一家獨大,第二、第三支柱剛剛起步的特征。后續在政策層面需加強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等第二、第三支柱發展,并推動其在投資結構上增加權益類資產配置,間接提升居民參與權益市場比重。
對于金融的需求方——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同樣需要提升居民金融素養,推動居民資產配置的優化。從理論角度看,居民金融素養越高,對風險資產的認可度及配置比例通常越高,在長周期內能夠獲取更優的預期回報率、更低的風險(Lusardi &Mitchell,2007)。從實踐中看,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2021)》可知,全球范圍內,中國消費者在金融素養上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金融市場尤其是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在金融基礎知識尤其是投資分散化、風險收益關系的理解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對于股票等風險資產的參與度和理解能力相對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居民多元化配置資產的意愿。后續金融監管機構和從業機構應當繼續做好投資者教育工作,尤其是充分發揮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券商主體、公司國家級投資者教育基地作用,為投資者普及金融知識、宣傳正確的投資理念,培育更多的合格投資者,使其在更廣泛地理解參與金融市場的同時,能夠自主判斷投資價值,作出相對理性的投資判斷和決策。
(三)穩住房地產市場預期
盡管從長期來看,中國居民資產從以房地產為主的實物資產向金融資產轉向是大勢所趨,但短期看房地產在居民財富中的地位仍較難取代。而國內房地產市場自2021年以來持續處于深度調整中,全面回暖尚需時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由2021年的近18億平方米降至11億平方米出頭,房地產投資累計下降近25%,而70座城市二手房價指數自2022年以來已有接近兩年時間持續處于負增長區間。
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對居民資產帶來直接和間接的負向沖擊。首先,作為居民資產單一資產中占比最高的類別,房價持續下行直接帶來房地產財富的縮水,對居民總資產影響較大。其次,房地產是中國經濟擴信用的重要抓手,房地產上下游對GDP帶動接近二成,其持續下行對應內需修復缺乏抓手,對宏觀經濟帶來持續負向沖擊,一方面使居民收入增速下滑,另一方面也影響到居民的風險偏好。作為對比,2008年美國房地產的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全面的金融危機,居民房產和權益類金融資產大幅縮水。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果斷采取干預措施,一方面通過降低利率、延長貸款期限、提供再融資等形式救助購房家庭和房企;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刺激需求,最終使房地產和美國經濟在2009年走出衰退,進入復蘇周期。
現階段,國家已積極出臺多項房地產刺激政策,傳導至居民購房信心提振、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仍需時間,目前需耐心等待。2022年開始多項房地產刺激政策陸續出臺,包括“金融16條”、保交樓專項借款等供給側政策,以及調整首付比、按揭貸款利率、認房不認貸等需求側政策。2024年2月,國內貨幣政策啟動非對稱式降息,5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下調25基點至3.95%,遠超市場預期,有助于減輕居民購房的資金壓力,助力房地產需求穩定。未來,房地產領域或將持續迎來政策支持,隨著前期政策持續見效和居民購房信心邊際回暖,房地產市場有望企穩,對居民資產端的拖累有望收窄,但仍需密切觀察。
(四)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推動居民風險偏好提升
理論層面而言,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居民風險承受能力的提升,降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更有能力和意愿降低儲蓄、增加對風險資產的配置,國內外諸多實證研究均對此進行了論證(De Freitas &Martins,2014;Gormley et al.,2010;宗慶慶等,2015)。
與國際水平相比,中國居民更加偏好無風險資產、儲蓄率較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保障覆蓋度仍相對有限,難以有效對沖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居民預防式儲蓄需求較大。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截至2020年,中國社保支出(不含醫療)占GDP比重為7.2%,在有數據統計的185個經濟體中排名第66,明顯低于美國(18.9%)、日本(16.1%)、德國(19.4%)等發達經濟體。而新冠疫情以來居民資產端受到明顯沖擊,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不穩定,在資產配置上表現為增加無風險資產配置比例、降低房地產和權益類資產配置比例,總體更偏保守。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2023年居民部門新增存款分別為26.3萬億元、25.7萬億元,較2021年的19.7萬億元大幅提升。未來,居民風險偏好的回升,一方面有賴于宏觀經濟的修復,另一方面則需要政府部門加大財政支出力度,提升教育、醫療、養老等多項民生領域的社保覆蓋度。
——金融資產轉移
——基于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