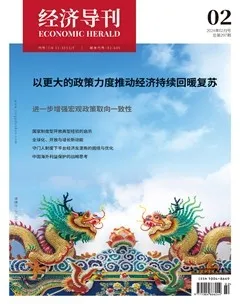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推動經濟持續回暖復蘇
楊凱生
我國經濟復蘇的路徑分析
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在供需兩端接連遭受疫情、全球供應鏈調整、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沖擊,經濟發展面臨較大壓力。2022年底解除疫情封控措施以后,我國疫后經濟復蘇體感“偏冷”,2023年全年實現5.2%的GDP增速,兩年GDP平均增速僅達到4.1%;通貨膨脹率為0.2%,遠低于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5%的目標。
當前經濟復蘇體感“偏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疫后恢復供給端領先于需求端。一方面,我國在需求端面臨更大沖擊。除了疫情之外,全球供應鏈調整對我國外需產生明顯沖擊,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對我國投資需求也帶來收縮效應,房地產和股市價格的下跌通過財富效應影響了居民消費。另一方面,我國供給端的恢復速度更快。工業部門復蘇跡象明顯,2023年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創下自3月份以來的新高,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1%;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5%,延續自3月份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復合同比增速僅為3.4%;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僅為3%,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速-9.6%;出口同比增速為-4.6%(美元計價)。
在供給恢復快于需求恢復的情況下,會導致價格下降、產出降低。此時,由于供給相對于需求存在過剩,如果需求遲遲不能恢復,經濟將內生地發生去產能調整,并導致預期的持續轉弱,進一步遲滯需求的恢復并加速去產能,從而影響供給的恢復。
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疫后經濟恢復需求端領先于供給端,使美國經濟體感“偏熱”。需求端,自疫情以來,美國居民收入增速是上升的,股市表現也較為強勁,居民消費能力沒有受到明顯沖擊,帶動疫后需求快速恢復。供給端,美國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及供應鏈調整的影響較大,國內勞動力市場也持續處于緊平衡,明顯推高了供給成本。美國在需求恢復快于供給恢復的情況下,價格上升,產出降低。此時,由于需求相對過剩,經濟產生內生性擴產能趨勢,推動經濟進一步趨向均衡。
需進一步加大政策組合力度
面對當前經濟增速放緩、通脹偏低、體感“偏冷”等情況,在統籌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的平衡時,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尤為重要。在需求恢復相對滯后的情況下,及時通過擴張性政策拉動需求,鞏固疫后供給恢復成果,要避免由于短期信心不足演變成長期的增長潛力下降,導致長期平衡增長路徑的改變。
我國宏觀政策組合與面臨的難點
2023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總體對貨幣主導寄予了更大希望。2023年,我國降準兩次,累計釋放流動性超1萬億元;降息兩次,公開市場7天期逆回購利率和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比2023年初分別下降20BP、25BP。受制于地方債務風險加大和收支矛盾的加劇,財政進一步擴大支出的難度加大。2023年,政府一般公共支出與政府性基金支出總和同比上升1.3%,兩年平均同比增速為2.2%,遠低于疫情前3年12.1%的平均增速。2023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增速保持27%的較高水平,但其中新增債券占比僅為50%,且同比增速為-2.7%,地方政府到期債務依靠借新債還舊債償還的比重達到90%。
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重大難點是貨幣政策傳導受阻,經濟已接近“流動性陷阱”區域。“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指的是貨幣(流動性)需求彈性無窮大的一種狀態,此時無論增加多少流動性都會積淀起來,從而使得貨幣政策失效。具體來看,一是我國M2增速較快但流動性卻顯現趨緊跡象。2023年,我國M2增速9.7%,這個速度不低。2023年我國銀行業借差增量明顯上升;自8月份以來,銀行間市場存款類機構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持續位于政策利率上方運行,與其相比,非銀行機構流動性更加緊張,銀行間市場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偏高。二是長端利率的下行沒有刺激投資的擴大,貨幣擴張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的效率較低。2023年,長期貸款利率是下行的,但長端利率的下降沒有提升企業和居民的中長期貸款需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處于低位,202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僅為3%,為近20年來的次低,僅高于2020年的2.7%。
適當的政策組合十分重要
現階段通過財政政策加力拉動經濟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其一,由于受到收入的約束,消費在短時間內難以彌補外需和投資造成的需求缺口。從短期看,自疫情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速趨緩,難以支撐消費快速擴大。從長期看,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尚不足1.2萬美元,收入的增長仍需要通過投資的擴大拉動。其二,從消費結構看,商品消費占比較高但增長空間有限,服務消費刺激短期內還難以明顯見效。我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含餐飲)占GDP的比重達36.5%,而美國為31%;服務消費中,商業服務、房地產和批發零售三項之和與美國的差距占中美GDP差距的95%。房地產風險正是本次需求端受到沖擊的重要因素之一,房地產消費的刺激在居民預期未扭轉的情況下恐難明顯見效;商業服務、批發零售等領域消費的擴大需要培育相關的服務模式,短期的需求刺激政策難以快速見效。其三,在消費難以快速擴大彌補需求缺口的情況下,投資增長趨緩會進一步抑制居民消費。企業降低投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進一步影響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企業業績表現下滑也對股票價格造成負面影響,進一步影響居民財產性收入。
在通過財政政策擴張拉動經濟的同時,也需要關注財政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一是政府支出的擴大可能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要避免簡單地將居民消費轉化為政府消費。二是政府投資可能對企業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政府投資的擴大有可能提高經濟的均衡利率,從而對企業投資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部分抵消政府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政策組合建議
當前拉動經濟復蘇回暖的政策組合,應以“財政促‘進、貨幣維‘穩”。財政政策發揮拉動需求回暖的箭頭作用。一是總量上仍然要擴大力度。在投資、消費、外需面臨沖擊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必須要有足夠的力度才能彌補需求缺口,并緩解預期持續走弱趨勢。建議2024年財政赤字率保持3.5%左右水平。二是結構上要注重區域平衡和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結構上要避免“弱者更弱”,積極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提高仍有較大投資缺口地區的投資能力。產業結構上要兼顧政策傳導效率和經濟結構轉型。一方面要抓住產業鏈條長、吸納就業多的產業作為當前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提高財政支出擴大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效率;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財政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要通過財政支出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的長期潛力。三是發揮財政政策的撬動作用,更好放大財政乘數效應。財政支出應著眼于撬動其他資本,要善于算“大賬”,通過優化風險和收益分配機制,帶動社會資本更多地參與投資,既提高了投資規模,也有利于提高財政項目投資效率。四是財稅體制改革的優化調整。要加快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制度,簡化稅率結構、優化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和健全消費稅、財產稅,更好引導消費結構優化、帶動消費總量擴大。
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擴張,助力對沖財政擴張的擠出效應、清理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一是配合財政政策的擴張,適度對沖財政擴張帶來的利率上升導致的擠出效應。一方面,配合財政支出擴張,將利率控制在合理水平,避免在企業和居民長期預期未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由于利率上升進一步壓制企業和居民的內生性投資需求;另一方面,運用直達式等“準財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配合,優化和積極支持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提高財政政策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傳導效率。二是進一步優化對地方債務的清理和風險化解,為財政支出的擴大提供更大空間和保障。目前在加大銀行信貸投放的情況下,要注意強調銀行的風險意識,還要注意引導各地政府充分考慮銀行資金成本、經營成本等業務發展規律,不簡單搞一刀切,要與金融機構共同協商確定執行利率,支持銀行可持續發展。三是調節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產生和擴散。一方面,政府債發行吸收市場流動性,在短期可能導致市場流動性緊張,需要貨幣政策配合予以對沖;另一方面,在經濟預期偏弱的環境下,房地產、地方債及其他風險可能劣變并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通過貨幣政策操作防止風險擴散演化,避免短期波動影響持續導致中長期潛在增速的下行。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