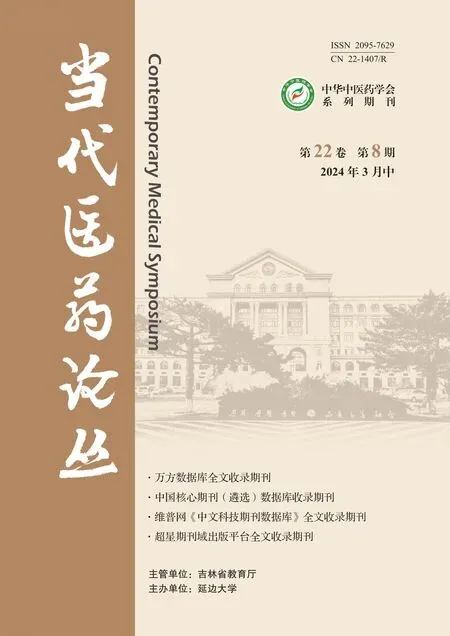藥物涂層球囊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的應用效果分析
馬蘇林
(北京核工業醫院心血管內科,北京 102413)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在冠心病的治療中十分常用。支架和球囊作為介入治療中最常用的器械,近年來發展迅速[1]。器械的結構和特性決定了其性能,在實際使用中,醫生會根據不同類型器械的特點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技術。臨床診療工作中,支架、球囊等器械的選擇主要是根據靶血管病變的特點,操作者可以根據器械的性能做出綜合判斷[2]。每種器械都有自己的特點,因此臨床介入醫生面臨著復雜的器械選擇問題。熟悉器械并有確切的循證醫學證據支持,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介入治療的成功率,減少術后并發癥。介入治療的發展離不開這些重要器械的改革[3]。隨著生物醫學工程技術的發展,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已從開始的經皮腔內冠狀動脈成形術發展到藥物洗脫支架置入術,能夠減少冠狀動脈再狹窄的發生[4]。如今,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支架是使用最普遍的醫療器械,通常由不銹鋼、鎳鈦合金或鈷鉻合金制成。心臟支架最初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裸金屬支架(BMS)、藥物洗脫支架(DES)和生物可吸收支架(BVS)等技術演變。每一次技術升級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一代技術的不足,藥物洗脫支架可謂是介入醫學領域的最大革新和亮點。但藥物洗脫支架置入術仍有一定的再狹窄概率[5]。另外,臨床尚未形成統一、科學地處理冠狀動脈分叉病變、小血管病變的方法[6]。近幾年來,藥物涂層球囊導管受到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該技術是一種新型的技術手段,它利用球囊作為藥物載體,球囊膨脹期間能夠迅速轉移抗細胞增殖藥物,作用于靶病變血管,使冠狀動脈快速吸收藥物,有效預防血管再狹窄的發生[7]。而與藥物洗脫支架相比,這種方法不需要在血管中預留永久性植入物,減少了后續冠狀動脈的正性重塑,并可預防炎癥反應的發生[8]。采用這一方法可以擴大冠心病的診斷范圍并選擇更有效的治療手段。本文就藥物涂層球囊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的應用效果進行探討分析[9],現詳細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基線資料
于2019 年1 月至2020 年12 月期間抽取冠心病患者60 例。這些患者均接受了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采用隨機數表法將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30 例。對照組中包括16 名男性和14 名女性,年齡在42 ~79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0.93±1.46)歲。觀察組中包括17 名男性和13 名女性,年齡在42 ~80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0.93±1.51)歲。兩組基線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對比。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口服300 mg 阿司匹林和300 mg 氯吡格雷,之后每日服1 次阿司匹林(100 mg/次)、1 次氯吡格雷(75 mg/次)。手術時,使用普通肝素(劑量100 U/kg)抗凝,手術過程中每小時追加肝素1000 U,同時對活化凝血時間進行測定,指導調整肝素用量。所有患者均采取橈動脈穿刺,取常規體位開展冠狀動脈造影,了解病變冠狀動脈的具體情況。對照組:采用普通球囊(Sprinter 快速交換球囊)擴張冠狀動脈,按1:3 比例稀釋造影劑,為球囊充氣加壓,控制初次充盈的時間為30 s,壓力為8 個大氣壓,逐漸增加充氣時間和壓力,最終達到90 s,在排空球囊后將其撤出。研究組:采用藥物涂層球囊(Vesselin)擴張冠狀動脈,使用高親脂性紫杉醇進行涂層,球囊直徑2 ~3 mm,先用普通球囊對靶病變位置進行擴張,當內膜未出現明顯撕裂、夾層時送進藥物涂層球囊,直到靶病變位置,完成擴張,擴張速度1 atm/5 s,漸漸增加到6 atm,直至達到最大壓力并維持此狀態30 ~60 s,同時確保球囊兩側均超過病灶區域至少3 mm 的長度。術后兩組均持續隨訪6 個月。
1.3 觀察指標
(1)觀察并比較兩組治療后動量冠狀動脈造影結果,包括血管(右冠狀動脈、回旋支、前降支)病變段直徑、血管長度 。(2)比較兩組術前、術后即刻及術后6 個月的病變段最小管腔直徑 。(3)比較兩組晚期管腔丟失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后定量 冠狀動脈造影結果
治療后定量冠狀動脈造影結果顯示,兩組的血管直徑、血管長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后定量冠狀動脈造影結果(mm,±s)

表1 兩組治療后定量冠狀動脈造影結果(mm,±s)
組別 例數 血管直徑 血管長度觀察組 30 2.51±0.03 13.18±0.91對照組 30 2.52±0.02 12.86±0.81 t 值 1.519 1.439 P 值 0.134 0.156
2.2 兩組手術與隨訪數據
術前,兩組的最小管腔直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即刻及術后6 個月,觀察組的最小管腔直徑均大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晚期管腔丟失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兩組手術與隨訪數據(mm,±s)

表2 兩組手術與隨訪數據(mm,±s)
最小管腔直徑組別 例數晚期管腔丟失術前 術后即刻 術后6 個月觀察組 30 0.81±0.02 2.54±0.01 2.20±0.01 0.32±0.03對照組 30 0.82±0.02 2.51±0.02 1.64±0.02 0.90±0.03 t 值 1.936 4.899 137.171 74.878 P 值 0.058 <0.001 <0.001 <0.001
3 討論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是一種通過心導管技術來擴張狹窄的冠狀動脈以改善心肌血液循環的方法,包括經皮腔內冠狀動脈成形術和冠狀動脈內支架植入術。介入手術技術及器械的發展能優化手術過程,減少術后并發癥,為患者提供更大的益處[10]。近年來隨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各種新型介入器械層出不窮,其中最常見的器械是球囊和支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于冠狀動脈小血管病變患者而言,由于血管管腔相對較小,若使用支架介入治療,可能因為支架膨脹不全而引發再狹窄[11]。如果僅僅使用普通的球囊擴張,除了彈性回縮外,術中還可能對血管壁造成撕裂等損傷,后續產生嚴重的副作用,如急性管腔收縮、管口橫截面損失等[12]。即便術中沒有發生任何并發癥,術后2 ~3 個月也極易因內膜增生而出現再狹窄,這意味著再次血運重建的可能性無法避免。我們應仔細權衡各種治療方案的益處和風險,除了要注意血管解剖外,還要考慮患者的臨床情況、技術因素和現實情況[13]。2014 年,歐洲心臟病學會指南推薦藥物涂層球囊和新一代DES 作為支架內再狹窄(ISR)治療的首選策略[14]。
目前,臨床尚未形成統一、科學地處理冠狀動脈分叉病變、小血管病變的方法,研究該患者群體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采用藥物涂層球囊的效果,能夠進一步優化手術策略,為心血管疾病的治療提供更好的路徑,減少手術并發癥,改善冠心病患者的預后[15]。與傳統支架相比,藥物涂層球囊具有諸多優勢,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證實了它在治療冠狀動脈小血管病變、冠狀動脈分叉病變、冠狀動脈慢性完全閉塞病變和冠狀動脈彌漫性病變等方面的優勢[16]。首先,藥物涂層球囊沒有金屬框架,有助于維持涂層藥劑分配的一致性,使得藥劑能在特定血管壁部位實現均衡覆蓋,并且能夠保持初始的血管解剖形態,避免在治療冠狀動脈小血管病變和分叉病變時對血流造成影響。另外,當處理ISR 問題時,藥物涂層球囊能有效規避需要采用雙層支架進一步縮小血管管腔 的問題,大量試驗已經證實ISR 是藥物涂層球囊治療的適應證之一。再者,藥物涂層球囊不含聚合物基體,可降低慢性炎癥反應與晚期血栓形成的可能性,因此有可能縮短雙重抗血小板治療時間(僅需治療1 ~3 個月)[17]。除了以上提到的患者群體之外,藥物涂層球囊相較于支架,更適用于那些高出血風險患者,如血友病、有出血病史、消化道潰瘍或嚴重腎功能損傷群體。對于正在服用抗凝劑或近期接受過手術治療的患者,如心房顫動患者、人工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血管內皮功能異常或短期內發生過ISR 的患者,藥物涂層球囊十分適用,同時還適用于不愿意接受支架植入的患者[18]。
基于循證醫學,我們應為患者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并靈活參考指南。最近幾年,藥物涂層球囊為冠心病的治療開辟了新途徑。藥物涂層球囊攜帶有抗血管內膜增生藥物,藥物釋放后可抑制血管內膜增生,進而抑制平滑肌細胞增殖,預防靶病變血管再狹窄。紫杉醇屬于紫杉烷化合物,具有較高的親脂性,吸附率高,可抑制血管內膜增生,對細胞骨架形成產生抑制,阻斷細胞有絲分裂,阻止平滑肌細胞快速增殖,預防內膜炎癥反應的發生[19]。目前,紫杉醇是藥物涂層球囊中最常用的藥物涂層成分,在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具有顯著優勢。涂層球囊能夠高效釋放藥物,貼近血管壁,確保藥物濃度,使血管迅速吸收,發揮抗血管內膜增生的作用。使用藥物涂層球囊時,藥物釋放比支架的網格梁更均勻,能夠解決藥物釋放不均的問題。特別是在處理分叉病變時,在側支血管使用藥物涂層球囊可以全面釋放藥物,防止側支血管開口無藥物覆蓋,預防血管開口處再狹窄。此外,藥物涂層球囊無需金屬支架支撐,可以保持原始血管的解剖結構,預防異常血流出現,更適用于冠狀動脈分叉病變和小血管病變的處理。此外,藥物覆蓋的球囊沒有留下任何金屬網狀結構或聚合物基質,可以降低因植入異物而引發血栓的風險,從而縮短雙抗治療的時間,降低并發癥的發生風險[20]。
綜上所述,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使用藥物涂層球囊效果顯著,可有效預防再狹窄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