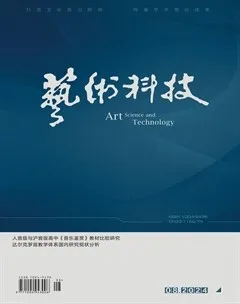論新媒體時代地方文化的回春與破圈
摘要:目的:長時間以來,在新聞媒體傳播和方言電視文本的展現中,關于上海的刻板印象被大量塑造并定型,這不僅加劇了地域歧視,造成了對地方方言和文化的偏見,而且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但隨著電視劇《繁花》的熱播,這一困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上海方言和文化重現活力。文章根據該劇的傳播特點,對其優勢展開思考。方法:文章從內容呈現、形象塑造、文化價值等方面,分析《繁花》在方言上的創新使用,如何實現集體記憶的消費;如何通過圖像、聲音和文本的結合實現形象凝聚,在敘事過程中刻畫鮮明的人物,引發觀眾的情感認同;作為一部文藝作品,它蘊含何種價值與內涵。結果:該劇塑造的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主義發展的現實情況,對上海與滬語的形象構建有利于打破刻板印象,促進上海地方文化繁榮與跨地域傳播,同時以視聽符號的藝術加工,喚醒港臺民眾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反映出優秀文藝作品對社會的正面影響。結論:《繁花》之所以能產生廣泛影響,不僅因為其內容優質,也離不開數字技術與新媒體的支持。觀眾通過網站實時彈幕、評論和社交軟件的討論推動文化交流和傳播,掀起了上海的方言熱潮和旅游熱潮,推動了地方文化回春與破圈。
關鍵詞:? 《繁花》;電視劇;方言;地方文化;刻板印象;身份認同
中圖分類號:J905;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8-0-03
央視和騰訊視頻同步播出的電視劇《繁花》,口碑收視雙豐收,成為2024年第一個爆款劇。該劇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青年阿寶努力拼搏蛻變成寶總的故事。在成功的路上,他與爺叔、汪小姐、玲子等多個角色相互成就、相互扶持,而空降的李李、半路殺出的深圳股市強總給寶總和他身邊的人帶來了挑戰。劇中每條故事線都獨立而飽滿,畫面光影、色彩、構圖絕妙,服化道精致而復古,市井煙火氣與上流奢華風碰撞,呈現出20世紀迷人獨特的上海。《繁花》的角色形象鮮明,阿寶敢想敢拼,多次化險為夷,劇中的女性角色也獨立自強、不斷成長,具有積極的傳播意義。
1 繁華老上海的重現
上海誕生之時,就飽含著多種基因,是一個不同于其他傳統城市的復雜體,是一個開放多元、充滿生機活力、具有浪漫氣質又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是冒險家的樂園,是富人的天堂,又是中國現代工商業的搖籃[1]。八九十年代的上海,迎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快速發展起來,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
電視劇《繁花》改編自作家金宇澄同名長篇小說,體現了王家衛導演對小說的提煉創新。原著講述了在時代變遷的大背景下隨波逐流的人們的無奈,有人說這像一首“痛歌”。而王家衛導演的電視劇只選取阿寶這一角色展開敘述,講述了無名之輩蛻變成商界大佬的傳奇故事,更像是一首“贊歌”。
2 地方文化的突破與傳播
2.1 方言:超越隔閡達到共通意義空間
方言作為地方文化的特殊表現形式,彰顯著一座城市、一個群體的底蘊和特色。在電視文化生產場,尤其在以展現地方風土人情為主要內容的文本生產中,這種獨特的言語形式有望成為連接觀眾的紐帶,而這是標準普通話無法實現的[2]。
1956年,全國開始推廣普通話,使用統一標準的現代漢語有助于國家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的傳播,而方言則需要另尋發展突破的窗口。20世紀90年代,方言作品蓬勃發展。我國首部方言和大眾傳媒結合的作品是1982年由宋學斌執導的電視劇《人與人不同》。此后陸續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方言電視劇,如《山城棒棒軍》(重慶方言)、《老娘舅》(上海方言)、《鄉村愛情》(東北方言)、《一家老小向前沖》(長沙方言)等。但受時代和技術的限制,這些電視劇的傳播范圍有限。
《繁花》備受關注,不僅與金牌導演王家衛長達6年的打磨有關,還在于全上海演員陣容以及原聲滬語。滬語版《繁花》別具韻味和腔調,能使觀眾沉浸式感受老上海的魅力。《繁花》在很大程度上補足了近年來中國方言電視劇的空白,它憑借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優勢,帶動了以“方言”“地方文化”為關鍵詞的影視作品的傳播。許多觀眾在普通話版里發送彈幕推薦其他人去看滬語版,認為滬語版才有靈魂,更能展示真實的上海。還有觀眾表示,滬語版激發了自己對上海話的興趣,更想去上海旅游。同時,不少江浙滬地區的觀眾表示,觀看滬語版時,產生了“特別親切”“好熟悉”的正向感受。
新媒體時代,長短視頻平臺為獲取流量搶占市場,推出各種質量參差不齊的網劇、精簡過癮的短視頻。在此背景下,制作精良、劇情精彩、能體現時代格局和上海地方文化特色的劇本令人眼前一亮。劇中的“碰哭精”“十三點”“叫花子吃死蟹”“爺叔”等充滿滬腔滬調的方言,符合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語言環境。象征性社會互動理論認為,符號意義的交換有一個前提,就是交換的雙方必須有共通的意義空間。這里的共通意義空間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等意義符號共同的理解;二是大體一致或相似的生活經驗和相應的社會文化背景。雖然方言在傳播時可能形成隔閡,導致觀眾難以理解語義,但結合畫面和字幕,以及上海本地演員充滿神韻的家鄉話表演,觀眾能獲得克服方言阻礙的視聽享受。
2.2 歷史:集體文化記憶聯動與消費
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基本依據,是共同體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對大多數族群而言,集體記憶意味著基于“我們”的話語和行動而形成的共同的命運感、共通的文化血緣和共持的價值信念[3]。
《繁花》劇組斥資5億元搭建上海實景街道,力求還原90年代霓虹閃爍的“夜上海”。上海音像資料館提供了海量資料,用真實影像營造時代氛圍,還原20世紀的繁華上海。例如,第27集直接采用1994年國慶節東方明珠開燈儀式時的電視新聞報道片段,勾起了觀眾尤其是上海本地人對城市和整個國家的回憶。
劇中的和平飯店是寶總夢開始的地方,也是上海近現代歷史文化的豐碑,接待過無數中外名流;上海的代表建筑東方明珠作為重要元素貫穿整部劇,黃河路、進賢路、桃江路等劇中出現的地名在現實中亦是存在的。此外,劇中的上海特色美食也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如承載著汪小姐和寶總奮斗記憶的排骨年糕、寶總在夜東京必點的泡飯等。其不僅體現了上海的獨特風味,也映射出城市文化底蘊和人民生活。
除了地名和美食,劇中出場的費翔與溫兆倫也都是符合年代背景的當紅明星。第27集中,1994年元旦配樂使用了搖滾歌星竇唯版本的《無地自容》,而1994年正是中國搖滾的高光時期,是一個頗有紀念意義的年份。《繁花》整體背景宏大,但細節滿滿,導演擅長將虛擬故事和真實事物巧妙融合,給觀眾一種突破“次元壁”“夢幻聯動”的驚喜感和親近感。
3 價值塑造:《繁花》文化傳播啟示
3.1 角色構建:對現代與傳統女性的探索
女性符碼對女性的個體乃至女性群體都具有巨大的規訓力量,女性本身也在認可和同化符碼所規訓的意義結構,規訓分為內外部雙重監視[4]。Don Heider和Dustin Harp認為,即使有了互聯網等新技術,我們仍然處于一個女性被物化和邊緣化的交流環境中[5]。在大部分影視作品中,女性都是弱勢群體,而《繁花》對女性角色的塑造脫離了男強女弱的套路,更強調女性力量。汪小姐年輕漂亮,做事爽利能吃苦,被陷害后干脆離開了外貿大樓,拒絕寶總的幫助,決心自己干出一番事業。玲子看起來刻薄市儈,但她待人真誠熱情,人生規劃明確,在與寶總斷開關系后重新開始,將店經營得紅紅火火。在3名女主中,李李是最神秘的,她是從天而降的至真園老板,是可以和寶總對戰的商業女性,同時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方之間,從她幫助寶總解決仿制品問題和圓滿化解至真園風波能看出她有勇有謀。除了3名女主外,劇中其他女性也有自己的閃光點,她們或果敢或精明,體現出女性意識的覺醒,符合現代女性獨立自主、不畏困難、打破束縛的追求。
3.2 形象改造:真實與刻板印象的碰撞
美國傳播學者李普曼在《輿論》一書中提出,大眾媒介營造出的擬態環境是形成和維護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在社會和成員的形象構建中舉足輕重,同時對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印象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在影視作品中,各地的方言通常會和一定的形象聯系起來,如說東北方言的角色一般豪爽直率、說陜西方言的角色一般淳樸老實等。方言電視節目中存在的刻板印象,往往與傳播者迎合部分受眾的偏見密切相關。這種迎合不僅固化了成見,更使之成為辨識某一方言地域群體的顯著標簽。一旦這些刻板印象與負面新聞交織,便可能進一步升級,甚至誘發歧視行為[6]。而上海多年來都以“排外”“看不起人”聞名,有人認為上海話聽起來就不好惹,這與近年來網絡媒體傳播的上海負面新聞息息相關。
在原著中,金宇澄借人物表達了對上海的刻板印象的看法,認為任何人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那些批評上海人的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樣的。而《繁花》傳遞了原著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上海的口碑。劇中角色雖然并不都是完美的,每個人身上既有優點也有缺點,但正因如此才更具真實感。隨著此劇的熱播,網友評價上海話“越聽越好聽”、上海美食好吃、景色建筑好看等。
3.3 身份認同:大陸與港臺文化的共鳴
身份認同這一概念由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威廉于19世紀首次提出。身份認同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心理結構,涵蓋人們的自我認知、行為表現、情感體驗等多個方面。尼迪克特·安德森強調大眾傳媒在民族國家興起中的關鍵作用。他指出,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大眾傳媒則建立了群體成員之間的聯系機制,讓每個個體都能感受到“我們”的存在,進而促進民族認同。
《繁花》在港臺地區掀起了“繁花熱”。之所以能受到港臺觀眾的喜愛,不僅因為上海和香港都是國際化大都市,兩地的交流合作十分緊密,還因為兩地市民的生活狀態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劇中出現了不少香港元素,如張學友的《偷心》、beyond的《不再猶豫》等多首粵語金曲,至真園的干炒牛河、仙鶴神針、船王炒飯等港式粵菜。這些元素的出現,提高了香港觀眾的接受度。在臺灣地區,《繁花》的討論度也非常高,臺灣時事評論員賴岳謙在一檔節目中表示,《繁花》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加入了新文化,能讓觀眾感受到當時上海的魅力。并且對兩岸來說,劇中的和平飯店具有重要意義:第二次“汪辜會談”在此達成4項共識,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到此與滬臺商座談。有臺灣媒體人和臺商表示,劇中展現的部分元素能勾起自己的記憶,使自己頗有感觸。電視劇播出后,許多港臺影迷陸續赴滬打卡。
《繁花》展現的歷史細節和電影化的媒介呈現,平衡了娛樂性與文化性,突出了上星劇的社會功能、宣傳功能以及文化交流功能。其通過音樂、角色、藝術設計,以集體記憶喚醒港臺民眾的民族認同感,增強彼此之間“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感知和身份認同,從而增強群體內部的文化自信與自豪感。
4 結語
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繁花》以獨特的視角和精湛的制作,贏得了觀眾的喜愛和認可,上海方言與文化由此煥發出新活力。未來應繼續推動中國優秀文化作品傳播,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真正實現文化的多元共融。在此過程中,媒體和創作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應該用心制作更多優秀的文化作品,傳遞出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推動不同文化的對話和理解。
參考文獻:
[1] 張德祥.數風流城市,還看上海:長篇電視劇《上海,上海》芻議[J].當代電視,2010(11):13-14.
[2] 韓鴻.方言電視與話語權力[J].新聞界,2002(4):35-36,45.
[3] 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3):98-106,159.
[4] 董金平.女性符碼與女性規訓[J].學術探索,2007(1):56-59.
[5] 唐·海德爾.達斯汀·哈普.新希望還是舊權力:民主、色情和互聯網[J].霍華德傳播雜志,2002,13(4):285-299.
[6] 王淑娟.對方言電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及思考[J].傳播與版權,2014(8):74-75.
作者簡介:李唯(1999—),女,湖南常德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新媒體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