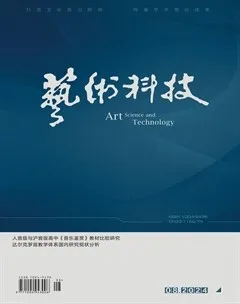精神分析視域下《涉過憤怒的海》的內核透視
摘要:目的:導演曹保平延續一貫的“灼心”風格,將老晃的同名小說搬上大銀幕。影片《涉過憤怒的海》以一個突發事件為圓心向外輻射兩個離異家庭,復仇行動中所體現出的一系列生存現實、倫理壓力及道德拷問,直接指涉眾多的社會問題,透露出所要傳達的精神內核。方法:文章基于影像文本,借助精神分析電影批評理論對該片的情感邏輯與精神內核進行剖析,透過精神分析的視角,運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等人的理論,挖掘并反思現代化進程中代際關系異化的深層動因,探討人性幽暗面的表達邊界。結果:傳統家庭血緣關系的淡化和異化逐漸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原生家庭所帶來的難以磨滅的創傷記憶引發親子關系與青少年成長的深刻反思。文章歸納出影片想要傳達的精神內核有關于現代社會傳統家庭中生產資料和精神訴求的矛盾沖突、復雜人性下的對抗與救贖、青少年成長中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創傷記憶與倫理缺位、關注下一代愛的教育的思考。結論:導演將個體自渡的哲思嵌入追兇復仇的行動邏輯和影像視效奇觀,通過探討原生家庭缺位背后的心理創傷與情感缺失,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實關注和人性悖論,傳達出一種對現代家庭結構性變化的人性追問、現實關注與文化思考。
關鍵詞:? 《涉過憤怒的海》;精神分析;內核;心理創傷;代際關系;倫理缺位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8-0-03
1 現實觀照的寓言:生存與行動邏輯的錯位
影片以老金的行動邏輯為脈絡展開,金麗娜的離奇死亡是整個故事的開端,老金為了追尋真相,踏上了跨海尋仇的旅程。這一事件引發了他內心的憤怒,開始懷疑每個角色的真實動機和身份。影片一方面呈現角色的行動路徑,另一方面通過現實層面的錯位對比觸碰生存環境所致的深層結構性問題。首先是兩家的階層區別,鄉野小島和現代城市別墅的空間對比直指漁民與富人身份的差異。在海島獨居的金隕石習慣了沖鋒搏擊與險境逃生,原始生存是他的第一要義。相比之下,景嵐的別墅則充滿富裕、生人勿近、冷峻危險的氣息,連同困住金隕石的地下室一起困住了彼此生活的階層差異。二者的生存與行動邏輯自然截然不同,一方在搏殺中突圍,另一方則善于調動資源。其次是對于子女而言,一個在被寵溺和無限包容的環境下成長,另一個則長期極度缺愛,鮮少得到愛的回應,因此兩人的愛情觀也不同。一個占有欲、控制欲突出,另一個近乎病態地追求愛;一個充滿戾氣、向外所求發泄,另一個自耗自戕。兩個天差地別的教育環境造就了性格的極端差異,也造就了成年人與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情感錯位。如果老金代表的是依靠原始積累的普通大眾,景嵐和李烈則代表了吃到現代化紅利的階層,但無論生產資料處于何種境地,他們在代際溝通上都是束手無策的。兩個家庭同樣面臨生存壓力和子女教育問題,在傳統觀念與現代社會形成的錯位夾縫中,他們都是子女背后的避風港。無論是何種父權,本質的思維邏輯都是對生存問題的解決與升級,而子一代在成長過程中的訴求則超越了生產資料,追尋超越物質的精神訴求,這難以調和的問題造就了家庭的錯位。因此,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傳統家庭親情的瓦解以及父母子女之間天然血緣關系的淡薄,逐漸成為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所隱喻的殘酷青春、殘酷中年是代際關系的錯位,也是時代的錯位。
2 復仇想象中的對抗與共生
“電影似夢”的觀點由來已久。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夢的生成是潛意識領域將主體白日經歷的殘余、身體刺激和夢思維作為素材,經過濃縮、移植、二次加工等夢的工作機制轉化成具象化的故事內容[1]。弗洛伊德在《夢的釋義》中專門闡釋了夢最根本的情感特征——夢是愿望的滿足。在夢境的“故事文本”中,夢的意義就在于滿足主體的愿望需求,因為主體在現實存在的生活環境中的愿望往往難以達成和實現。影片將現實中金隕石的犯罪復仇和娜娜的自殺過程串聯在一起。娜娜的日記記錄了自己在夢中對父親施以絞刑,身后的金隕石被懸吊在桅桿之上,自己劃船遠走。子輩的復仇在最后的段落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現,這種夢的意象毫無疑問便是由娜娜的思想變為的視象,而透過這個冷峻的視象,可以透析娜娜潛意識里的弒父情結。弗洛伊德曾將夢與幻想同歸于潛意識。娜娜夢中出現的老金慘死的視象是娜娜潛意識的幻想,進而決定了娜娜的報復性行動。娜娜在垂死時刻撥通老金的電話,或可理解為是娜娜的誤撥,但筆者更傾向于理解為,娜娜故意撥通老金電話卻并不發出求救信號,最終令老金懺悔自己錯過救女的時機,痛苦終生。這種醒悟及追悔莫及的心死報復才是娜娜的終極目的。
在影像文本的表層,《涉過憤怒的海》是一名父親為死于異國他鄉的女兒復仇的故事,但其核心沖突圍繞死者和疑兇兩個家庭的家長展開,由此,復仇故事便轉換成了對當代中國家庭關系進行追問的倫理故事。劇情片本身是建立在某種類型的基礎上的,那么,它的情節和人物就更濃縮、極致,情緒呈現不會那么散淡和自由,功能性更強[2]。《涉過憤怒的海》以類型片開始,最終打破了類型敘事的期待,將個體的困局和脫困的行動邏輯作為類型化敘述的核心,對生活清淡寫實進行變形創作,平衡白描化紀實化風格與敘事的功能性之間的關系,人復雜心理的表達更具克制與釋放的沖突張力。金隕石以一己之力追擊眾人,大起大落,幾經波折反轉,從高速公路的極限追擊到天降魚雨,再到車禍碰撞,在極度風格化的影像奇觀的加持下,這種幾近癲狂的復仇心理和戲劇手段將雙方對抗的力量和復仇情緒拉到了極點。復仇的焰火由激烈燃燒到無聲湮滅的間隙里滲入了家庭關系、仇敵關系這一系列難解的倫理議題,因愛的缺失所帶來的強烈情感沖擊反映在紛繁復雜、多元共存的時代,不同人群的后天性格和價值認識是天差地別的。
罪案雙方的對抗是影片強情節的基礎,而且對抗行動是密集、頻繁的[3]。關于金隕石的追兇可以大致分為兩個空間,從日本的地下通道到站臺,再到地鐵軌道,而后轉至國內漫展現場的追擊、旋轉樓梯到天臺,罪案雙方的追逐殊死對抗不留余地;最后以李苗苗的公路車禍生死未卜為懸念,以這場公共空間的個體緝兇作為結點。之后產生雙方對抗力量的反轉,復仇的戰場轉移到了金隕石的自由領地——海域。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老金逐漸發現自己可能才是真正的兇手,“緝兇”的概念在影片中被反轉,“懲兇”的意義也被消解,這對父母水火不容的極端對抗終結于一方的施救行為。極限境遇的終極狀態下,二人是仇敵,但完成了對彼此的救贖。生與死的關鍵時刻,呈現出人物性格的復雜以及對人性的思考。另外,景嵐用幻想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好母親的角色,將現實世界與現實規則從自己的生命體驗中消除了,她和李苗苗之間產生了一種畸形的共生關系。從她對李苗苗的絕對保護和付出中,人們可以嗅到濃烈的“創傷”氣味,或許李苗苗成了她未盡欲望的代言人,景嵐通過對李苗苗的絕對守護來滿足內心渴求保護的脆弱的自己。某種程度上,李苗苗的冷血肆意和景嵐絕對保護欲下衍生的冷漠高度相似。這種對抗與共生,是影片對復雜人性的表達與思考。
3 涉渡心海:個體創傷的心理追索
影片渴望表達的是對愛的失語。在力比多理論中,除了肉體的欲望,愛是弗洛伊德多次強調的一點。可以說,《涉過憤怒的海》中發生的一切皆因“愛”而起。娜娜初到日本學習日語,學不會說“愛”,娜娜愛苗苗,因為苗苗身上具有極強破壞力的占有欲恰恰能夠被娜娜置換為愛的力比多,人類對力比多的渴望變成了娜娜此刻對力比多終會消逝的焦慮。從本質上來看,娜娜和苗苗有相似的力比多需求,他們同時認定對方辜負了自己,而娜娜在自證清白的過程中,苗苗卻驚惶離開。無論是前面提到的夢還是力比多,都共同牽扯出精神分析的另一個關鍵詞,也是影片《涉過憤怒的海》中不斷閃回的童年。關于童年,弗洛伊德在描述夢的表達方式具有“記憶畫”和視象化特征時,用了“倒退”一詞來形容。“倒退”,不僅僅是退回到人類語言產生之前的記憶畫原初時代,還包括個體退回到自己兒時的情景。壁櫥這個獨特空間關住的是娜娜的童年陰影與父愛缺失,繪滿的無數太陽成了一種精神符碼,獨自等待照亮黑暗。某種程度上,死亡是一種終極無望的救贖,救贖了娜娜心里的恐懼與落寞,救贖她的不配得感覺。影片中所呈現出來的所有平行時空中的畸形,都源于過去一些共同瞬間的相似關系。相似的童年經歷讓娜娜終其一生都在尋找童年時期的“安全島”,也讓苗苗時刻處于被追趕和被驅逐的狀態。他們擁有和同齡人一樣的日常生活,卻也一直飽受著來自童年的隱秘圍堵,成為現實中的“虛實雙棲”者。
4 反成長與倫理缺位
影片《涉過憤怒的海》用一場聲勢浩大的“復仇”,揭開了病態家庭關系中父母儀式感愛子女的真實情況。這場原生家庭對個體命運的重大影響,不僅是對父母子女關系的反思,更是對家庭背后隱藏的傷痛和情感沖突的探討。娜娜的生命里沒有雙箭頭的喜歡,她幾乎沒有獲得過愛。娜娜成年后的行為,成為對童年時期創傷記憶的一種補償機制[4]。其童年經歷中“壁柜里的太陽”的創傷記憶,指向了原生家庭殘酷的倫理現實。影片中,金隕石忙于捕魚而忽視女兒這一現象被表述為熟視無睹的常見社會現實,家庭倫理的某種殘酷性并非完全由“惡”而生,而是在日復一日的平靜忽視和情感缺失中滋生的。童年的創傷記憶在李苗苗一方,則是作為害人者的身份出現的。重組的家庭、缺失的關愛,導致了他的孤獨與自卑,催生出暴戾與冷血。其對于憎恨的人和事,從小慣用摧毀的方式來解決。其實真正意義上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有可能偽裝得很好,他們可能情商、智商都特別高,人緣也特別好[5]。從娜娜的視角來看,李苗苗是溫暖的來源,但在面具之后,觀眾能看到他完整的惡。他的畸形性格、報復心理無一不透視出父母角色在家庭關系中的缺位,乃至精神世界的失教、失管、失控。
雅克·拉康提出了“鏡像階段”理論,認為嬰兒識別鏡中影像后,會與鏡中的影像做出一系列互動和反應。也就是說,嬰兒可以識別自我主體的存在,去探索自身與環境的關系,即完成拉康“鏡像階段”理論中的“一次同化階段”。而嬰兒在完成自我主體建構的過程中,還需要經歷“二次同化階段”,即嬰兒通過自我的認知和意識,接受社會話語秩序與結構,從而由“自然人”進化到“社會人”這樣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化”是和“他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曹保平原生家庭話題影片《狗十三》和《涉過憤怒的海》中,“他者”的話語權多以父之名的形式出現。不同的是,《狗十三》中對青春成長史的疼痛感表現是一個細密的抽絲剝繭的過程,這種陣痛更像一把刀垂直地捅進傷口,再不動聲色地拔出,撕裂開來,引導大眾自行反思與探尋;相較之下,《涉過憤怒的海》是對商業片和類型片結合的探索,以極限追兇、步步為營的強節奏敘事來深挖原生家庭背后殘缺的愛,最后發出痛批。在影片的敘事深度上,對于父親這一“他者”形象的審判和弒殺是武斷的。從思考深度出發,僅憑“父親”這一角色并不足以成為一個花季少女在個體意識與社會話語體系同化過程中走向毀滅的唯一“他者”影響因素。在敘事鏈條上,母親形象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讓娜娜最終選擇的合理性變得羸弱。罔顧是非的愛無法消融憤怒,癲狂的憤怒亦挽救不了深入泥淖的絕望。一邊是父權威嚴挾持下的愛,一邊是凌駕于道德理性上的偏執溺愛,導演用極致情緒的奇觀,燃燒了父親的復仇焰火,消融了母親絕望的溺愛,盛放了少女的毀滅,撕碎了親子關系中以愛為名的“遮羞布”,啟示觀眾重新審視為人父母者關于愛的教育,探尋人性中“愛的安全島”。
5 結語
在追兇復仇的具體行動邏輯和極度風格化的影像奇觀的雙重加持下,導演試圖傳達對現代家庭結構性變化的人性追問、現實關注和文化思考,呼吁關注愛的教育,關注青少年成長的心理問題。影片實現了三個維度的跨越。一是跨國,一場由中國到日本的跨國追兇;二是跨文化,在青年亞文化與成人文化之間進行了跨鴻溝式的文化認識與反思;三是跨階層,通過兩個家庭在極限境遇下處理危機的行動邏輯,思考生存與現實的錯位。這體現了個體自渡的哲思,每個人都如同孤島的受困者,在怒海中掙扎、涉渡、救贖、審判,“涉海”不僅是與故事相關的情節元素,也是個體涉過“心海”的寓言表述。
參考文獻:
[1] 孫榮.電影·夢·鏡子:精神分析視閾下中國動畫電影的創作策略研究:以電影《深海》為例[J].東南傳播,2023(9):70-73.
[2] 吳冠平,曹保平.過與不過的邊界:曹保平訪談[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6(5):19-25.
[3] 路春艷.《涉過憤怒的海》:孤島困局與涉海救贖[J].當代電影,2024(1):15-18.
[4] 陳曉云.《涉過憤怒的海》:復仇敘事、倫理追問與作者表述[J].電影藝術,2024(1):82-85.
[5] 曹保平,潘若簡,李牧歌.《涉過憤怒的海》:類型敘事、心理探究和社會觀照:曹保平訪談[J].電影藝術,2024(1):98-106.
作者簡介:趙碧瑩(1997—),女,江蘇泰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戲劇與影視學、藝術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