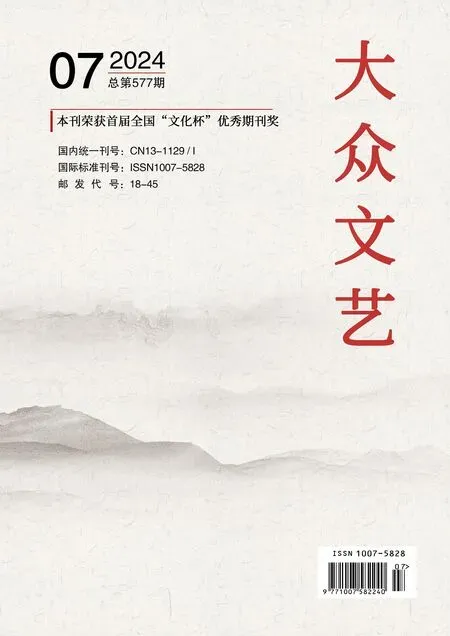坦培拉技法在綜合材料繪畫中的意義與實踐探索*
王田田 魏婷婷
(吉林藝術學院,吉林長春 137100)
在架上繪畫領域,綜合材料繪畫已經開始呈現面貌多樣化的發展趨勢。自1980年代綜合材料繪畫在國內開始發展以來,我國本土藝術家一直在用心耕耘,從未間斷對綜合材料繪畫的研究。目前基本建立了本土語言表達的綜合材料繪畫語境體系,坦培拉材料作為綜合材料繪畫的重要手段,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通過繪畫材料與方法的演變,著重探討坦培拉材料技法在當下綜合材料繪畫中應該如何理解該材料技法的繼承與應用,也能更好地在藝術創作實踐中不完全拘泥于傳統、勇于創新。
一、繪畫材料運用概述
法國索邦大學教授弗洛朗絲·德·梅格迪約在他的著作《材料與現代藝術》中曾表述過這一觀點:“藝術總是作為多種因素組合或者碰撞的結果,通過物質和形式體現出來,因此使得所有作品的形式與觀念最終以一種物質形態得以體現。一件藝術品不論她的形式如何,都是可見、可感的實體。因此,從廣義上講藝術史也可以稱為藝術材料史。”[1]這里所說的“材料史”不僅包含在藝術史的記錄中各個階段所運用不同繪畫材料的轉變,也包含現代藝術中藝術形態趨于復合性,進而產生的更為多元化藝術材料的應用,這是事物發展規律的必然,也是人類思維發展的必然。藝術從起源開始,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于繪畫材料的應用一直處于不斷演化過程中。繪畫材料的應用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呈正相關的關系,即物資匱乏的時代所運用的材料也必然匱乏;反觀當今,材料之所以涉獵如此廣泛與當今社會發展密不可分。但材料的匱乏并不代表藝術所呈現的面貌就會粗鄙,反而有時更能凸顯作品的張力與沖擊力,例如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中的公牛大廳所繪巖畫,歷經萬年的滄桑歲月,壁畫與巖石融合成渾然一體的色調和肌理,更加顯得渾厚粗獷,魅力無窮。再如從中世紀時期興起的濕壁畫所運用的坦培拉材料、中國早期石窟壁畫所運用的巖彩材料,無一不體現這種古樸的視覺沖擊,這一特征與現如今的綜合材料繪畫所追求的藝術表現語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對于早期的繪畫材料與技法的研究更顯得尤為必要。
二、繪畫方式的形成與發展
(一)“間接畫法”向“直接畫法”的演化
在中國,對于西方繪畫的認識,提到架上繪畫,大多數從業者會首先想到以油畫材料為主導的繪畫形式。其中緣由頗多,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后蘇聯繪畫對于我國的影響較大,尤其是1957年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的學員后來無不成為中國學院內油畫教學的中流砥柱,使得“直接畫法”與“現實主義”成了我國油畫學習與實踐的主要方式;其二是以徐悲鴻先生為代表的我國第一代歐洲留學畫家們接觸西方繪畫之時,西方繪畫也已經發展到以油畫這一材料為主流材料的時代,并且已然相當的成熟。他們回國后便投身我國美術教育,當時的國情亟須引進一套行之有效的美術教育模式以配合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張,所以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學院派現行的教育模式。因此,在西方繪畫教育引進之初,來不及去深入研究油畫之前的材料與技法,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的油畫普及教育都是建立在歐洲近二三百年的繪畫體系下逐漸發展至今的。現如今我們對西方傳統技法材料體系認識愈加完整,也逐漸匡正過去存在的“西方繪畫就是油畫”“直接畫法”就是歐洲繪畫的“唯一技法”這一錯誤認識。[2]在歐洲繪畫歷史中,存續兩千余年的“間接畫法”體系中有太多優秀的材料與技法值得我們去借鑒與研究,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古老的坦培拉繪畫。
中世紀時期的繪畫大都是以圣像畫為主,也是坦培拉繪畫的時代,運用單色不斷疊加的“疊色法”去生成自然、內斂的色彩效果,營造永恒的、超越人間的絕對精神。14-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們在人文主義思潮下,將目光由神的世界轉移到了人間,始于喬托的油性坦培拉技法增強了畫面中造型與空間的真實感,并于16世紀以后成為歐洲繪畫的主流技術。提香首次將繪畫的筆觸語言單獨提煉出來而被冠以“西方油畫之父”的美譽,極大展現了繪畫材料本身的審美價值,大家在關注畫面內容的同時發現凸起的筆觸竟然如此具有魅力,將繪畫材料的表現轉換為獨立的審美客體,之后卡拉瓦喬運用的深棕色畫底與提白罩染的技術進一步使油性坦培拉技法得到發展。17世紀的倫勃朗更是把油性坦培拉發展到了新高度,為了追求筆觸的效果,在底層用明亮的顏料堆積成筆觸后,等干透以后用沾有油彩的抹布將筆觸中凹陷的部分涂滿“污垢”,再將凸起部分擦拭干凈,進而營造一種畫面顏料堆積很厚的視覺效果,這對后來的“直接畫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貴支運用“一次過”技法,開始嘗試運用筆觸造型,且直接調和顏色以達到預期的色彩效果,這是具有開創性的嘗試。直到印象派繪畫時期,錫管顏料替代了畫家自制的動物膀胱顏料袋,工業的進步使繪畫材料也進行了一次革新,利于繪畫的油媒介也開始逐漸替代傳統的水油混合乳化媒介,“直接畫法”基本成為藝術家比較普遍運用的技法。同時,繪畫也更關注筆觸語言的運用,直接將調和好的顏料厚涂、堆砌,可更加酣暢淋漓地抒發畫家的主觀意趣與情感思想。“直接畫法”至此成熟并成為獨立的繪畫體系發展至今。[3]回望歷史,繪畫材料從傳統水性坦培拉材料演變為油畫材料,再逐步發展到如今運用現代材料作為藝術創作主體的現當代繪畫,其中繪畫材料的演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需求變化而完成了轉換。探尋材料演變的目的不是為了復述歷史,而是更為直觀地展示如今綜合材料繪畫的底層邏輯,對傳統繪畫材料的學習作為綜合材料繪畫實踐的切入點才是要義。
(二)再由“直接畫法”轉向“間接畫法”
現如今,對于“間接畫法”的研究除了具有歷史意義,同樣具有文化價值。中國對于西方繪畫的學習,從理論到實踐,基本建立在“直接畫法”的系統之上,雖然部分院校也開設有坦培拉、古典油畫等課程,但主流依然是“直接畫法”為主的教學模式,對于油畫的源頭、有著千年歷史的“間接畫法”還是缺乏系統的實踐與探索。傳統意義上的“間接畫法”就是通過層層單色罩染,加以局部提白,色彩的豐富性依靠多層罩染后,底層反色融合形成色層,進而使得畫面色彩比直接調和的色彩顯得高級、柔和、雅致,這是“直接畫法”所不能達到的。從廣義上講,只要不是運用“一次過”的方法,而是通過某種繪畫材料層層堆疊、反復打磨,逐漸塑造與經營畫面的方式都可以稱之為“間接畫法”。以坦培拉材料技法為代表的“間接畫法”,之所以被許多美術學院的實驗藝術系在教學實踐中安排為綜合材料繪畫課程的基礎課程,二者在除了材料應用有區別以外,在技法與情思等諸多方面都有著內在共通性。但無論繪畫語言與繪畫材料如何轉變,架上繪畫實際上都離不開三個基本語言,即造型語言、色彩語言和材料語言。這三大藝術語言系統在歷史中一直交替、轉換、交織著各自的權重,在不同的時代參與著不同的藝術創作。分析繪畫的發展史,造型語言與色彩語言在長時間中處于藝術語言第一要素,主導著繪畫的風格與樣式,到了20世紀初,人類基本完成了對兩大系統語言的探索與命題實踐,藝術史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藝術材料語言的演變是一個漫長并且復雜的過程,從“間接畫法”到“直接畫法”是美術史中有跡可循的,研究綜合材料繪畫從興起到現在的綜合材料繪畫作品我們又發現,材料作為繪畫語言主體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成為許多當代藝術家更加確切的表現個人思想情感以及主體觀念的有力手段,也使得藝術家長時間地專注于將材料與作品進行有機統一,不斷進行學術探討與觀念碰撞,綜合材料藝術家們逐漸發現“間接畫法”似乎更為適合作為材料性繪畫的表現技法。
三、以坦培拉為代表的“間接畫法”在綜合材料繪畫中的實踐運用
(一)西方綜合材料繪畫的“間接性”
那些古老的坦培拉繪畫流傳至今,作為研究材料性繪畫的我們,除了贊嘆古代大師們巧奪天工的技藝,也應該關注其繪畫過程中的間接性給作品帶來與眾不同的視覺感受,還有些壁畫色層受損導致的剝落更是給作品增添了趣味性,這些視覺經驗對于當代的材料性繪畫技法的有著重要的指引意義。學習坦培拉繪畫的“間接畫法”并不是要原封不動的運用到綜合材料繪畫中,而是運用“間接畫法”的技術思路進而轉換為綜合材料繪畫的“間接性”。西方較早的在架上繪畫中運用材料進行實踐,從最初相對單純的拼貼逐步轉為多種、多層材料相互覆蓋,使藝術家的藝術表達多樣化,這樣的作品更容易使觀者沉浸在藝術鑒賞中。因為材料語言是一個復雜而強大的符號系統,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神經,從而在欣賞過程中達到某種精神共鳴。
國外對于運用綜合材料繪畫的嘗試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藝術家開始在創作過程之中將不同的媒材應用在自己的畫面之中,用來探索新的繪畫形式。立體派的作品中,拼貼是一個常用的技巧,用于畫面的聯想和重組,來突破固有的畫面程式。到了20世紀中葉,藝術家對于綜合材料繪畫的研究更為深入,應用也更加廣泛。巴爾蒂斯為這一時期坦培拉材料探索的代表,他運用酪素乳劑為媒介,混合油畫顏料或者調和好的色粉,由于酪素乳劑會使油畫顏料降低油性的效果,因此畫面看起來既有坦培拉多層間接的效果,又具有油畫顏料相對粗獷的筆觸語言。巴爾蒂斯的作品可以明顯地看到坦培拉技法的影響與應用上的轉換,為之后偏重繪畫性的綜合材料繪畫產生了很大影響。20世紀后期,隨著現代藝術的發展,西方繪畫在觀念和形式上的翻新層出不窮,多種媒介材料的運用使繪畫語言的綜合性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意大利藝術家阿爾貝托·布里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殘布、紗布、塑料布等材料進行拼貼覆蓋,配合色調沉郁的紅褐色,仿佛血染的繃帶,使作品發出無言卻刺耳的回響,昭示著戰爭的災難,展現一種嶄新的、不同以往的視覺體驗。另一位綜合材料繪畫的先驅——西班牙畫家安東尼·塔皮埃斯將沙土、水泥、白灰等用于傳統壁畫底子的材料直接作為繪畫材料進行藝術創作,將這些日常中并不起眼的材料變成了令人驚嘆的作品,在視覺上充滿原始、粗獷的生命力,使古老的材料元素被放大,被提取為藝術語言主體,運用材料的技法上也明顯趨于間接性,傳遞著當代藝術的精神力量。[4]
(二)中國綜合材料繪畫的“間接性”轉換
進入21世紀以后,綜合材料繪畫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全世界的藝術家們不斷探索新的表現形式和創作手法,將多種材料和媒介融合在一起,創作出更具表現力和創新性的作品。我國的前衛藝術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崛起,綜合材料繪畫也成了重要組成部分。藝術家們更加大膽地使用各種材料和媒介,創作出具有沖擊力和創新性的作品,成了國內學術界所廣泛關注的對象。彼時我國藝術家思索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構建本土的繪畫語言體系,將西方綜合材料繪畫轉換為符合本國語境的支點上,推動中國架上藝術的整體發展。而綜合材料繪畫語言體系本土化必需思考以下幾個問題:首先,依然需要運用“間接畫法”為主要創作技法的前提下尋找本土化出路;其次,在觀念表達上,應立足于本土文化思考之上,探索中國傳統藝術精神表達;再次,在材料選擇中應首要考慮材料本身的精神性,避免濫用以及為材料而材料的窘境;最后,在畫面的形式選擇上要符合中國傳統審美觀念,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現行的形式體系。這不僅是當時需要思考以及探索的問題,在當下乃至未來的綜合材料繪畫語境中依然是必需思考的問題,我國探索該系列問題的先行者是以胡偉、張元等為代表的一代綜合材料藝術家們,他們的探索基本奠定了近幾十年中國綜合材料繪畫的基本調性,即在形式上運用含有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精神的物質材料為載體,內容上以偏重體現民族性、文化性為主要傾向,技術上依然以坦培拉材料與綜合材料混合,運用一定的“間接畫法”完成,力求達到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統一、主觀情感與客觀物象的有機統一。
(三)坦培拉繪畫材料自身的當代性
在多數畫家的印象中,坦培拉技法是有著固定程式的,一提到坦培拉就想到濕壁畫、古典技法、提白罩染以及汪小湖等這類技法,程式上是這樣沒錯,但如果跳出傳統技術層面來看,它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思維方式,將坦培拉材料中的乳劑與色粉置換成其他的中介物質,在將不同的物質材料運用坦培拉的技術思維使它結合到畫面中,那么我們面前的物質世界可以被作為“中介物質”的材料就有著巨大的可能性空間。在綜合材料繪畫過程中,將材料語言轉化為繪畫主體語言的時候,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思維的展現,是坦培拉技法在當代的思維性轉換,同時也是綜合材料繪畫不可或缺的思維方式。藝術家在作品中充分體現繪畫的材料性,將材料與人性有機結合,使作品具有更加寬廣的表現力,將材料語言延展為創作語言,材料的多樣性以及技法間接性,營造著看似偶然,但也都是基于理性的瞬間,定格凝固于畫面之上。同時,當下對于坦培拉材料繪畫的研究目的并不是為了在實踐中復原其技法與樣貌,坦培拉材料本身也兼備繪畫性與材料性,拋開傳統坦培拉技法,只將它看作一種繪畫材料也不失為一種優秀的、表現畫家情感的手段。
四、結語
綜合材料繪畫作為一種自由繪畫,在當下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必然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坦培拉這一古老材料技法的創造性使用也對綜合材料繪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探索性的思維方式,轉換材料的表象形象而去解析其內在的文化精神,在綜合材料繪畫領域展現具有時代性、民族性的多元化藝術語言與精神指向,結合材料語言獨特的審美屬性,營造更為統一的畫面內容與形式結構,表現新時代的藝術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