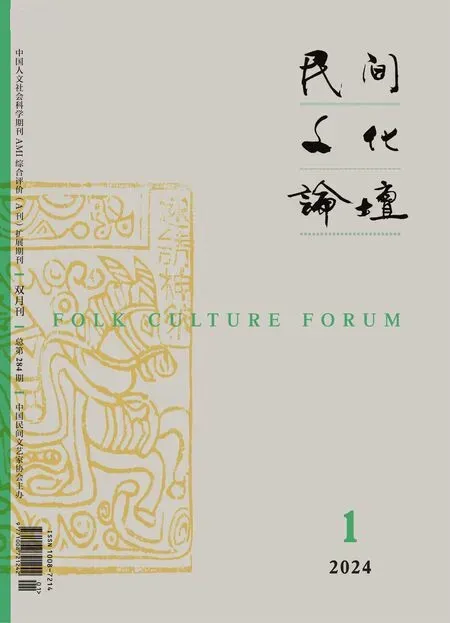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真髓是基質要素傳承
劉魁立
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工作,正如裴亞軍主任所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①本文是劉魁立在上海大學舉行的“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委員會2023 年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林玲博士依據錄音整理成文,發表前作者對文稿做了審核。過去我們有一位姜椿芳老先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革”期間他在獄中就已開始構想《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在此這之前是沒有《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目前不少參與其事的老先生雖已相繼過世,但在當時籌劃并付諸實踐此事,對后來整個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文化教育、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以及軍事科學等各個學科和領域都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發行后,緊接著修訂了第二版,近年來又陸續推出第三版。第三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傳統紙質版,另一種是電子版(網絡版)。其中網絡版進行了多媒體配置,帶有互動功能,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展開對話。這樣就可以集思廣益,進一步推動學術研究。
而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這項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撰同等重要,是一件立基的工作。大家常說我們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人人都是信息員,這個時候假的信息、錯的信息,往往都是魚目混珠的,我們有一位施愛東先生就是專門做這些“謠言”研究的。事實上,有些假信息在某種程度上容易辨認,但有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就很難辨認了。這類信息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實際上是荒謬的。就像剛才項兆倫部長所講到的,有些概念界定是不規范的。當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這類信息或許還能夠有一點真理的味道,但若從系統論的角度,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來看,并不能推進整個科學的發展。所以我覺得非遺名詞審定這件事情,也同樣是一件立基的、重要的工作。正如剛才裴亞軍主任所講,目前全國在名詞審定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而在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工作中,我們上海大學能夠主動、勇敢地承擔起非遺名詞的審定任務,無疑是了不起的。當然,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也要非常審慎地、負責任地把這項神圣的工作完成好。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有些地方可能已經突破了我們對文化的原有理解。在過去的民俗學領域里,鐘敬文先生曾經提出“文化分層”一說。所謂文化的層次論,是指在上層文化與底層文化中間還存在市民性的中層文化。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這種文化的層級性被打破。比如說對四九城的推翻,大家都知道二環作為北京的一個界限,二環以里的內環是貴族文化圈在起作用,像造辦處制造、修繕、收藏的那些御用品,普通老百姓是沒有辦法享用的。即便那些工匠、技師源自老百姓,但他們依然很難接觸到這類物品。文化自然也就分了層次,四九城內就是典型的上層文化、貴族文化。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四九城被推翻了。譬如我們在最初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時,推選項目都是一些上層文化的代表。就像古琴,古代老百姓是沒有機會接觸它的,但在當下卻為普通民眾、全國人民享有。特別是當古琴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后,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讓自家孩子去學古琴。如此一來,就把過去的上層文化真正變成了全民性文化,這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做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當然提及這一話題,可能還會有非常多的內容要講。就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工作而言,剛才項兆倫部長已經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我認為還有一些需要考究的地方——進入標準。比如以掐絲鑲嵌為制作技藝的景泰藍以及其他名器都進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但《易經》、陰陽學說目前尚未進入這一領域。包括前些時候,我們也做過一個討論,春節期間的一些儀式哪部分可以進入將來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遺項目中,哪部分不能進入,這些都是需要分辨的。又比如說姚慧芬的《骷髏幻戲圖》刺繡作品,畫面中骷髏牽線表演,其后墻則由上百種針法再現而成,墻面上刺繡的每一塊磚都代表著一種獨特的針法。姚慧芬通過《骷髏幻戲圖》系列作品,將所有刺繡的針法進行了統計與展示,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那么具體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工作,是否需要將每一個針法都收錄進來,這是需要分辨的。總而言之,非遺名詞審定過程中一些非常復雜、非常細致的工作都是需要審慎對待的。這是我的第二個想法。
第三個想法就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領域里,我們通常會提及“非遺的主體是什么”這樣一個問題,其中講到最多的是“傳承人”。但在我們心目中,雖然可能有、可未必一定有地位的是我們的“受眾”。大家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受眾”,文化這樣一個實踐活動能夠存在嗎?一個講故事的人如果沒有一個聽眾,那他是沒有辦法講下去的。比如說一位老奶奶如果沒有身旁小孫子需要哄睡時,她是不會自言自語講故事的;說書人如果沒有聽眾,同樣是沒有辦法說下去的;演戲也是如此,一個人在舞臺上只是自顧自地表演,大家一定認為他是扮瘋的。我開個玩笑,只有說夢話不需要對象,其他講述都是需要有對象、受眾的。當然,我們的民間手工藝制品也需要進入市場。在過去許多情況下,我們曾反對非遺的商業化,或者稱之為功利性,強調不能把市場看得太重。可如果沒有市場,又如何將傳承人的貢獻為整個社會所享用呢?這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們需要反對的不是市場,不是商業化,而是過度商業化。我們更需要反對的是遺忘或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最核心的“基質要素”。如果最基本的基質要素受損,那就很難做到傳承,同時也說明保護沒有到位。基質要素守護屬于非遺事象自身在傳承過程中保持基本同一性的規定性范疇。時代在演進,環境有變化,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時代和環境當中,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但是,基質要素是衡量一種事物不是他種事物或者沒有蛻變、轉化為他種事物的一種規定性尺度。非遺的基質要素,是指非遺事象在傳承發展過程中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種特有屬性,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基質要素的守護是非遺傳承的真髓,是任一非遺事象的靈魂。靈魂在,則事象在;靈魂變了,則事象也隨之變了;靈魂消亡,意味著事象生命結束。我認為,我們必須注意守護的非遺基質要素的核心內容包括基本性質、基本結構、基本功能、基本形態以及作為主體的個人、社區、群體的價值評估等五個方面。非遺保護是整體性的,這些核心內容是保護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制定、審定各類非遺名詞時,心里一定要有受眾。這樣才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對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的強調;這樣才能把整個社會聯系在一起,而傳承的對象自然也是向這些人傳承。如果傳承人、傳承群體心里沒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尊重與熱愛的話,那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不可能靠傳承人、傳承群體自己將其延續下去的。因為他沒有動力。而動力的來源恰恰是受眾,是整個社會。另外,文化的多樣性也是由此產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這種“互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非常重要的動力。因此,我覺得,我們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時,或許不一定在文字上體現,但是心里一定要有“受眾”這樣一個對象。有時候我會采取這樣一種辦法,把傳承人叫作“動力主體”,而受眾叫作“接受主體”,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相互推動的傳承機制。這樣才能夠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延續,而非遺保護也才能有一個理想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