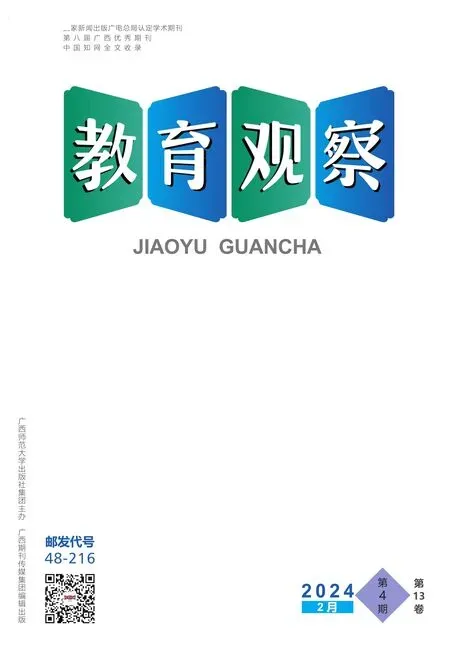互聯網背景下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
——基于可供性視角
王 娟,張鵬飛
(1.湖北工程學院社會工作系,湖北孝感,432000;2.三亞學院社會學院,海南三亞,572000)
一、引言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網絡社會的崛起[1],帶來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數字化已成為勢不可當的潮流和趨勢。在教育領域內,風險全球化和生活數字化引發了傳統教學方式的變革,“互聯網+”的教育方式成為一種普遍的數字化教學形式。觀照專業領域內,社會工作傳統的實踐教學方式存在實踐場域不足、路徑單一和非持續性等問題。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若不及時更新知識體系和實踐框架,不僅難以回應新興的實踐議題,還會有被進一步學科邊緣化的風險。在上述兩重背景下,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方式急需數字化轉型,以適應數字化教育的新環境。基于此,本文以可供性理論為基礎,旨在探討兩個問題: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數字化轉向的實踐范式何以可為?通過回答上述問題,為社會工作實踐教學的數字化轉向提供新的視角。
二、文獻回顧
在國內,社會工作專業處于發展上升期,對社會工作實踐教學問題的研究仍在探索階段,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社會工作實踐教學中的本土化研究。例如,有學者針對現階段本土實踐教學中普遍存在的“教育先行”問題,提出了構建全程融合式實踐教學體系。[2]還有學者探討了特定區域(如西部地區)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欠缺的成因[3],剖析了制約社會工作實踐教育發展的師資力量、招生現狀、實習督導配置等客觀因素[4]。其二,針對某一具體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或教學原則的運用展開研究。例如,根據“老年社會工作”課程內容及主題,優化實踐教學的設計與實施方案。[5]以“小組工作”為例,開展自主學習導向的實踐教學活動設計和與之配套的制度建設。[6]這類研究強調案主自決原則在實踐教學中的本土化應用,認為這些原則應貫穿專業教學始終。[7]其三,對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模式的探索。這類研究主要圍繞視角和方法兩個維度展開討論。在視角維度,主要從循證教育學視角出發,探索教師與學生的個性化體驗、教學智慧與教學證據有機融合的教學形態[8],從社會工作實驗教學設計的角度提高實驗教學的效果[9]。對方法維度的討論則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創辦自營的社會工作機構改善實踐教學中出現的問題[10];二是運用薩提亞模式的“成長模式”理論與雕塑技術,對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改革做出了探索[11];三是提出了反思性實踐教學模式的觀點、特征和方法[12],將項目雙重嵌入社會工作實踐教學過程[13],將服務學習理念融入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14],為創新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提供啟發。
綜上可知,過往研究多集中于對傳統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模式的探討,要么集中于對傳統社會工作實踐教學中現存問題的探討,要么集中于對具體教學方法或具體理念在具體社會工作專業課程中的運用說明,缺少對數字化教學背景下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方式轉型的探討。盡管有少數學者注意到互聯網對社會工作的影響,論述了網絡社會和網絡社會工作的特點[15],闡述了社會工作微觀方法在互聯網中的適用性問題[16],并提出了專業的網絡社會工作應回應網絡社會問題及完全通過網絡手段進行助人實踐的方法倡導[17],但這些研究更多的是將互聯網視為一個客體或一個外在環境與結構。在此視角下,互聯網可能會對專業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的某些潛在功能進行屏蔽,進而限制其在社會工作實踐教學中的作用,因而需要一個新的主客關系視角重新審視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的內在邏輯。基于此,本文嘗試引入可供性理論,為審視數字化背景下專業實踐教學轉型的內在機制、可行性路徑提供一個新的解讀視角。
可供性理論最早由詹姆斯·吉布森提出,用于強調環境屬性使個體的某種行為得以實施的可能性,他從生態學的視角揭示了行動者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關系。[18]這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概念,為分析數字化時代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轉向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可供性理論強調了主體與環境互動的可見性、可連接性和持久性。因此,本文將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與互聯網視為兩者互動中的兩個主客體,重點從可見性、可連接性及持久性三個維度分析互聯網嵌入社會工作實踐教學環節的可行性,以推動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
三、邏輯機理
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對社會工作人才的需求不斷加大,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為更好地回應數字化時代對社會工作人才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需求,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需要依托互聯網深入開展實踐教學改革,構建和發展數字化時代下的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互聯網為創新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方法提供了客觀條件,使傳統的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轉向數字化教學成為可能。而社會工作從傳統向現代變革的教學方式實踐自覺則構成了專業教學轉向的主觀條件。
(一)傳統社會工作教學困境與教學創新要求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提出,社會工作專業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必須涵蓋實踐教學環節,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的時間要求不少于800小時。[19]但在當前的社會工作專業教學中,理論教學是剛性要求,而實踐教學則是柔性選擇,加之受客觀實踐場域環境的制約,致使傳統的社會工作實踐教學陷入實踐場域不足、路徑單一和非持續性的困境。
首先,實踐教學場域不足。由于社會工作專業成立時間不長,課程設置的科學性還在不斷優化。因此,許多高校在設置社會工作專業課程時,優先保證理論教學所需。重理論、輕實踐的教學傾向使實踐教學所需活動場地和設備極為有限,實踐教學場域僅限于本校的活動場地和多媒體教室,很少使用專業的社會工作實訓室。盡管有部分高校設置了社會工作實訓室,但使用率不高或變成多功能活動室。雖然部分高校與校外社區、企業簽訂了實踐教學協議,但僅有少數校外實訓基地能真正滿足實踐教學需求,較難達到標準化實訓場地的要求。
其次,實踐教學路徑單一。當前很多社會工作專業的實踐教學仍以教師為中心,以教室為主陣地,以講授為主要方法,未能凸顯實踐教學的實務性、操作性和創新性。即使少數社會工作實踐教學運用了情境模擬、案例分析等教學方法,學生也對案例的理解有限,很難產生理論與實踐碰撞的共鳴,更難將專業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致使理論知識與實務能力脫節。此外,微課教學、翻轉課堂等新興的教學方法較少被運用,對項目化和網絡化操作平臺的使用也較少。學生缺少實踐課程在場感和接觸實踐資源、服務項目的機會,進而影響其參與實踐課程的積極性。
最后,實踐教學的非持續性。傳統的專業教學觀念認為,實踐教學是理論教學的補充。因此,實踐教學逐漸被邊緣化,實踐教學的時間和資源被擠占、實踐教學流于形式的現象屢見不鮮。以湖北某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為例,專業綜合實踐課程共七項:兩周的社會調查與社會實踐;兩周的社會統計學軟件的實踐運用;四周的服務性實習與指導;四周的專業見習;兩周的學年論文實習;六周的專業實習;十周的畢業實習。在這七項實踐中,僅有服務性實習與指導是由學校統一組織在暑期進行的,而其他實踐課程則由學生自主選擇,實踐教學安排缺乏規范性與統一性,實踐教學的持續性難以維持,因而實踐教學目標難以實現。
(二)互聯網為實踐教學的數字轉向奠定了基礎
傳統的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方式基于固定時空,未能突破時空場域的限制和整合跨區域的教學資源。如何積極融入“互聯網+”的教學圈,充分利用互聯網互動的跨時空、可記錄性和數字化便利,通過互聯網賦能專業實踐教學,建立社會工作教學信息平臺,實現社會工作實踐教學在理念與方法等方面的創新與突破,是突破傳統實踐教學困境的關鍵。例如,在居家隔離期間,社會工作者利用互聯網收集社區居民需求,為其提供精準服務,在社區封閉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論,互聯網的可供性包含可見性、可連接性和持久性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恰好為專業實踐教學的數字化轉向奠定了基礎。
首先,互聯網的可見性為創新實踐教學場域提供了物質基礎。湯普森認為,可見性是由時間與空間共同構成的特定坐標決定的。換言之,那些與我們共享相同時空坐標的人和事即為可見的。曼紐爾·卡斯特指出,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信息技術革命重新塑造了我們的生活場景。[1]丹尼爾·米勒提出了物的謙遜,警示人們應該重新將注意力放回事物物質性的一面。他認為,物越日常性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參與我們的生活實踐,我們就越無法覺察其作為物質與運行機制的過程,即人們常說的熟視無睹的狀態。我們身處網絡社會而不自覺,隨處可見的無線網和移動媒體顛覆了傳統的面對面模式的可見性運作方式,使得可見性開始從時間和空間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產生新的可見雙方的互動關系。互聯網賦能實踐教學,不僅是技術社會發展使然,更是迎合了“Z世代”學生習得專業實踐知識的場域轉型。[20]
其次,互聯網的可連接性拓寬了實踐教學的現有路徑。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5.6%。[21]線上辦公用戶規模達5.40億,占網民整體的50.6%。手機網民規模達10.65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8%。[21]這些都為社會工作數字化實踐教學提供了有利條件。當代大學生個體作為“數字原住民”,其經驗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現實社會經驗,網絡社會生活已經成為他們另一種社會生活經驗,即“網生代”大學生的個體經驗由虛擬生活和現實生活的經驗共同構成。因此,社會工作線上實踐教學將成為傳統線下教學的有益補充。
最后,互聯網的持久性突破了實踐教學不可持續的障礙。傳統實踐教學存在兩個不足。第一,師生互動。當教學目標達成或教學課時完成時即停止教學,師生互動也隨即停止。然而,實踐教學的停止并不等于學生思考和反思的停止。隨著教學的停止,學生在實踐中的困惑可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第二,傳統實踐教學既不能全面準確地記錄教學過程,也無法永久存留實踐文本信息。互聯網具有隨時在線的可及性且擁有強大的存儲性,能夠有效彌補傳統實踐教學的缺陷。這為隨時解答學生的實踐困惑和延時實踐教學提供了條件。此外,互聯網包含任意海量信息,是信息共享平臺,使數字化記憶成為常態。因此,實踐教學過程中的一切信息都可以借助互聯網,以文本、音頻、視頻等方式永久保存。
四、實施進路
互聯網場域及數字技術具有可供性,并通過這些可供性帶來了教學方式的改變。可見性、可連接性和持久性的結合可以讓師生超越傳統的物理課堂聚集在一起,可以讓學生超越地理社區的界限開展實習實踐。這些方式既能為學生或教師個體賦能,也能為社會工作實踐教學增能。可見性體現在實踐場域可見與獲取實踐場域的可能性,擺脫了傳統實踐教學在場之維的困局;可連接性體現在師生與生生之間或學生與實踐服務對象之間建立線上連接與互動的可能性;持久性則體現在通過互聯網技術提供持續實踐的可能性,且實踐信息易于留存。具體而言,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數字化轉向實施進路如下。
(一)利用可見性突破在場之維,創新實踐場域
“人在情境中”是社會工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無論是做研究還是進行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實踐,都必須將個體放到他所處的環境中進行,注重個體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環境間各要素的關系,用系統的方法分析情境中人們的行動。隨著網絡社會中公共無線網和移動媒體的普及,隨時在線的狀態意味著人們時刻處于互聯網情境中,對周圍物理環境的參與度降低,更熱衷于虛擬社區的互動。這為師生共同適應互聯網場域實踐教學提供了條件。因此,在互聯網情境中,首先,高校需要整合各種零散的網絡教學資源,如慕課、微課教學、翻轉課堂、TPR實訓平臺等,搭建一系列的網絡實踐教學空間,在專業實踐教學的不同階段給學生相應的指導。其次,專業教師要重視互聯網技術在專業實踐領域的應用,通過自身學習和指導學生在互聯網場域中進行實踐演練,從而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學生的學習能力。最后,師生要共同運用網絡實踐教學資源及平臺,充分利用課程實踐、項目服務實踐等機會進入互聯網教學情境,營造網絡空間的在場感和實踐感。
(二)運用可連接性創新實踐路徑,拓展實踐方法
傳統的社會工作實踐教學過程注重面對面教學,以此實現對學生的全方位實踐學習指導。然而,時間與空間的客觀因素會制約面對面的連接,從而影響實踐教學效果。以數字為載體的網絡空間連接悄然興盛,加速了“無接觸社會”的到來,實現從傳統連接到數字連接的轉變。在網絡異步平臺中,大家無須在行動的時間維度上保持一致。因此,教師要充分利用線上連接的優勢引導學生及時參與、分享與反思。第一,教師可利用線上連接的隱蔽性,鼓勵實踐對象更加開放地進行自我反思,進而獲得更多的專業性和情感性支持。第二,充分發揮線上教學的補充作用,將受空間限制的線下實踐教學延伸至無限空間的線上教學,擴寬實踐教學溝通的廣度。[13]第三,通過各實踐教學環節線上線下的協同性,激勵學生充分發揮主體擅長網絡連接的優勢,提升學生實踐學習的獲得感,從而增強其主觀能動性與自我效能感。
(三)通過持久性拓展實踐深度,拓寬實踐對象
傳統的實踐教學主要依據教學大綱完成一定的理論學習和實踐學習,而嵌入互聯網的實踐教學則可以借助數字工具延長師生課程結束之后的繼續交流互動。此外,學生實踐后由教師引導的專業反思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的面對面實踐教學模式受到各種物理空間的制約,無法保證教師對學生的持續關注,因而實踐反思常常被懸置。互聯網場域和數字技術突破了傳統的時空局限,將師生更密切地聯系在一起,能夠保證實踐數據被及時、準確、永久地留存查閱。首先,教師需要指導參與實踐教學的學生及時準確地錄入各類實習實踐的文本信息,形成反思的電子數據資源庫。其次,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形成的人際關系,其專業關系可以在不違背專業倫理的情況下延伸至互聯網空間,且可以據此發掘潛在的實踐服務對象。同時,隨著參與實踐教學討論的人數與討論的時間不斷增加,學生的實踐經驗在互聯網上被聚合,形成特有的實踐分享場域和慣習,拓展了實踐教學的深度。最后,教師要關注社會工作四大系統,即改變媒介系統、服務對象系統、目標系統和行動系統,將社會工作四大系統與網絡聯結,利用網絡的關聯性和持久性拓展實踐對象,從而提升實踐教學效果。
五、結語
當前,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迫切需要回應傳統的教學問題和新興的實踐議題。因此,社會工作實踐教學需要數字化轉型以快速適應社會的新特點。數字技術不僅帶來了新技術范式和突破式創新,也為社會工作實踐教學創新突破提供了重要機遇和技術窗口。技術是人和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的驅動力。如果數字技術也讓我們從具體的本地互動中脫離出來,那就可能給我們造成真實的威脅。社會工作實踐教學的數字化轉向并不是摒棄所有傳統教學模式,而是借助互聯網賦能,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在互聯網時代,包括手機在內的每一種媒體都有自己獨特的可供性和一系列的潛力與限制。實踐教學的物理課堂、基地等地域不會消失,地理意義的實踐基地或社區依然意義重大,我們需要做的是讓互聯網賦能社會工作實踐教學,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讓熟悉之事不再陌生。我們既要充分利用數字教學的可見性、連接性、可持續性的優勢擺脫傳統專業實踐教學的場域限制、路徑單一、非持續性的困境,也不能忽略傳統教學中的情境真實性對實踐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