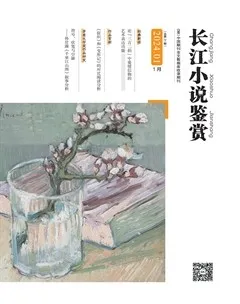從文學倫理學批評視角解讀《心》中“先生”的倫理悲劇
劉愛玲
[摘? 要] 夏目漱石被譽為日本“國民大作家”,其晚年代表作《心》分為“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遺書”三個部分。其中,“先生和遺書”是《心》的核心及高潮。在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影響下,個人主義與傳統精神發生沖突,使得新舊知識分子陷入悲劇之中。小說中,“先生”在“利己”和“利他”思想的交織中經歷情感煎熬,深刻反映了明治時代的新舊思想變革。本文借助文學倫理學的批評方法,對《心》的倫理環境和倫理主線進行深入解析,回歸文本分析“先生”的倫理困境和婚姻悲劇,審視個人主義與明治時代精神的沖突對新舊知識分子產生的悲劇影響,從理論層面揭示人的復雜性以及遍及人世間的倫理意識。
[關鍵詞] 《心》? 文學倫理學批評? 倫理環境? 倫理困境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040-04
夏目漱石被譽為日本“國民大作家”,其晚年代表作《心》分為“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遺書”三個部分,深刻描繪了明治時代知識分子利己主義者內心世界的可悲,呈現出人物面臨選擇時所經歷的豐富而復雜的自我與倫理之間的沖突。雖已流傳百年,但《心》對于人物內心的孤獨、猜忌以及欺騙等情感層面的描繪,至今仍然保持著卓越的時代價值,為當今社會思考道德和人性的永恒提供有益的參照。我國文學界對《心》一直保持著高度關注,但從文學倫理學批評視角進行的研究寥寥無幾。我國文學倫理學批評的開端可以追溯至2004年,以聶珍釗為代表的學者們掀起了一股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熱潮。聶珍釗指出:“文學倫理學批評同傳統的道德批評不同,它不是從今天的道德立場簡單地對歷史的文學進行好與壞的道德價值判斷,而是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1]
《心》的人物設定與倫理學息息相關。本文嘗試運用文學倫理學的批評方法,對《心》的倫理環境和倫理主線進行深入解析,回歸文本分析“先生”的倫理困境和婚姻悲劇,進一步反思小說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對現代社會和個體生活的影響。
一、《心》的倫理環境和倫理主線
“先生和遺書”是《心》最重要的部分。信件中描寫了“先生”神秘的過去。“先生”在童年時期失去雙親,他的父母將遺產全部委托給叔父,并由叔父擔任監護人,供養他在東京接受教育。然而,在第三個夏天回鄉時,“先生”察覺到叔父的態度突然轉變,叔父竟然欺詐騙取了他的遺產。至親叔父的這一行為對“先生”造成巨大沖擊,決定再也不回故鄉,并返回東京。在東京,“先生”搬進了軍人遺孀“夫人”和她的女兒“靜”的家。在與“靜”相處的過程中,他不知不覺喜歡上“靜”。但因年少時被叔父欺騙留下心理陰影,他一直下意識地對他人保持戒心,使得他一直不能表白自己的心意。與此同時,“先生”的朋友K因為欺騙養父母而被斷絕關系。“先生”出于善意,安排K和自己同住,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向崇尚道的K也喜歡上了“靜”。“先生”私下里瞞著K向“夫人”提出與“靜”結婚的請求。得知此事的K選擇了自殺。婚后,“先生”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沒有向妻子“靜”坦白一切,獨自承擔因K自殺產生的罪惡感,最終選擇和K一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倫理環境是文學作品存在的歷史空間。文學倫理學批評要求在特定的倫理環境中分析和批評文學作品,對文學作品本身進行客觀的倫理闡釋,而不是進行抽象或者主觀的道德評價。”[2]小說《心》的背景設定在日本明治時代(1868—1912),正值日本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時期。這個時代承載著西方思想和傳統日本觀念的激烈沖突,在文明開化的推動下,曾經受制于父系家族制度的女性開始主張個人意愿,但仍然受到家父長制的影響。“家父長制”是指在父系家族制度中,男性通過絕對的家長權力支配和統率家庭成員。在明治時代,“家父長制”強調父親的權威,特別是在戀愛和婚姻方面,父親的批準是必須的。《心》開頭描寫“我”的朋友不愿意父母包辦婚姻,在東京附近游玩卻收到母親病危的電報,雖然明知是父母的一場騙局,仍然選擇回家。這個情節生動展現了“家父長制”對個體決策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先生”的所為則更為鮮明體現了對這一制度的抵抗。他拒絕了叔父為其安排的與表妹的婚事,這是對傳統倫理觀的反抗,也表達了“先生”對自由戀愛的追求,強調了個體對于婚姻選擇的自主權。
“文學倫理學批評指出,幾乎所有的文學文本都是對人類社會中道德經驗的記述,幾乎所有的文本都存在一個或數個倫理結構,這個結構可以稱之為倫理線,倫理線是文學文本的縱向結構。而文學文本的一個個倫理結,則被倫理線串聯或并聯在一起,構成文本的整體倫理結構。”[2]《心》全篇聚焦于“先生”這位利己主義者的內心世界,構成小說的倫理主線。通常而言,文學作品除了主線外,還蘊含著數條與主線相交織的倫理副線。其中,“家父長制”“家督繼承”“男尊女卑”構成近代日本家制度的三大支柱。以“家父長制”為主的傳統社會倫理觀形成了縱向倫理線。明治維新引入的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逐漸深入社會各個領域,使得明治民法所規定的家制度逐漸脫離實際生活。《心》的第一部分描繪了“我”在人頭攢動的鐮倉海邊邂逅一個西洋人的情景。“洋人皮膚白得非同一般,一進小茶棚就引起我的注意。他把地道的日式浴衣往長凳上一甩,抱起雙臂往水邊走去。除了我們穿的那種褲衩,他身上再沒有別的。這點首先使我驚異。”[3]明治維新后,西方文明開化的思潮在小說中形成了橫向倫理線。可以由此看出,傳統封建制度與西方進步思想之間逐漸產生了倫理沖突。
二、“先生”的倫理困境
“倫理困境是由于倫理混亂而給人物帶來的難以解決的矛盾與沖突。”[2]要想理解人物面臨的倫理困境,必須進入文學倫理環境或倫理語境中,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心》的最后部分“先生和遺書”是核心及高潮。為更好地了解“先生”這個人物,本文嘗試對“先生和遺書”進行解構,從“叔父背叛”和“背叛朋友”兩個方面進行解讀。
1.叔父背叛
“先生”是家中獨子,由于父母雙亡,年幼無依,根據父母的遺愿,由叔父擔任其監護人照料他的一切,主要有“供養到東京讀書”和“婚姻”兩件大事。在學業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叔父很支持并幫著打理家事。然而,在婚姻問題上,叔父很強勢地要求“先生”和自己的女兒結婚。以婚姻問題為切入點,受過西方人文思想教育的“先生”和有著傳統家制度思想的叔父之間產生了無法調和的矛盾。土屋健郎指出:“先生”的人生悲劇正是在那里孕育而生。按照當時的社會觀念,婚姻是維系家制度存續的重要一環。但是,叔父給安排的姻緣,在思想前衛的“先生”眼里是惡意逼婚。從那時起,“先生”開始察覺到叔父對自己的態度變化,開始懷疑叔父的真實動機。于是,“先生”與叔父展開關于遺產的談判,這個時候,“先生”才知道叔父推動自己與其女兒結婚的真正目的是將女兒推給“先生”,以期將遺產據為己有,合理化侵占遺產。在遭遇至親叔父的背叛后,“先生”陷入“繼承家產”和“變賣家產”的倫理困境:結婚進而繼承家業或者不結婚繼續求學。面對這樣的倫理困境,“先生”做出的倫理選擇是大膽違背傳統的家制度,變賣家產拋棄故鄉,追求自由。當時正值走向文明自由的明治時代,“先生”原本是一個懷抱雄心壯志的年輕人。然而,受到叔父的欺騙后,他變得厭世多疑,對金錢和財產產生過度敏感,甚至對人失去了信任,陷入人性善惡的倫理困境,內心充斥著謹慎、孤獨、痛苦和寂寞。
2.背叛朋友
如果將叔父的背叛視為“先生”陷入倫理困境的起因,那么最終引發“先生”做出倫理選擇,走向自殺道路的原因是好友K的自殺。“先生”和K是同鄉好朋友。他們一起在東京的大學努力學習,彼此心靈相通,相互支持。K成長于當醫生的養父母家庭,骨子里一直信奉真宗,有強烈的自我主張,為了追求自己的精神成長違背養父母的愿望并拒絕妥協,以至于被養父和親父兩方面遺棄,但是K沒有放棄自己,決定兼職做夜校的教師以賺取學費。然而,由于長期努力兼顧學業和工作,K的健康和精神受到雙重傷害。在同一時間,“先生”被叔父欺騙,決定離開父母的墓地和故鄉。“先生”和K是同鄉,也是被故鄉遺棄的人。“先生”看到K患上神經衰弱,出于友情和慈悲之心邀請好友K同住,此時他們之間似乎是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的關系。“先生”對K的人品非常了解,絲毫沒有考慮到K會愛上“靜”。直率的K向“先生”告白愛上“靜”后,兩人變成了情敵。值得一提的是,K并不知道“先生”對“靜”有好感。先生以“談戀愛沒有上進心”打擊K,因為K受宗教的影響,平素主張“為了道,可以犧牲一切”,包括戀愛。
在整個過程中,“先生”一直陷入倫理兩難的矛盾困境。一開始,他信任叔父,并主動幫助好友K,展現了尊重傳統和注重倫理的一面;然而,為了追求個人愛情,他竟然采取卑劣手段傷害朋友,甚至欺騙隱瞞、先發制人,展現了利己自私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一面。矛盾的“先生”將如何抉擇?選擇愛情,還是友情,是利己,還是利他?他不愿失去唯一的朋友,同時也不愿將心愛的女孩讓與他人。在個人利益受到威脅、陷入友誼和情敵的雙重倫理關系困境中,備受痛苦的“先生”最終屈服于自己的利己主義。為了確保擊敗K,他私下向房東夫人表達了對“靜”的愛慕之情和娶妻意愿。當K知道二人的喜事后,第一句話說的是“是嗎”,這種冷漠無法稱之為慶祝朋友喜事應有的反應。K原本就已深陷對“靜”的愛情和對信仰堅守的困境難以自拔。在愛情上,“先生”和K的關系呈現為勝者和敗者。但在友情上,“先生”卻一定是輸家。“先生”采取卑鄙手段,未能坦誠表達自己的意圖,背著K奪走了“靜”,這是作為一個人在道德上的失格。因此,在K自殺事件中,“先生”認為自己和叔父是同一類人,在緊急情況下,為了滿足一己私欲,可以毫不在意地傷害他人。“先生”對人類,包括自己在內,感到失望,選擇與K一樣以自殺了結一切。也許,對友情的背叛可能代表了“先生”面對道德和人性的倫理困境時,最終做出的倫理選擇。
三、“先生”和妻子“靜”的婚姻悲劇
就文學文本而言,倫理選擇往往同解決倫理困境聯系在一起。我們的生活由一系列倫理選擇構成,道德和人性也都在倫理選擇的過程中逐漸形成。
1.結婚前
“靜”的家庭與其他家庭迥然不同之處在于,靜的父親犧牲于中日甲午戰爭,于是家中男性“父權”轉移到母親身上。“靜”的母親代替父親展現家庭權威,對女兒的教育明顯體現出“家父長制”。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社會環境對女性的期望是成為“賢妻良母”,主要表現為在婚姻中展現對丈夫的尊重與服從,同時在育兒方面承擔起精心照顧子女的責任。為了將“靜”塑造成“賢妻良母”,“靜”的母親決定讓她接受女子學校的教育,包括烹飪藝術、紡織技巧、插花藝術和鋼琴演奏等。令人驚訝的是,在“靜”的婚事上,母親直接表示不需要征求本人意愿,完全由她操辦。“靜”的后半生在短短不到15分鐘內就被母親處理完畢。這個安排的決斷力和迅速執行展現了擁有“父權”的母親的果斷與權威。
“這種時候, 我心里便奇異地涌現不安。我不認為這不安完全來自同年輕女子的對坐, 總好像有什么使我心神不定, 一種出賣般的不自然的態度折磨著我。而對方卻坦然自若, 全無羞澀的樣子。”[3]盡管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難以改變,但在文明開化時代,新女性逐漸突破傳統的桎梏,展現出獨立思考的能力,表現得直率果敢,不再盲從。小說中,“靜”在明確心意后,當“先生”與K旅行返程,大大方方毫不猶豫地展現出對“先生”的照顧。對于“先生”而言,“靜”散發出在新時代大膽開放、前所未有的女性魅力。于是,“先生”對“靜”一見鐘情,心中原本深植的對他人的猜忌和不信任出現了細微動搖。在此之前,由于“靜”頻繁與K交談,“先生”其實對“靜”并不信任。“先生”領悟到愛情的力量可以改變一個人對周圍的看法時,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對人際交往產生新的思考。
2.結婚后
“先生”和“靜”的愛情是明治時代的悲劇。被至親叔父奪走家產后,“先生”依附于家庭的情感紐帶被徹底摧毀。“先生”對他人持有警惕心態,沒辦法信任他人,包括妻子“靜”,最終夫妻關系陷入倫理悲劇。
“先生”與“靜”這對夫婦的感情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搶先K而突然產生的,相識相戀并未經歷過激情澎湃,也沒有傾心傾意的濃情蜜意。“靜”在思想上與傳統的日本婦女不同,作為“賢妻”細心照料丈夫的日常起居,卻沒有機會成為“良母”。“有個孩子就好了。”[3]盡管“靜”十分渴望擁有一個孩子,但“先生”始終堅持自己永遠不會有孩子,并將此視為“天罰的結果”。“先生”年輕時離棄家鄉的倫理選擇,導致家制度的斷裂。如今,婚后選擇不育,不僅反映了“先生”對家族制度的徹底放棄,同時也凸顯了對K的內疚的人性善惡自我倫理懲罰。
然而,這一切都使得“靜”成為這場倫理悲劇中的犧牲品。“靜”為了與丈夫建立心靈上的聯系,付出了極大努力。她親自照料丈夫的飲食,面對整日閑散、封閉自我的丈夫,依然默默陪伴,體貼溫柔。“先生”深深地熱愛妻子,然而這份感情卻將他緊緊地禁錮。他從未向共度多年的妻子袒露心跡,從未透露他每個月去雜司谷墓地祭奠的人就是K。因為“先生”強烈的自尊心阻止了他全盤坦白,不允許妻子了解他的陰暗一面,也不忍心讓妻子對以前三人的回憶留下陰影。“先生”明明有辦法得到最親近妻子的理解,卻因為缺乏勇氣而感到更加悲傷無助。“先生”在復雜的情感中掙扎,始終無法擺脫對K的愧疚,開始迷失自我,對生活感到厭倦,陷入孤獨與絕望,真切體驗到K曾經的孤獨和無助,最終只有和K一樣以死來尋求解脫。
四、結語
明治時代,西方個人主義傳入日本后,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倫理規范,人心發生急劇變化,倫理沖突下人心不可調和。夏目漱石筆下的“先生”在“利己”和“利他”之間掙扎,內心充滿煎熬和多疑。夏目漱石晚年代表作《心》以其豐富深邃的倫理環境和主線,深刻地探討了在文明開化的浪潮下,個人主義與明治時代精神之間的激烈沖突對新舊知識分子產生的悲劇性影響。《心》在倫理層面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倫理觀念的變革對個體命運的深刻影響,為現代社會提供了重要啟示。
參考文獻
[1]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J].外國文學研究,2010(1).
[2]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3] 夏目漱石.心[M].林少華,譯.青島:青島出版社,2012.
[4] 馬敏.論夏目漱石作品《心》中“先生”的倫理糾葛[D].北京:外交學院,2015.
[5] 馬全婧.夏目漱石小說《心》中“先生”的感情世界[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6(1).
[6] 侯冬梅.夏目漱石《心》的文學倫理學研究[J].西部學刊,2017(3).
[7] 李諾,史歌.淺析夏目漱石《心》的家庭成像[J].名作欣賞,2021(36).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