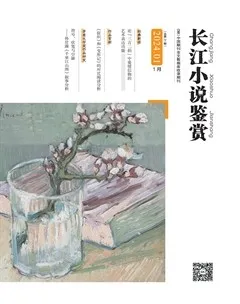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鏡花緣》傳播研究綜述
曹儀
[摘? 要] 傳播屬性是文學的基本屬性。《鏡花緣》的傳播研究,是指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鏡花緣》通過不同方式經由不同媒介的傳播、接受和反饋等主要環節,而具有的階段性表現。《鏡花緣》的傳播自其定稿之時即已開始,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不斷演進。在不同時期,對《鏡花緣》的傳播研究表現各異。因此,在系統梳理文獻與宏觀把握的基礎上,廓清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是開展此項研究必須首先完成的基礎工作。
[關鍵詞] 《鏡花緣》? 傳播研究? 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121-04
目前學界對于晚清時期具體起止時間的限定尚未達成一致認識。費正清的《劍橋中國晚清史》將1800年—1911年作為晚清的起止時間[1];史革新的《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則明確把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劃分為晚清時期[2];王建朗與黃克武主編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涉及時段為1840—1911年[3]。其中,1840—1911年作為晚清時期之界限,為學界主流之觀點,故本文即以此為據,將其作為課題研究的時段界限。
結合《鏡花緣》在晚清及之后的具體演變和歷代學者對《鏡花緣》傳播研究的實際表現,《鏡花緣》的傳播大致可分為萌芽期、延伸與停滯期、初步發展期和發展深化期四個階段,并表現出鮮明的內在演進特征。
一、晚清時期:萌芽期
1840年—1911年可為《鏡花緣》傳播研究之萌發階段。晚清學者關于《鏡花緣》在此時期傳播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們的序、題詞和評點中。夢莊居士為回答讀者“汝又指為無稽之外國事何居”的疑問,于《雙英記序》(1855年)中曰:“子不見《鏡花緣》舍內地而專言外國乎?是宗也,非創也。”[4]他指出《鏡花緣》與前人作品之承繼關系。“滬北俗子”于《玉燕姻緣全傳》(1894年)序,云:“是以《鏡花緣》者,曠其見聞之夥;《紅樓夢》者,運其筆意之深:事雖不同,各逞其胸中抱負而有所發泄也。”[5]對《鏡花緣》的藝術魅力和文本創作與傳播者自身志趣的密切關聯作了簡要說明。王韜在《鏡花緣圖像敘》(1888年)中有言:“悔修居士謂北平李子松石,竭十馀年之力,而成此書,功固不淺哉!然今之繪圖者出于神存目想,人會手撫,使其神情意態,活見楮上,當亦非易。兩美合并,二妙兼全,固闋一而不可者也。”[4]其對晚清時期插圖本小說流傳的積極意義做了明確點示。此外,關于《鏡花緣》在晚清時期的傳播效果也不乏精到點述。陸以恬于《冷廬雜識》(1856年)中曰:“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為余言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臺郡時,求者甚眾。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遍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涂。舊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6]定一的《小說叢話》(1903年)對此亦有提及:“中國無科學小說,惟《鏡花緣》一書足以當之。其中所載醫方。皆發人之所未發,屢試屢效,浙人沈氏所刊《經驗方》一書,多采之。”[6]該評價雖是對《鏡花緣》中醫方之實效的例證,然而亦包含了小說傳播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實際影響。
這一時期,《鏡花緣》開始向朝鮮半島、日本、英國、美國等地區傳播。1835年,朝鮮的洪羲福將《鏡花緣》翻譯為朝鮮文,這是該小說域外傳播的初起,此后《全本繡像鏡花緣》《繪圖鏡花緣》《圖像鏡花緣》等不同版本也逐漸傳入當時的朝鮮[7]。但國外學者對《鏡花緣》的品評大都以譯本為基礎,對作品內容加以批評與討論,幾無對小說傳播情況的研究,故不贅述。
總體而言,上述所及文獻雖未明確聚焦于《鏡花緣》在晚清時期的傳播研究,但其對于該時期《鏡花緣》相關傳播情況的評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文本在這一時期被接受以及被傳播的廣度,故為萌芽期。
二、辛亥革命至改革開放前:延伸與停滯期
辛亥革命至改革開放前,為《鏡花緣》傳播研究的延伸與停滯階段。此階段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階段,對《鏡花緣》的傳播研究甚少且缺乏新見,僅簡單聚焦于《鏡花緣》的版本流變和才學價值。如胡適于1923年在《〈鏡花緣〉的引論》中指出:“約1810—1825為《鏡花緣》著作的時期;約1825,《鏡花緣》成書;1828,芥子園雕本《鏡花緣》刻成;1829,麥刻謝像本付刻。”[8]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鏡花緣》歸入“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認為《鏡花緣》的藝術描寫雖“作者匠心,剪裁運用”“尚能綽約有風致”,然“于小說又復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已”[9],對《鏡花緣》的藝術風貌及其“才學”特質的優缺點均做了明確的論釋。第二個時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時期發表的有關《鏡花緣》研究的論文,主要著眼于該小說海外游歷和眾才女游宴逞才這兩大部分內容的精華與糟粕,并進行闡釋,探討這一現象出現的成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長之《新版的“鏡花緣”》,該文著重從前言和注解兩個方面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鏡花緣》進行品評,強調引言的“思想陣地”作用和注解在提高讀者閱讀體驗和閱讀能力方面的功能[10],初具現代傳播意識。
與之前相比,這一時期有關《鏡花緣》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對其版本的考辨和主題思想、藝術價值的探討,大體仍屬于前人研究思維的延續,故此階段為《鏡花緣》傳播研究的延伸與停滯階段。
三、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期:初步發展期
據不完全統計,1978-1999年,學界有關《鏡花緣》的專題論文共73篇,20世紀80年代后,有關該書的研究專著有4部出版,此外,各種校注本、改編本也不下30種。1984年,孫佳訊重新梳理歷年所論有關《鏡花緣》考證的文章,寫成《〈鏡花緣〉公案辨疑》一書,對于《鏡花緣》的作者生平和版本流變做了細致可靠的考證,為日后開展傳播研究提供了必要基礎。另有李奇林對于《鏡花緣》續作的研究,簡要涉及《鏡花緣》在晚清時期的文本傳播。其人批判性地指出蕭然郁生版《新鏡花緣》在思想藝術和諷刺風格上均體現出對原作的承接與創新。一方面,蕭然郁生版《新鏡花緣》提倡的改革社會之方案由李汝珍版的模糊空幻變得清晰實在;另一方面,諷刺對象由原作的“乾嘉時期的清王朝”到續作的“慈禧統治下的清王朝”,給“清王朝的‘立憲丑劇來了一個大曝光”[11]。李奇林還從續書與原著的關聯程度、續書寫作的主題思想,以及續書的語言風格和心理描寫幾個層面對兩版《新鏡花緣》進行對比,直言蕭然郁生版《新鏡花緣》“針砭時弊有力、令人振聾發聵”,陳嘯廬版《新鏡花緣》則“思想內容貧乏,藝術結構松散”[12]。以上所論,均為《鏡花緣》的傳播研究提供了可以依憑的落腳點。
與前一時段相比,這一時期對《鏡花緣》的研究數量增多,但其傳播研究并非研究熱點,對其傳播及發生變化的研究多為簡單點評,未能捕捉并揭示出《鏡花緣》不同版本變化的深層原因與傳播效果,對其版本流傳與變化的異同與風格也缺少系統的研究。因此,這一時期可為初步發展期。
四、21世紀至今:發展深化期
21世紀以來,伴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思想的解放,《鏡花緣》的研究理論與視角變得更加多元,研究者們嘗試運用新的邏輯思路和話語體系對傳統經典進行重新闡釋。目前關于《鏡花緣》的傳播研究既有整體性考察,也有針對性的個案討論。
1.綜合考察《鏡花緣》的傳播概況
宋莉華在《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一書中指出《鏡花緣》“以炫耀學識才情為旨歸”的特點與乾嘉年間大興考據之風不無干系,小說的通俗意味被沖淡,作者的審美旨趣與讀者的文化品位之差異使小說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隔[13]。范正峰《〈鏡花緣〉傳播研究》一文對《鏡花緣》在1919年之前的刊刻與版本流傳做了梳理,認為“蘇州原刻本對《鏡花緣》的傳播意義重大,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其傳播的源頭”[14]。琪日蓋的《〈鏡花緣〉接受研究》一文則從小說的續作、仿作、序、題詞等角度綜合考察讀者對《鏡花緣》的具體接受過程和接受狀態,指出“續仿作者模仿《鏡花緣》的結構和諷世風格,并賦予文本不同的時代意義,體現了其對文本的參與意識和能動作用。序和題詞則體現了身為讀者的序者、題詞者對小說的接受程度和內容”[15]。胡如意《〈鏡花緣〉傳播研究》則通過對《鏡花緣》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傳播環境、傳播方式和受眾群體的宏觀梳理,對《鏡花緣》從創作之初的人際傳播到定稿之后的印刷傳播,再到戲曲傳播、海外傳播做了細致翔實的梳理[16]。
2.通過對續仿作的研究分析其與《鏡花緣》傳播的內在關系
《鏡花緣》在晚清時期的續書、仿作,主要有華琴珊的《續鏡花緣》、蕭然郁生的《新鏡花緣》、陳嘯廬的《新鏡花緣》和秋人的《鏡花后緣》。《鏡花緣》的續書仿作,反映了清代文人從不同角度對作品接受的過程。王瓊玲認為華琴珊版《續鏡花緣》“雖承接了三才女至女兒國輔政的框架,內容卻大寫教場比武及戰陣征伐之事,并無具體的經世致用之學”,思想層面“大開時代倒車,與原著《鏡花緣》之基本精神已有天壤之別”[17]。唐妍通過對《鏡花緣》與《續鏡花緣》中女兒國一節的比較研究,對同題材不同女性想象所傳遞的文人內心想法進行了深入闡釋,認為前者看似為女性代言,實則“以拯救弱者之名來獲得對強者的身份認同”,后者則是“通過命運的女性化呈現,固守內心的家國想象”[18]。辜美高對秋人的《鏡花后緣》做了深刻闡釋,認為其在寫作手法和文本結構等方面很大程度地沿襲了《鏡花緣》,且內容緊湊、不炫耀才學,是“真正的女性烏托邦小說”[19]。另有方冠臻、蘇恒毅等人對《鏡花緣》續仿作中的女性議題之異同加以討論,提出應結合當時社會文化現實進行思考,而不是單純地對其續仿作的內容和思想價值進行批評[20]。這些研究雖未特意從傳播角度對《鏡花緣》的續書、仿作現象進行解讀,但對不同小說文本內容進行了細致分析、與原作的對比研究,對其價值內涵和評價標準演進進行了探討,為人們了解《鏡花緣》在晚清時期的文本接受與傳播情況提供了有意義的解讀。
3.對晚清時期《鏡花緣》插圖本傳播的研究
晚清時期,西洋鉛石印刷術的傳入為古典小說圖像本的發展和傳播帶來了新的契機。宋莉華《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及傳播》一文對明清小說插圖發展階段進行了梳理,以王韜《鏡花緣圖像敘》等為例,指出插圖是小說傳播的重要媒介,對小說文本傳播和藝術審美創造皆具積極意義[21]。程國賦和李國平的《論明清古典小說的近代插圖本傳播——以小說評點與插圖的關系為中心》一文,可以看作是對上述觀點的進一步細化,該文指出王韜為點石齋本《鏡花緣》作序,意在以名人效應來壯大小說之聲威,進而實現評點、插圖的商業出版功能,提出“評點、插圖、文本三者聚集交互,衍生出小說傳播之重要合力”[22]。陳洵的《李汝珍〈鏡花緣〉研究》通過分析《鏡花緣》不同插圖本與小說文本的互文性關系,進一步指出插圖不僅豐富了小說文本的內容與意義,而且促進了小說在普通民眾和儒生士子間的廣泛傳播[23]。喬光輝《論廣東芥子園〈鏡花緣〉插圖的文本接受》一文指出《鏡花緣》芥子園本中古器皿、游戲圖案等才學化的插圖與文本的才學特點相得益彰,插圖通過像贊補充文本的缺失,豐富了文本內涵,也流露出了讀者對文本的接受情況[24]。李旭婷《鏡中花,畫中意——從〈鏡花緣〉三個插圖本看讀者對小說接受的轉變》一文,以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芥子園刻本、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以及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孫繼芳彩繪本三個典型畫本為考察對象,指出讀者對《鏡花緣》的接受從最早注重女性的忠孝節義和閨閣風流,到對世情的諷刺意義和教化功能,最后到重視其中的神怪和海外游歷部分,反映了讀者的接受轉變與社會生活的關系[25]。邱芳芳、柳飔和李燁婧的《論<鏡花緣>插圖文本接受》將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廣東芥子園刻本和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進行對比解讀,探討插圖與文本的互文關系,認為芥子園版本遵循傳統,點石齋版本挑戰傳統的審美意識,其隱含的正是處于不同背景的繪工在不同社會接受傳統下之于文本的態度[26]。
五、結語
綜上所述,學界對《鏡花緣》的傳播研究,內容和角度都日益拓展,逐漸擺脫舊有的研究模式,體現出前人學者價值各異的學術思考和人文關懷,為近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文學傳播層面的參考。盡管如此,這一研究仍有不足之處。其一,部分研究依然停留在簡單地套用某些傳播學理論,通過堆砌的史料和陳列事實的方式對其傳播現象進行研究,而對其傳播規律和傳播特點的系統性研究相對不足,且缺少相應的文本細讀和感悟支撐,如何從文學傳播的層面,對《鏡花緣》的傳播全景進行清晰而合理的闡釋,是后續研究需要深思的問題。其二,《鏡花緣》在傳播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應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而又各具特色的,但現有的部分研究雖嘗試從傳播學的角度對《鏡花緣》的傳播情況進行闡釋,然其定義大多過于泛化,并未對其獨特性進行充分挖掘。其三,現有研究的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全面的問題,大多聚焦于對該作品傳播媒介和傳播接受情況的研究,在對《鏡花緣》文本傳播的研究中,研究者對插圖本的觀照最多,對續仿作、評點等方面的關注相對不足。基于以上幾點,《鏡花緣》的傳播研究仍具可探索的空間。
參考文獻
[1] 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2] 史革新.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3] 王建朗,黃克武.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4] 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5]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6] 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 上[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
[7] 閔寬東.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研究之綜考[M].李英月,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8]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M].大連:實業印書館,1943.
[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北新書局,1926.
[10] 長之.新版的“鏡花緣”[J].文學遺產,1956(9).
[11] 李奇林.并非“狗尾”、“蛇足”—寓言小說《新鏡花緣》簡論[J].明清小說研究,1993(1).
[12] 李奇林.兩部《新鏡花緣》之優劣比較[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3).
[13]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4] 范正峰.《鏡花緣》傳播研究[D].重慶:四川外國語大學,2019.
[15] 琪日蓋.《鏡花緣》接受研究[D].深圳:深圳大學,2019.
[16] 胡如意.《鏡花緣》傳播研究[D].南寧:南寧師范大學,2020.
[17] 王瓊玲.妄續新篇愧昔賢《續鏡花緣》研究[J].明清小說研究,2001(4).
[18] 唐妍.從《鏡花緣》到《續鏡花緣》看女性群體想象的交易[J].明清小說研究,2014(4).
[19] 辜美高.《鏡花后緣》的發現、比較與詮釋[J].連云港高等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0(4).
[20] 方冠臻.《續鏡花緣》所反映女性意識之時代變異[J].東吳中文研究集刊,2015(1).
[21] 宋莉華.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及傳播[J].文學遺產,2000(4).
[22] 程國賦,李國平.論明清古典小說的近代插圖本傳播——以小說評點與插圖的關系為中心[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
[23] 陳洵.李汝珍《鏡花緣》研究[D].南京:東南大學,2012.
[24] 喬光輝.論廣東芥子園《鏡花緣》插圖的文本接受[J].廣東社會科學,2013(3).
[25] 李旭婷.鏡中花,畫中意——從《鏡花緣》三個插圖本看讀者對小說接受的轉變[J].明清小說研究,2014(2).
[26] 邱芳芳,柳飔,李燁婧.論《鏡花緣》插圖文本接受[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6(2).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