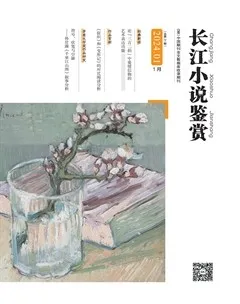符號、伏筆與空缺
郭賢姝
編者按:
茅盾文學獎作為我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見證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屆得獎作品反映了豐富的社會風貌與人文關懷。茅盾文學獎的歷史可追溯至1981年,獎項設立之初,便秉持著對文學創作的高度重視,注重反映社會現實,弘揚優秀文化傳統,推動文學創新。茅盾文學獎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注重對社會問題的關切,歷年獲獎作品多角度深刻地剖析了社會風貌、人性困境以及時代命題,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一面鏡子。從家庭瑣事到國家大義,從個體命運到民族歷史,獎項作品以飽滿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呈現出一個個生動而立體的畫面。
2023年8月,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公布獲獎名單,包括《千里江山圖》在內的五部作品獲獎,2024年度,我們將開設新欄目“茅盾文學獎作品研究”,《符號、伏筆與空缺——孫甘露〈千里江山圖〉敘事分析》便是該欄目第一篇文章,未來,我們將帶領讀者深入挖掘茅盾文學獎作品的獨特價值,揭示其中蘊含的文學審美與社會關切。相信這不僅將為讀者提供一次深刻的文學閱讀體驗,也將為廣大文學研究者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
[摘? 要] 不同于先前先鋒主義敘事姿態,孫甘露將筆觸伸向歷史與現實,以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千里江山圖”計劃為原型,創作紅色革命諜戰小說《千里江山圖》。孫甘露將先鋒性敘事技巧融入現實主義敘事,運用符號、伏筆、空缺等先鋒性敘事技巧使作品懸疑色彩驟增:身份符號在推動情節發展的過程中隱現出神秘、含混、緊張的敘事效果;伏筆鋪設的懸念與線索使故事結構嚴密緊湊、有跡可循;敘事空缺使故事曲折中斷,撲朔迷離,陷入“在場”與“不在場”的矛盾境地。對孫甘露而言,《千里江山圖》與其說是先鋒主義的回歸,毋寧說是先鋒性的超越與突破、現實主義的大膽嘗試與探索。
[關鍵詞] 《千里江山圖》? 敘事? 符號? 伏筆? 空缺
[中圖分類號] I106.4?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094-05
作為先鋒主義“最先鋒”的代表,孫甘露以奇詭的實驗性語言、顛覆性的敘事圈套、謎一樣的夢境幻覺著稱,其創作的《信使之函》《訪問夢境》《請女人猜謎》等都是先鋒主義的典型代表。
2023年,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獲得茅盾文學獎。不同于先前先鋒主義敘事姿態,“孫甘露將目光聚焦特定的時代語境,深入觸摸現代革命歷史,傳承十七年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寫實精神,又借鑒諜戰小說的懸疑氣質,凸顯英雄情結和家國情懷”[1]。諜戰小說因跌宕起伏的戲劇性情節與懸疑燒腦的敘事氛圍向來受到大眾尤其是青年讀者喜愛,麥家的《暗算》《風聲》、海飛的《麻雀》等諜戰作品就是如此。相較先前的諜戰作品,孫甘露將符號、伏筆、空缺等先鋒性敘事技巧融入紅色敘事,使作品懸疑色彩驟增:符號在推動情節發展的同時展現出神秘、含混、緊張的敘事效果;伏筆鋪設的懸念與線索使結構嚴密緊湊、有跡可循;敘事空缺使故事曲折中斷、撲朔迷離、疑云重重。《千里江山圖》多重反轉的顛覆性敘事、戲劇性故事情節以及濃重的懸疑色彩也具有巨大的市場前景。對孫甘露而言,《千里江山圖》與其說是先鋒主義的回歸,毋寧說是先鋒性的超越與突破、現實主義的嘗試與探索。
一、身份符號:含混、神秘與緊張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符號由能指和所指兩部分組成。”[2]羅蘭·巴爾特在索緒爾的基礎上區分了符號第一層和第二層的表意,把他們分別稱為表面意義和引申意義。在語言系統中,人物的姓名、代號,作為一種身份表征,實質也是一種身份符號。在地下黨進行革命斗爭的特殊環境下,人物的身份代號作為重要符號,其“能指”在特殊語境下被賦予特殊的“所指”內涵。伴著作者高超的先鋒性敘事技巧,作為符號的代號不斷地與敘事發生各種糾葛,產生不同的敘事效果。
老開、西施、浩瀚是作品中三個重要的人物代號,也是重要的敘事符號,三個敘事符號互相構成情節交織網,共同推動故事情節發展,使敘事節奏緊張刺激。老開是中央特派員,是“千里江山圖”計劃的宣布者與小組負責人。故事的開頭是一場緊張重要的絕密會議,但會議還未開始卻被突如其來的國民黨捉捕行動打斷,眾人陷入逃亡與追捕的混亂中,本該拿著骰子與組織接頭并宣布計劃內容的老開神秘失蹤。就在黨組織成員與老開失去聯系的同時,“上級從內線得到情報,有一個代號叫‘西施的特務,很可能潛伏在我們內部”。于是,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下,尋找并保護“老開”,找出內鬼“西施”便成了黨組織的當務之急和重要行動力。浩瀚是中共中央的重要領導,“千里江山圖”計劃的重要一環便是護送浩瀚同志撤離上海。對國民黨來說,抓到浩瀚相當于破壞了“千里江山圖”的絕密計劃,扼住了共產黨的咽喉。于是,尋找浩瀚、破壞共產黨的計劃便成了國民黨的主要行動力。在接下來敘事中,國共兩黨緊緊圍繞尋找浩瀚、老開、西施展開了一系列緊張刺激的行動,于是國民黨對抓到的六名共產分子嚴刑拷打,審問浩瀚的下落,審問之后又假意釋放、誘餌釣魚;共產主義者對林石的懷疑與分歧;除“鬼”衛道的作品主人公陳千里姍姍來遲、隆重登場。
巴爾特將“語言結構以不可察覺和不可分離的方式將其能指和所指‘膠合在一起的現象稱為同構(isologie)”[4], 當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不能膠合在一起,無法形成同構時,便會產生含混、悖論、神秘的敘事效果。老開是舊上海流行的一種俚語,其所指的表面意義是老板、有錢人,可引申為具有重要身份地位或領導地位的人。在小說中,代號“老開”指向的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特派員、“千里江山圖”計劃的宣布者與小組負責人。西施這一能指所對應的所指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后引申為美女的代稱,然而小說中代號“西施”的所指對應的卻是國民黨的一位男性特務。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歧義產生了含混的敘事效果,讀者被西施的常用所指所迷惑,根據慣性將特務西施與作品中的女性聯想審視,因而落入了作者的敘事圈套,偏離了正確解謎方向。浩瀚這一能指對應的所指表面義為“水勢盛大”,引申義為“廣大”“繁多”。浩瀚作為代號,其所指同樣另有深意。小說中,浩瀚總是形影無蹤,永遠處于被尋找的過程中,正如浩瀚所指一樣,尋找浩瀚就如在浩瀚無垠的茫茫大海中撈針,在此語境中,浩瀚又被賦予了一種神秘性。
索緒爾認為“符號具有任意性”[2],由于人物身份被符號化,符號又具有任意性,人物身份的代號因此成為人物的一張身份面具,面具下的真真假假往往是神秘與含混不清的。在代號的面具下,作者獨具匠心地編排了兩場精彩絕倫的面具表演。
第一場表演是真假西施戲。“旋轉門”一章中,崔文泰鬼鬼祟祟地與國民黨特務負責人葉啟年接頭,顯露出可疑行徑。“除夕”一章中,作者更是通過崔文泰的心理活動直接揭示出崔文泰的西施身份,“今后,你的代號叫‘西施”[3]。而后,在接下來轉移金條的過程中,崔文泰的內鬼身份被發現,他在貪欲的驅使下不惜得罪兩黨,夾帶“金條”逃亡,結果只得到幾個秤砣與一打廢舊報紙。崔文泰西施身份的暴露是小說的重要轉折,然而,正當讀者感到大快人心時,作者接下來的顛覆性反情節敘事卻無情地打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崔文泰不是真正的西施,真正的西施另有其人。因此,作者也設計了第二場表演戲來揭曉真相。
第二場表演是“貍貓換太子”的身份置換戲。在共產黨地下工作中,共產主義者常使用化名,按照規定的聯絡方式和暗號與對方接頭,并且作為絕密情報,沒有人懷疑化名的使用者是誰,這是身份置換得以實現的大前提。易君年作為文中的重要人物,一直沉著冷靜、顧全大局、深謀遠慮,在主角陳千里出場前,身為凌汶、衛達夫等成員的領導,一直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在國民黨特務沖入會場的那一刻,他甚至為了保護老開,掩護其身份免遭暴露將骰子放入自己的口袋中。正是這樣一位令讀者深信不疑的“正面人物”,隨著陳千里通過茄力克對盧忠德身份的指認,易君年身份徹底暴露。原來,歐陽民反叛、盧忠德“假死”,都是為西施順利潛入共產黨內部鋪路。盧忠德將龍冬殘忍殺害后,使用了龍冬即將執行任務的化名易君年,成功打入共產黨內部,實現了身份置換。至此,真相浮出水面,易君年是盧忠德也是真正的西施。在作者精心設計的真假西施以及“貍貓換太子”的身份置換表演中,讀者時刻都感受到一種含混、燒腦、真假難辨的閱讀障礙,同時代號下未知的神秘與好奇又時刻吸引著讀者的閱讀興趣,牽動著讀者破譯與解謎的心緒,而揭秘的過程又無限延長了讀者的陌生化審美體驗。
二、伏筆:暗流涌動
“褪卻真實歷史背景和重大主題的外衣,小說的內核可以看成一個精彩的‘陳千里捉鬼的故事。”[5]“內鬼”崔文泰是被國民黨策反的共產主義者,“外鬼”盧忠德(代號西施,化名易君年)是國民黨精心培養的特務分子。小說中最精彩的地方正是眾人對二“鬼”從懷疑到定位再到緝捕的過程。刨根問底、追根溯源,讀者可見伏筆和線索在作者構思縝密的敘事中隱現,每一條線索環環相扣,每一個細節都值得推敲。
伏筆出現在人物的對話、神態、心理甚至是微妙的潛意識等細節描寫中。從眾人對“外鬼”易君年(盧忠德)側面的下意識的感覺或評價中,易君年的身份其實早露端倪。“身份”一章中,伏筆隱藏在眾人心理活動的較量中。其中,林石與梁士超都對易君年表現了懷疑心理:“林石心想,這個易君年,一面讓大家不要討論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這個話題,他的好奇心很重。”“還有這個書畫鋪老板,為什么一直阻止他們討論老方的問題呢。”[5]“租客”一章中,陳千里向衛達夫了解易君年的相關情況,衛達夫提到老方交代的任務:“他特別跟我說,讓我先不要告訴老易。”[5]老方的安排暗示了易君年身份的可疑。
歷史敘事往往要求作者秉持“零度情感”寫作,以盡可能客觀真實地呈現歷史事實,然而,在描寫易君年和陳千里的對手戲時,隱含作者微妙地暗示了正義與邪惡的褒貶傾向。“賽馬場”一章中,易君年與陳千里第一次見面時,小說中多次寫到易君年點煙、抽煙、扔煙頭這一動作細節,使讀者無意中將易君年與煙鬼聯想,而革命者與煙鬼的形象大相徑庭。當陳千里向易君年道出自己的姓名時,“聽到這個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5],易君年這個可疑舉動,說明他可能聽說過老師葉啟年與陳千里的過往,而陳千里的突然出現也令其感到驚訝和慌張。在與陳千里交談過程中,作者寫易君年“臉上忽明忽暗”這一神態細節,而“陳千里覺得自己看不清對方的表情”[5],這一描寫也暗示了易君年立場的不確定性及性格陰沉。當陳千里向易君年打聽監獄中發生的事情時,易君年細碎的動作被陳千里敏銳地捕捉:“他在躲閃什么?陳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隱約感覺對方窘迫地笑了一下。”[5]在光明磊落的陳千里的對比映襯下,易君年表現出慌亂、緊張、反常與可疑的樣子。先前勸說同事們和平友愛,不要相互猜疑的易君年竟變成了背后說下屬壞話的小人。陳千里離開后,易君年先“隨手把《笑林廣記》扔進了一輛路過的垃圾車”[5],隨后“又點上一支煙”[5],緩步行走,直到“在鞋底碾滅煙蒂”[5]才回家。扔《笑林廣記》可見其玩弄心理,“在鞋底碾滅煙頭”是想把敵人踩在腳下的隱喻,可見其陰狠與毒辣。在此,隱含作者將反派易君年的本性暴露無遺,一個陰沉、冷漠、老辣、狠毒的小人形象瞬間躍然紙上。
作品在揭示崔文泰是內奸前,也曾對崔文泰進行過細致的伏筆描寫。會議開始前,參會眾人都高度緊張,觀察留意周邊環境,而崔文泰出場時,作者寫他“忽然起意,滿心想喝一碗豬雜湯”“喝完最后一口湯,嘴里還嚼著燒餅,慢悠悠站起身”[5],描寫了他貪吃、懶散、造作的一系列行為,他身上絲毫沒有革命者絕密會議前該有的警惕謹慎的感覺。而此刻,一輛國民黨汽車停在菜市場街角,“有人湊近車窗,小聲朝車內說了幾句話,隨即快步離開”[5]。作者在此并未交代此人是誰,但崔文泰此時所處的位置正是菜市場,據此讀者可以大膽猜測此人正是崔文泰。崔文泰與游天嘯交談的內容很可能與接下來國民黨的抓捕計劃有關,得知計劃后的崔文泰巧妙逃脫,因而未被抓捕入獄。由此,作者對崔文泰的內奸身份其實早有伏筆和暗示。
除去捉內鬼過程中的伏筆與細節,小說中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情節。讀者由小說開頭可以得知,共產黨巡捕房內線無名氏身份暴露后,不惜以赴死的方式通知眾人國民黨的抓捕行動開始了。老方的犧牲只有陳千里看到了,易君年卻宣稱從巡捕房內線情報得知老方犧牲了,而巡捕房的內線早就暴露了,易君年怎么得來的情報?答案不言而喻。此外,易君年和龍冬關系其實在小說中也早有暗示。當凌汶第一次提到龍冬時,易君年突然脾氣暴躁情緒反常,凌汶總是下意識地在易君年身上尋找龍冬的影子,甚至易君年本人也常將龍冬與自己做比較:“易君年又一次看見茶幾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龍冬碰到這樣的情況,他會不會也是這樣當機立斷?”[5]易君年和龍冬通過作者之筆無形間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也是作者對易君年和龍冬關系的一種伏筆和暗示。
《千里江山圖》作為孫甘露對諜戰題材的一次成功嘗試,其超越性和閃光點就在于融諜戰小說的懸疑色彩與先鋒性敘事技巧于一體,在反情節的顛覆性敘事描寫中打破讀者的期待視野。正當讀者因期待視野的打破而感到巨大落差時,作品中一條條有意無意鋪設的線索或伏筆突然間顯現,讀者便在恍然大悟中,獲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富有張力的閱讀與審美體驗。
三、空缺:疑云重重
縱觀整本小說,不難發現,作品明暗兩條線索相互交織。明線是國共兩黨圍繞“千里江山圖”計劃進行的緊張刺激的博弈和斗爭,暗線是陳千里與葉桃、葉啟年的愛恨情仇與恩怨糾葛。然而,作者在非線性敘事中設置了大量敘事空缺,產生了大量的文本斷裂,造成了在場與不在場的矛盾。“不在的話語不斷從在場的話語的邊緣侵入本文,它宣告本文的不完整性和不充分性”,不在場一方面將存在帶入疑難叢生的境域,另一方面又“預示了存在的可能性”[6]。找到空缺,彌合不在場,拼湊出完整的敘事積木,成為讀者探索解謎的任務和興趣。
小說中出現的第一種空缺是懸念式空缺,即作者在敘事中不先做交代,故設懸念,在片段性的碎片化敘事或伏筆線索中逐漸講述內容,填補空缺。陳千里作為故事的主角,卻很晚才在小說中出場,而在此前很大篇幅的敘事中,陳千里處于不在場的空缺狀態。這種不在場從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讀者的誤讀,在陳千里出場前,讀者被臨危不懼、機智勇敢、深明大義的易君年深深吸引,無論是其被國民黨特務圍捕前藏骰子的臨危不亂、受審時寧受電刑而不屈服的大義凜然,還是在林石受懷疑時的肝膽相照,文本都賦予了易君年足夠的主角光環。按照讀者的期待視野,易君年應是無可非議的主人公,然而真正主人公陳千里的突然出現卻打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正因如此,陳千里先前空缺的這一反情節的顛覆性敘事伴著讀者期待視野落空的反差產生了巨大的審美意蘊,賦予讀者無限的陌生化審美體驗。
敘事過程中,作者總是拋出一個個誘人的橄欖枝,引出一個人物或一個新的話題,但每次卻都欲言又止,留給讀者的是疑云重重的空缺。小說中最大的懸念性空缺便是龍冬,“照片”一章,從寥寥幾筆敘述中讀者得知龍冬犧牲了,但是有關龍冬的犧牲過程以及細節是空缺的,易君年看著龍冬的照片展開聯想以及二人的關聯亦是空缺的。作者留下了一系列空缺的懸念引起讀者好奇后卻不急于填補空缺滿足讀者的期待視野,反而轉向其他敘事,然而在進行大段無關的敘事后又再次提及龍冬,吊足讀者胃口。“銀行”一章中,林石突然向凌汶提及龍冬,并告知其一個驚人的事實:龍冬沒犧牲!這一戲劇性的轉折使敘事變得撲朔迷離,但龍冬的具體下落和細節還是沒有詳細展開,留給讀者的還是空缺。“興昌藥號”一章中,莫太太再次提及龍冬沒有犧牲,可她也說不上龍冬的具體下落,舊的空缺未解,新的空缺又出現。作者關于龍冬的欲言又止使帶有懸念的空缺像一只無形的手不停地推動敘事發展,一面是讀者跟著空缺尋找真相,一面是作者借陳千里之手揭曉真相,這樣,讀者無意之間與作者完成了復調對話,實現了雙向互動。同時,小說中多次提到龍冬下落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重復敘事,這種重復敘事造成了事件的撲朔迷離,加深了懸疑色彩。
小說中出現的第二種空缺是神秘性空缺,即作者在敘事中始終未做交代,重要人物和事件粗線條勾勒或一筆帶過,留下無限的空白、想象與闡釋空間。“千里江山圖”計劃是小說的文眼和主題,是小說中最核心也是最應重點介紹的內容,但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留下大量讀者迫切想要了解的神秘性空缺。整部小說圍繞“千里江山圖”計劃實施過程中共產黨人“內憂外患”的處境和遭遇,陳千里及時捉“鬼”破局,保證計劃順利進行展開敘述,而計劃的主要內容僅由寥寥數語的對話轉述。“千里江山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計劃?詳細的開展過程是怎樣的?計劃的最終結局如何?作者沒有描寫,留下一個神秘性敘事空缺。小說在結尾時僅表現了陳千里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性格特征,早在年初一晚他就安排了明暗任務,“在凌汶和盧忠德去廣州時,他自己帶著梁士超去了汕頭,另外打通了一條絕密交通線”[5]。打通交通線本是一項大工程,也是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此長的故事時間,作者卻用極短的敘述時間一筆帶過。陳千里如何打通的這條交通線?打通過程中都遭遇了什么?讀者亦無從知曉。
故事中人物的死亡也都是神秘的,死亡的原因及過程也都是空缺的。易君年殺害凌汶時,作者省略了殺害過程,僅展示了易君年殺人后“撕下一片門聯,擦了擦手上的血”[5]的動作細節。歐陽民反叛,卻仍舊被殺,衛達夫雖假意反叛,但用有價值的情報換取了葉啟年的信任,為什么也逃不了死亡結局?眾人做誘餌被捕后在龍華監獄是如何喪命的?神秘性空缺使讀者十分好奇。除上述敘事空缺外,讀者可能還有以下一大串疑問:國民黨計劃落空后,有沒有進行追蹤與反撲,新的追捕計劃是怎樣的?葉啟年最終的結局如何?陳千里如何與浩瀚同志接頭,又是如何護送浩瀚同志的?“胭脂用盡”的小鳳凰有沒有再見盧忠德了卻遺憾?雖有缺憾,然故事已落幕,種種空缺和遺憾只能交給讀者進行自由遐想與闡釋。
四、結語
作為一部優秀的紅色諜戰小說,《千里江山圖》將上海空間、革命歷史與間諜題材融為一體,在日常性與戲劇性相交織的敘事中實現了情節密度、歷史高度與人性深度的有機統一,散發著耀眼的光芒,在映照殘酷歷史的同時,對現實仍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參考文獻
[1] 孫強,黃靜姝.歷史敘事與精神重塑——讀孫甘露《千里江山圖》[J].西部文藝研究,2023(5).
[2]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 孫甘露.千里江山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
[4]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
[5] 《千里江山圖》:至暗之時,至亮之光[N].文藝報,2022-07-18(8).
[6]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特約編輯 劉夢瑤)